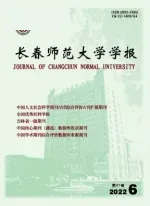谈纳兰性德诗词的“关东题材”及其民族文化心理
2010-08-15孙浩宇
孙浩宇
(长春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学院,吉林长春 130032)
纳兰性德作为清词中兴的杰出代表,其在词史上的成就和地位每为后人推重,况周颐称其是“国初第一词人”,王国维赞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于是,人们在吟赏纳兰婉丽凄艳的爱情词作时,常为其风华绝代的短暂生命和爆发式的才情所啧叹。其实,爱情题材只是纳兰写作的一个方面,纳兰还有待更多角度的认识和观照。这里我们想谈一下纳兰诗词中的“关东题材”。关东作为满兴之地,无论对纳兰还是清皇室都有着特殊意义。有清一代,对关东的记忆和礼拜深刻影响着清皇室及满清贵族的民族文化心理。而纳兰家世与清皇室的关系又有其特殊性,因此以纳兰“关东题材”的诗词为中心,来探究其写作心理及所折射的民族文化心理,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
一
按照地理区划,所谓“关东题材”指纳兰写于关东之行及反映关东风物的作品。据《清实录》载,纳兰曾两次东出山海关到今东北地区,一次是康熙二十一年二月至五月,“癸巳,上以云南底定,海宇荡平,躬诣永陵、福陵、昭陵告祭”,纳兰扈从。一次是同年八月至十二月,“庚寅,上遣副都统郎谈、公彭春等,率兵往打虎儿、索伦,声言捕鹿,以觇其情形”,即作为“特使”随觇梭龙 (按梭龙即索伦)。作为满清贵胄兼皇帝近臣,纳兰的这两次“东北公出”实为难得,而其留下的作品更是耐人寻味。
纳兰“关东题材”有诗、词两类,其大致作于同一时期的诗与词常常在情感与风格上有所差异,这或许是有意为之。纳兰作为扈从的诗作不免有应制之嫌,因此常有一层应承言志、冠冕堂皇的气息。而词作则缘情而发,常是羁旅行役、枕上孤眠的把玩之作,情感更为细腻。
山海关算是纳兰关东之行的起点,大致作于此间的词有:《长相思》(山一程)、《如梦令》(万帐穹庐人醉)、《浪淘沙·望海》、《浣溪沙·姜女祠》、《一络索·长城》等数阕 (关于诗词系年、地域的论定,难免会有主观臆断的因素,故对具体作品,学界时有争论,本文划分以有明确的风物特征为准的),而诗作只有一首《山海关》,当然数量多寡或不足证纳兰的性情和好尚,但两种体裁在纳兰手中的区别却是显见的。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长相思》)
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如梦令》)
纳兰在词中的倾向是表达思乡的深切与羁旅的孤寂,所谓“王事兼程促,休嗟客鬓斑。”《(塞外示同行者》)还有点公务在身的责任和焦虑,这都是在诗中少有的真实心绪。再看七律《山海关》:
伫立巍巍山海之间,作为扈从的诗人心情激动,诗中表达出了盛世的自信、伴驾的荣幸和恢宏的气度,虽不免应承歌颂,但意境壮阔,与诗人的身世和角色都很匹配。而同为此间登临之作,《浣溪沙·姜女祠》则这样写到:
海色残阳影断霓,寒涛日夜女郎祠。翠钿尘网上蛛丝。澄海楼高空极目,望夫石在且留题。六王如梦祖龙非。
就写作对象而言,纳兰作了一个转变,即从气势峥嵘磅礴、充满武功征服意义的老龙头转为具有传奇色彩、富于抗争和哀怨意味的姜女祠。同是山川胜景,诗作着力于对险要地势的勾勒和战略意义的渲染,俨然士大夫的眼光与情怀;而词作则注意对光与影一时之景的捕捉,着眼更为细腻,景中见情,更显出一份真实的感动。从情感看,前者尊贵昂扬,胸怀凛然;而后者一句“澄海楼高空极目”则道出了纳兰常有的兴亡慨叹。在另一首《浪淘沙·望海》中,词人更是解放自我,性情至极,“踏浪惊呼”“沐日光华还浴月,我欲乘桴”,出入天地、造境神奇的浪漫主义风格,与不免正襟危坐的诗作判然有别。
按照行踪所及,除了山海关之作,纳兰的“关东题材”大致分为以盛京 (今沈阳市)为中心和以乌剌(即兀喇,今吉林市)为中心的两组作品。“盛京一组”包括《兴京陪祭福陵》、《盛京》及《卜算子·塞梦》、《台城路·塞外七夕》等数阕。“乌剌一组”包括《菩萨蛮》(问君何事轻离别)、《浣溪沙·小兀喇》、《忆秦娥·龙潭口》、《青玉案·宿乌龙江》、《一络索》(过尽遥山如画)、《满庭芳》(堠雪翻鸦)及《柳条边》和《松花江》等作品。盛京是满清皇族龙兴之地,而乌剌则是纳兰先祖居所,这种区划对于康熙及满清皇族或不明显,而对纳兰却有着隐微的情感差别。
据清史记载,纳兰世家经历了从降族到望族的转变。纳兰始祖本是蒙古土默特氏,土默特在灭了纳兰部后,据其领地称为纳兰,又称“纳喇”、“那拉”。后纳兰氏举族迁至叶赫河岸,号叶赫国,纳兰氏遂亦称叶赫那拉。在前清满洲的统一中,叶赫部首领、纳兰曾祖金台什为努尔哈赤所灭,其子降,隶为满洲正黄旗。而其妹孟古则早已是努尔哈赤之妃、皇太极之母。纳兰氏降后因战功而成为满清八大贵族。至纳兰明珠,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傅又晋太子太师,更是权倾朝野。明珠妻觉罗氏为英亲王阿济格第五女。纳兰世家与清皇室曾经的恩怨情仇,遂埋下叶赫那拉氏报仇的家族传统。清文宗咸丰曾从其母那里听到一个传说,哪怕叶赫那拉只剩下最后一个女人,也将夺取爱新觉罗的江山。这种诅咒让人毛骨悚然,其仇恨之深自不待言,但对于纳兰本人,其地位和身份决定了其情感表达的复杂和深微。这从纳兰的盛京和乌剌作品中或可找到些许痕迹。
在盛京一组作品中,纳兰难免有对康熙帝的附和。“龙盘凤翥气佳哉,东指斋宫御辇来。”(《兴京陪祭福陵》)“拔地蛟龙宅,当关虎豹城。山连长白秀,江入混同清。”(《盛京》)皇家的排场,盛京的山川形势都写得隆重浩茫,气势磅礴,这样自然能让圣听熨帖。到了乌剌——纳兰氏的发祥地,纳兰的作品则变得富有深味。
是处垣篱防绝塞,角端西来画疆界。汉使今行虎落中,秦城合筑龙荒外。龙荒虎落两依然,护得当时饮马泉。若使春风知别苦,不应吹到柳条边。(《柳条边》)
据载,饮马泉在今吉林省中南部,为纳兰先人世居地之中心。纳兰到此,并没有朝拜先人故地的激情澎湃,反而以“汉使”自喻,更多是身来蛮荒、满眼萧索的生疏之叹,这与纳兰满清贵族的身份明显不合,也与人们常有的朝祖意味了不相干。个中原因当与纳兰世家的那段荣辱史不无关系。边地初春,其“别苦”自有一种作为叶赫后代与“故土重逢”时的奇怪情感。此时的纳兰家族声名显赫,权倾一时,但这一切都源自灭祖臣服所得,是灭祖的仇家所给予的恩赐。而以侍臣身份归来更平添了几分压抑和沉重,千里锦还却丝毫没有扬眉吐气的快感,这就是纳兰心头的那份尴尬和苦涩。在《菩萨蛮》中,词人写道:
问君何事轻离别,一年能几团圆月。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春归归不得,两桨松花隔。旧事逐寒潮,啼鹃恨未消。
满清贵胄多生于北京,称北京为故乡也理所当然。然纳兰甫一回先祖居地,就表达出强烈的归思,不免是与上述的特殊情绪有关。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评价“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二句:“亦凄惋,亦闲丽,颇似飞卿语,惜通篇不称。”张草纫在《纳兰词笺注》中对结句“旧事啼鹃之恨”这样注释:“整阕词的主题是思家。若以旧事指历史上的旧账,那末‘恨未消’的对象就是当今的皇族了。形诸笔墨,恐作者没有这么大胆。而且前六句与后二句的意思分隔了。”联系清初文字狱之盛,张氏之言似很合理可信,但需考虑的是,清代文字狱多出于统治者对汉人的压制,纳兰作为“刑不上大夫”的满清贵族和“倍受信任”的近侍,作“党同伐异”的对象此时尚无可能。而陈氏之评更是因艺术玩味忽略了词作背景,“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仅指归思自是一层意思,但联系为通篇情感抒发的复杂周折则更顺理成章。
能够平复纳兰心中压抑和尴尬情绪的一种方式就是对兴亡之感的强烈认同和反复抒发。《忆秦娥·龙潭口》:“兴亡满眼,旧时明月。”《浣溪纱·小兀喇》:“犹记当年军垒迹,不知何处梵钟声,莫将兴废话分明。”或许只有通过这种似乎通脱和超越的表达,纳兰的心才能得到一丝安慰。
须知今古事,棋枰胜负,翻覆如斯。叹纷纷蛮触,回首成非。剩得几行青史,斜阳下、断碣残碑。年华共,混同江水,流去几时回。(《满庭芳·堠雪翻鸦》)
纳兰的兴亡之感已远非其“关东题材”所能局限。《望海潮·宝珠洞》:“汉陵风雨,寒烟衰草,江山满目兴亡。”《南乡子》:“霸业等闲休,越马横戈总白头。莫把韶华轻换了,封侯。多少英雄只废丘。”《蝶恋花》:“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这种兴亡之感与其伤逝之心是交织在一起的。《采桑子》:“须知秋叶春华促,点鬓星星。遇酒须倾,莫问千秋万岁名。”《于中好》:“惊节序,叹沉浮。浓华如梦水东流。”《江城子·咏史》:“若问生涯原是梦,除梦里,没人知。”此间我们看到了道家的举重若轻和佛家的空幻,但情感却是低沉的,没有半点的空灵飘逸,这与以上所分析的纳兰家世的荣辱和深隐的内心是密不可分的,不再赘述。
二
前一部分我们勾勒了纳兰诗词“关东题材”的大致风貌,并谈及纳兰的家世以及其作品中所表达出的兴亡伤逝之感。从作品看,作为满清贵胄,纳兰对东北地域和满族族别的认同都显得不够,这可称作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的缺失。长白山是满族人民心中的圣山,金大定十五年 (公元1175年)世宗完颜雍始册封长白山为“兴国灵应王”,至清康熙帝后,拜祭长白山便成为清帝例行的规制。这种对长白山的崇拜和礼赞可以说源自满族人民心中最淳朴的文化情感,就如汉族人之于龙凤图腾。因此每个接近并朝拜长白山的满族人都是激动和振奋的,这自然表现在他们对长白山的深情热烈讴歌之中。数次到达吉林乌剌的康熙帝留下了《入乌喇境》、《柳条边望月》、《望祀长白山》、《阅乌稽》、《松花江放船歌》、《江中雨望》、《泛松花江》等诸多作品,真实的写景之作表达了他对先祖图腾的热爱和膜拜之情。反观纳兰,其留下的有关作品只有《柳条边》和《松花江》等三首诗作。下面我们将纳兰的《松花江》与康熙的《松花江放船歌》略作对比。
宛宛经城下,泱泱接海东。烟光浮鸭绿,日气射鳞红。胜擅佳名外,传讹旧志中。花时春涨暖,吾欲问渔翁。(纳兰《松花江》)
纳兰的五律描绘了松花江的平稳开阔,“烟光浮鸭绿,日气射鳞红”的情景捕捉堪称奇美,但通篇看却显得循规蹈矩,感情很克制。而康熙帝的这首诗采用古体,笔调雄伟高昂,感情充沛热烈。情、景、人交融一体,放船又放歌,将诗人的愉悦和高涨渲染得淋漓尽致,其中彰显的是环宇初定之时,清皇室所代表的昂扬劲健的民族文化精神。这恰是纳兰心中所缺少的,当然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的缺失与前文我们谈到的纳兰家世有关。
深究纳兰的民族文化心理,在满族意识缺失的另一面则是对汉族文化的极度追慕。据载,纳兰爱才重友,所交游的严绳孙、顾贞观、秦松龄、陈维崧、朱彝尊、姜宸英等俱是汉族名流才俊,纳兰还曾在徐乾学帮助下编纂《通志堂经解》等。有人甚至推想,纳兰身出南方汉族。笔者觉得从民族精神风貌上看,说纳兰是满清贵族,确实不如以汉人待之更为合理。纳兰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才情横溢又兼具士大夫情怀。当然,有人也曾将纳兰的有关交游当作康熙帝或明珠的政治手段来解读,不过一个侧面例证是无法忽视的,检视纳兰作品,与“关东题材”寥寥几篇中偶尔泛泛的风物描写相比,纳兰对扈从南巡的记忆显然更为深刻隽永,省江南、登东岳、幸阙里,纳兰留下了更多的作品,从风物描写到历史评述可见其对江南汉族文化下富庶繁荣的无限追思和回味。纳兰有一组《忆江南》(江南好十首)俱是此类作品。
除去家族历史因素,造成纳兰民族文化心理的原因有三:一是由儒家“大一统”思想所形成的传统的民族文化意识;二是清初特殊的民族文化环境;三是家庭和自身的政治处境。
中国的民族意识有很多宝贵的因素,比如包容、尊重、相互学习等,当然还有一个核心,就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毕竟在中国数千年的民族形成和融合过程中,汉族一直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引领着时代前进的方向。而汉民族意识的主导因素主要源自儒家,从夏商周的统一意识到秦朝“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中国文化中一个最强有力的声音就是统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里没有地域之别,也没有民族之说,因为在很长的历史阶段 (可以说在抗日战争之前),中国的“国家意识”要强于“民族意识”,“国家利益”要高于“民族利益”。所谓“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绝不仅是带来生活的便利,更强化了人们的统一意识。于是在传统文化营养中生长的纳兰自然就形成了一种无地域、无差别的“大民族意识”。且与清皇室比,这种意识更纯粹,因为纳兰没有满清贵族的优越感,常常不被这种身份束缚,这就使得其民族意识中多了一层宝贵的平等因素。
清初特殊的民族文化环境是决定纳兰民族文化心理的又一重要因素。满清民族文化最初即是属于汉民族文化的一个“亚文化”,姑不论满洲成立及此前对汉民族文化的学习,即使在八旗入关之后,满族对汉文化的吸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除了坚持提倡儒家思想之外,在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也积极主动地吸取汉族文化,这也是清代文化巨大发展并集前代大成的重要原因。满清贵族作为统治者,在文化心理上与汉族政权又有所不同。除了为我所用的自豪感,又力图彰显满族文化的特殊性和主导性。如强制剃发和着旗服以推进满民族文化形式,在教育上坚持继承骑射课程和满语课程等。满清统治者要在汉文化和自身民族文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以达到以少总多的统驭目的 (包括政治上的以汉入旗措施),彻底将汉文化纳入到满族文化的范畴之内,真正实现“满汉一家”。这种同化和被同化的融合进程直接影响了满汉文人的民族文化心理。
纳兰性德的父亲明珠,在撤藩、征葛尔丹等大事件上对康熙有鼎助之功,这也造成了其得以结党专权并又最终失势。据《清实录》载,“明珠广结党羽,满洲则佛伦、格斯特及其族侄富拉塔、锡珠等,凡会议会推,力为把持;汉人则国柱为之囊橐,督抚藩臬员缺,国柱等展转徵贿,必满欲而后止。”乾隆给明珠的评价是“徇利太深,结交太广,不能恪守官箴”。纳兰天资聪慧又身为近侍,应该最洞察圣心。以《清实录》中铲除鳌拜的上谕为例:“鳌拜结党专权,紊乱国政,纷更成宪,阁上行私。凡用人行政,鳌拜欺藐联躬,态意妄为。文武官员,欲令尽出其门,内外要路,俱用伊之奸党。”纳兰知道康熙把满族贵族的结党专权,恣意妄为视为大忌,这就造成其为宦的矛盾心理和行事的极端谨慎。如《昭君怨》:
深禁好春谁惜?薄暮瑶阶伫立。别院管弦声,不分明。又是梨花欲谢,绣被春寒今夜。寂寂锁朱门,梦承恩。
从作品中,我们看到纳兰对实现政治理想的渴望和对仕途的履薄之心。以纳兰的处境和智慧,他所看到的远不仅是官场的黑暗,也包括康熙驭下的叵测以及政治权势对人性的扭曲。于是,纳兰只能落落寡合,其交游也只限于汉族文士,且多为身在下层者。
三
通过第二部分的梳理,我们可以形成这样一种理解:纳兰对儒家文化和传统民族意识的接受,对自身政治处境的深刻认识,其父明珠炙手可热的政治权势,加之纳兰家族与清皇室的世代情仇,促成了纳兰特殊的民族文化心理,即对满清贵族身份的淡化和压制,而趋向于对汉族文化的极力追慕。
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纳兰对汉族传统文化的追慕以及尽力交结汉族下层文士名流其实有两层含义。一则有意:可以藉此掩饰自己的政治抱负,减少康熙帝对满清贵族结党专权的隐忧,同时与清初“满汉一家”,推重汉文化的思想一致。二则无意:纳兰身出饱学经世的贵族之家,确实对儒家思想与诗词创作等汉文化精髓有着良好的素养。有清一代,纳兰的身世、际遇和天资是特殊的,其文化心理和人格气质也是特殊甚至唯一的。
[1]张草纫.纳兰词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张秉戌.纳兰词笺注[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3]马迁骝、寇宗基.纳兰性德诗集诗论笺注[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4]纳兰性德.通志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
[6]张佳生.满族文化史[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
[7]赵志忠.满族文化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8]关纪新.满族作家文学史[EB/OL].[2008-05-19].http://iel.cass.cn/news_show.asp?newsid=3730&detail=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