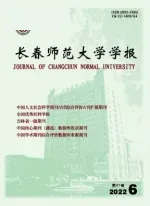中国古代戏曲团圆模式的三种类型及其文化精神探略
2010-08-15杨再红
杨再红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厦门 361021)
大团圆是古代戏曲最重要的结构模式,也是自王国维以来中国古典悲剧研究中最具争议的问题。它之所以备受关注,正在于悲喜相错的美学特征使中国戏曲没有产生西方式“纯正”的悲剧与喜剧。喜剧是不需要特别强调团圆的,只有在悲喜剧和悲剧中,团圆模式才会引人注目,因为它直接影响着一部戏的总体风格。抛开戏曲有无悲剧这一理论难题 (这种界定不仅涉及到哲学美学等民族文化内涵,更要面对不同戏剧形式所导致的迥异审美风格的尴尬),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戏曲并不缺乏悲剧色彩,先离后合、始困终亨的情节构铸模式决定了大多数戏曲与苦难、痛苦、焦虑、感伤等悲剧性因素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团圆则意味着苦恶终有报应。从悲剧意识角度言之,它恰是中国戏曲用以拯救苦难、弥合痛苦最重要的方式,体现了人类希望从困顿、失序、苦难与痛苦中被解放出来的共通心理。就此而言,无论从乐天的民族精神、尚圆的文化心理,还是从封闭保守的文化类型以及补天的意识愿望等角度来探析其形成的根源,这一模式为我们提供的艺术世界图景都应当是乐观的、积极的。具体到戏曲叙事中,剧作家总是会设计一个甚至多个拯救者形象来充当苦难的见证者和挽救者,大团圆则是拯救行动成功的直接标志。
然而,中国戏曲的写意原则使得剧作家强烈的拯救意愿对叙事本身往往造成了过度的干预,从而使大团圆包含了非常复杂的内涵,其背后的文化精神也逐渐从乐观拯救指向悲观幻灭。本文试图从三种最典型的大团圆模式入手分析其内涵的复杂性并梳理其文化精神的发展演变轨迹。
一、真实团圆——天道正义的胜利
先离后合、始困终亨的典范,拯救行动完全成功。主人公的意愿得到实现或部分实现,所遭遇的苦难获得了补偿,团圆的喜庆最终主导了全戏的情绪体验,无论是主人公还是观众的悲剧性感受在剧末都得到了释放。这类戏不缺乏悲剧色彩,但往往被最后的团圆所消解,可以归入好事多磨一类。一般来说,古代戏曲拯救者形象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专门的拯救者,其在戏曲中只作为苦难的解救者出现,而不是苦难的承受者,如清官、皇帝等等,类似于今天戏剧观念中正剧的救难者形象;自我作为拯救者,主人公既是苦难的承受者,也同时是自身命运的挽救者。学界公认的戏曲悲剧以及具有较强悲剧色彩的戏曲多以主人公自我作为拯救者,因为这种类型的拯救者一般更能突出主人公与自身所处生存环境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对抗,因而较之以他人作为拯救者的戏曲更具悲剧性。真实团圆中的拯救者多表现为他者拯救,如马致远的《荐福碑》、关汉卿的《蝴蝶梦》等。这类戏的悲剧色彩是颇为浓郁的,从戏曲描绘的主人公命运遭际来看,《荐福碑》中张镐的坎坷遭遇不仅在元代具有代表性,同时也是历代失意文人的缩影,马致远则用其愤激之笔将千古文人不遇的悲哀与怨叹发泄得淋漓尽致。然而,戏的后半部,主人公的飞黄腾达使其悲剧命运由原来的必然性、普遍性转变为一种偶然性、暂时性的苦难事件,因而这种苦难与困顿终将在范仲淹之类的拯救者的帮助下获得解救,由此带来的团圆结局也冲淡了全剧的悲剧色彩。尽管马致远在戏中多次表达了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与悲愤情绪,如“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涂越有了糊涂富”,可谓是其悲剧感受的集中抒发,但从全剧的情绪体验来说,拯救的成功、主人公意愿的最终实现给予了苦难以希望,无论是主人公还是观众的悲剧感都得到了释放。《蝴蝶梦》同样如此,剧中有对权豪势要横行的灾难性现实的揭露,有对王婆牺牲亲子以救其他二子性命的悲剧心理的刻画,也有死亡的痛苦与威胁,而以包公为代表的清官拯救者最终解救了这一切。明清戏曲中这一类团圆也不少,如孟称舜的《桃花人面》,尽管剧中将主人公对爱情的追求描写得“字字带血痕”,但作为自我爱情的拯救者,主人公的至情至性终使有情人成为眷属,可以说爱情意愿实现的喜庆补偿了生离死别的悲剧体验。
任何文艺产品都是时代社会风尚与传统文化精神共同作用的结果,上述团圆最能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乐观精神,剧作家所要表达的正是天道正义终会胜利的世界观,在这一观念的支撑下,全剧最终体现出一种理性的乐观色彩。如《荐福碑》中冒名顶替者受到惩处,有真才实学者终登黄榜;而《蝴蝶梦》第四折的唱词则将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推至顶点:“九重天飞下纸赦书来,您三下里休将招状责,一齐的望阙疾参拜。愿的圣明君千万载,更胜如枯树花开。捱了些脓血债,受彻了牢狱灾,今日个苦尽甘来”。《赵氏孤儿》《精忠旗》《清忠谱》《崖山烈》等均有着此类文化精神。
二、勉强团圆——天道正义的迷惘
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主人公的意愿得到部分或全部的实现和满足,但贯串于全戏的剧作家的拯救愿望却并未真正实现,这一类拯救多为自我拯救;另一类是主人公从苦难中被成功地拯救出来,但其意愿并未实现或者其悲剧性遭遇所造成的精神伤害并未真正得到补偿,这一类拯救也多属于他者拯救。
第一类可以《牡丹亭》等戏为代表。《牡丹亭》究竟应归入悲剧还是喜剧,学界曾有过热烈的探讨①。全戏的总体风格之所以引起众多学人的争议,正在于人物大团圆结局的喜剧性并未能冲淡弥漫于戏中的悲剧色彩。从汤显祖讴歌“至情”的创作题旨来看,团圆反而暴露了剧作家无法排谴的现实悲剧感,杜丽娘超越生死的爱情为取得现实的合法性仍不得不屈从于她曾用生命反抗过的“理”,因此,汤显祖让理的最大代表——皇帝成为全剧最关键的拯救者。为情而死,又因情而生,一切以生命为代价的行动在与理的媾合中实质获得的不是肯定而是否定。汤显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用那个时代的方式暴露和提出了时代的问题,即团圆不仅未能弥合情理冲突带来的痛苦,反而凸显了至情理想在理法世界中必然的悲剧性命运,揭示出团圆主义背后的文化悲剧意蕴。
第二类可以杨显之的《潇湘雨》为典型。张翠鸾由于父亲的解救摆脱了被发配、谋害的悲剧命运,但夫妻团圆的结局不仅不可能弥合她精神上的创痛,重新与薄情寡义的崔通生活在一起反而增强了主人公命运的悲剧色彩。该剧的拯救者是有权势的张父,因此较之其他受清官、皇帝等象征天理王法的拯救者解救庇护的受害者来说,张翠鸾的获救过于偶然,也过于脆弱,一旦她所倚仗的权势不存在了,她有可能重新陷入悲惨的境遇之中。一些研究者指出该戏以团圆收场,“比一般的大团圆结局尤其显得不合理”[1],这种不合理一方面反映出剧作家主观意愿对客观叙事的干预过度,一方面也暴露出剧作家面对悲剧性社会现实时无法寻求到新的解救办法时的无奈。这一类戏在团圆的背后同样包含着深沉的悲剧性。
从文化精神来看,此类团圆中的文化精神随着世界观的变化已有了不同。《潇湘雨》中天道正义实已让位于权势,张翠鸾的获罪、获救以及夫妻重圆,试官之女最后沦为奴婢的遭遇,人物的沉浮经历中不是天道正义而是权势官位起了决定作用。在这样的世界图景下,无辜善良却无任何权势的人遭受痛苦和死亡威胁就成为一种必然,人们可以依赖的只有偶然的好运、意外的巧合。可以说不可捉摸的命运之迷代替了天道正义的理性法则而成为世界的支撑,由此剧中流露出对不确定世界图景的深深困惑和迷惘。而《牡丹亭》则因为描绘了阴阳、情理、梦想与现实两种世界图景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情绪体验及风格。剧中虽不乏至情必胜的喜剧,但更多流露出的则是面对现实的无力与无奈,是试图打破理性法则却终究不得的深深困惑与痛苦,可以说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情怀已弥漫于戏中。
三、团圆的逐渐打破——天道正义的幻灭
表现为拯救的无力或失败,主人公遭受肉体或者精神上的毁灭。中国古代戏曲中团圆结局被彻底打破的只有《桃花扇》一剧,大部分戏曲均以虚幻的团圆来补偿现实的破碎,主要表现为梦圆、仙圆、冥报等等,而以洪的《长生殿》最具典范意义。《长生殿》情节上的冲突在理想世界中得到解决,而结构上的冲突,即前半部的现实界与后半部的虚幻界的矛盾却无形中得到了强化,如《重圆》中有“仙家美眷,比翼连枝,好合依然。天将离恨补,海把怨愁填。苍苍可怜,泼情肠翻新重建”的咏叹,与这一理想形成反差的却是作者在自序中发出的“情缘总归虚幻”的浩叹,由此更凸现出马嵬埋玉的惨痛现实,阴阳两隔的永恒悲剧。因而以纯情作为拯救的意愿在现实世界中随着它的化身——女主人公的香消玉殒不能不变得极其脆弱与无力,正如有学者所言,洪虽选择了团圆,但“其实早已在心理深层将其彻底打破”[2]。
古代戏曲深具悲剧色彩的剧作大多都存在着梦圆、仙圆等结局,即使是《窦娥冤》《汉宫秋》《娇红记》《千忠戮》《清忠谱》等被学界公认的戏曲悲剧也均有着此类结局。与其它两类团圆相比,这类团圆的悲剧性无疑是最强烈的,它展示了人类正常合理的欲求在实践过程中惨遭现实否定和毁灭的命运。杨贵妃对专一挚诚爱情的渴望与其社会身份、政治地位之间,窦娥的至贞至孝与黑暗现实之间,建文帝的政治理想与残酷的权力争斗之间等等均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在此过程中,人物主体为实现自己的意愿,挽救自身的命运都进行过或强或弱的挣扎、反抗,但最终只能走向毁灭,或付出生命代价,或被迫放弃自己的理想,或重新与现实媾合。虚幻的团圆确可暂时给观众以情绪上的缓冲、精神上的慰藉,但并不能以偏概全地将此归结为瞒和骗,归结为中国文化悲剧意识的淡薄。戏曲的俗文艺特征使其不能不考虑观众的审美趣味,团圆模式遂成为戏曲创作中必须遵循的文学惯例而很难轻易打破。
同时,中国文艺一贯追求含蓄婉约之风格,艺术形式与其所表达的内涵之间往往存在着悖反现象,所谓长歌当哭,寓悲于喜均是这一美学追求的具体表现。王国维先生曾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用“欧穆亚”一词来概括这种精神,即主体处于不愿屈服又无法逃离的两难境况中的一种自我慰籍方式,内心深处的痛苦借游戏诙谐的外在形式来抒发。宗白华先生也有类似的见解。[3]古代戏曲团圆模式与其内涵之间同样存在着形式与内涵分裂这一特点,尤其是文人剧作家往往有着复杂的文化心理结构,在满足大众审美要求的同时,其作为文化传承者面对不合理的现实人生所产生的忧患、悲哀以及对解救之路的探寻在戏曲创作中都会或隐或显地暴露出来,因此以虚幻的团圆来弥补现实的破碎,将拯救意愿的实现寄托在超人间的虚幻之境只不过是为绝望的现实增添一点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可以说正从反面暴露出剧作家始终徘徊于希望与绝望之间,挣扎于想要超越悲剧性的现实人间却又无法超越的矛盾痛苦心理。当这种矛盾痛苦发展到救无可救的彻底绝望时,剧作家渗透在戏曲中的悲剧感就会冲破固有的大团圆模式,使其创作内涵与表达形式走向风格的统一,《桃花扇》对团圆模式的打破正是这一发展倾向的必然结果。可以说在一个个破灭与死亡的悲剧世界中,传统的价值准则以及理性的乐观精神遭到了质疑和挑战,团圆模式的彻底打破则宣告了这一乐观精神的终结,悲观幻灭遂成这一类团圆背后的总体风格倾向。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文化用以拯救苦难、弥合痛苦的一种方式,团圆模式是传统文化乐天精神最显明的体现。王国维先生对此已作过精辟的总结:“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色彩:始于悲则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厌阅者之心,难矣!若《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其最著之一例也……”[4]这种乐天精神渗透在叙事艺术中,表现为剧作家描绘了一个终极意义上的乐观主义艺术世界图景,尽管其中不乏苦难、悲伤甚至是毁灭和死亡,但天道正义的道德逻辑使一切的苦难变成了偶然性、暂时性的事物。任何形式的背后都包含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蕴,大团圆模式正是上述乐天精神在艺术中的一种呈现方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今天的人看来纯属虚幻的‘大团圆'结局,是当时人们的世界图景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王法和天道的存在使任何现实的痛苦、罪恶都变成了一种偶然,变成了天道循环的一个过渡环节,正义终归会取得胜利。这个世界图景所表达的是乐观主义的世界观。不仅《窦娥冤》如此,《赵氏孤儿》《琵琶记》《精忠旗》等许多悲剧都是‘大团圆'式的结局,有的即使情节本身不能导致‘大团圆',也要以虚幻的方式或具有心理补偿、抵销悲剧气氛的方式结束,如《汉宫秋》结尾斩毛延寿、《娇红记》结尾羽化成仙。总之,悲剧主人公们所遭受的苦难、所经历的伤感经验,在古典的世界图景中最终都要被证明属于偶然的或局部的现象,只有正义、天道才是永恒的,因此,这些悲剧归根到底体现的是一种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的乐观主义世界观。”[5]
然而,没有一成不变的传统,时代风云的动荡、三教合流的思想发展趋势使传统本身受到了巨大冲击,这些都会促使人们重新面对和思索传统,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的个性解放思潮更引起了人们对传统的怀疑、对抗、思索甚至否弃。这些变化都会被剧作家带入到戏曲创作之中,最终通过叙述模式的悄然变化由隐而显地表现出来,因此,大团圆作为一种叙述模式虽相对固化,但其背后的文化精神仍存在着一个细微的变化过程,而这一过程恰是通过剧作家所描绘的世界图景及其传达出的世界观念的微妙变化具体呈现出来的,尽管从乐观到幻灭的发展轨迹相对整个戏曲史来说是比较微弱的,却与整个明清文学的悲观幻灭走向是相契合的。
[注 释]
①郑振铎称其为“离奇的喜剧”(《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赵景深则视其为悲剧(《<牡丹亭>是悲剧》,江苏戏剧,1981年第1期);叶长海认为其是“悲剧和喜剧揉和在一起的”悲喜剧(《中国古代悲剧喜剧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112页。
[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57.
[2]任晓润.情缘悲剧与历史悲剧的交汇融合——《木寿杌闲评》、《长生殿》、《桃花扇》悲剧意蕴探寻[J].社会科学战线,1992(4).
[3]宗白华.悲剧的与幽默的人生态度[M].艺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75-76.
[4]王国维.红楼梦评论[M]//王国维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213.
[5]高小康.市民、士人与故事:中国近古社会文化中的叙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