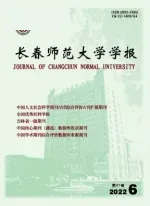晚清中韩关系走向近代外交的历程
2010-08-15李晓光陶常梅
李晓光,陶常梅
(1.长春师范学院东北亚研究所,吉林长春 130032;2.合肥师范学院政法系,安徽合肥 230061)
晚清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由衰落走向灭亡的时期,而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也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在这样动荡的环境下,清政府的外交也不得不随之改变,进而中国传统的对朝政策伴随着清朝对外关系的改变而发生着变化。尽管清政府已经认识到了中国对朝传统政策存在的危机,而且为了解除危机,也将对朝政策作了重大调整,但最终也没能使对朝传统外交政策继续下去。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并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后,中朝传统的宗藩朝贡关系走到了尽头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随之,中朝关系在经过一番调整后进入了短暂的平等外交阶段。从清政府派驻韩使节的变化,可以看出中韩关系一步步走向了正常化,并签订了标志中韩间平等外交关系的第一个条约——《中韩通商条约》。尽管这种平等的外交关系很短暂,但中韩关系还是向前迈了很大的一步。
一、晚清中韩关系走向近代外交的背景
晚清政府被迫将中国宗藩体制下的传统外交模式让位于新兴的近代外交模式,开启了中朝关系短暂的新篇章。面对这样的改变,清政府是无奈的,又无法阻止,这是由下面的原因造成的。
1.晚清中朝传统宗藩关系遭遇挑战并开始调整
近代以后,中国传统的对朝外交政策出现了危机,这既有不可逆转的国际因素,也有清朝和朝鲜国本身的原因。在清朝方面,经历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其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清朝的外交和外交政策发生了改变,同时,中国的思想界也开始活跃起来,对外部世界开始重新认识并向近代思想迈进。在朝鲜方面,日本借“云扬号事件”发动了对朝战争,迫使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这成为朝鲜脱离清中朝宗藩关系的第一步,中朝宗藩关系开始遭遇到了挑战。
在日本吞并中国的藩属国琉球后,清政府意识到了日本对朝战争并迫使其签订《江华条约》不是最终目的,它的真正目的是要将朝鲜变成第二个琉球。换句话说,就是琉球事件直接促使清政府改变了对朝外交政策。在以后与朝交涉中,清政府加强了对朝军事合作,强化了外交中的领导地位,并改变与朝经济交流模式。清政府所做的这一切,是对此前中国对朝政策的重大调整,唯一的目的就是强化中国“宗主国”的地位,使中朝宗藩关系能沿着既有的轨道走下去。
2.甲午战争使中朝传统宗藩关系终结
1894年,日本凭借对俄英的外交承诺与保证,依靠美国的外交支持,获得了有利于对清开战的国际形势。同时,利用朝鲜国内农民起义的变乱积极出兵朝鲜。而此时的清朝则无力对抗日本,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建议中日两国军队同时从朝鲜撤退。清朝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日本的同意,中日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携同参议李经芳、参赞马建忠离天津前往日本谈判。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条约的第一款中明确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1]这标志着中国对朝传统外交政策——宗藩关系的彻底结束,同时,也标志着东亚华夷秩序的终结。1898年,清政府派徐寿朋为驻朝公使,开始了与朝鲜恢复外交关系的新的一页。但派驻公使并不是一开始就实行的,是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的。
二、从清派驻韩使节的变化看中韩关系走向近代外交的历程
尽管甲午战后,中日两国间签订的《马关条约》中明确规定朝鲜“独立自主”,中朝间传统的宗藩朝贡关系也因之终结,但是,中朝间并没有建立正式的近代外交关系,下面就从清驻韩使节的变化来看一下中韩关系走向近代外交的历程。
1.商务总董
甲午战前,袁世凯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代表清政府在朝鲜处理中朝间的关系。就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袁世凯再三请求清政府允准其回国,7月19日袁世凯奉调回国,他的职位由唐绍仪署理。而这时朝鲜所处的形势也日益危重,为使清政府能随时了解朝鲜的情况,驻韩人员要随时把朝鲜的情况向清政府报告。因此,唐绍仪在清政府没有下达正式任命前,就已经代替袁世凯在朝鲜行使职权了,从7月14日起,国内收到的电报就已由唐绍仪署名拍发了。唐绍仪接任后,继续在公署向李鸿章和总署通报朝鲜局势,一直坚持到7月22日。
7月23日,日军围攻朝鲜王宫,也攻掠了中国驻韩总理公署。唐绍仪到英国总领事署暂避,他与国内的联系就此中断。8月1日,唐绍仪又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到仁川搭乘德国轮船抵达烟台。8月4日,他再乘船赴天津述职,结束了代理袁世凯担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职务。
这样,在甲午战争爆发后,朝鲜就没有中国的政府官员主持事务。总理衙门于1895年2月1日致英国公使欧格纳函称:“查贵国前署总领事在朝鲜驻扎,经袁道讠乇其代为照料,足徵睦宜相关,甚为可感……所有中国在韩商民以及公署房屋,本署均托其随时代为保护……必能善为兼顾,使华民均受其惠也。”[2]清政府将在朝华侨事宜委托英国驻朝使节代为管理,在朝侨民的利益就受到了损害。为了商务需要和尽量维持清朝在朝鲜的特殊政治地位,清政府也不能无人在朝。为此,时任浙江温处道的袁世凯给北洋大臣王文韶的建议是“拟请咨明总署,由宪台遴派熟习情形为守兼优之员往驻韩京,名系充当商董,隐以维持商务,遇事请驻韩英员出名办理,并坐催各项债款。至朝鲜情形,亦可随时探报。”[2]也就是说清政府要选派一个熟悉朝鲜情形的官员,以商董的名义去朝鲜首都,明可维持商务,暗可随时探报朝鲜国内的状况。
因此,《马关条约》签订后,北洋大臣王文韶在回复总理衙门的公函时称“韩事未定,仍以饬派商董经理为宜。”[2]12月1日,王文韶又咨呈总理衙门:“照得上年朝鲜肇乱,所有通商各口华民商务,系驻韩英总领事代为经理。现在中日和议已成,华商之在韩贸易者,须有商董照料,以资保护而兼弹压。查三品衔候选知府唐绍仪,在韩年久,熟悉情形,堪以派为朝鲜通商各口华民总商董,遇有交涉事件,商请英总领事妥为办理,并随时催还朝鲜贷款。应需薪水、公费等项,照另单酌定数目,在于收回韩款项下核实支销。”[2]由此可以看出,商务总董不具有官方性质,不代表清政府在朝鲜行使权力。它是民间性质的,所需要的经费都是从其在韩收回的款项下支出。清政府的这一做法,体现了他对朝鲜“独立自主”的地位是不甘心完全承认的,但又不愿意就此失去与朝鲜的联系渠道的复杂心态。对此,王文韶在复文中有明确的表述:“朝鲜局势未定,改委员为商董,庶不著迹。盖筹周至,钦佩无量。经费由索回韩款项下开支,亦与出使无涉。”[2]
清政府根据王文韶的建议,决定委派唐绍仪为“朝鲜通商各口华民总商董”,前往朝鲜照料在韩华商的利益。稍后,他的名义再改为“委办朝鲜商务总董”。
唐绍仪就任商务总董后,根据实际情况设立了仁川、汉城、龙山三处委员,每处各设书识一名,仁川听差三名、汉城听差二名,日本通事和朝鲜通事各一名。另外,元山和釜山两口华商不多,书识、听差每口各设一名。
在这个时期,唐绍仪在朝鲜的主要工作就是围绕立约与派使问题,巧妙地与韩周旋。
2.总领事
唐绍仪在朝鲜虽为商务总董,但并无官方的地位,一切中朝交涉仍然由英驻韩总领事代理。这样,朝鲜也以此为借口,不承认商务总董的权力。
1896年7月16日,总理衙门电商正在法国访问的李鸿章。李鸿章根据当时的情况在回电中指出:“查英、法、德驻韩皆总领事,南美如秘鲁、伯理维亚等小国,俄、奥、德亦派总领事。按公法应由总署寄信凭于彼外署,不递国书。尊拟准订通商章程,设总领事正合。”[3]7月27日,总理衙门上奏:“豫筹朝鲜通商办法,拟准商订通商章程,准设领事,不立条约,不遣使臣,不递国书。中国派总领事一员驻扎汉城,代办使事,以存属国之体。”[2]由此可以看出,清政府对与朝订立通商章程和向朝鲜派驻总领事之事的态度开始转变,但还没有完全承认朝鲜“独立自主”,还想继续维持清朝曾为上国的尊严和体面。
11月5日,委办朝鲜商务总董唐绍仪给总署的函中再次提到向朝鲜派驻总领事之事,“窃以韩王派使念切,此时卑府虽经暂为驳阻,不过一时权宜,若不变通,设法与之订立贸易章程,恐其一旦派使前来呈递国书,尤难置之不理……似莫若由均署援照公法寄文文凭于其外部之例,知照该国外部,仿照英德特派总领事驻扎韩京,妥议税则,并派领事分驻各口。”他还指出,这样“可息韩王派使之心,并可免他国使员煽惑之议,且日后中韩交涉之事,亦得有所持循矣。”[2]
11月18日,总理衙门附奏札派总办朝鲜商务总董候选知府唐绍仪充驻扎朝鲜总领事,在致朝鲜外务部照会稿中称“……查有三品衔侯选知府唐绍仪熟悉情形,公正明练,堪以派往朝鲜,作为中国驻朝鲜总领事官,先行会同贵外部妥细拟章程,禀由本王大臣核定具奏。”[2]24日,总理衙门上奏光绪帝的奏章得到批准。唐绍仪被任命为驻朝总领事,使唐绍仪在朝鲜有了正式的、官方的身份和职权,负责与韩国进行中韩通商章程的交涉事宜。中朝正式建立了官方的联系,这是中朝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前奏。
1898年10月14日,唐绍仪接到本籍来电报“丁外艰”,急切回家奔丧,因此,让汤肇贤暂行代理总领事之职。10月22日,唐绍仪接到总理衙门电谕,批准他回原籍奔丧,并正式任命汤肇贤暂时代理总领事。四天后,唐绍仪将关防文卷及报销册等移交给了汤肇贤。
3.公使
1897年10月12日,朝鲜国王在国内民众的拥戴下正式宣布称帝,将国号改为“大韩帝国”。这使韩国在政治上处于跟中国、日本同等的地位。
鉴于国际形势和中朝两国共同利益的需要,总理衙门对韩的态度有所改变,认识到:既然令朝鲜自主,就应当按公法遣使订约,“以广怀柔之量,而联车辅之情。”[2]于是,清政府不再背有大国包袱,同意与韩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向韩国派驻公使。1898年8月11日,光绪帝下旨命:翰林院编修张亨嘉著赏给四品衔,派充驻扎朝鲜国四等公使。但张亨嘉以“亲老丁单,势难远役,沥陈下悃”为由拒绝充朝鲜公使,清政府奏准。[2]接着,礼部谨奏为请旨事,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称: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奉上谕,安徽按察使徐寿朋著开缺,以三品京堂候补,派充出使朝鲜国钦差大臣。[2]
光绪皇帝又于10月20日下谕旨,“派原安徽按察使徐寿朋以二品衔候补三品京堂作为全权大臣与韩国外部酌议通商条约事宜。”[2]
由于清廷官僚机构办事拖拉和朝鲜国内政局的不稳,1899年1月25日徐寿朋才以“全权大臣”的身份抵达汉城。次日,徐寿朋向韩国外部大臣朴齐纯递交了照会和国书副本抄录。照会中写道:“本大臣钦奉我大皇帝谕旨,派充全权大臣,敬赍国书前来贵国,酌议通商条约,兹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行抵贵国都城。请烦转奏贵国大皇帝,请示觐见日期时刻,以便亲赍国书。”[4]2月1日,徐寿朋觐见韩国皇帝,呈递国书。国书中写道:“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韩国大皇帝好……中国认明贵国独立自主,怀远旧好,近察时艰,辅车唇齿之义,尤当共切讲求。”[4]这封国书完全体现了中国对韩国“独立自主”地位的承认与尊重,从此,中韩关系进入了平等交往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20日,徐寿朋与韩外务大臣朴齐纯开始就签订《中韩通商条约》举行会议,经过近半年的会谈,中韩两国就《中韩通商条约》的条款大致达成了一致意见。中韩双方于9月11日在汉城签订《中韩通商条约》,内容共计15款。《中韩通商条约》经两国皇帝批准后,于同年12月15日在汉城互换后,立即生效。《中韩通商条约》的签订,彻底结束了中朝间的宗藩关系,标志中朝两国平等外交关系正式建立。
此后,根据此条约,中朝两国互派使节驻扎对方首都。清驻朝鲜总领事馆设在汉城,于仁川、釜山、镇南浦设领事馆。韩国首任驻清使节为沈相薰,他于1900年2月赴北京就任。
在这个短暂的平等外交时期,中国派驻韩国的公使共有徐寿朋、许台身、曾广铨三位。在日本逼迫朝鲜签订《乙巳保护条约》剥夺大韩帝国的外交权后,各国都撤回了驻韩公使。1906年2月3日,中国政府也撤回了出使韩国的大臣曾广铨,改设总领事馆,派马廷亮为首任驻韩总领事,这是中韩关系的一大转折。
三、总结
甲午战争的结果,使中国与朝鲜传统的宗藩关系得以终结,并开启了新的一段外交历程。通过清派驻韩的民间性质的商务总董,再经过官方性质的总领事的过渡,到官方性质的公使确立等使节的变化历程,可以看出这种新的外交关系的确立过程,也是清政府在逐渐摆脱对朝鲜那种固有的观念的过程。尽管那种固有的大国观念还没有彻底从清统治者的意识中抹去,但清政府为了迎合世界的变化,也为了自己能在这一潮流中站稳脚,还是顺应了这一变化。
[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M].北京:三联书店,1957:614.
[2]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1972:4029,4517,4540,4563,4561,4968,4958~4959,4965,5133,5135,5165,5160.
[3]中国史学会.中日战争:第4册[M].新知识出版社,1956:239.
[4]高丽大学校亚细亚问题研究所.旧韩国外交文书:第9卷:清案2[M].韩国:高丽大学出版部,1962:323,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