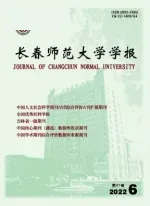略论3-6世纪北方社会习俗对疫病的影响
2010-08-15王飞
王 飞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吉林长春 130012)
3~6世纪北方地区疫病频繁暴发,对当时社会各层面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与冲击。对于导致疫病频发的因素,已有学者作以探讨考察,但这些学者大都关注这一时期政治局势、军事行动以及自然灾害对于疫病的影响,而对当时社会习俗对于疫病所造成的影响却鲜有研究。但事实上,这一时期北方社会习俗对疫病的发生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有的习俗可能会加剧疫情的传播与蔓延,有的习俗甚至会直接导致疫病的发生。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的民众卫生情况、饮食习惯及丧葬习俗等社会习俗对疫病所产生的影响作以初步探讨。
一
首先对当时民众卫生情况对疫病的影响作以考察。现代医学知识告诉我们,民众的卫生条件和习惯对预防传染病有着很重要的影响。而民众的卫生条件主要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是个人洗沐情况,二是民众所处的生活条件。我国古代民众的洗沐习俗,在秦汉时期已初步形成。彭卫先生在《秦汉时期洗沐习俗考察》一文中指出,“考察秦汉时期的洗沐习俗,由其洗沐方式和盥洗设备可看出洗沐已成为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这是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1]但这种生活习惯当指社会某些特殊群体而言,尤其是指有条件的社会上层,而汉代是小农的汪洋大海,对于这些小农而言,由于生活条件的限制,个人卫生条件一般不会太好。王充在《论衡·解除篇》中指出:“人民居土上,犹蚤虱着人身也。蚤虱食人,贼人肌肤,犹人凿地,贼地之体也”。可见普通百姓身上生虱子是比较常见的。不仅是普通百姓,就是一些上层人物身上也会因沐浴少而生虱子,如《风俗通义·过誉》记述东汉大将军梁冀从事中郎赵仲让“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魏晋南北朝时期,沐浴习俗可能较汉代更为普及,特别是社会上层对于勤沐浴之习可能更为普遍,如《南史·梁本纪下》载南朝梁简文帝撰写《沐浴经》三卷。但对于广大普通民众而言,由于生活条件的限制,能真正做到经常淋浴的人恐怕为数不多。殷伟、任玫著《中国沐浴文化》一书在《魏晋南北朝贵族沐浴奇习》中也认为条件优越的沐浴至少是中产以上的人家才可以为之,应该说是为贵族沐浴所定的程序,贫苦百姓是无法享受的。[2]此外就算当时的上层社会人士,对沐浴的态度与作法也不一致。如晋朝的王猛常扪虱而谈,当然他不会经常沐浴。由于个人卫生条件不好,身上长有虱子等寄生虫,这为传染病的产生与传播创造了条件。
民众居住条件与生活环境也会对疫病产生影响。这一时期的人口应主要是集中在广大乡村,对于住在乡村的普通民众而言,其居住条件与生活环境都相对较差。据张承宗、魏向东在《中国风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一书《居住与建筑风俗》中考证:“至于汉族人民,仍以住房为主。这一时期普通百姓居住的房舍,大多采用木构架结构,墙壁为干打垒的土墙,屋顶或呈悬山式或为平顶,房屋多围成院落,内设畜栏和厕所。民间最为简陋的住房,纯为草、竹等自然材料建造,既不牢固,又低矮潮湿,居住环境十分恶劣。”[3]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普通汉族百姓生活条件相当简陋。此外,由于其房屋多围成院落,内设畜栏和厕所,这样一来,卫生条件将进一步下降,这种设施会加重对生活区域的污染,从而有利于病菌的繁殖与传播。对于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而言,其居所以搭帐蓬为主,类似于今天的蒙古包,如《南齐书·河南传》载:“河南,匈奴种也。汉建武中,匈奴奴婢亡匿在凉州界杂种数千人,虏名奴婢为赀,一谓之“赀虏”……多畜,逐水草,无城郭。后稍为宫屋,而人民犹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对于何为百子帐,《南齐书·魏虏传》载有“以绳相交络,纽木枝枨,覆以青缯,形制平圆,下容百人坐,谓之为‘伞’,一云‘百子帐’也。”通过以上记载,可见这种百子帐的结构是比较简单的,其并没有专门的用于处理粪便等排污设施,因此卫生条件也普遍较差,这也利于病菌的滋生与传播。由于普通民众的居住与生活条件较差,尤其是卫生条件简陋,这既会引发疫病,也有利于疫病的传播与蔓延,如曹植《说疫气》载“建安二十二年 (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4]此则表明生活条件简陋的贫困之家感染疫病的机率要远远高于生活条件优越的富贵之家。此外,就生活条件而言,一般来说,城市内的居民生活条件要好于居住在乡村的民众,但在中国古代社会,城市内也未形成有效的公共卫生设施,况且城市内人口密度大,人口流动频繁,因此城市内也往往暴发疫情。如这期间先后为国都的洛阳、长安等地区,均暴发过大规模疫情,《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三年春正月戊子……京都大疫。”《晋书·武帝纪》载:“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太半。”《陈书·徐陵传》载:“开皇十年,长安疾疫,隋文帝闻其名行,召令于尚书都堂讲《金刚般若经》,寻授国子博士。”
二
这一时期的饮食习惯对于疫病也有很大影响,如北方地区流行的寒食节。据说这是为了纪念春秋战国名臣介子推,北方地区要绝火寒食一个月。《后汉书·周举传》记载:“举稍迁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者。举既到州,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由此可知,东汉中期在今山西太原一带就流行寒食这一风俗,而且是在冬天寒食一个月之久,以至于老幼体弱者多有死者。也正是因为这一寒食风俗导致有很多民众病死,所以周举才提倡禁寒食,用温食。而其结果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看来周举这种说教式方法禁寒食实际作用不太大,这一习俗并未由此而禁。为进一步禁止寒食,曹操曾下达过《明罚令》,其云:“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有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子胥沉江,吴人未有绝水之事。至子推独为寒食,岂不悖乎!且北方冱寒之地,老少赢弱,将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5]周举禁寒食还只是从说教的角度,而曹操下达《明罚令》禁止寒食,则是从国家法令层面禁止寒食。由此可以推断,这一时期的寒食不仅从太原扩大到上党、西河、雁门一带,其所带来的危害,特别是对当时民众健康的损害一定是较前更为严重,否则不会以国家法令形式加以禁止。但这种习俗并未因此而禁绝,十六国时石勒曾禁寒食,但很快又取消了禁令。据《晋书·石勒载记下》载:“勒正服于东堂,以问徐光曰:‘历代已来有斯灾几也?’光对曰:‘周、汉、魏、晋皆有之,虽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为变,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乡之神也,历代所尊,或者以为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为之亏,况群神怨憾而不怒动上帝乎!纵不能令天下同尔,介山左右,晋文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书曰:‘寒食既并州之旧风,朕生其俗,不能异也。前者外议以子推诸侯之臣,王者不应为忌,故从其议,傥或由之而致斯灾乎!子推虽朕乡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乱也,尚书其促检旧典定议以闻。’有司奏以子推历代攸尊,请普复寒食,更为植嘉树,立祠堂,给户奉祀。勒黄门郎韦谀驳曰:‘案《春秋》,藏冰失道,阴气发泄为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复何所致?此自阴阳乖错所为耳。且子推贤者,曷为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虽为冰室,惧所藏之冰不在固阴冱寒之地,多皆山川之侧,气泄为雹也。以子推忠贤,令绵、介之间,奉之为允,于天下则不通矣。’勒从之。于是迁冰室于重阴凝寒之所,并州复寒食如初。”通过这段记载可知,寒食这种习俗在十六国影响又所扩大,石勒虽曾下令禁寒食,但也没能达到目的。北魏时期寒食这一习俗仍在流行,并影响很大,因此朝廷再次禁寒食,《魏书·高祖纪》云在延兴四年 (即474年)朝廷下令“辛未,禁断寒食。”但事实上,这种习俗还是有其强大生命力,并未因朝迁的一再禁止而停止。据上可知,自汉代起在北方地区就开始流行寒食这一习俗,此后直至北朝这种习俗在北方长期流行。这种习俗在寒冷的北方地区流行,必定会导致多种消化道疾病的产生和蔓延,以至于经常会有人由此而死亡,这也必然会对北方地区疫病,特别是消化系统的疫病产生推动作用。
除这一时期北方地区寒食习俗对疫病有所影响外,北方民众的饮食方式与饮食结构对于疫病的发生与传播也有一定影响。据张承宗、魏向东在《中国风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一书《饮食风俗》中考证:“现在人们都习惯三餐制,但在先秦时期,先民们大都一日两餐,以适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业社会作息规律。汉代以来,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财富逐步增加,一日三餐制方才出现并逐步普及开来,但两餐制在贫穷家庭依然存在,直到唐代以后,一日三餐制才彻底取代了两餐制。魏晋南北朝是由一日两餐向一日三餐过渡的时期。与一日两餐制和一口三餐制并存一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食制与合食制也并行不悖。”[3]这一时期是一日两餐向一日三餐过渡的时期,对于广大穷苦之家的民众来说,应还是一日两餐,辛勤的劳作而只能一日两餐,其结果是多数贫困之民会引发营养不良,从而导致这些人降低对疫病的抵抗能力。而这一时期用餐方式从分食制开始走向合食制,这种合食制则会通过食物传播细菌与病毒,加大疫病传播的机会。对于这一时期普通民众的饮食生活,张承宗、魏向东在《中国风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一书中认为,当时民众普遍陷于贫困状态,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是经常性的情况。在相对安定的时期,老百姓的日子稍稍好过一点,富裕人家一年当中还能吃上几次肉。[3]生活水平如此之低,则必会造成广大民众营养不良,一旦有疫情发生,这些人便很难抵制住疫病的侵袭了。
三
还一个与疫病密切相关的生活习俗就是这一时期的丧葬制度,其中尤以丧葬礼仪与葬法影响最大。汉代以来,特别是汉武帝时期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逐步占主导地位,这对丧葬制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汉代的丧葬礼仪,据徐吉军、贺云翱著《中国丧葬礼俗》第二章《事死如生的丧葬礼仪》载,汉代的丧葬礼仪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葬前之礼。这一阶段包括招魂、沐浴饭含、大小敛、哭丧停尸等项内容;第二阶段为葬礼,包括告别祭典、送葬、下棺三个环节;三是葬后服丧之礼。这其中沐浴饭含要为死者沐浴;大、小敛要为死者穿衣入敛,赤贫者往往不用棺椁而以板床代替,甚至用草席卷尸;外地亲属要赶回奔丧。[6]如若死者是因染疫病而亡,那么这一系列的丧葬礼仪将成为传播疫病的重要途径。如为死者沐浴、入敛以及要停尸三日,这样一来,死者会成为传染源,而参与丧事的亲朋好友则成为被传染的重要对象。以上所言是汉代丧葬礼仪,魏晋时期与汉代基本相同。《晋书·礼志》云:“古者天子诸侯葬礼粗备,汉世又多变革。魏晋以下世有改变,大体同汉之制。”北魏时期,虽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其丧葬礼仪也很快汉化,沿承了魏晋之俗。对此,金爱秀在《北魏丧葬制度初探》一文中有详细阐述。[7]事实上,以上所述的丧葬礼仪风俗也确会带来疫病的传播。如《南齐书·孝义传》载:“建武二年 (495年),剡县有小儿,年八岁,与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小儿犹恶,不令其知。小儿疑之,问云:‘母尝数问我病,昨来觉声羸,今不复闻,何谓也?’因自投下床,匍匐至母尸侧,顿绝而死。”赤斑病即为麻疹,是一种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此记载虽是发生在南方地区,但这种现象在当时南北方是一致的。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小儿母是因感染赤斑病而死亡,但其死后尸体并没有被直接处理,而是被置于其家床下,这无疑会增加周围人员的感染机会。对于参与因染疫而亡者的丧礼会传播疫病,这一时期的医家已有所认识,如隋《诸病源候论》在谈及丧注候时云“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住易傍人也。人有临尸丧,体虚者则受其气,停经络腑脏。若触见丧柩,便即动,则心腹刺痛,乃至变吐,故谓之丧注。”[8]此记载明确指出因染注而死亡者会死后传染他人,特别是若人有临尸丧,其中体质虚弱者染病的机率会更高。这也说明当时这种现象较为普遍,否则医家不会将此种现象专例为一种症候。
除丧葬礼仪对疫病的传播有所影响外,这一时期死者的埋葬方法对于疫病的传播也有较大影响。若从防治疫病的角度看,对死者的最佳埋葬方法当首推火葬。因为通过火葬,死者所携带的细菌或病毒都会被一同消灭。但可惜的是,这一时期仅是部分少数民族地区采用火葬方式,如《晋书·石勒载记下》:“又下书禁国人不听报嫂及在丧婚娶,其烧葬令如本俗。”这说明十六国时期的羯人是采用火葬风俗的。此外,这一时期的突厥人也有火葬风俗,如《北史·突厥传》载:“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绕帐走马七匝,诣帐门以刀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但对于人数众多的汉族人,或是汉化了的少数民族而言,主要还是采用土葬方式,这与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影响日深有直接关系。儒家提倡事死如生,入土为安,但这种土葬方式实确有利于疫病的传播。对于3~6世纪的北方地区而言,饥荒、战乱频繁,曹操所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现象时有发生,大量人口死亡后暴尸荒野,这无疑会加剧疫病的传播与扩散。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的民众生活条件、饮食方式以及丧葬制度等习俗都会对疫病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有的习俗会加剧疫病的传播与蔓延,有的习俗则可能会直接引发疫病,因此这也应该是考察影响疫病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
[1]彭卫.秦汉时期洗沐习俗考察[J].中华医史杂志,1999(4).
[2]殷伟,任玫.中国沐浴文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11.
[3]张承宗,魏向东.中国风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23,47,70.
[4]赵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5]欧阳询.艺文类聚: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62.
[6]徐吉军,贺云翱.中国丧葬礼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84-85.
[7]金爱秀.北魏丧葬制度初探[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15.
[8]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二十四[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6: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