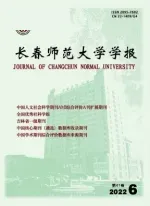诗性叙事及其审美功能
——读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
2010-08-15郭国旗
郭国旗
(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3)
法国诗评家雅克·马利坦认为,诗歌语言的诗性意义的获取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要扫除“逻辑理性”,一是要捕捉“诗性直觉”。[1]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两者内含深厚的情感因素。由于诗人的情感介入,诗歌语言不仅具有了削弱和消解普通语言具有的那种生活世界条理化、组织化、结构化、有序化的能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开放的领域,使物象、意象作‘不涉理路’‘玲珑剔透’的近似电视水银灯的活动与演出”[2]。诗歌语言的深具内在张力的组合法则体现了它本身具有的表现性倾向,它突破普通语言根深蒂固的语法规范和事理逻辑的桎梏,建构了一个具有增值性的意义空间。普通语法的事理逻辑性使得诗歌意义的生发受到限制,因此,诗歌语言的组织建构就是要在最大限度内消解语法逻辑,造成各意象间呈现出一种“未定位”或“未定关系”,从而“使读者获至一种自由观、感、读解的空间,在物象与物象之间作若即若离的指意活动。[2]正是对普通语言语法规范的“有意歪曲”与“有意触犯”,诗歌才得以产生。[3]
一
小说与诗歌在形式和审美机制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文类特征。在各种诗歌体裁中,艺术意识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体现在自己的语言之中;诗人的语言是他自己的语言,诗人始终不可分地存在于这语言之中,换言之,诗人是纯然直接地表现自己的意图。[4]诗人是有感而发,也就是借诗歌抒发自己的不可遏制的情感,因此诗歌语言遵循其本身所特有的情感逻辑法则,它不可避免地要消解普通语言的语法逻辑。英国新批评的代表人物I·A·理查兹将语言分为指称性的实用语言和非指称性的诗歌语言,诗歌语言是对实用语言的“陌生化”[5]。正是由于这样的“变形”和“陌生化”,提供鉴赏主体想象力和情感力渗入的契机,从而才能使人们在对诗歌语言的审美关照中,建构起一个异于常态的情感空间。[3]燕卜逊在《含混七型》中提出“含混”一说,他认为在诗歌中“含混”可以是一种强有力的表现手段,他说,“这些含混我觉得大部分是美的。”[6]在诗歌中,“含混”之所以能成为一种表现手段,因为在歧解中可以不断生成新的意义,而多种意义的并存必然拓展诗歌艺术世界的想象空间。
然而小说却不同于诗歌。小说意在讲故事,人物事件 (行动)是故事的第一要素,叙述语言通过对虚构事件的重新组合来编织情节,情节制造悬念进而推动故事,时间序列和因果联系 (即事件展开的逻辑性)成为了叙事话语和文本阐释的主要依据。在小说叙事中,“含混”和“陌生化”一般不表现在语言层面上的歧解上,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叙事的变形和不完整性。传统小说大多具有叙事的完整性,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要素一应俱全,故事全都有始有终,且线索明晰。而现代小说却有意识地追求叙事的不完整性,自始自终保持叙事的不透明性,留给读者一种期待中的想象。二是内涵的不确定性。传统小说作品的意蕴是封闭而自足的,现代小说作品中却有意地留下许多空白,需要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填充。诗性叙事主要是指现代小说的诗化倾向,即叙事话语表现出来的对普遍叙事语法的逻辑背离。当代印度籍女作家阿兰达蒂·洛伊 (Arundhati Roy)的《微物之神》(1997)正好体现了小说叙事的诗化特征,它的诗性叙述话语使该小说具有了诗歌语言“陌生化”的审美功效。
二
《微物之神》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印度西南沿海喀拉拉州的故事,故事的展开基本围绕着两件神秘、忧伤又恐怖的事件:首先是双胞胎艾斯沙和瑞海尔的混血表姐苏菲默尔从伦敦来阿耶门连度假,然后在一个雨夜同表弟妹玩“出逃”游戏时溺水身亡;其次是上层叙利亚基督教家族的离婚女子阿慕与贱民维鲁沙之间演绎出的一场跨越种姓、阶级的爱情悲剧,结局是维鲁沙遭警察血腥暴力致死,阿慕客死他乡,双胞胎兄妹骨肉分离。故事并非复杂,然而作者富有想象力的叙事手法却使它产生出不一般的审美效果。小说出版后不久就成为了全球畅销书,并荣获了英国小说布克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洛伊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印度籍女作家。
《微物之神》的成功首先应当归功于它明显的诗化叙事特征。它对传统的逻辑叙述和理性阅读的背弃,给了读者全新的阅读体验。首先在叙事者的安排上就有悖常理,超出了经典叙事学所界定的叙事者范畴。它表面上采用的是第三人称故事外叙述,也即非人物叙述,但却又不同于一般的故事外叙事,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很强烈地意识到,隐含作者、叙述者和人物产生了重叠。造成读者的这种阅读体验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叙述者的话语方式让读者体验到了叙述者深沉的情感介入;其次是书的献词有很明显的指事功能,读者自然会把玛丽·洛伊和LKC(洛伊和她的胞弟)同阿慕和艾斯沙依次对位。因此,只能把它界定为第三人称叙述伪装下的人物叙述或自传体叙事。也就是说,小说作者站在了诗人的位置进行书写,叙事也因此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情感色彩。小说作者隐藏在叙事之外,采用非个性化的叙事,正是服从了抒情诗的原则。作者向读者展示的不是人物形象,不是性格、个性、典型,而是抒写“我”对本民族在后殖民语境下的一系列生活事件、人性本相的切身体验和内心感受。
在当代叙事理论中,叙述距离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叙述者在故事中的参与程度,即他/她与故事中人物和行动的情感距离;二是指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在道德、情感或思想上的距离。叙述距离会影响到读者从叙述者那里得到信息的可信程度以及它的道德和情感色彩。[7]正是叙述者的特征使得《微物之神》的叙述距离产生出了动态势能。叙述通过拉近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叙述者与人物以及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增强了叙事的可信度,促进了作者与读者近距离的情感交流,也增加了读者对人物的理解和同情。作者若即若离的立场又让读者在情感付出的同时又能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清醒理性地审视文本的深层蕴意。
《微物之神》在视角安排上也体现了很强的诗化倾向。叙述者在讲述发生在几十年前的故事时,明显地放弃了叙述当下的权威眼光。绝大部分叙述都通过双胞胎小兄妹的视角过滤,在场景的轮换过程中,他们的视角也在不断交替。读者跟随着孩子们懵懂、好奇的目光,敏感地打量着印度阿耶门连小村庄的那些既古怪又可怜、既平凡又琐碎的微小事物。叙事语言的文体特征也表现出了孩子气的亲切和稚嫩:句式简单,语言形象,充满了感性的想象。按照热奈特对视角的分类,这个文本的视角模式当属于“故事内聚焦”[8]。在这种采用人物“故事内聚焦”的叙事中,事件往往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物对事件的感受。正如米克·巴尔在讨论叙事视角的修辞效果时指出,“任何呈现的‘视觉’可以具有强烈的操纵作用,因而难以与感情相分离,不仅难以与属于聚焦者和人物的感情,也难以与属于读者的感情相分离。”[9]《微物之神》通过对视角的创造性运用,再现了人物在生活中的感受和认知状况,开启了读者的情感世界。这样,“有血有肉的”作者与“有血有肉的读者”就有了更深层次的情感交流。[10]尤其是读者能够站在故事外,清醒、理性地审视孩子懵懂无知的目光,与作者的思想、感情及其伦理意识产生强烈的碰撞,进而迸发出智性的火花。
传统叙述注重的是故事事件的时间序列和因果联系。布鲁克斯就很强调叙事的时间性:“我们也许可以把情节看成逻辑……其命题仅仅是通过时间的序列和进程来展开的……我们要整理从人类的时间性意识中抽取的那些意义,原则性的整理成序的力量便是情节。”[11]H·玻特·阿博特同样也把时间作为叙事的主要特质,他说,“叙事是我们人类把对时间的理解组织起来的原则方法”。[7]热奈特对叙事的时间性则更是推崇有加,《叙事话语》共五章,其中就有三章专门讨论叙事时间。[8]然而,《微物之神》却采用了淡化情节的非时间性叙述,这正好体现了诗歌重抒情轻叙事的体裁特征。叙述沿着双胞胎兄妹在故乡的重逢 (仅一天)和二十三年前 (仅十三天)发生的往事这两条线索展开,线索纠缠在一起,增加了叙事时间的模糊性。全书共二十一章,各有标题 (绝大多数都是场景名称),且篇幅长短不一。章节与章节的叙述在现在和过去之间交替,甚至在单独章节中也常有“回闪”和“跳跃”。例如,小说第一章就采用了很明显的循环式叙述,故事事件发生的自然顺序被彻底打乱,呈现给读者的是一系列貌似无关的细节:瑞海尔从美国回到印度与离散二十三年的孪生哥哥艾斯沙团聚,双胞胎的出生,苏菲默尔的不幸遇难,阿慕的最后离家,伊培家族的历史,以及警察在维鲁沙身上施暴,等等。另外,单个事件的叙述中也常常出现断裂,表现为一个事件还未交代清楚,另一事件又插了进来。
《微物之神》采用的是一种逻辑与非逻辑混杂的叙事策略,它以诗的超逻辑的张力结构,将那些不可能同时发生或不可能成为事实的东西,变成了可能。因而文本叙事是以超时间的共时表达来建构故事的,这是一种超逻辑的叙事。当然,尽管叙事有了非逻辑的表征,读者还是可以依靠细读来发现深藏在叙述断层之间的逻辑。在《微物之神》中,叙述进程是依靠细节的堆叠来推动的,层层叠叠的细节催生出迷宫般的意象,故事的悬念在这些意象中若隐若现。帕帕奇的“蛾背上的簇毛”、“蜥蜴的眼睛”、公路上一只“青蛙形的污渍”、“枯萎的玫瑰的气味”、“历史之屋后阳台墙壁裂缝里的小蜘蛛”、如同“玫瑰色天空中的一阵灰色烟雾”的蝙蝠和“像铅一样凝重的米那夏尔河流”以及那只在艾斯沙失去至爱亲人后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病残的老狗,所有这些意象形成了一张复杂、朦胧的网,像雾一样笼罩着整篇叙事。每章以场景命名也都是作者的刻意安排,它突显了意象并置的效果。它摆脱常规的线性叙事,模仿记忆的偶然性、片段性和非连续性特征,让场景来推动叙述的进程:让每一个场景都激发出一个回忆的片段,然后再把记忆的碎片拼接起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诚如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所言,《微物之神》的叙述话语重空间而轻时间,将地点比喻为以时间为“背景”的“形象”,因此比很多其它的叙事更清楚地阐明了对空间的补偿性强调。[12]另外,两个故事之间有二十三年的漫长时光被“省略”了,出现了很长一段叙述空白。而交织在一起的本来应该是两个很短暂的故事,却被叙述的“停顿”和“描写”无限地拉长,叙述在细节的重复与堆砌的过程中缓缓推进。缓慢的叙述进程产生了强烈的修辞效果,读者在充分体会叙述话语的深刻与凝重的同时,领会到了相隔二十三年的两个故事之间的紧密关联。故事的结尾则更是体现了对传统叙事语法的背弃,可以说它是一个没有结尾的“结尾”:它只是中间发生的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的一个片段的再现。这种叙述安排让读者清晰地感觉出了作者叙事的伦理倾向:既抒发了自己的悲悯情怀和批判意识,又表达了对爱的未来的美好憧憬,读者沉重悲戚的情怀也终于有了些许希望的慰藉。
可以说,《微物之神》的诗性叙述表现出了很强的空间化趋势,叙述犹如意识流一样挣脱了时间的束缚,顺着飘荡的情绪在一个场景与另一个场景、过去与现在之间跳跃。从审美角度来考虑,传统叙事重人物、重情节。它主要是靠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以及人物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诉诸读者的感官,因此,显得比较外在化和表面化。而诗性叙事重抒情、重表现人物内心微妙的心理变化,通过这种变化诉诸读者的心灵感应,因此,这种审美体验更内在、更含蓄,作品意蕴也就更深沉和隽永。小说叙述的时间性注重的是事理逻辑,诗性叙述的空间化则更容易触发真情感悟。可以说,洛伊用诗化的笔触创造了感性的叙述——作品的非线性叙述、跳跃的故事情节、繁盛如热带植物的意象、孩子般稚嫩而充满感性的文字,使读者一翻开书就进入到一种凄美的情境。于是,读者情不自禁地与叙述者和人物一起体验真情,感悟生活。正是这种诗性叙事将读者引向了抒情诗式的阅读,把读者对于客观事件的认知转向了对主观心灵的感悟。
三
《微物之神》之所以打动读者,是因为它的诗性叙事首先让读者进入到了抒情主体的情感世界,然后再引导读者去阅读故事背后的深层意义。作者始终突出了“爱”的主题,思考了决定着人类文明根基的久经考验的价值:父母之爱,夫妻之情,诚实、善良之于虚伪、野蛮的优越性等。在整部小说中,作者一直在思考和追问“谁应该被爱,如何被爱,以及得到多少爱”[13]。作者正是通过对于这些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的利用,使读者参与到了丰富和惬意的叙事进程中来。
《微物之神》讲述了后殖民时代背景下,印度特有的“贱民”与“非贱民”这个顽固的种族等级制度下各种大小人物的种种困境与困惑,卑微与愚昧。小说严肃拷问并批判了后殖民时代印度的种性制度、男权优势、政治投机、宗教压迫,以及由这一社会语境决定的“爱的规则”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小说触及了印度民族的劣根性,自始至终透露出作家的悲悯情怀和反叛意识。
苏菲默尔溺水身亡的直接起因是孩子们半夜跟大人们玩“出逃”游戏,而“出逃”正是瑞海尔和艾斯沙对自身边缘化处境的无声抗拒。《音乐之声》中那些“肤色雪白而洁净的小孩子”让瑞海尔和艾斯沙在紧张地等待与他们那位有着一半英国血统的表妹初次见面时感到了自己身上不可弥补的肮脏和淘气。阿慕也在恰克的白人妻子玛格丽特到来以后,常常在不经意间对自己的孩子涌出了“远远超越实际所需的愤怒”。因为从小就被边缘化,阿慕养成了“一种顽固而鲁莽的癖性”,在成长过程中,常常目睹身为父亲——那位在“令人窒息的闷热中,仍然穿着那套三件式西装”的大英帝国昆虫学家,在母亲玛玛奇和自己身上施暴。为了摆脱没有爱的家庭,她不惜选择了一桩没有爱的婚姻。离婚后走投无路的她带着双胞胎回到阿耶门连,成为了没有“法律地位”而不受欢迎的人。无奈之中,阿慕只好求助于“微物之神”。小人物维鲁沙的悲剧在他的“目光和阿慕的目光交会”的一刹那就已经注定了,因为他“见到了至当时为止一直被禁止进入的事物”。同是父母所生,阿慕和哥哥恰克的命运截然相反,恰克同“贱民”女性有染不仅没有让家族难堪,玛玛奇甚至还在家屋里另设小门以照顾他的“男人之需”;而阿慕同维鲁沙的爱情却被视为违背了“爱的律法”,被家族亲人所抛弃。
无论是苏菲默尔、瑞海尔和艾斯沙,还是阿慕和维鲁沙,他们的悲剧都牵涉到了印度后殖民语境下的种性制度、男权优势、政治投机、宗教压迫等敏感的问题,这些问题全都不是偶然和孤立的,它们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形成了印度复杂而尴尬的社会现实。以“微物之神”维鲁沙为例,他遭政府机器暴力致死的原因有:逾越种姓界线的爱情、宝宝克加玛的“指控”、革命党人皮莱同志的出卖。但是,直接导致他的悲剧命运的是他的生身父亲维里亚巴本,他目睹阿慕和维鲁沙逾越了爱的界限,在奴才的忠与父亲的爱之间他选择了前者。他向主子玛玛奇告发并表白,“说他愿意杀死自己的儿子,愿意将他碎尸万段。”这种亲情关系的严重扭曲使读者对那个残酷的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正如斯坦福·弗雷德曼所言:“作为一个政治隐喻,该小说提醒我们,还要注意‘心之黑暗’。换言之,我们不仅要注意西方帝国主义和二十世纪晚期的跨国主义的余威,还要注意印度之‘心’中树起来的黑暗的边界。”[14]
四
海德格尔认为,文学是人们在天地之间创造出来的崭新的诗意的世界,是借文字展示的诗意的生存的生命。日常生活是非诗意的,我们只有通过文学的引导才能达到诗意,感受无限,领悟神圣。[15]在马尔库塞看来,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人,其感性能力被工具理性压迫已近泯灭,因此“自由所需的前提条件就在于一种感性的能力。”[16]文学是充满感性的语言艺术,它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异化”超越现实的压迫,实现人的生命本能的升华,建立与现代工具理性相反的“感性秩序”。
诗歌与小说同为语言的艺术,本来就是一对最亲近的“姐妹”,尤其是在当代,这两种艺术要素的相互渗透更是司空见惯。因此,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向作为意象文学的诗歌靠拢,是文学文类之间的正常的交流,只不过《微物之神》走得更远,更富于创造性,它完全摆脱了叙事理性的羁绊,走向了诗的感性世界。洛伊凭借自己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向传统的逻辑叙述和阅读理性发出了挑战,创造了独具魅力的诗性叙事,从而让读者获得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
[1]雅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M].刘有元,罗选民,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225.
[2]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35,170.
[3]穆卡洛夫斯基.标准语言与诗的语言[M]//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篇选编(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415,424.
[4]M.M.Bakhtin,The Dialogic Imagination,Michael Holqist(ed.),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trans.),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285.
[5]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6:85.
[6]赵毅衡.“新批评”文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104.
[7]Abbott,H.Porter.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Narrativ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74,3.
[8]Gérard Genette,Narrative Discourse,Oxford:Basil Blackwell,1980:189,33-160.
[9]Mieke Bal,Narratology: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London: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7:144.
[10]Wayne C.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Chicago,IL:U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163.
[11]P.Brooks,Reading for the Plot:Design and Intention in Narrative,New York:Vintage,1984:xi.
[12]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空间诗学与阿兰达蒂·洛伊的《唯物之神》”,宁一中,译[M]//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M].申丹,马海良,宁一中,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12.
[13]Arundhati Roy,The God of Small Things,New York:Random House,1997:117(所有标注页码的引文均出自此文本,未再加注。)
[14]James Phelan and Peter J.Rabinowitz,(ed.),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5:202.
[16]马尔康塞.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M].北京:三联书店,1989: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