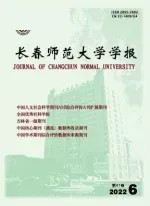释“格义”:佛经翻译策略之辨
2010-08-15刘桂杰
刘桂杰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郑州 450011)
佛经翻译在中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自《法句经序》始有翻译理论著述。从支谦到北宋赞宁,历经千余年,产生了诸如“五失本,三不易”、“厥中论”、“五不翻”、“六例”等译经方法和策略,经历了从直译到意译,再到直意译的圆满调和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佛教对自己“他者”地位的认同使得佛经翻译开始附会中国传统的道、儒、法等各家思想,以迎合中国统治者的喜好、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适应中国文化。同时,本土译者在“损异”而“善我”的译经实践中加速了这一进程。“格义”就是“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1]。佛教经典通过“格义”翻译策略成为中国本土文化价值的附会者和迎合者,得以在中国传扬,虽然其呈现的样态“先旧格义,于理多违”,但是其与中国文化思想的杂合并融合促进了佛经翻译中国化的进程,在哲学、语言、文化和翻译策略等方面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内容,在翻译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格义”探源①
(一)佛经翻译中国化
隋唐以降,佛教在中国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佛教经典也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跨文化传通,佛经翻译也要逾越不同语言文化的界限所形成的天然鸿沟。为了在中文语境中建构佛教的话语系统,扩展佛教的域外世界,外籍僧人在努力地融入汉语语言文化系统的同时,汉地佛经译家也在精研佛经的基础上将其与中国文化融合,以适应汉语语言文化系统。究其精神实质而言,“格义”这种“附会中西之说”的策略推动了异质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使不同文化视阈趋同成为精神努力的方向,使佛教文化与儒、道文化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2]
佛教经典的翻译,使佛教东渐有了文本支持。早期的佛经翻译,以儒、道等的文化观念来比附佛教观念,以文化的杂合 (不是融合)来推动佛教的发展;道安提出“先旧格义,于理多违”,以儒、道的义理来比附佛教中的“事数”总是有违佛法本义的。但是任何一个宗教思想的发展,任何一个哲学的抽象,都不免有一个接受—继承—创新的过程。佛教从汉末传入,几经劫难,不断调适,与中国固有文化融汇,逐渐实现了中国化的转型进程。因此,“格义”使得佛经翻译走上了中国化即儒道化的不归路。[1]
(二)“格义”探源及认知
据流传甚广的资料显示,道安是把“格义”作为佛经翻译策略的第一人。但是作为概念,“格义”最早见于梁代《高僧传》:“时依雅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郎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3]。由此看来,“格义”就是用人们所熟知的儒、道家经典中的义理、名词概念等去比拟或配附佛教经典中的“事数”,使佛经中深奥的义理得以理解。“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即是用一种文化中的概念去比附另一种文化中的概念以达到视阈融合。“格义”不是“格”某物的“义”,而是两种业已存在的“义”的类比。[3]道安及其之前的佛经译家文体归于古朴,“格义”之风使然也。
“格义”策略作为佛教传入中国并希冀为中国文化接受的权宜之计,对于佛经翻译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以儒、道家的经典去比附佛教经典“事数”,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阐释”的过程,是佛教为中国文化接受的必经阶段。以中国文化为视角,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理据,佛教经典义理的传通中难免会有意无意地存在理解上的偏差或偏见,会重重地染上中国文化的色彩;作为异质文化和“他者”地位的认同,在与中国文化的交流融合中,会失去自身,最终消融于中国语言文化语境之中,形成新的文化内涵。
二、现代视角下的阐释
佛经翻译时期“格义”作为一种翻译策略,尽管“于理多违”,但却适应了质朴之风,有天然之语趣,外籍僧人与中国译经家都乐于用外典 (儒、道家的名词概念)来翻译佛经的概念、词语。[4]“格义”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杂和之途中的必要性、作用及其在佛经翻译中国化中的意义,笔者以现代的视角,从哲学、文化和翻译策略等方面对其理论阐发。
(一)哲学:二元悖论之自然选择
佛教经典作为一种文化,具有文化的特征:文化是共享的、可习得的、动态的。佛经翻译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亦应具有文化交际的固有特征:接受、融合和创新。“格义”在面对本土文化和异质文化的二元选择时,以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思维”,即以儒、道哲学去比附佛法精义,其实质是将中国固有的哲学概念 (主要是老庄哲学概念)和词汇与佛教中的“事数”进行比附,借用中国原有哲学概念解释佛法,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佛法精义。自汉至北宋,慧远援引《庄子》疏解佛学的“实相”,以及以“无为”释“涅般木”、以儒家“五常”配“五戒”,即以“仁义礼智信”比附“五禁”等,此种方法是不符合佛法本义的,由是失之牵强。它在佛教东渐、融会的早期,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终究不是长远之计。伽达默尔认为,“任何带有译者本体思维的翻译都是诠释的,想要达到所谓的唯一的意义是不可能的”。在汉语语境中来理解佛教精义,“以‘道’来理解‘菩提’(bodhi)、以‘无’来指代‘空’(sunyata)、以‘无待’来代替‘涅’(nirvana)……”[5],都是本土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强势侵入和归化。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格义”是以中国原有概念“格”佛学之“义”,哲学上要走出“格义”时代之说最起码的要求,就是“通顺”。走出“格义”时代,关键是要将原来“不通顺”的解读变成“通顺”的,而不在于简单变换格式。[6]此处“通顺”,当然应有“不失本”之意。
(二)文化:相通、杂合之合理选择
“格义”策略在佛经翻译中一方面推动了文化间的交流融合,但同时似乎忽视了佛经读者接受异质文化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证明了人类文化的精神相通性。如前所述,文化是可以习得的、动态的,不同地区和种族的文化具有特殊性亦具有类同性,这种类同表现在佛经翻译中国化过程中的连类比附具有合理性,是文化间“趋同”现象的反映。高圣兵等 (2006)认为,“格义是实现思想交流与对话的无奈选择,是杂合思想之化生的必然选择”[2]。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当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输入国内时,国人会以文化间的相通、动态适应为认知预设,将本土文化的某些侧面与之连类、比附、相配,以此诠释新的文化样态。
“格义”是以诠释理解异域文化为认知指向,突显了诠释者 (译经家)的主体和本土文化意识,以超越语言文化的天然鸿沟,达到不同文化间的视阈融合。从本义上来说,采用“格义”策略来沟通佛典中国化的道路,就是将中国儒、道等家的典籍同佛典中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名词概念“粗暴”地进行对等理解,使佛典精义中的文化异质与儒道合流,谓之文化杂合。在跨文化传通和融入中国文化世界的目的前提下,佛教这种文化异质只能接受自己“他者”的地位。因此,这种比附格义的策略在当时是合理的选择。
(三)翻译策略:归化异化之无奈选择
佛经翻译文体经历了“文”“质”之争,终以惠远厥中之论“质文有体,义无所越”告一段落;翻译方法经历了“名”“实”之辨,继道安、罗什之后,僧睿以“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7]概之。名实之辨反映在翻译策略上,在笔者看来就是归化、异化如何选择的问题。“只要异域文化进入本土文化,无论译者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策略,其不可避免地具有语言文化上的杂合”[8]。“格义”策略在佛经翻译中的采用,以理解异域文化为指归,以过度的归化为导向,对佛典精义的曲解是难免的。作为跨文化交流,佛经翻译也要有一个发送和接受信息的机制,这种机制要交际效度的制约。翻译效度由趋同和趋异两个因素影响,效度与趋同度成正比,与趋异度成反比。过分的趋同 (杂合)无法为目的语文化接受,过分趋异 (流散)则会曲解异域文化精要,引起文化僵化。在佛经翻译中,“格义”方法就是以两种业已存在“义”的类比来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显然会有交际失败的危险。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说,佛教文化在向本土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其信道 (channel)必须是畅通的,但是由于语境、文化、思维、民族性等因素的影响,这种“理想之国”是难以实现的。
(四)身份认同:文化体现之历史选择
在翻译实践中,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还是某一特定领域的文化,识别文化身份可以突显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潜质,保护本民族的核心文化价值不受破坏并得以彰显。传统中国文化观念中的“自我中心论”和“中国本体论”形成了中国文化实体化和实质化的洪流。考察佛经东渐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格义”这种“中学”附会西学的策略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但是,文化从来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事物,文化身份的认同也就成了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文化多元性的现实告诉我们,所谓的文化“纯洁性”已经成为文化开放和交流融合的桎梏。事实上,一个民族或文化实体本着原有的文化基质,按自己的意志去消化,吸收其他文化的成果并最终超越之,是现今各文化发展的共同历程。因此,我们应该在保护本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同时,吸收异质文化,在“文化自我”和“他者文化”的交流中进步、发展。
文化身份从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会因文化的杂异而存在,随文化的杂合而变化。翻译在以巨大的力量构建对异域文化再现的同时,也构建了本土文化[9],佛经翻译尤其如此。考察译经史,归化和异化策略的争辩就是“文化自我”和“他者文化”地位何为主、何为辅的历史反照。
三、结语
一部中国翻译史,有一半是佛经翻译史。季羡林大师曾言:“中华文化的长河有两次新水的注入,其中之一就是从印度来的水”。显然,这“印度之水”就是佛经翻译或曰西学东渐。在佛经翻译中国化的过程中,“格义”策略影响了多位译经大家,尽管“附会格义,于理多违”,但在佛经译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对佛经翻译的了解,我们可以发现译经过程并未完全受制于宗教思想的藩篱,而是借鉴了中国传统儒道之家的思想,使佛经翻译深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以儒道来比附发挥佛典精义,使其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系统。为维护自身文化的纯洁性对外来文化一味地否定拒绝,是不可取的;而如果脱离了相关的语言文化语境,强作比附阐释,亦会引起文化僵化甚或文化冲突。因此而言,“格义”在佛经翻译时代,特别是中国化兴盛的时代,是具有必然性的,也是必经的阶段;以现代的视角,在文化多元和“超地域文化共核”共存的现实下,在接受外来文化上应保持一种开放的自信态度。“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通中,既有西方文化的东方化,也有东方文化的西方化,在共同性中寻找差异性,在差异性中寻找共同性”[10]。但这种差异、碰撞和冲突是可以调和的,会在发展中对话最终融合。
[注 释]
①根据陈寅恪、汤用彤等的研究,“格义”比较完整的注解是在《高僧传》第四卷。本文主要关注“格义”翻译策略的现代阐释和反思。对“格义”本义的详解,见《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
[1]张申娜.从“格义”看佛教中国化[J].河池学院学报,2007(3):16-19.
[2]高圣兵,刘莺.“格义”:思想杂合之途[J].外语研究,2006(4):52-56.
[3]张舜清.对“格义”作为言“道”方式的反思[J].学术论坛,2006(6):22-25.
[4]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55-57.
[5]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96.
[6]张耀南.走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格义时代”[J].哲学研究,2005(6):56-61.
[7]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21.
[8]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J].中国翻译,2003(4):3-8.
[9]韦努蒂著,查正贤译.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C]//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59-360.
[10]刘登阁,周云芳.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