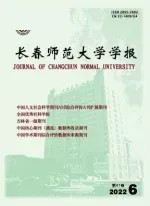《诗经》中的“物感”观
2010-08-15王惠丹张桂琴
王惠丹,张桂琴
(1.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国际部,北京 100102;2.大连广播电视大学文法系,辽宁大连 116021)
“物感”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最为重要的范畴之一。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代诗歌中就已出现了“物感”萌芽,只是此时之“物”与“感”是处在一种无意识的混融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创作观念中,创作主体往往将自然人格化,赋予它们与人相同的生命情感及意志,把它们当作与人类自身的情感相同相通的对象。万物有灵观念和互渗律观念使人们产生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同情同构、物我交感等观念。在这种观念的观照下,此时的“物”与“感”之间几乎是处于一种尚未被人们拿出来思考的混融状态。
一、先秦“物我”观与“物感”观
远古时期,人们笃信人与天地自然是为一体,自然具有和人类相同的器官,自然万物就是人,人就是自然万物,人与自然具有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先民们看待自然与现在我们较为客观地看待自然的情况不同。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认为:“对原始人来说,纯物理 (按我们给这个词所赋予的那种意义而言)的现象是没有的。流着的水、吹着的风、下着的雨、任何自然现象、声音、颜色,从来就不像被我们感知的那样被他们感知着,也就是不被感知成为与其他在前在后的运动处于一定关系中的或多或少复杂的运动。……原始人用与我们相同的眼睛来看,但是用与我们不同的意识来感知”[1]。原始先民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有某种神秘的联系,他们将自然万物人格化,像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那样来观察自然万物,以己度人,并且,正如身体上的一些变化会给人带来影响一样,人与自然万物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神秘的相互影响和约束。先民在漫长的狩猎、采集和原始农业生活中,通过自然外物获得各种必需的生活资料,是他们生存下去的根本,所以对自然的依赖使先民与自然之间充满了亲切的感觉。“自旧石器时代开始的采集和渔猎活动使中国史前先民培养了对物象的观察和体悟能力,物象之间的巫术或相似联系成为中国人早期思维关注的一个恒定目标。”[2]
然而自然并不总是给予人们所需要的一切,同时也给予人们种种磨难。洪水、火灾、雷电、地震……原始人不能解释这些现象,因此神秘感、恐惧感必然相伴而来。在不期而来的灾难中,人们也不是全然逆来顺受,《山海经》里记载的“精卫填海”、“鲧禹治水”,《淮南子》里“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共工怒触不周山”等等,都反映了原始人类对抗恶劣的自然灾害的活动。尽管如此,在先民的意识中,人与自然万物总是密不可分、同体同构的,其关系神秘而不可更易。“正是在中华民族的祖先对于人与自然关系这种原始体验的基础上,人们建构了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影响最为深远‘天人同构’的宇宙模式。”[3]
原始人类在漫长的农业生产过程中,情感活动和自然外物之间便形成了一种神秘的、难以言说的但却是强烈的、极为密切的对应关系。这种“物”与“感”之间的神秘对应、先在的联系,其实就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也就是文学创作中“物感”无意识混融状态的基础。“集体无意识”就是人与自然之间那种神秘的关联的意识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中积淀下来的结果。荣格曾这样说:“每一个意象都凝聚着一些人类心理和人类命运的因素,渗透着我们祖先历史中大致按照同样的方式无数次重复产生的欢乐与悲伤的残留物……表现着一种感知和行为的确定类型”[4]。“在人类精神发展史上,巫术宗教和艺术在情感文化领域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原始图腾到一神崇拜,从巫术的祭祀到宗教仪式,艺术曾作为巫术宗教的伴侣而出现。”[5]也就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巫术曾是人类科学、艺术、哲学、宗教、政治等文化的雏形,是当时的人类唯一可能创造出来的文化形态。”[2]最早的中国文学形式——诗歌,在其开始的时候并不独立,而是依存于巫术宗教的、以与诗乐舞合而为一的形式存在着。《河图玉版》记载:
古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三尺,吹之如嗥,三人被发而舞。
巫术、宗教仪式中的“咒语”可认为是诗歌最早的雏形。巫术、宗教仪式是人们娱神的一种方式,通过这样的仪式,人们与自然中神秘的“鬼神”相通相连、对话交流、呼唤祈求,进而对人类和自然发生影响,以利于人类的活动。在祭祀活动中,巫觋一边舞蹈,一边念诵咒语,并有音乐的伴奏,其中咒语和音乐、舞蹈都是先民们沟通天人的方式。《吕氏春秋·古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就表明了在远古时代歌、乐、舞三者是相互结合的,并没有独立的形态,在祈祷、娱神的仪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后来的“诗”作为一种“徒歌”,在其内容上仍有一段时间保留着“咒语”的某种特质。相传为伊耆氏的《蜡辞》就很明显地表明了这种特质: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牲》)
虽然是以祝词的面貌出现,但本质上具有“咒语”的作用。人们试图利用自己的语言去影响、改变自然。利用语言影响自然是原始巫术中的交感巫术的一种,这种原逻辑的思维方式,反映着先民对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神秘联系的思考,以及先民试图通过“咒语”的方式,起到沟通自然、连接外物的作用。正如论者所言:“相信人与动物、植物或周围其他事物存在神秘的联系,是原始思维或神话思维的共同特征。……从心理机制上说,巫术是人类高度自我中心的产物,是人用情感试图同化外在世界的一种顽强的意志……科学讲求对现实的顺应,巫术则将现实向自我中心式的欲望同化,遵循的是一种‘情感逻辑’,它和神话思维一样,运用类比和认同两大虚构性原理将自然同化为人类形式。在这种巫术性的思维投射中,人与外物处于一种互惠、互感和相互联系的关系网中,他们构成一个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2]。在后来的诗歌中也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原始思维遗留下来的痕迹,虽然那时候的诗歌已然失去了咒语的性质,但仍然体现着积淀在思维中的那种人与自然之间互相关联的但却以无意识状态存在的混融状态。
二、《诗经》中的“物”“感”关系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诗经》中,“物感”已初露苗头,只是这时“物”与“感”(人类内心的情感)之间呈现出无意识混融的特点,如《王风·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重章叠句,往复回环的咏叹,表达了诗人古朴苍凉又激越悲愤的情感。”[6]在诗的三章中,描写自然植物“稷”分别使用了“苗”、“穗”、“实”,是植物在自然生长中变化的不同形态;而表现人内心情感的“摇摇”、“如醉”、“如噎”,则显示出心情的变化。随自然物的生长,心情也变得愈加沉重,内心情感与自然物之间的变化显然有着某种对应关系。“苗因风而动,恰似心情的摇摇不能自持。抽穗的醉态正如忧心的沉醉,结实的高梁,对应着诗人心忧难受好像高粱米噎在喉中。物景与心境相连,自然时间与心理时间同步,物貌与心貌同态,呈现出一个特定的心物同态结构。”[7]对于这首诗是有意如此构思抑或是随口吟唱而出,虽然学界各有主张,但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出原始思维中那种人与自然相通相联、同体同构的印记。
《诗经》中所描写的自然外物与创作者内心情感尚未明确形成固定的对应关系,“物”与“情”形成明确的对应关系是后人对自然更为客观的认识、对创作愈发自觉的情况下形成的结果,这样的对应是在中国诗歌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固定下来的,也是“物感”思维发展的结果。《诗经》中自然外物与内心情感之间常常表现为一种没有主观情感投射的随手拈来的关系,其中的“物”与“情”之间是一种无意识的关联,是“物感”初始的萌芽。比如《周南·关雎》一篇: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顾颉刚先生在其研究中曾援引郑樵《读诗义法》中的观点:“‘关关睢鸠’……是作诗者一时之兴,所见在是,不谋而感于心也。凡兴者,所见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类推,不可以理义求也。”《关雎》的作者随手拈起“雎鸠”作为诗歌的开头,不一定有什么特指意味。再如以下的例子:
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陈风·衡门》)
两诗中都提到了“鱼”这种自然物,然而前诗接着写的是王室的衰败,后诗写的是婚姻和爱情,所写到的自然外物与所反映的内心情感之间并没有确定的关联。“物”与“情”之间固然可能有着某种指向的倾向,却仍属一种无意识之下的抒写。再如: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南·桃夭》)
同是写到“桃”这一事物,却是表达幸福与悲伤两种截然相反的感情。这样的例子有很多,都表现出诗人对自然事物的随意拈取、无目的性的态度,是一种无意的感受过程,不是某“物”必然引起人们内心某种感情,也不是一定通过目之所及的某种“物”来抒写内心的情感,“物”与“情”之间没有必然的确定指向性。
可以说,《诗经》中有些诗歌中用来开头的自然之物与诗中的情感情绪之间客观存在着某种较为稳定的联想关系,但这些自然景物不是作者内心之“情”受到自然外物的真实触发,也不是“物”感发了人内心的情感,只是口头文学中类似行吟诗人那样,说到某种情境之时便取出一些自然景物来进行烘托,而不是“情”与“物”之间现实的互动关系。
三、《诗经》中的“物感”观
《诗经》中自然物候与表达的感情之间不仅较少存在明确的规定性指向,而且还常常作为一种随意的、习惯性的呈现手段。孔子认为《诗》中的自然物候只是为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一方面出于儒家简朴率真的追求,另一方面恐怕还是由于《诗经》本身并没有较多提供自然与主观情绪相契合的经验。”[8]而后代论《诗》的各种言论中所说的那种情与物的契合、对应关系,那种与人们所认可的情物关系达成的一致,更可能是在这种艺术现象产生以后,漫长的文学创作积累对人们审美观念产生了影响的结果,是一种“以己度人”的现象。不过必须承认,后人总结出来的《诗经》中的:“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表现手法,与“物感”有着密切的联系,“物感”就是在“他物”与“所咏之词”间建立起一种细腻的、密切的、对应的联系,利用“所咏之词”的形式体现出“物”与“情”在人们心灵中一种互动感发的关系。那些原始诗歌中的物象、意象深深埋藏在中国古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当人们在现实中遇到某一境况时,这些原始意象便极容易被激活,形成一种强烈的情感活动,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学中“物感”所包含的“感物而动”、“情以物迁”等活动的情感活动模式。
原始先民遗留的一些原始思维方式和集体无意识观念相融合,使《诗经》中的自然外物与内心情感之间呈现出一种无意识的混融。包括诗歌创作在内的“中国人所有的实践领域都体现着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就包括它所特有的那种整观宇宙和比类取象的审美特性及艺术特质。”[9]“原始思维是以集体表象为基础的。集体表象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客体形象与情感-运动因素相融合”,其联想性是“无迹可求、无理可绎”的;而艺术思维则是“客体表象与作者的主观情感相结合的产物”,其“基本逻辑则为:类比。”[9]如《诗经》中的《采薇》、《东山》等篇,就都有着这样转化的痕迹。如《小雅·采薇》: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诗中自然物候和诗人的情感心境几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极具感情深度的作品虽然在《诗经》中所占比例较少,但在文学史上却是值得记取的巨大进步,“物感”所包含的情感与自然物候的关系、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在这里几乎都可以找到答案,甚至可以说在这样的创作里已经体现了物感的完整要求,只是这时物感的理论尚没有出现罢了。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艺理论与文学创作始终无法同步的规律。
可以说,《诗经》中“物”与“情”的关系尚带有一种无意识的混融性,然而积淀在人们思维中的创作经验在其后“物感”的发展流变过程中却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主体意识较强地介入了创作之中,开始审视自然之“物”与内心之“情”的联系,并且在创作过程中得以体现时,“物感”才能进入更为高级、更为自觉的发展阶段。
[1][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4-35.
[2]梁一儒,户晓辉,宫承波.中国人审美心理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24,61,34.
[3]赵辉.心旅第一驿: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心态之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381
[4][德]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M]//神话——原型批评.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100
[5]吴中杰.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史论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57
[6]王立.文人审美心态与中国文学十大主题[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3:425
[7]张法.中国艺术:历程与精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83
[8]竹杖芒鞋:汉赋的文学启发意义[A].“国学论坛·汉魏六朝文学论坛”=http://bbs.guoxue.com/list.asp?boardid=4:2002-02-24.
[9]成水金.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先秦散文发展线索探寻[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157,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