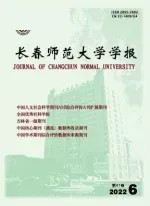论嵇康养生思想及其玄学特质
2010-08-15孙浩宇
孙浩宇
(长春师范学院《昭明文选》研究所,吉林长春 130032)
养生是嵇康“竹林之游”的重要内容。据《晋书》记载,“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嵇康约在魏正始八年 (公元247年)退居山阳 (今河南焦作有山阳区),“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这就是名传千载、让人神往的那段“竹林之游”。在此我们想关注的是嵇康“竹林之游”的生活状态。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可见,嵇康是竹林名士中最特别最坚定的一个。《晋书》载嵇康“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自述“抱琴行吟,弋钓草野”,“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乌,心甚乐之。”可见其竹林生活的内容主要是服食导养、游观山泽和弹琴咏诗等。《琴赋》 (并序)中说,“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识音者希,孰能珍兮;能尽雅琴,唯至人兮。”嵇康认为,音乐有愉悦身心、养性养生的极佳功效,而弹琴的又一功能则是希求一种“至人”间的交流,这是友朋交游的需要。故嵇康退居山阳,养生是很重要的生活方式,这也是其“长好《老》《庄》”的一个体现。
还需说一下嵇康“退而不隐”的困顿和矛盾。作为“有奇才,远迈不群”、“龙章凤姿”又“与魏宗室婚”的贵戚,嵇康的竹林生活并非单纯地养生那么平静。魏正元二年 (255年),嵇康差点响应丘俭讨伐司马师;次年,嵇康作《管蔡论》,其中暗含声讨司马氏的政治寓意。其时魏帝曹髦在太学与儒生讨论经义也论及管蔡,这传达出一个信息:退居的嵇康与曹魏集团还有暗中的联系和呼应。难怪嵇康自言“昔惭柳惠,今愧孙登”(《幽愤诗》)。无论进退,嵇康一直处于矛盾之中。这种状态造成了其人生的悲剧,这也是我们探究嵇康养生及玄学思想的入口。
嵇康的养生生活还包括饮酒和清谈。“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意毕矣。”(《与山巨源绝交书》)魏晋人流行吃“五石散”,吃了之后,浑身发热,要脱掉衣服,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饮酒常是与吃药并行的,自然属于养生行为。至于“清谈”,又称“玄谈”。一般是远离世事、崇尚虚无、空谈名理,以求理和娱乐为宗旨。这种玄谈的话题便构成了玄学的思想内容,如有无之辩、名教自然之争、言意之辩、声无哀乐等。养生也是当时名士辩难的一个重要话题,嵇康、向秀留下的答难论文可视为这种玄谈的文字形式。
一、嵇康等魏晋名士为何重养生
魏晋名士有很强的养生意识,其原因大致有三:第一是现实因素,汉魏以来人们的生命忧患意识增强。当时的战争、政治动荡以及灾疫造成的伤亡巨大,人们的心灵饱受生离死别的苦痛与折磨,人生短促、朝不保夕的慨叹在汉魏诗文中触目皆是。《薤露》:“薤上露,何易。露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古诗十九首》里有“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寄一世,淹忽若飙尘。”嵇康、阮籍身处魏晋易代之际,复杂的政治斗争更让他们毫无安全感可言。在《咏怀》中阮籍写到“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人生如尘露,天道邈悠悠。”“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这种对生命的忧患意识激发了人们对养生求仙的向往和渴求。于是阮籍有“焉见王子乔,乘云翔邓林。独有延年术,可以慰吾心。”“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咏怀》)嵇康有“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寿?思欲登仙,以济不朽。”(《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幽愤诗》)“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游仙诗》)“齐物养生,与道逍遥。”(《四言诗》)
第二是思想观念,养生受道家、道教的影响很大。道家养生观发端于老子。老子主张善待生命,认为养生的关键是保持和气不散,反对吃药、补气等外在的益生措施。庄子继承了老子,《庄子·养生主》专谈养生问题,主张人应从身心两方面的困境中挣脱出来,善待生命,顺应自然。庄子还提出养生以养神为重,追求一种精神自由、自在的境界。《淮南子》继承和发展了庄子养生重在养神的思想,强调养神,反对无穷的声色、贪欲和奢侈,主张抛弃思虑,回归自然。嵇康讲“宁如老聃之清静微妙,守玄抱一乎?将如庄周之齐物变化,洞达而放逸乎?”(《卜疑集》)体现了在养生思想上对老、庄的衣钵相承,在方法上则接受道家及道教的清静寡欲,以最终达到养神养生的目的。
第三是时代好尚的驱使。养生最能体现魏晋名士的精神风貌,名士们不仅乐衷吃药、饮酒、导养,更喜欢琴酒诗吟之中的扪虱而谈,而养生也是他们清谈的重要内容。嵇康、向秀留下了专门论文;阮籍在《咏怀》中谈到“处哀不伤,在乐不淫。”“何用养志?守以冲虚。”“逍遥逸豫,与世无尤。”“列仙停修龄,养志在冲虚。”《世说新语·文学》载,“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王导过江已至东晋,而颜延之《家训》中专辟《养生》一章,更在嵇康没百余年后,可见魏晋重养生的流风之盛。
概言之,养生风气的形成源自乱世的疼痛、观念的凝结和时风的浪漫,这是儒、道、玄交织的三层因素,也构成了养生与玄学在认识基础和思维理路上的共同之处。故养生虽未必是玄学的核心话题,但却很好地反映了玄学的某些精神特质。比如道学养生讲求的任自然与名士风流中的纵酒和疏狂的矛盾。阮籍“母终,饮酒二斗,吐血数升”以及“恸哭穷途”的行为,不仅与养生背道而驰,同时也体现了魏晋名士思想基础和心理深层的复杂矛盾。
二、嵇康养生思想与道及儒之关系
嵇康生活在中国“士”文化精神的形成期,其身上已体现出一种试图游骋儒道的气质。嵇康的养生思想在魏晋名士中很有代表性。这其中就表现为玄学以道家为基础,出于儒、入于道又终难离儒弃儒的矛盾性和调和性。
嵇康养生理论的出发点是本出自然、和于自然,这首先肯定了养生的可行性前提。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难养生,向秀就持这种观点。对此,嵇康在《养生论》中指出原因:“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肠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气,思虑销其精神,哀乐殃其平粹。”认为凡此六种都是养生之大碍。长生之所以难见,就是因为人们“惟五谷是见,声色是耽”的缘故。嵇康又从庄子的“齐物论”出发,指出难养生的原因只是违背了物性。客观外界一切事物 (包括人的才、神、性)都是以“自然相待”的“元气”、“五行”为其形成的物质基础,而“不假人以为用”。认为客观事物都是阴阳两气、矛盾运动的结果,只要合于天道,再“导养得理”,便可“以尽性命”。这种养生观破除了天命论,有肯定人为努力的积极作用。
嵇康讲由物性到人命的养生之术。所谓“夫至理诚微,善溺于世,然或可求诸身而后悟,校外物以知之者。”“性命之理,因辅养以通”,肯定了物性和人命的相通,也明确了辅养长生的科学性。“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欢蠲忿,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鱼不养,常世所识也;虱处头而黑,麝食柏而香,颈处险而瘿,齿居晋而黄。”(《养生论》)由此看出嵇康对物性(药性)的认识,通过“食之气”得以相应地“蒸性染身”。《答难养生论》又讲“橘渡江为枳,易土而变,形之异也。纳所食之气,还质易性,岂不能哉?故赤斧以练丹发,涓子以术精久延。以松实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烟。务光以蒲韭长耳,邛疏以石髓驻年。方回以云母变化,昌容以蓬易颜。”以道教仙人为例,强调服食易性、导引养生的方法,为人们追求养生指出了操作门径。
嵇康讲重神不轻形的养生之道,提出“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形神一直是道家所热衷的问题,庄子认为“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强调精神对生命的绝对作用。而嵇康则提出了更为辩证的形神并重的养生观点,“或弃世不群,志气和粹,不绝谷茹芝,无益于短期矣。”他重视养形,这就把老庄的养生观具体化,增强了操作性。嵇康主张“呼吸吐纳,服食养身”,这是养形,但养形的最终目的是“纳所食之气,还质易性”,这是养神与养形交互为用。所谓“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就进一步在形神相亲并重之中体现出养神对养生的支配性作用,而这种决定作用又是建立在“神须形以存”的认识基础之上的。“或琼糇既储,六气并御,而能含光内观,凝神复朴,栖心于玄冥之崖,含气于莫大之者,则有老可却,有年可延也。”由养形而求养神,并以养神为宗,这体现了嵇康养生观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比起老庄是一个进步。
关于嵇康养生与儒 (当时所谓名教)的关系常为人们所忽略,其实嵇康“世传儒业,有俊才”而“长好庄、老”,这便是他思想中儒道并存的先天条件,联系嵇康的身份和处境,我们不难体会到嵇康养生思想中兼容儒道的合理成分,这可归结为一个从养德与养神 (养性)到养生 (养形)的理路。《释私论》中说:“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以违道为阙。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恶;虚心无措,君子之笃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无身,吾又何患’。无以生为贵者,是贤于贵生也。”这段论述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可说是嵇康作为玄学名士向名教虚伪性挑战的思想总纲。而值得注意的是,嵇康的思想是出于名教后反名教的,其思想的指向或说出发点其实是儒。嵇康力图调和并打通儒道,其养生思想亦不例外,既要道家的任自然,又要以儒道中的“德”为约束,以德的“度”来克制欲望,打通物情,走向养生。在《答难养生论》中,嵇康提出养生有五难,“名利不灭,此一难也;喜怒不除,此二难也;声色不去,此三难也;滋味不绝,此四难也;神虑转发,此五难也。五者必存,虽心希难老,口诵至言,咀嚼英华,呼吸太阳,不能不回其操,不夭其年也。五者无于胸中,则信顺日济,玄德日全。不祈喜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此养生大理之所效也。”这名利、喜怒、声色、滋味、神虑也是儒道中“德”的范畴,是嵇康谈养生大道的前提。
在《六言诗》和《秋胡行》里,嵇康拈出了尧舜、唐虞、子文、原宪、东方朔、老莱妻等一系列道德典范,并就“功德”、“世道”、“智慧”、“名身”、“道德”、“劳谦”、“忠信”等作了阐述,其“养德”内涵的儒道并举思想更为明显,其中“富贵忧患多”“酒色令人枯”都是“养德”“养生”箴言,而《名行显患滋》、《生生厚招咎》、《名与身孰亲》则说出了二者的密切关系:“独以道德为友,故能延期不朽。”“故顺天和以自然,以道德为师友,玩阴阳之变化,得长生之永久,任自然以托身,并天地而不朽者,孰享之哉?”(《答难养生论》)此处“道德”都是会通儒道的。总之,嵇康的养生思想正是以道家的任自然和以神为主、形神并重思想为根本,融入了儒家的养德 (修身),又继承了道教的性命相通观念,即儒道合璧、“术”“道”一体。
三、嵇康养生思想的玄学特质
养生思想具有很强的玄学特质,是嵇康思想的特色内容。那么这种玄学特质是如何体现的呢?首先就是思想基础的矛盾性。玄来自于儒道调和。无论是阮籍的由儒入道,还是嵇康的家世儒学而长好老庄,其实都体现为一种玄学名士在思想基础上兼有儒道的矛盾理路。《颜氏家训·劝学》谈到“玄学”说:“夫老、庄之书,盖全真养性,不肯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史,终蹈流沙;匿迹漆园,卒辞楚相,此任纵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业,弃之度外。”“嵇叔夜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之流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诫之譬也;”“彼诸人者,并其领袖,玄宗所归。”“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这段文字明确了玄学的精神本源是以老庄道学为主。嵇康的养生之术“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与山巨源绝交书》)正与此一脉相承。至于“直取其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颜氏教子,直言玄学局限。其实玄学本就不是世间哲学,而是精神或说心灵层面的,所以自然不能用玄学对现实人生的指导性来衡量。玄学名士也不免想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他们的心理、思想、行为充满了矛盾和背离。《晋书》记载嵇康“天质自然,恬静寡欲”,这种表象下隐藏的却是嵇康的坏脾气,“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这就不仅是与养生之道相矛盾了。嵇康对钟会、吕巽的态度正暴露了他对世间的关注和心灵的激荡,他对曹魏宗室的不离不弃与“越名教而任自然”其实并不相符。嵇康并没有超越,他还逡巡于现实的泥淖。这种矛盾便是嵇康们的局限,是其与孔、老、庄的差距,这便是名士与圣人之别。在孔、老、庄那里,思想和行动是统一的,这是哲学体系完善的实现。孔、老、庄没有竹林之游,他们能居世间思考而游刃有余;嵇康等玄学家则是假身世外却拘泥物内。“吕梁可以游,汤谷可以浴,方将观大鹏于南溟,又何忧于人间之委曲?”(《卜疑集》)或许嵇康们入于道的初衷就是以道消解儒,以精神的超越排解现实的苦恼,而非抛弃儒,彻底地凌驾世间。既然其本身就未必有以矛盾思想解决痛苦现实的苛求,那我们又何必苛责?其实,这种“越名任心”、以道消解儒的思想正是后世士大夫“外儒内道”精神的滥觞。
第二个玄学特质是话题的超验性及推理的演绎性。“玄”的涵义本身就包蕴着超验性。《老子》第一章讲:“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十五章讲:“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王弼《老子指略》指出:“玄,谓之深者也”。《庄子·在宥》讲:“乱天之经,逆物之情,玄天弗成。”向秀《庄子注》说,“发明奇趣,振起玄风。”《周易·坤》中说:“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杨雄拟《周易》作《太玄》,其中《玄告》讲:“天以不见为玄,地以不形为玄,人以心腹为玄。”由此可归纳“玄”之义有三:一是微妙、奇妙、深邃。二是不可识、不可测。三是指代天,引申为天道、自然。这种玄妙的超验性就是玄学的旨趣、理路和精神。嵇康的《养生论》讲:“世或有谓神仙可以学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寿百二十,古今所同,过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两失其情。请试粗论之:夫神仙虽不目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而论之,其有必矣。”《答难养生论》讲:“又责千岁以来,目未之见,谓无其人。即问谈者,见千岁人,何以别之?欲校之以形,则与人不异;欲验之以年,则朝菌无以知晦朔,蜉蝣无以识灵龟。然而千岁虽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辨矣。彭祖七百,安期千年,则狭见者谓书籍妄记。”养生本就是富有超验意味的话题,而这种以“未可知”为“已知”,以所谓“已知”推断“未知”,甚至是拿未证结论作论证前提的方法更见出玄学清谈演绎推理的特点,所谓“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难以目识”。嵇康的养生理论有很多创新性的科学内涵,如“慎众险于未兆”的慎微如著论等,但推理的演绎性难免不够精密。当然这也是受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限制。
第三个玄学特质是论证的思辨性。思辨性是哲学对无限事物本质的辩证理解,玄学的思辨性常常是超越实证的抽象论证。“然事亦有似非而非非,类是而非是者,不可不察也。”(《释私论》)这是典型的玄学思辨。冯友兰将玄学界定为辨名析理,而玄学的目的常常并不在于名和理的结论,而在于言辞本身,在于玄谈辩难、玄妙难测的过程,即对思辨性的追求。这种思辨特征也多次出现在嵇康关于养生的论述中,“夫为稼于汤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虽终归焦烂,必一溉者后枯,然则一溉之益,固不可诬也。而世常谓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伤身,轻而肆之,是犹不识一溉之益,而望嘉谷于旱苗者也。”“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养生论》)“然则欲与生不并立,名与身不俱存,略可知矣。而世未之悟,以顺欲为得生,虽有厚生之情,而不识生生之理,故动之死地也。”(《答难养生论》)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中,魏晋玄学被当作连接两汉经学和宋明理学之间的津梁。但事实上,从内容体系看,玄学对“道”的创新并不多,也不够完整。除了注解“三玄”外,其特殊贡献在于突破两汉的唯物哲学和经验论方法,对印度佛学思辨体系的接受。相比于孔、老、庄个人哲学的“吾道一以贯之”、体大思精,玄学名士的思想远不够完备,他们善于清谈较为具体的话题,喜欢将哲学生活化、情趣化。所以就某位玄学名士而言,其思想常是养生、音乐、言意、形神等某一内容、某一方面。如果将孔、老、庄称为圣人哲学的话,那玄学哲学更适合说成是嵇康等几代名士们“散金碎银”、熔化提炼的搭配和组合。不过其思辨的智慧还是极具魅力。
[1]戴明杨.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韩格平.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3][梁]萧统.文选[M].[唐]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晋]陈寿.三国志[M].[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
[5][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6.
[8]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4.
[9]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鲁迅.鲁迅讲演全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