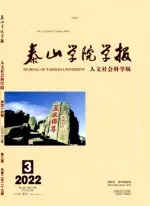孟子辟墨杨纵横论
2010-08-15万光军
万光军
(1.山东政法学院马列部,山东济南 250014;2.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孟子以时代大儒自居,对很多非儒学派都进行了批评,在这些诸多非儒学派中,哪一个、哪一些才是孟子批评最为有力的学派呢?为什么要如此严厉地批评他们,批评他们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批评他们?结果怎么样呢?孟子批评了兵家、法家、农家、纵横家、告子、陈仲子、杨朱和墨子等学派(人)。孟子对农家、兵家、法家还基本上是理论批判,而对陈仲子、夷子、墨子、杨朱的态度就不完全是理论批判,主观的讽刺、挖苦、甚至道德辱骂开始出现了,显示了孟子对非儒学派 (人)的态度并不相同。在非儒学派中,杨墨是孟子反对的主要论敌;在杨朱与墨子中,墨子又是(比杨朱)更让孟子反感的人。
孟子认为农家的理论是“伪”,不能治理好国家。“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孟子.滕文公上》下引只注篇名)并且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孟子指出了儒学的社会分工具有历史合理性。孟子认为兵家和法家的耕战都只追求战争和财富、而没有确立仁 (义)的优先地位,所以是“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从仁义优先的角度,孟子指出“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离娄上》)从今古的角度,“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告子下》)孟子认为纵横家公孙衍、张仪等人虽然可以“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但他们不是真正的大丈夫,而只是些权力、利益的妾妇。“是焉得为大丈夫乎?……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滕文公下》)孟子称告子的理论会祸害仁义。“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告子上》)其实,严格说来,告子的“仁内义外”只害义而不害仁,而告子的自然人性论以为“仁义戕贼人性”才会是“祸害仁义”。孟子虽然批评告子,但还没有辱骂告子,对告子的态度还是相对客气的。孟子因为陈仲子“辟兄离母”,而讽刺陈仲子,“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滕文公下》)孟子挖苦墨家的夷子是“二本”。“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滕文公上》)孟子批评、辱骂墨子和杨朱,一是因为杨墨皆言利 (不言义)。“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尽心上》)二是因为墨杨倡兼爱为我、是无父无君、是害仁害义。“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滕文公下》)
通过比较,就孟子对他们的态度而言,虽然他们与孟子的观点都不同,孟子对他们进行评点、批评在所难免,但在态度上还是有些 (轻重)不同:孟子对农家、兵家、法家的批评态度还比较客观;对告子的态度也还算客气;而对夷子、陈仲子、杨朱和墨子的态度就很不客气,含有讽刺、挖苦、甚至辱骂的成分①。态度是形式上的,不同态度来源于他们对孟子思想的不同方面构成了挑战。孟子思想的核心词汇是仁义,最重要关系是家国关系。农家要求“与民并耕”、反对等级剥削,这基本不涉及孟子理论的核心 (仁义),并且也容易进行批驳,所以农家并不构成大的挑战。兵家、法家的耕战政策的优点与缺点很容易看到,也很容易批驳,所以兵家、法家的影响虽然也很大,但孟子也并未放在心上。对于告子,虽然告子的自然人性论对仁义的性质 (自然性还是社会性)、结构(“仁内义外”还是“仁义内在”)有所冲击,但告子的自然人性并非毫无道理,告子也并非完全不按照社会要求而行 (如告子也敬长),有些行为还让孟子佩服 (如先孟子不动心),告子也重家 (仁内),因此告子的有些思想虽然也冲击到了孟子的仁义,但孟子并未辱骂告子。“率天下而祸仁义,必子之言夫。”态度依然还是相对客气的,或者说孟子对告子的批评态度虽然严厉,但还未到辱骂的地步。孟子挖苦夷子是“二本”,即两个父亲;单独看来似乎并不严重,但在高度重视家族传承的宗法社会里,这一句话的含义当然是很不客气的,其理由就是墨家兼爱、薄葬不合乎孟子的标准。孟子因为陈仲子“辟兄离母”,把“义”放在了“仁”之上,所以是“以小害大”,实质就是没有把家庭放在第一位,违反了孟子家庭优先的标准,所以对陈仲子进行讽刺。孟子对于杨朱批评的两条理由可以合二为一,杨朱“为我”而不“为君”②、“为身”而不“为义”,实际上放弃了人应尽的社会责任,孟子的批评是站在儒学一般立场(而非孟子自己的特定立场)上的批评,比较容易理解;由于杨朱的观点威胁到了孟子的核心“义”,所以孟子称之为“禽兽”。对于墨子,孟子主要列举了两个方面:一是功利治国而不是仁义治国,二是兼爱而不是差等之爱。两者相比较,虽然功利治国也威胁到仁义的优先 (如孟子开篇就讲“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应该与墨家提倡功利有很大关系),但孟子还是主要从兼爱的角度辱骂墨子为“禽兽”。可见,孟子认为墨子“功利”与“兼爱”的两个威胁中,兼爱是更为致命的。综观这些非儒学派,孟子以他们对自己的核心观点威胁的远近、轻重而对之态度有所不同;反过来,从对他们的不同态度上也可以看出,仁义是孟子的核心词汇,重家是孟子的典型立场。
孟子不仅从横向的时代角度、即与当时诸多非儒学派进行比较的角度对自己的立场进行了一定表述;他还从纵向的历史角度对自己的立场进行了表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使禹治之。……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词,邪说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无父无君,是周公之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词,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滕文公下》)孟子认为人类历史从尧舜禹时代发展到自己的时代,共经历了三次大灾难:一是尧时发生水患,而大禹治水;二是尧舜之后出现了如纣王一样的暴君,而周公辅佐周武王平定天下;三是以下犯上的暴行频出,孔子写《春秋》而纠正。前三次虽然有大灾祸,但都有圣人给予解决了、并且解决地很好;孟子认为自己的时代面临着新的、第四次大灾祸,就是杨墨之言;与前三次一样,孟子认为如果自己也解决好了这次大灾祸,自己也会成为新圣人 (以承三圣),孟子对此是很有信心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
如果把横向角度的时代评价和这次纵向角度的历史考察相比较,可以更为明显地看到:如果说在横向的时代考察中,兵家、法家、农家等学派还有一席之地的话,而在纵向的历史考察中他们都不见了、或者说不值一提了,而只剩下了墨杨;其间批评墨杨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墨杨讲利、而是“充塞仁义”、“无父无君”。在此,孟子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甚至唯一任务就是批驳墨杨,目的就是捍卫仁义、维护家国。通过孟子对不同学派的态度,对杨墨的极力批评态度的比较,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地说,仁义是孟子的核心词汇、家和国是孟子努力维护的最主要社会关系;而墨子和杨朱分别对仁与义③、家与国构成了严峻挑战,墨杨也就成了孟子所认为的最主要论敌④。并且如果严格地一一对应,杨朱为我是无君害义、墨氏兼爱是无父害仁,后面的顺序应该是“无君无父是禽兽”、而不是“无父无君是禽兽”;反之如果按照后面的“无父无君是禽兽”,则前面的顺序就应改为“墨氏兼爱是无父,杨氏为我是无君”,而不是“杨氏为我是无君,墨氏兼爱是无父”;孟子是“知言”高手,但在此处没有很好地做到一一对应。按照孟子仁对义的优先、家对国的优先、父子对君臣的优先,此处的顺序严格说来应该是“墨氏兼爱是无父,杨氏为我是无君,无父无君是禽兽”。
孟子认为,墨家的兼爱是害仁、害家、害父,杨朱的无君是害义、害国、害君,所以他们是孟子的最主要论敌⑤,所以孟子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甚至道德辱骂是可以理解的;或者说,“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公孙丑下》)在整体上,无论是害仁还是害义、害家还是害国都是对人的两大伦的损害,墨杨威胁到了孟子努力维护的人之大伦,所以孟子称之为禽兽。进一步而言,孟子虽然重视家和国,但在家和国之中、孟子更重家,所以,虽然杨朱和墨子都是孟子最重视的两个论敌,但在二者之中,墨子又是重中之重、是孟子两大主要论敌中的头号论敌;由此,孟子对墨子的攻击也就更为猛烈了。
孟子批评、辱骂墨子是可以理解的⑥,但在结果上,孟子的批评和辱骂最多能使自己和墨子的立场差异更为明显,而很难真正驳倒墨子。客观说来,在儒墨显学中,孟子有吸收墨子思想的地方,如仁义、如对天与命的区分;孟子也有反对墨子的方面,如仁义与功利、如道义论与功利论、如差等与兼爱。暂不考虑孟子对墨子的吸收,而主要讨论孟子对墨子的批评;孟子批评了墨子的功利和兼爱,在其中,兼爱是孟子最为关注的。
功利的思想在当时有很大的吸引力,“墨家学派在春秋末年已与儒家并称显学,它以‘兼相爱’、‘交相利’为基本主张,将原始的人道原则与现实的功利原则结合起来,从而既满足了人们对仁爱的渴求,又合乎人们求利的需要,在理论上颇具吸引力,其声势似乎已渐渐压倒了儒家。”[1](P4)但功利思想的明显局限会把人功利化、把人视为工具,会无视等级制,这些局限使孟子的道义论在批评功利论时很有说服力。功利论也会涉及到管仲的霸道,但这对于已经坚信“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和“仁者无敌”的孟子而言,批评功利和霸道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态度上,孟子对急切功利的梁惠王也是说“不仁哉,梁惠王”,没有过分批评;对行霸道的管仲也是“尔何曾比予与是”,是严分彼此,也没有道德辱骂。而对于兼爱,孟子是最为反感的。兼爱与差等之爱相对,兼爱要求普遍的、平等的相爱;普遍的爱要求对所有人都要爱,不能没有不爱的人,墨家提出“尚贤”就是对宗法伦理的“只爱亲不爱人”的一种突破,与孟子的“邻人斗而不救”形成对比;反之,孟子的“邻人斗而不救”也应是有所指的,应是指向墨家兼爱的。平等的爱要求对所有人的爱应是平等的、不是差等的,墨家提出“视人之身若其身,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国若其国”,这样就把自己与他人、自己之父与他人之父、自己国家与他人国家放到了绝对平等的地步,这样不能突出自己对于他人、自己之父对于他人之父、自己国家对于他人国家的优先,实质而言就是威胁到了儒学的“推己”、“推恩”,威胁到儒学在体系上理论与现实的局限。
全面说来,“推己”包括平等地推和差等地推。这两者在孔子那里都有:如“伐柯伐柯,其则不远”和“忠恕”基本上就是平等地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就是差等地推。在当时宗法社会,平等地推具有理论合理性、理想性,差等地推具有现实合理性。就现实而言,平等地推是对现实的批判、差等地推是对现实的维护。就理想而言,平等地推虽在现实会遇到困难(包括制度、人性),并且会永远遇到困难,但它的合理性决定了它依然是有生命力的;差等地推虽具有现实 (制度、人性)的合理,但基本上应是被逐步调整的。就儒学而言,它涉及到理想 (理论)与现实,也涉及到道德上的君子小人。在君子小人之间,儒学在理论、理想上设计了人性平等、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在现实上还是讲君子小人的差别,在道德上应该由君子引导小人,由君子引导小人实质就是差等之爱、而不是平等之爱。这样儒学既有理论(理想)上的抽象的平等,又有现实上的具体的差等;或者说,平等地推与差等地推实际上就是理想与现实、平等与差等之间复杂关系的另一种表达。简言之,平等具有理论合理性、但具有理想性,差等具有理论的局限性、但具有现实合理性;墨家讲平等、不讲或少讲君子小人,儒家讲差等(推己、推恩),很重视君子小人。君子小人的差别当然不仅限于道德,也包括地位、经济等,但儒学多把它们道德化,即君子小人的差别主要是道德上的差别。理想上平等地推虽具有合理性、但具有理论的抽象性,这种抽象性使得理想的平等往往不知如何操作、由何操作及最后如何等情况而流于空想,不能得到切实地实施;与之相对,现实的差等(君子小人)在具体操作上则很容易找到由何操作及如何操作,从而避免了理论的空想。但从发展趋势上说,平等地推必然带来平等,差等地推必然不能(完全)否定差等。从理论的角度,理论具有自身价值和工具价值,其工具价值有论证、维护现实的一面,其自身价值有批判、引导现实的一面;在宗法伦理上,孟子对理论论证、维护现实的一面强调的很多,而对理论批判、指导现实的一面重视的相对不够。
孟子不能摆脱自己的特定时代和特定立场,也就难以摆脱自己的局限,甚至以自己的局限为根据、为合理,进而去批判别人。如孟子说夷子是“二本”,而在孟子之前就有姜尚被称为“尚父”、管仲被称为“仲父”、后来的诸葛亮被称为“相父”,这些“二本”不但不是对人的侮辱,反而是儒学所认可的很高荣誉。如陈仲子因义而辟兄离母虽然得不到孟子的认可,但并不妨碍齐国人以之为“义士”。与墨家讲兼爱、不能突出家庭 (父亲)的优先相对,孟子 (舜)为了维护家庭 (父亲)而“窃负而逃、乐而忘天下”就不能仅仅说是一种理论假设了,而可以说是理论的必然,并且很有可能会变为现实的必然;至少孟子自己早就说过君子有三乐,其一就是“王天下不与”,这也表明孟子晚年对政治的热情虽有所减弱,而对家庭的执著却依然未减。在理想人物上,墨子重禹。“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禹求焉。”(《墨子·兼爱下》)墨家重视大禹,孟子也就只能并且必然重视大舜了,这不仅是时间上大舜先于大禹,更是因为二人在家庭上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所致。
在孟子(儒学)理论内部,存在着抽象的平等和现实的差等;在理论外部,存在着墨家的平等和孟子的差等,这两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各有所侧重。在理论内部的抽象平等和现实差等的关系上,孟子的抽象平等的合理性最终被现实的差等所代替,孟子甚至运用理论自身 (仁对义的优先)和逻辑结构 (大小、内外、先后、本末)来为现实差等进行辩护 (而不是对现实差等的局限性进行自身批判);在理论外部的墨家平等与孟子的差等关系上,孟子运用理论辩论和道德辱骂来为现实差等进行辩护 (而不是针对墨家的主张而反思儒学自身),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家庭、父子关系的差等和优先。在家庭、父子地位上,儒学理论上要求抽象平等,墨家要求现实上平等,孟子则要求现实上的差等。孟子在理论上也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现实上优先自己父亲,墨家要求“视人之家如其家”。内部观点的矛盾与外部观点的矛盾纠缠在一起,使得孟子很难真正驳倒墨子。全面说来,如果对家庭、父子的“优先”并不导致对作为“后”的国家、君臣(及他人)的(完全)忽略和否定,则平等与差等之间的差异还不明显,矛盾还不太尖锐;只有家庭、父子对于作为“后”的国家、君臣(及他人)的优先变为了本末关系、变为了只顾本而不顾末,即家与国、父子与君臣只有在不可得兼时,平等与差等之间的差异才会明显、之间的矛盾才会尖锐。当然,平等与差等之间的差异有明显与不明显、矛盾有尖锐与不尖锐的区别,不能只讲一方面、夸大一方面。如因为孟子称墨子为禽兽就认为儒墨之间的就是始终对立、处处对立的,这种态度也有简单化的倾向。历史来看,人类应从自然走向社会,这一过程是逐步克服自然局限性(保留自然性的真诚)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漫长的、也很可能是痛苦的,但又是必须的。人都有自我、自然的状态,这种自然、自我是真实的,无视它而抽象地无条件地拔高则只会得出一个抽象的、空洞的人,甚至就是一个虚伪的人;这种自然、自我虽然真实,但还不是全部、还没有完善,要由自然进入社会、由自我进入人人 (整体);如果仅仅局限于自然、自我的状态而固步自封、不肯前进,甚至以自然、自我为根据而否定、拒绝社会和整体,这时的自然、自我虽然还存在、还真实,但已不再是(社会、整体角度)正确的。从逐步完善的过程来说,人对自我的克制有一个限度,对自然的克服有一个过程;在一定过程中、在一定限度内,在社会、在整体、在道德应然角度人们虽然已经意识到了自然、自我的局限,但还是对自然、自我的局限给予了一定容忍,不是苛刻地求全责备;但另一方面,不求全责备并不就意味着自然、自我的某一行为就是正确的⑦,甚至以其局限为“完善”而抱残守缺;人们的容忍有一定限度;并且在容忍错误之外,人们对积极克制自我、克服自然而努力向社会、整体靠拢(其中可能会受到一些损失)的人给予了道德赞美,如大禹、闵子骞。大禹是克家以为国(社会)、闵子骞是克己以为家 (并且没有损害第三方的权益),所以孔子称“无间”、“不间”;相对而言,(孟子)舜窃负而逃乐忘天下表明他们最终以小害了大、损害了他人的应有权益,以自然否定了社会,是停留于人的局限而没有努力克服而进至社会、整体;由此孟子、舜的言行受到人们的怀疑、进而被调整也就是必然的。
在诸多非儒学派中,孟子指出“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尽心下》)以为在这场大辩论中自己是最后的胜利者,也即差等之爱是最合理的观点,这也是需要分析的。实际上,孟子不是处于“墨子 -杨朱 -孟子”系列的最后,孟子而是处于“杨朱 (告子)-孟子 -墨子”系列的中间[2],在结构上,杨朱 (告子)是孤立的自我、孟子是处于家庭关系中的自我、墨子是处于社会角度的自我,这是一个由小到大的结构,按照孟子不以小害大的逻辑顺序,孟子能很容易地驳倒比自己更小的告子,但也很容易被比自己更大、更彻底社会化的墨子所驳倒。在义理上,“逃墨必归于杨”是很有可能的,但“逃杨”不是归于儒、而是很有可能归于墨,也即孟子批评杨朱(告子)必然倒向墨家(或与墨家一致),孟子批评墨子必然倒向杨朱、告子(或与杨朱、告子一致),孟子处于杨朱 (告子)与墨子之间,处于尴尬的境地。告子、杨朱具有道家的自然主义色彩,告子的重家和杨朱的重身都可以说是自然主义,都可以说是广义上的“仁内义外”;墨子的兼爱既重自己的家又重别人的家、既重自己的身又重别人的身,所以可以说是广义上的“仁义内在”;而孟子是双重立场,孟子重视家庭接近于自然主义,即孟子的家先国后、家内国外也可以说是“仁内义外”;孟子的儒学一般立场要求他重视人的社会性,人的社会性会要求爱己也爱人、爱己家也爱人之家、爱己身也爱人之身、爱己老也爱人之老,即人的社会性会推出广义上的“仁义内在”;这样,孟子既是“仁内义外”,又是“仁义内在”;或者说孟子对抗告子的“仁内义外”时运用的是“仁义内在”,孟子对抗墨子的“仁义内在”时运用的是“仁内义外”,孟子似乎是左右逢源。
家庭既具有自然性又具有社会性;自然性与差等相关、社会性与平等相关。孟子以社会性对抗告子、杨朱的自然主义,即以“仁义内在”对抗“仁内义外”,这是没有问题的、肯定会取得胜利。孟子以重家的自然主义 (差等)对抗墨子的社会性(平等),似乎也可以说取得了“胜利”。但是如果综合孟子的胜利可以看出,孟子对抗杨朱所取得的胜利的“仁义内在”与墨子的“仁义内在”是一致的,孟子对墨子所取得胜利的差等(“仁内义外”)与告子、杨朱的立场(即仁内义外)又那么相像。可以说,孟子的双重立场使得他在单独对付任何杨朱(告子)或墨子一方时都能取得某种“胜利”,但在杨朱 (告子)和墨子双方共同对孟子进行攻击时,孟子只能以墨子反对杨朱 (告子)、只能以杨朱 (告子)反对墨子,这不是左右逢源,而是左右为难,其根源就是论敌的不同立场和孟子的双重立场之间的复杂纠葛关系。孟子为了驳倒不同立场的杨朱(告子)和墨子,(似乎)可以具有双重立场,但这种双重立场在他理论体系内部就不能完整统一起来,这对建立严格的理论体系而言是不允许的;反之,如果孟子建立了单一的理论体系,他要么站在理论的严格立场上,坚持彻底的平等、改造儒学的等级、差等,要么坚持彻底的家庭优先的自然主义立场、缩小甚至取消社会性;但这两方面孟子都不能做。自然性可以保留,但自然性显然不能成为人的本质所在,人的本质只能是社会性,如果以自然性为人的本质就会走向道家,作为儒家学者孟子显然不能以自然性为人的本质;坚持彻底的平等会否定宗法伦理和等级社会,孟子显然还未做好这样的理论准备和理论勇气。
对于禽兽,在孔子、《论语》那里没有出现禽兽,而是出现了两次鸟兽;禽兽也不是孟子首先运用的,如在孟子以前就出现过;如《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中有“然二子者,譬如禽兽,臣食其肉,寝处其皮矣。”又如《墨子》中有“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墨子·尚同上》)“禽兽也,则曰牡牝雌雄也。”(《墨子·辞过》)孟子大量运用禽兽似乎主要不是受孔子思想所影响、而应主要是受墨子思想所影响;在《孟子》中,禽兽与鸟兽、野兽都有所运用;但无论就数量上、还是重要性上,孟子对禽兽的运用及产生的影响显然都是最大的。鸟兽就是动物,孔子讲人与鸟兽的区别就是在讲人与动物、自然与社会的区别;而禽兽既可实指又可喻指,在实指时是指动物,在喻指时是指人⑧,或者说名义上是指动物 (禽兽),实际上是指人,这样,孟子的“禽兽”表面上是实指,实际上却是喻指,或者说实指与喻指的统一,借用动物没有道德来说明庶民丧失了道德从而如同禽兽,而孟子的道德就是仁义、尤其是重视家庭优先。孟子从人与禽兽的角度来解释仁义道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既然人异于动物,就不能再混同动物、等同动物;既然人高于动物,就不能再低于动物,否则把禽兽与人相连就是对人的道德侮辱,让人低于动物就是人性的沦丧;后世讲“禽兽不如”、“衣冠禽兽”等无不是在说明人不可丧失道德、或丧失道德的可耻下场。在兼爱与差等上,孟子既然不能在理论上驳倒墨子,也就加上了道德辱骂⑨,只是这种辱骂只在孟子角度上成立,对于墨子则未必成立。
质言之,儒学 (孟子)具有双重立场:即自然与社会、平等与差等;从积极意义上,儒学的这种复合性为与各种非儒学派相互交流、相互合作提供了很多可能;从消极意义上,儒学的这种双重立场使得儒学似乎完美、左右逢源,而实际上各因素之间矛盾不断出现;不能把儒学建立在一个绝对稳固的基础之上,也就摆脱不了诸多非儒学派的不同角度的相对攻击;既然自身体系就存有矛盾,其他学派的不同角度的批评也就很有可能是成立的。历史来看,儒学的这种双重立场在孔子那里就存在,只是还没有分化;到了孟子这里,儒学自身的理论矛盾进一步分化了,加之儒学与非儒学派的冲突进一步尖锐了,原先在孔子那里存而不论、隐而不显的矛盾显露了出来、尖锐起来了,孟子坚持双重立场表明他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想要处理好这些问题,但他的左右为难表明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些问题;就是从历史上看,儒学也始终没有真正解决好这一双重立场的问题。这样,儒学自身理论内部的矛盾,非儒学派的不同方向的冲击始终存在下去了;每当儒学自身反思、或外部思想进行冲击时,儒学的双重立场总会被一再提及。
[注 释]
①有人从忠孝角度进行了分析,如“儒、墨、杨三家之间的分歧与争议,主要体现在对‘忠’、‘孝’问题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上”。(参见徐华:“从‘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看儒、墨、杨之异”,载《文史哲》,2001年 4期)也有学者认为孟子称杨墨为禽兽,“非以禽兽喻杨、墨,它只是一个学理的阐释,一种理论的批判,而不是一时激愤的情感宣泄”,“对杨、墨之学给予了必要的理论批判,而非以禽兽喻杨、墨,不是什么骂街、使用语言暴力。”(参见苗润田:“孟子非以禽兽喻杨墨”,载《文史哲》,2007年第 3期)
②“为我实即不为君,不为天下。”参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2页。
③朱熹对仁与义的解释有的是正确的,如“杨朱但知爱身,而不复知有致身之义,故无君;墨子爱无差等,而视其至亲无异众人,故无父。无君无父,则人道灭绝,是亦禽兽而已”。(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 317页)有的则不正确,如“为我害仁,兼爱害义”。(同上书,第 412页)其实,为我而不为君、故而是害“义”,兼爱不能突出爱父、故而是害“仁”,即杨朱是害义而不是害仁、墨子是害仁而不是害义,二者在孟子这里的界限是非常清晰的,不能混淆、不能替换,也说明朱熹对仁与义的敏感程度、自觉程度不如孟子。
④冯友兰先生指出“孟轲所说的‘四端’和‘四德’归结为‘五伦’。孟轲认为,五伦之中,以‘君’、‘父’两伦为最重要,而当时的道家和墨家,正是对这两‘伦’有所破坏。”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 375页。
⑤“孟子攻击最力的论敌是墨翟和杨朱。”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 143页。
⑥“客观地说,人类从没有君臣之别到‘君臣有义’,从没有父子之别到‘父子之亲’,也确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是人类社会走出混沌状态的重要标志。从这个角度看,孟子所说‘无父无君是禽兽’自有它的合理性和理论根据。”参见苗润田:“孟子非以禽兽喻杨墨”,载《文史哲》,2007年 3期。
⑦宗法伦理的存在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即使完全讲兼爱的墨家似乎也不能完全视而不见。它表现为对宗法伦理行为的认可、容忍程度的不同,如人们虽然怀疑舜封其弟象的行为,但反应不是很激烈,表现了对宗法伦理的一定容忍;而对舜“窃负而逃乐忘天下”行为的反应肯定是很激烈的。“如果损失不太严重,或者伤害只涉及少数人,在当时也就只好劝说这些受害者从‘大局’出发‘认了’、‘忍了’。但这并不能改变这种行为的本质”,“这只不过是人类社会一种习惯性的尚未克服的弱点而已。”参见邓晓芒:“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评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证明集》”,载《学海》,2007年第 1期。
⑧禽兽指动物与指人,在《孟子》中都有,如“无父无君是禽兽”是比喻指人;如“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就是指动物。冯友兰先生看到了禽兽含义的复杂性。他指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就是有跟其他动物不同之点”,他同时也提醒我们,此处的禽兽“并不仅只有生物学的意义,而且有逻辑和道德的意义。”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第 366页。
⑨“墨家讲兼爱,孟子斥之为无父无母,是禽兽,这种辩论,已近乎人身攻击,而缺乏一种宽容的雅量。”参见杨国荣:《孟子评传》,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
[1]杨国荣.孟子评传[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4.
[2]郝长墀.墨子是功利主义者吗?——论墨家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J].中国哲学史,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