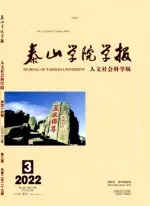法律方法研究中本体论倾向的哲学评析
2010-08-15郑金虎
郑金虎
(泰山医学院社科部,山东 泰安 271016)
近年来,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中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本体论倾向,对于这一倾向的认识在法律方法研究中是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不仅关系到如何对法律方法进行定位的问题,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法律方法研究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与突破点的选择,本文试图从哲学视角对法律方法可能的贡献、法律方法研究的定位等问题进行哲学层面上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法律方法研究中的本体论倾向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我国法律方法研究中的本体论倾向
近年来,我国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日渐呈现出繁荣的态势,“中国法学界关于法律方法论的研究似乎进入了高潮”[1],不仅学术界表现出了空前的研究热情,相关的外文著作大量译入,国内研究成果大量涌现,而且法律方法的具体研究也在不断深化和拓展,呈现出研究层次的深入化和研究方向的多样化趋向。也正是在这一态势下,我国目前的法律方法研究中也已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本体论倾向,主要表现为:在一些具体法律方法的研究上,有些学者提出了“向本体论回归”的主张并作出了相关的努力[2]。
对于这一倾向的不同认识,是一个关系到如何对法律方法进行定位的根本性问题,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法律方法研究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与突破点的选择。对于我国目前法律方法研究中出现的本体论倾向,陈金钊教授认为:“虽然法律方法论属于实用性学科,但它毕竟不是实践本身,仍然是理论形态。所以,在研究中存在一些本体论和宏观理论也属于正常。”[3]陈教授的观点蕴含着他的学术宽容和对学术探讨的褒奖,但就作为一个具体的学术问题而言,本文对此有不同理解。作为陈老师的学生,本人无论是学养还是见识都无法与陈老师同日而语,在此提出这一问题也绝不是以“当仁不让于师”自居,只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并将自己的一些理解一并求教于陈老师。
二、法律方法相关问题的哲学探讨
探讨法律方法研究中的本体论倾向问题,要涉及到法律方法可能的贡献、法律方法研究的定位等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仅囿于法学层面上是难以作出透切的分析的,我们还需要将其提升到哲学层面上进行根源性的分析,以寻求对这些问题更根本意义上的解释。
(一)法律方法相关问题的哲学依据
法学领域的本体论问题是哲学本体论在法学学科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以哲学本体论为依据的,因此,探讨法律方法的本体论倾向问题也须从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入手,而这其中最有直接关系的则是法律的一般与个别及其关系问题,二者之间的互动地带正是法律方法存在的意义空间。
探讨法律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首先要涉及到哲学层面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从哲学意义上来说,一般和个别、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辩证的统一,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一般和普遍性只能存在于个别和特殊性之中,并且通过个别和特殊性表现出来;而个别和特殊性又与一般和普遍性相联系而获得了自身的规定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正象德国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所讲的那样:“特殊的东西不仅包含普遍的东西,[4]而且也通过它的规定性展示了普遍的东西”,而“普遍性并非单纯是一个与独立自存的特殊事物相对立的共同的东西,而毋宁是一个不断地在特殊化自己而且在它的对方里仍明晰不混地保持它自身的东西。”[5]对于这种统一性,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虽然一些独一无二的特性使得他或她成为这个特殊的人,但每一个具体不同的人所拥有的某种 (共同的)东西使得他或她成为一个人。”[6]另一方面,一般与个别、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又具有对立性的一面,它们之间的统一是一种辩证的统一,即既对立又统一,而不是绝对的等同。一般和普遍性是对若干具体事物共同本质的反映,因而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个别和特殊性除了一般和普遍性所反映的共同本质外还具有自己多样的独特个性,具有更多能为人所直接感知的具体形象性。在人们的认识过程中,正是这种辩证的差别,形成了个别和一般、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互动。
作为一种具体的事物现象,法律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表现为司法过程中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法律规范是一般性规定,体现着法律的一般;而法律事实是个性化的事实,体现着法律的个别。在现实的司法过程中,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即二者之间既具有统一性,又有相互对立的方面和因素,是一种辩证统一的互动。
它们之间的统一性表现为,法律规范作为一般性的规定,概括和反映了同类法律事实的共性,而具体的法律事实也内在地具有法律规范所反映的这些共性,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根据法律规范对案件作出判决。司法实践在形式上被认为是用一般性的法律规范解决个性的纠纷的过程,亦即法官将一般的法律规范个别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基本的推理模式是演绎,即从大前提 (法律规范)向小前提(案件事实)推进的。在这一推理过程中,法官依据“法律规范→案件事实→判决”的三段论式推理模式将法律规范运用于具体的案件事实并作出司法判决,法律规范实现了对法律事实的统摄与规制,体现了法律的一般和个别的统一性的方面。
另一方面,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之间又具有相互对立的方面和因素,法律事实必然会具有法律规范所无法描述或包容不下的个性特征,它们之间不会是“全等”的关系而必然存在“断裂”和“紧张”,这种“断裂”和“紧张”最终会在法律规范适用于案件事实的过程中动态地显现出来,表现为法律事实对法律规范的“挑战”或“叛逆”。“无论法律被制定得多么周详,它毕竟只是一套由概念和规则交织复合而成的逻辑系统(准逻辑系统),繁复庞杂的社会事实不可能与之天然吻合。在立法过程中被立法者浑然不觉的法律自身的漏洞、歧义、模棱两可、含糊不清,无论其潜伏期有多长,迟早会在司法过程——这是规则与事实的摩擦地带——暴露出来,法官于是必须面对那些由此而生的疑难案件。”[7]
另需明确的是,尽管在司法实践中法律的一般与个别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互动,但这种互动并不能完全消除它们之间的“断裂”和“紧张”,因为,它们之间的这种“断裂”和“紧张”根源于法律的一般与个别的对立统一关系,只要我们不能使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完全等同起来,它们之间的对立也就无法彻底消除。
(二)法律方法可能的贡献之哲学探析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分析法律方法就不难发现,法律方法发挥作用的空间只能是司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律方法之实质是融合案情、正式法律与活法并服务于一个可接受之答案这一根本目的的方法。”[8]具体而言,法律方法在这一过程中最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即法律方法可能的贡献是什么?对此,学术界已有类似的探讨,对于“法律方法论究竟要做些什么”问题,陈金钊教授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并总结为三个方面:即“(一)探寻法律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追求判断的正当性或者可接受性;(二)为达致理解,寻找法律的正确使用方法;(三)发现法律或立法者的意图,探寻客观意义避免误解。”[9]陈教授的这一判断,核心的内容也可表述为两点,一是法律方法论要“发现法律或立法者的意图,探寻客观意义避免误解”,这其实是对法律规范的认识问题;二是“寻找法律的正确使用方法”,“探寻法律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追求判断的正当性或者可接受性”,这其实是如何处理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之间的关系问题。这里,陈教授已从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关系的角度触及到了法律方法可能的贡献问题。
本文认为,对于“法律方法可能的贡献是什么”问题的回答,应当基于对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的辩证关系的认识。二者之间具有统一性,法律规范作为一般性的规定,概括和反映了同类法律事实的共性,而具体的法律事实内在地具有法律规范所反映的这些共性,由法律规则到个案判决的转化才有了可能,法律方法才有了用武之地;而另一方面,二者之间又具有相互对立的方面和因素,法律规范的抽象性、普适性、一般性使它永远无法与具体的法律事实完全等同起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法律的一般与个别的对立是法律方法永远无法逾越的“卡夫丁峡谷”。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的结论是:法律方法可能的贡献不是引导我们达致对法律规范的“真”的理解,或法律事实的客观真相的还原和再现,而只能为我们提供一种理性工具,使我们能够寻求一种关于具体案件纠纷的具有可接受性的、妥当的解决方案。法律方法可能贡献方面之局限,不是由于研究成果的水平,而是根源于哲学意义上法律的一般与个别的天然矛盾,在司法实践层面上也还是由于司法过程的认知取向。
(三)法律方法研究的定位问题
法律方法研究的定位,涉及到两个问题,即法律方法的认知取向和法律方法的工具性问题。
1.法律方法的认知取向
法律方法的认知取向须服从于司法过程的认知取向。司法过程是一个解决个性纠纷的过程,其最终目标是要使某一具体案件纠纷得到妥善解决,亦即寻求一个解决纠纷的最佳方案,虽然司法过程中也存在对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的探究,但却有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认知取向。从对法律规范的认知来看,对法律规范特别是法律原意的探究是司法过程的基本任务之一,这是将法律规范正确地运用于法律事实的前提条件,“多样的解释方法无非是向法律的原意更加靠近”,[10]但司法过程对法律规范的探究有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认知取向。“法律解释学的最终目的,既不是发现对法律文本的正确解释,也不是探求法律意旨的准确把握,而是为某种判决方案提出有根据的且有说服力的法律理由。”[11]另一方面,司法过程所要认定“事实”是一种主观事实(即一种有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对这种事实认识的目的是要确定其要援引的法律规范,而不是为达致对客观意义上的事实真相的还原与再现,在对法律事实的认定过程中,大量认知者的主观因素被掺入进来。“法律事实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它们是根据证据法规则、法庭规则、判例汇编传统、辩护技巧、法官雄辩能力、法律教育成规等诸如此类的事物而构设出来的,总之是社会的产物。”[12]综上,司法过程是一个以最佳判决方案为追求目标的认知过程,并不以对法律规范的“求真”理解和对法律事实客观真相的还原或再现为最高目标。这一过程,“需借助社会科学与经验知识对各种判决的社会效果进行预测并进行法益衡量,最终确定最佳的判决结果,以期实现司法对实质正义的要求。然后通过法律方法、法律论证对判决结果进行合理性、合法性论证,以期实现司法对形式正义的要求。从而,达到司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有效统一。”[13〗法律方法是服务于司法过程的,其认知取向也应服从于司法过程的认知取向,所以,法律方法的认知取向也应以最佳判决方案为追求目标,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对法律规范的“求真”理解和对法律事实客观真相的还原或再现。
2.法律方法的工具性问题
法律方法与哲学本体论有着根本不同的终极目标。司法过程是法律的一般向法律的个别转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法官借助于各种法律方法力图消除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之间的对立与紧张而使二者统一起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律方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从其本性来说,其作用都是工具意义上的,“法律方法是法律人处理纠纷的一种工具,它在种种成文法与事实之间架构起一座桥梁,从而疏通了由法律规则到个案判决的转换过程,使种种纠纷在法律范围内得到解决,从而对法治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14]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法律解释学和法律方法论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发展出一套用以处理疑难案件的司法操作规程。”[15]与此根本不同的是,“本体论是以追求终极实在为依归,以奠定知识基础为任务,以达到终极解释为目标的,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方式。”[16]
综上,哲学本体论是以终极意义上的“真”为追求目标的,其探求方向是形而上的,是与法律方法“形而下”的追求方向是相反的。因此,我们应从工具意义上来定位法律方法及其研究方向。
三、结论
以上对法律方法相关问题的认识,已内在地包含着对法律方法研究中本体论倾向的不赞同。法律方法研究中的本体论倾向是受哲学解释学影响的结果,“20世纪兴起的哲学解释学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图式,有使解释上升为法概念本体之趋势。”[17]
前文对法律方法相关问题的分析表明,法律方法发挥作用的空间是司法过程,它可能的贡献是为我们提供一种理性工具,使我们能够寻求一种关于具体案件纠纷的具有可接受性的、妥当的解决方案,因此,在研究定位方面,我们应从工具意义上来定位法律方法及其研究方向。所以,法律方法研究中的本体论倾向是我们目前法律方法研究中应当保持警惕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貌似抬升了法律方法的地位,实则颠覆了其理性工具的本质,打乱了法律方法的应有定位,最终将法律方法的研究引向歧路。
[1][9]陈金钊.法律方法的概念及其意义[J].求是学刊,2008,(5).
[2]焦宝乾.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理论[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王彬.法律解释的本体与方法[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1).
[3]陈金钊.法律方法论研究的高雅与媚俗[J].政法论坛,2009,(3).
[4][5]李武林.欧洲哲学范畴简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
[6][美 ]斯通普夫.西方哲学史[M].丁三东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
[7]桑本谦.理论法学的迷雾——以轰动案例为素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8]周赞.我国法律方法研究的一种方法论反思——基于法社会学的视角[A].陈金钊,谢晖.法律方法(第 3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
[10]谢晖.解释法律与法律解释 [J].法学研究, 2000,(5).
[11][15][17]陈金钊.关于法律方法与法治的对话[J].法学,2003,(5).
[12]苏力.送法下乡[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3]李传先.法律原则的适用方式与方法 [J].前沿,2009,(1).
[14]丁志勇.浅析法律方法的价值与局限[J].工会论坛,2008,(5).
[16]宋红娜.试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体论的关系[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