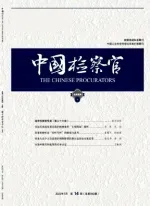权利冲突视野下的检察宣传
2010-08-15张雪松
文◎张雪松
权利冲突视野下的检察宣传
文◎张雪松*
检察宣传工作中经常会面临一些权利冲突。这些冲突更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对其性质和界限认识模糊所造成的。本文选取检察宣传中常见的三对权利冲突现象,尝试做了一些分析,以期能够对检察宣传工作有所裨益。
采访权与侦查权
现代社会中,基于刑事犯罪案件的特殊外部性以及民众的知情权等原因,刑事案件过程中的媒体介入现象越来越普遍。刑事犯罪侦查阶段的适度公开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是,在采访权与侦查权的碰撞中既有火花也有尴尬。
(一)采访权的性质
采访权是一项直接与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权、监督权和由宪法推导出来的知情权密切相关的权利,是这三项宪法权利实现的基础。没有采访权,这三项宪法权利的实现就要大打折扣。因此,在许多国家的法律制度中,采访权都受到特别保护。比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美国最高法院在一系列判例中直接确认了采访权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德国《基本法》则明文规定人人皆有采访信息的权利。德国一些州的新闻法规定新闻记者有向政府部门取得新闻材料的权利。我国宪法中也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这项权利中就包含了采访权。
(二)采访权介入侦查的必要性
采访权作为一种由宪法权利派生出来的权利天然地可以介入到一切涉及到公共利益和人权保障的领域。刑事犯罪侦查活动作为国家公权力行使的重要领域也自然无法回避社会大众和新闻媒体的视野与监督。采访权介入到侦查权主要基于以下三点:一是犯罪行为有着特殊的外部性,即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和公众人身财产安全的威胁。二是采访权的介入是对于侦查权行使的最好监督,可有效地防止司法专横和司法腐败,遏制刑讯逼供。三是采访权的介入有助于树立检察机关的公共形象,有助于民众了解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相关情况。
(三)采访权与侦查权的冲突与调和
从上文可知,采访权与侦查权并不是天然对立面,反而应当是相辅相成。但是,为什么在更早些的时间里,侦查阶段的检察官们一遇记者采访就如临大敌呢?究其根本,就是侦查秘密原则与新闻公开之间的冲突。要想调和这一矛盾,首先就应当了解侦查秘密原则的内涵。侦查秘密原则有两层含义:一是对犯罪嫌疑人保密,即侦查机关不得以违反侦查目的的方式把侦查的情况向犯罪嫌疑人泄露;二是对社会成员保密(主要指新闻媒体),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侦查机关及有关知情人不得对外透露侦查情况及侦查中了解到的情况。
近年来,随着现代民主政治对于政务公开、知情权保障等理念的追求,有部分学者也开始主张侦查公开,同时实务界也开始了侦查公开的实践。可以说,侦查秘密原则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秘密与公开相结合的原则。侦查的适度公开已经成为司法公开的重要内容。
我们认为至少以下四种情况采访权可以介入侦查权:一是社会影响极大,民众反映十分强烈的案件应当在侦查阶段允许采访权介入;二是为预防同类案件的发生,有助于增强职务犯罪预防效果的侦查活动应当允许采访权介入;三是为推进侦查活动,有助于发现侦破犯罪案件线索、抓捕犯罪嫌疑人等情况下应当允许采访权介入;四是舆论对某一侦查活动存在误读或者社会民众对于某一个案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应当允许采访权介入。
报道权与人格权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对于案件的评价必须是合乎法律规范的法律陈述。这在很大程度上区分于媒体报道的道德化或者情绪化。而媒体对于案情的渲染和评价可能会侵犯到犯罪嫌疑人的人格权。
(一)人格权的界定
人格权是指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为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尊严所必须具备的人身权利。人格权包括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具体权利。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的实质精神,犯罪嫌疑人的人格权不受非法侵犯。但在实践中,那些误报、过度报道或者真名报道的犯罪新闻报道常常会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格权。
(二)新闻报道可能侵犯的人格权类型
新闻报道一般会涉及到犯罪嫌疑人的肖像权、姓名权与名称权、名誉权和隐私权。仅以姓名权为例,当犯罪事件发生后媒体多在报道中披露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年龄和住所,此即所谓真名报道。但这显然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不仅导致犯罪嫌疑人过早地被贴上犯罪分子的“标签”,自审判前就开始遭受“精神上的惩罚”,而且伤害了那些被无罪宣判人员的“社会复归权”。
(三)报道权与人格权的博弈与平衡
报道权最大的理论支撑在于犯罪行为的特殊外部性导致了民众具有知晓犯罪行为基本情况的权利,这关系到民众对于犯罪行为的知情权和民众对于司法活动的监督权。因此涉嫌犯罪人员的人格权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其涉嫌的行为已经危害到社会的整体利益,民众有知晓和预防的权利。媒体对刑事案件进行的真名报道是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制裁”机能。综上说述,我们认为媒体报道权是基于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所产生的合法权利。媒体报道权对于犯罪嫌疑人人格权的介入是其社会预防、社会教化功能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当然,报道权不能不加限制地介入犯罪嫌疑人的人格权,其界限应当界定在如实、准确、合法地报道犯罪案件本身,尤其是对于处于刑事检察阶段的案件报道更加应当注重犯罪嫌疑人作为特定诉讼阶段当事人的人格权保障。
舆论监督权与独立司法权
当前,新闻媒体对于司法个案的广泛关注和热衷报道已经成为舆论监督的一个鲜明特征。尤其是网络媒体的横空出世,更加增添了舆论监督的互动性、广泛性和持续性。从“躲猫猫”、“俯卧撑”、“70码”、“邓玉娇”等网络热门点击词就可以看出,舆论监督已经高度介入到个案的司法实践当中。这一现象已经越来越多地引发了学界和实务界的关注。让人担心的,媒体的过度介入可能影响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独立司法权。
本文中所谓独立司法权,即是指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都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的权力。而舆论监督权来源于宪法关于公民的言论自由、监督权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公民的知情权,与独立司法权一样是不可侵犯的宪法性权利。两者并不存在理论上或者逻辑上的矛盾,因为媒体行使舆论监督权并不一定能够影响到司法机关的独立司法权。但在现实操作中却存在因为媒体的过度介入而影响司法实践的现象。
媒体的舆论监督之所以会影响司法独立,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一是媒体角色与司法终局性。司法权本质上是最终裁量权,司法官除了法律之外没有别的上司,排除一切干扰,独立自主地依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事实的认识、证据的判断作出裁决,才能保证结果的公正。大众传媒在介入司法过程中角色是舆论监督者,即根据所掌握的资讯对事件本身做全面、客观、理性的报道和公开,而不是以自己的好恶判断为出发点,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审查审视姿态,即所谓充当“法官的法官”,这样的角色定位最终损害司法裁判终局性的性质,也将干扰相关部门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二是媒体与司法的不同表达方式。司法活动追求的是法律正义,它要求法院和法官尽量抛弃非理性、非法律的道德伦理标准去判断是非。传媒追求社会正义的目标同司法是一致的,但它同司法不同的是它更多关注的是观念上的公正,是一种道德性的情感与评价。新闻媒体报道的道德立场往往使传媒囿于情感性判断,而较少顾及司法行为技术化、理性化、程序化的运作方式,并且常常无法恰当地过滤公众所宣泄的与法治要求并不完全一致的社会情绪。由此看来,加快媒体与司法机关的相关协商沟通是十分必要和亟需的。
行文至此,本文所述内容即已结束,但是本文所罗列之问题仍继续存在。如何在检察宣传工作中协调上述权利。冲突仍然需要我们不断的思考和摸索。
*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检察院政治处[100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