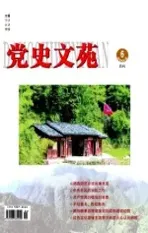罗坊会议若干史实新探
2010-08-15汤静涛
汤静涛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江西南昌 330006)
罗坊会议若干史实新探
汤静涛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江西南昌 330006)
罗坊会议是红一方面军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标志着红一方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由战略进攻向战略退却的传大转折。本文根据原始文献和权威史料,拟对罗坊会议战略决策作一简要回顾,对罗坊会议争论问题作一概括疏理并对罗坊会议争议人物作些分析评述。
罗坊会议 战略决策 重要人物 评价
一、科学地把握罗坊会议
从红一方面军撤围长沙到罗坊联席会议,红一方面军经过了袁州会议、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罗坊联席会议以及其后的前委会议。在红一方面军内部,逐步摆脱立三错误的影响,逐步走向统一,把红军的行动逐步转向正确方面,完成红一方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战略进攻向战略退却态势的转折,绝非一次罗坊会议就能一蹴而就。
袁州会议实现了最初的转变。尽管撤围了中心城市长沙,红一军团于1930年9月13日在株洲发布《攻取吉安的命令》,这是在反对立三错误上迈出的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但从整个战略口号上来看,还是进攻大城市,同党中央提出的进攻口号仍然是一致的。9月28日,当红一方面军总部机关、部队到达袁州(宜春)地区时,红一方面军前委立即在这里召开会议,就红军究竟是先打吉安还是先打南昌的问题展开讨论。对于这个问题,自撤围长沙以来,虽然在株洲、萍乡以一军团的名义下发了进攻吉安的命令,但在红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并没有统一认识。袁州会议对此进行了激烈争论,有些干部还是反对先打吉安。他们的理由是:先打吉安后打南昌,就是不执行中央的指示,就是断送中国革命高潮。通过争论,会议最后还是确定按原来的决定先打吉安,并以一军团的名义于9月29日下午发出“照原计划拟于明(30)日由此地(宜春城)出动,经分宜向吉安前进”的命令。袁州会议,坚持了攻打吉安的计划,这是实际纠正立三错误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进一步说服教育干部摆脱“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步骤。
峡江会议从思想更前进一步。10月4日,红军攻占了吉安,红一军团及红一方面军总部各机关在吉安工作了10天。虽然党中央已经在9月24日于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红军停止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的决定,但是,由于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封锁和交通不便,三中全会精神并没有传达到红军中来。从10月13日的命令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红军的军事行动还是要进攻中心城市。10月17日,红一方面军前委抵达峡江召开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敏锐地指出了国内形势的变化,正确地判断蒋介石要集中兵力对付红军。会议对时局问题作出了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进攻革命的估计,指出红军的任务必须为打败敌人的进攻作好准备。毛泽东强调:“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反动统治阶级争取改良主义的领导权未解决之前,来一个一省首先胜利,继续此胜利的发生与扩大,来冲破消灭反革命联合的进攻。”毛泽东在峡江会议上的这些分析,从根本上否定了李立三认为军阀混战是越打越大,最后自己灭亡的错误估计。因此,峡江会议对于纠正立三错误对形势冒险主义的估计,克服其在红一方面军的影响,从思想上转到正确路线上来又向前进了一步。
太平圩会议出现反复和波折。10月20日,红一方面军总部机关及一军团继续向袁水流域推进,22日到达峡江太平圩。为了继续讨论红军的军事行动问题,前委于10月23日又召开了会议,这就是太平圩会议。根据敌情通报,国民党军阀战争暂时缓和,正调兵遣将准备大肆进攻红军。敌谭道源师全部开到了南昌,许克祥师已到了九江,金汉鼎、毛炳文两个师都开来江西,公秉藩师扎在抚州,袁州有湘敌罗霖的部队。根据敌情严重的变化,太平圩会议立即改变了峡江会议进攻南昌、九江先占领高安的行动计划,决定用7天时间(即从10月24日到30日),将主力部队靠新余、清江的袁水两岸配置,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准备在这一带摆开架势,创造战胜敌人的条件。太平圩会议对敌军将要进攻我军的形势,相对来说看得比较清楚了。但是,太平圩会议面对敌人的进攻,对红军是继续前进还是后退、到底在什么地方反“围剿”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甚至发生激烈争论,有些高级干部仍极力主张前进打进攻之敌,要继续采取攻打南昌、九江的军事行动。
罗坊联席会议及其后红军前委会议完成伟大战略转折。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部移师罗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前委委员和省行委领导人。在讨论中,大家通过对形势的分析和对两次攻打长沙的教训以及占领吉安的成功经验的总结,认识到在敌人对南昌、九江大量增兵,加强固守,一步步向我红军、江西苏区进攻的情况下,红军必须改变原来的进攻计划。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取得一致共识。因此,10月26日,会议正式形成了会议决议案(即《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决议案明确指出:“目前在敌人大举增兵与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势之下,单凭红军轻袭南昌、九江,而且红军相当给养都不具备,运输条件十分缺乏,这无疑的要成为游击式的进攻,结果攻不下又转而他往,反使一省胜利延期实现。所以这一轻装袭取的游击观点与争取一省首先胜利有计划的有布置的战略绝不相容,应加以严重的纠正。”[1]P194
10月30日,红军前敌委员会在罗坊决定了诱敌深入的方针。[2]P24611月1日,朱德、毛泽东下达《红一方面军移师赣江东岸分散工作筹款的命令》,表示“方面军以原任务拟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这样,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式移师赣江东岸,拉开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序幕。
从历史发展看,红一方面军前委自撤围长沙至罗坊的这几次会议是紧密相联的,目的都是为了克服立三“左”倾军事冒险主义错误。红军撤围长沙至袁州会议是反立三错误的良好开端,峡江会议开始了转变,太平圩会议停止了红军进攻但认识并不一致,罗坊联席会议及其后前委会议是这几次会议的继续。罗坊联席会议及其后前委会议所作出的重大决策,使红一方面军完全转到正确路线上来。罗坊联席会议及前委会议并非孤立的、突兀的,而是发展的、前进的必然。罗坊联席会议决定了战略目标、战略方向,红军前委会议决定了战略方针、战略方法。至此,红一方面军真正开始了由战略进攻到战略退却,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伟大转折。
二、理性地分析罗坊争论
罗坊会议,名曰中共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参加者,自然就是这两个委员会的成员。遍查史料,我们未能发现罗坊会议参加者的直接文献依据。众多文献中,亦无诸如罗坊会议纪录或罗坊会议纪要等核心材料。《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自述》以至权威部门所著《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亦未披露完整参会人员名单。《朱德选集》《朱德年谱》《朱德自述》也不曾披露参会名单。最新出版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称:“毛泽东、朱德、周以栗、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李文林(江西省行委书记)、曾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出席了会议。”这与同样权威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编委会编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中指出的“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何长工等参加了会议”似乎不太一致。与亲历者何长回忆录亦有差别。何数部回忆录均称亲自参加了罗坊会议。在1987年解放军出版社版的《何长工回忆录》还说:“记得峡江会议的参加者均出席会议,彭德怀同志没有参加。”我们所见最早一位亲历者1962年1月的回忆录称:“1930年10月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原是赣西南特委,立三路线时改为中共江西省行委的)在峡江县罗坊举行过重要会议。到会的人,除由毛主席主持会议外,有彭德怀、袁国平二同志,军队还有其他同志(忘记了姓名)参加,江西省行委有李文林、曾山、陈正人三人,还有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同志也参加了会议。”[1]P249该亲历者在“文革”中的回忆录,又有新的说法:“罗坊会议是毛主席主持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朱德,一军团有林彪、罗荣桓、黄公略、罗炳辉,三军团有滕代远、彭德怀、袁国平、何长工,地方上是李文林、陈正人和我,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总共是10多个人。”[1]P256由此可见,罗坊会议出席者似乎成为需要考证的问题。
红一、三军团永和市会师后,成立红一方面军和中共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中共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但前委成员有何人氏,《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不曾公布;《朱德传》仅称:“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彭德怀等为委员。”综合分析,罗坊会议的参加者,一种可能应是中共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的委员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委员,或是这两个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第二种可能,应是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团领导人和所属第四、第三、第十二、第五、第八军的主要军政领导,江西省行动委员会领导人及中共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其名单如下:主持人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兼红一军团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参加者: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红一方面军兼红一军团总司令朱德,红一方面军兼红一军团参谋长朱云卿,红一方面军兼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杨岳彬,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红三军团总政治委员滕代远,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八军政治委员袁国平,红三军团参谋长兼红五军军长邓萍,红四军军长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政治委员蔡会文,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谭震林,红五军政治委员张纯清,红八军军长何长工。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常委、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常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等。
罗坊会议文献,目前我们只看到一份联席会议决议,即《目前政治形势与红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同样具有文献价值的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散见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的一些文章中,这些文章,只是零星地、偶尔地提及罗坊会议,并无专门论述。朱德的论述,新版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诗词集》偶尔提到,还将罗坊自注为峡江,而非新余。[3]P350然而,我们却看到大量老同志文革时期的回忆录。权威部门的领袖传记称:“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红军绝不能冒险攻打南昌,必须采取诱敌深入作战方针。开始讨论时,少数人不赞成这个主张,李文林、袁国平提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4]P238罗坊会上是否有过激烈争议争论,是否少数人不赞成毛泽东主张,是否有人提出言辞过激以至立三路线的主张,我们不掌握第一手史料,不敢冒然下结论。一位亲历的红军高级将领回忆说:“会议不象峡江会议争议得如此激烈。”而峡江会议,“地方上的几位同志很少发言,主要是‘看会’,看军队同志的态度”。[5]P290-291这显然与权威部门传记所引回忆针锋相对、大相径庭。然而,客观理性分析考察一下罗坊会议前后真实情形却是非常有意义的。
罗坊会议前不到20天,即10月7日,江西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在《宣布本府成立及政纲》的《布告》中称:“消灭军阀制度,完成全省总暴动,争取武汉及附近各省首先胜利,完成苏维埃的胜利。”[6]P200同一天,江西省苏维埃大会通过的《坚决进攻南昌九江决议案》指出:“当前的伟大任务就是怎样完成夺取江西全省争取武装首先胜利去促成全国暴动,吉安暴动之胜利是江西全省胜利的开台,紧接着就是南昌九江的夺取,中间决不容有一刻的停留……一刻不停的坚决进攻南昌九江是全江西工农革命群众紧迫的实际任务。”[6]P202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并非仅仅山沟里的江西地方党,其委员包括张国焘、毛泽东、彭德怀、罗炳辉、滕代远、陈毅、黄公略、杨岳彬、朱德等53人。罗坊联席会议决议开宗明义指出:“吉安的胜利就是江西一省胜利的开始……不仅号召全江西革命群众最近期间完成江西总暴动,对于争取全国革命胜利,同时是有伟大意义的。”[1]P187决议特别强调,“反对争取一省政权的游击路线”[1]P193、“争取江西首先胜利是一方面军与江西党部的当前任务”[1]P195、“坚决以阶级决战答复敌人的进攻,争取江西首先胜利,在革命高潮之前加紧反对一切改良主义、改组派、第三党、AB团取消派及最近蒋介石之国民会议欺骗政策”[1]P196。决议规定一方面军“目前的战略是在占领南浔占领南昌九江的总目标下,继续吉安胜利,争取进一步的胜利,即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1]P201。前引权威部门领袖传记称毛“明确提出红军决不能冒险攻打南昌”,“少数人不赞成”,不知此结论如何下得?一位方面军领导人的回忆似乎透露了一些真实情况:“经过充分讨论和毛主席以及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耐心说服,我们接受了毛主席不去打南昌的正确意见,当然我们的转变并不是开一次会议解决问题的。而是毛主席费了很大的功夫,费了最大的耐心,开了许多次会,我们的思想才通。”[4]P238罗坊红一方面军前委会后,朱毛颁布《红一方面军移师赣江东岸分散工作筹款的命令》,仍有人思想不通。毛泽东1936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五章第二节“战略退却”中指出:“人们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但是有了这一次经验之后,在后来的几次以对‘围剿’时,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7]P214在红军高级干部中,仍有人主张不过赣江,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8]P160朱德在1944年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时说:“长沙打不下,准备折回江西。但中央不准,有些干部也反对回江西,还要我们去打武汉、打九江。红三军团大部分同志亦不同意折回。”[9]P68毛泽东也感慨:“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7]P213
上引权威文献表明,罗坊会议前后,攻打长沙、武汉、南昌、九江等大城市、中心城市,不仅是中共中央的指令,而且也是红一方面军和江西党内普遍的认识,毛泽东、朱德也概莫能外。罗坊之前,太平圩、峡江、袁州诸次会议,党内红军中反反复复已争论了一路,要客观地理性地分析罗坊的争论,不必过度渲染和夸张。在革命队伍内部,在共产党内,在红军高级领导人之间,出现任何不同意见或这样那样的争论都是正常的,都是可以允许的,这种争论是不同认识的争论,是不同观点乃至观念的碰撞,不必上纲上线更不必称之谓路线之争。相反,通过不同观点的交锋、撞击,最终达成了思想认识的统一,避免了党内及红军内部原则分歧乃至分裂,这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好事。因此,罗坊会议开成了一个团结的会、共同对敌的会。会议的成功召开及其后战争实践,无论在对敌斗争还是正确解决党内不同认识,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成功范例。
三、公正地评价罗坊会议争议人物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袁国平、李文林似乎评价不高、颇具争议,固然与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有关,罗坊会议“持不同政见”或倍受诟病的态度,或许也是重要原因?其实袁的态度并非代表个人,前文已述此处不再重复。李文林作为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江西地方党组织最高领导人,即便有自己观点,甚至有与前委不一致的观点,也无可厚非,更不必过分苛责。相反,从毛泽东、朱德有关论述中,我们看不出李文林与前委的原则分歧或根本对立,彭德怀、滕代远等红军高级领导人也不曾描述过李文林在会上的态度言论。前委与行委联席会议第二天,行委就与前委共同署名发布《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半月之后,11月11日,又与前委共同署名发布《红军第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江西省行动委员会通告》。11月20日,毛泽东又以总前委代表身份致信江西省行委,通报水南情况,近期敌情,“并望省行委……每天各有一个信送到总前委,务使消息灵通为要”[6]P210-211。倘李文林固执己见或与前委原则分歧,又如何解释迅速联合署名发文?毛泽东又如何一如既往地信任与尊重?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致林彪著名的通信《对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中,对李文林及其“李文林式”根据地非常推崇。毛泽东指出:“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配合着从斗争中训练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武装从乡暴动队、区赤卫队、地方红军以致于超地方红军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10]1941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六大以来》时全文刊印了此信。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也删去了“贺龙式、李文林式”。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两度谈到李文林。在《苏维埃运动》中称:“一九二八年春天,由李文林和李韶九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江西的兴国和东固活跃起来。这个运动以吉安一带为根据地,这些游击队后来成为第三军的核心,而这个地区本身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11]P57《红军的成长》则说:“1930年春,李文林、李韶九领导的几支游击队改编为红军第三军,由黄公略任指挥,陈毅任政委。”[11]P62
这些收入《六大以来》《毛泽东自述》的文字,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毛泽东对李文林的真实评价和态度。按照惯例,党和国家领导人或军队高级将领或根据地、红军创始人诞辰百年之际,都要举行相应规模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2000年、2006年分别是李文林和袁国平诞辰100周年,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对“赣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和“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的李袁二位革命先辈的任何纪念活动。正如虽然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遵义会议后仍指责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抗战初期对日作战与毛泽东方针相左,并不影响林彪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和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一样,我们对于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袁国平、李文林能否更宽容一些,能否更客观公正一些,能否尽可能少些个人恩怨?在罗坊会议过去80周年,即将迎来建党90周年的今天,我们史学界、理论界应当具备这种气度和胆识。
注 释:
①1930年10月26日的 《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署名“红军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其后11月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江西省行动委员会通告》,11月10日的《宣传动员令》均称“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或“中国共产党红军第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故本文尊重历史文献,称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而不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
[1]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委、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室编,1988年版。
[2]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朱德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4]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5]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6]江西党史资料(第7辑),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委、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室编,1988年版。
[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11]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汤静涛,男,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处长。
1930年10月25日,中共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在江西新余罗坊举行联席会议①,史称罗坊会议。罗坊会议是红一方面军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奠定了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的坚实基础,标志着红一方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由战略进攻向战略退却的重大转折。因此,罗坊会议在红一方面军反“围剿”作战史、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上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根据原始文献和权威史料,拟对罗坊会议战略决策作一简要回顾,对罗坊会议争论问题作一疏理和概括,并对罗坊会议的争议人物作些分析述评。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