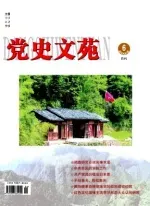选择与被选择的变奏——略论五四运动的历史逻辑
2010-08-15戚桂祥
戚桂祥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南昌 330027)
五四运动至今已九十余年,九十余年来,对五四运动回忆和评论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这场运动不断地被解构与重构。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时至今日,它在中国历史中到底具有什么意义,似乎并未更加清晰,反而却显得日渐模糊了。正如《五四运动史》的作者周策纵先生所指出的:“在中国近代史上,再没有任何的主要事件像‘五四’运动这样惹起各种的争论,这样广泛地被讨论,可是对它的正式研究却又是如此贫乏不足的了。 ”[1]P1
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评价,特别是通过对近几十年来一系列有关五四运动再思考的文章和专著进行梳理,可以总结归纳出三个主要观点:一是认为五四运动的主旨是爱国、反帝,五四运动的意义主要在于开启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二是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滥觞,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革命不断、罪恶丛生、道德败坏,都与激进思潮借五四运动盛行,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联。三是认为五四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可惜因“救亡压倒了启蒙”而半途夭折。
上述关于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不同观点,折射出不同时期、不同意识形态下人们对于五四运动的反思与认识。九十年来,在与五四运动的持续对话中,五四运动本身渐行渐远地模糊起来,不同时代赋予了五四运动更多的现实烙印。后人固然有其后见之明,然而我们更应该警惕的是对五四运动的隔岸之误。本文试图通过回溯历史,对五四运动时期的学人在当时国内外环境下的种种选择与被选择进行梳理和解读,以期揭示五四运动本身所蕴含的某种历史逻辑。
五四运动的复杂性与多面向性使得我们很难对其起迄日期作严格的断限,应将五四运动看作历史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本文将五四运动的讨论限定在1917年初到1921年年底的五年之间。①
一、个人觉醒与社会改造中选择与被选择的变奏
(一)在民主与科学旗帜下聚合的启蒙者
1917年1月,陈独秀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并将《新青年》从上海迁来北京编辑。他把主编《新青年》与改革北大结合起来,帮助蔡元培罗致人才。与胡适、陈独秀同年进北大的有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先后进北大的还有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陈大齐、朱希祖、刘文典、沈尹默、沈兼士、马裕藻等多人。稍后,鲁迅也来北大兼课。一时间知识精英荟萃,北大气象为之一新。他们都为《新青年》撰稿,使《新青年》阵容更加强大,新文化潮流更加澎湃,并形成了一个围绕《新青年》的生气勃勃的文化团体,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在解构旧文化的同时建构新文化。
在《新青年》周围的知识分子和北大发生了关联以后,新知识分子的意见受到高度的推崇和广泛的关注。辛亥革命以后日趋黯淡的政治和社会局势,使得新文化人极度的愤怒和困惑,列强依然对我国虎视眈眈,国内军阀混战导致乱象纷呈。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将中国政治危机归结为人民对于国家和政治缺乏干预的热情,“一般商民,犹以为干预政治,非分内之事;国政变迁,悉委诸政府及党人之手”[1]P3。 一群声望卓著的知识精英,希冀通过新文学、新思想的传播,唤起民众的个人觉醒,以图挽救中国的政治危机,改善中国的政治生态。
“五四”时代,个人独立渐成社会转型的新趋势。新文化运动批判儒家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以个人主义批判礼教之宗法主义家族伦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新知识分子不但努力介绍西方思想和体制,而且还致力于对中国固有的文化道统进行颠覆性解构。陈独秀倡言现代生活以个人独立主义为原则,其兼有伦理上之个人人格独立、经济上之个人财产独立和政治上之个人精神独立之义。吴虞则指出,儒家以孝悌作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其主张孝悌,旨在维护君亲长上的专制威权。[3]李大钊强调,东方文化之短,在于不尊重个性,视个人仅为集体中不完全之部分,而个人之价值全为集体所吞没。[4]胡适大力阐扬易卜生主义,主张个人的充分发展是人类的最终目的,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就没有社会的进步。[5]他还批评礼教的节烈观念是一种男子专制的贞操论。[6]并且为五四时期受礼教迫害的女青年李超作传,谴责礼教男尊女卑、无后不孝的宗法观念和家长族长的专制。[7]鲁迅则抨击节烈是非人道的封建夫权主义的畸型道德,并批判孝道之长者本位道德的反进化本质。[8]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选择,是通过对儒教的批判,扫除儒教威权主义政治理念的束缚,将人们从其桎梏中解放出来,进而以诸多个人之觉醒唤起社会之觉醒。
但是,在民主与科学旗帜下聚合的启蒙者们,在苦寻破壁之道中分分合合,学术舞台中心频繁改旗易帜。当各种西方思想诸如民主、科学、自由主义、实验主义、人文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潮水般涌来时,不少启蒙者莫衷一是,自身也陷入了迷惘。而当外侮频仍时,“救亡”便压倒了“启蒙”。是继续坚守“启蒙”,还是转而担当“救亡”?在多元思潮的激荡下,他们的分道扬镳就成为某种必然。
(二)在多元思潮的激荡下分道的救亡者
(1)不谈政治的初衷与不得不谈政治的现实。《新青年》启蒙者由于见解、兴趣等的不同,造成他们在思想领域的自由市场里的选择出现显著差异,并在经历诸多论战后分道扬镳。胡适在1931年对这段经历作了如下的回忆: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但是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虽抱定不谈政治的主张,政治却逼得我们不得不去谈它。民国六年第二学期陈先生(陈独秀)来到北大,七年陈先生和李大钊先生因为要谈政治,另外办了一个《每周评论》,我也不曾批评它,他们向我要稿子,我记得我只送了两篇短篇小说的译稿去。[9]P51由此不难看出,胡适想把《新青年》杂志办成纯学术性的刊物,以达到他的所谓“中国文艺复兴”的梦想。他选择了自由实验主义,对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持反对态度;但动荡的时局逼迫他们不得不谈政治,清谈沙龙必然在民族危亡的冲击下遭受倾覆。
(2)问题与主义。当现实逼得他们不得不去谈论政治时,启蒙者自然不得不转换自己的社会角色。然而,“怎样谈政治”又成了他们新的选择。陈独秀在“五四”前期的观点与胡适相似,但到“五四”后期,陈的群体意识逐渐疏离个人主义而归宗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让阴霾密布的思想天空拨云见日,向“五四”激进知识分子闪耀着革命的真理光芒。陈的思想演变,表征着启蒙运动后期道德理想主义的复兴和市民文化的衰微。[10]P84而胡适信奉的“实验主义”,主张“只谈问题,不谈主义”,只承认一点一滴的进化,反对根本性的变革,必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随着陈独秀、李大钊等左派知识分子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对垒,“五四”先驱们迅速分化为两大阵营。“问题与主义”之争,又使这种分裂公开化、激烈化。诚然,“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语)但“主义”是时代的旗帜,是历史车轮的引擎。但不论怎样,他们的选择不仅影响了此后两人不同的人生趋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
(3)救亡与启蒙。其实,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整个现代西方思想文化,都可以在“五四”之前的中国找到其各自的代言人。从这样的视角来审视五四运动,它不再是平原上突然冒出的高山,而只是绵延的山峦中更高的一座山峰。仰望这座山峰,人们会发现,革命与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髓。在“拿来主义”盛行的特定历史语境下,“启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泥潭。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启蒙”本身催化和加速了“救亡”。也许《新青年》知识分子一开始点着的是一团取暖的小火,但四周的干草借着风势迅速蔓延,便渐渐燃成了燎原大火,以致自己也身不由己地被这火势所裹挟。起初,他们选择启蒙民智,希冀实现“英雄造时势”;但日趋迷离的政治乱局,又使其左翼选择救亡图存,雄辩地诠释着“时势造英雄”。透过当年《新青年》知识分子的纷争与聚离及其不同的人生道路,充分揭示了在大浪淘沙的社会转型时期,这种选择与被选择的历史逻辑。
二、渐进改良与激进革命中选择与被选择的变奏
(一)在军阀内乱中改良越改越“凉”
五四运动直接起因于各界人士对巴黎和会及 《凡尔赛条约》出卖中国权益的抗议,而这个危机又根源于日本与德国对山东权益的争夺。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接续性后果之一。从洪宪帝制失败后,围绕参战问题,段祺瑞政府与总统黎元洪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府院之争”。出人意料的是,这场府院之争的结果竟然是1917年6月的张勋复辟事件。从洪宪帝制到张勋复辟,中国国内政体选择问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政治选择问题纠结在一起,政局态势错综复杂,时代列车呼啸着驶入了一个历史拐点。
随着意识形态博弈的逐渐加剧,知识精英的价值取向各奔西东。左翼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宣传热忱与日俱增,右翼热衷于改良主义的教化和践行,中间派则彷徨观望。然而,严酷的军阀内乱令改良越改越“凉”,一代右翼“启蒙”巨擘像流星般辉煌地殒落;而颇具政治胆识的左翼“五四”先驱,“欲变其世,先变其身”,羽化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借助苏俄外援搅热了沉寂的赤县神州。
(二)在苏俄外援中革命越革越“热”
五四运动引起了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东方革命的高度关注。五四运动结束不久,共产国际就派遣使者与五四运动领导人取得联系。嗣后,晚年的列宁做出了一个影响整个20世纪的重大战略调整,将目光由西方转移到东方,退出战争赢得和平以巩固革命成果,在东方拓展革命空间。
在这之前,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个在东亚各国人民当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并当即得到政治局的批准。接着,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的身份来到远东,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给他的指示是:1.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2.我们对待中国、蒙古和朝鲜人民的态度,应当是唤起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摆脱外国资本家压迫的自觉行动。3.实际上,我们应努力支援东亚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还应同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关系,并通过出版铅印刊物、小册子和传单来加强鼓动工作。4.必须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组织。[11]P38-39
1920年4月,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中国,开始开展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次年,用马列主义武装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登上了历史舞台。据李达回忆:1920年春季,第三国际东方局派了一个代表来到中国,他的名字是Vitinsky。我们替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吴廷康。他是和他夫人同来的……他首先到达北京,和李大钊等数人交换意见。当时,苏联宣布废除沙皇压迫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一般知识分子都对苏联有好感,所以新文化界人士到处请吴廷康讲述苏联情况,对于当时像云雾一般的苏联,有了相当的了解。特别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更喜欢与吴廷康相联系。当时充任英文翻译的是张太雷。由于李大钊的介绍,吴廷康到了上海,首先访问了新青年社的陈独秀……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吴廷康就劝陈独秀、李汉俊等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12]P6与此同时,吴廷康还接触了孙中山、吴佩孚和陈炯明。
苏俄领导人与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的直接接触,是在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不仅在会上几次发言,而且受到列宁接见。契切林也同张秋白进行了几次会谈,讨论了孙中山国民党与苏俄的关系问题,双方意见完全一致。[13]P53-54至此,苏俄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确立了友好关系,并为以后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一战的结束与苏联的成立,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运动和政治变革提供了全新的历史选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点燃的革命星星之火,在苏俄的外援下渐成燎原之势。北伐战争,第一次国共合作,在一个短暂的时段内,一系列重大事件相继发生,革命越革越热,选择与被选择的历史逻辑在此生动地展现。它雄辩地告诉人们:每一次历史进步,都是以巨大变革为动力,这是社会发展的黄金法则。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五四”精神,是新时代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
三、“五四”精神的历史投影
“五四”文化凝结着历史,“五四”文化连结着未来。在新中国六十年的征途上,处处撒下“五四”精神的历史投影;即令在文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阶段,也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传承了求新思变的“五四”精神。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五四运动中选择与被选择的变奏所揭示的大转折时代的历史逻辑,更是被精彩演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人们的思想同五四时期一样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态势。在全面反思和拨乱反正的时代诉求中,初始的选择是“摸着石头过河”。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日趋提速,促使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核心的高层领导,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的巨大改革魄力,变奏为邓小平理论及其一脉相承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凸显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高度的前瞻性,极大地升华了“五四”精神。30年来,在不断迸发真理光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统领下,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引领下,我国呈现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以崭新的雄姿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就是“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新的社会剧变时代所呈现的历史逻辑。
注释:
①在1917年,新起的思想界人物,以《新青年》杂志和国立北京大学为中心,团结他们的力量,发起新思想和新文化改革,1921年以后,运动已发展为直接政治运动,以后几年里,思想改革和社会改革多多少少遭受忽略。因此,我们很有理由把五四运动定在1917年到1921年这段时期之内。
[1][美]周策纵著,陈永明等译:五四运动史[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99.
[2]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J].上海: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1916年 2月).
[3]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J].北京:新青年,第2卷第6号.
[4]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J].北京:言治季刊,第 3 册.
[5]胡适:易卜生主义[J].北京:新青年,第 4 卷第 6 号.
[6]胡适:贞操问题[J].北京:新青年,第 5 卷第 1 号第 3 册.
[7]胡适:李超传[J].北京:新潮,第 2 卷第 2 号.
[8]鲁迅:我之节烈观[J].北京:新青年,第 5 卷第 2 号;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J].北京:新青年,第6卷,第6号.
[9]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胡适于1931年10月 30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说)[C].陈东晓编:陈独秀评论[M].北京:北京东亚书局,1933.
[10]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9月1日)[R].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2]李达自传[R].党史研究资料(第 2 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第1页—第2页;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R].“一大”前后(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3]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1922年 2月 7日)[R].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