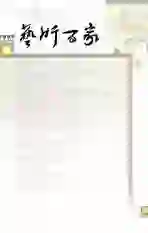宋代仕女画风与宋代社会风气
2010-05-10王宗英
王宗英
摘要:宋代是仕女画风由晋唐以来的古典之风向明清以后世俗风格转变的重要时期,在风格上形成了宋代独有的特征,这既是艺术发展的自律性结果,也是社会风气的折射。
关键词:宋代;仕女画风;社会风气;端严秀丽;美术史;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J21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09)07-0114-05
一、宋代仕女画风格特征
历史进入北宋,社会在向前发展,但是随着礼教的深入和理学的兴起,社会风气反而谨小慎微起来,男女之大防成为不可逾越的礼数,甚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仕女画殊乏容身之地,因此,一方面,仕女画数量在北宋明显减少;另一方面,仕女画在意境、表现形式等方面也开始拘谨保守。以至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卷一中发出“士女牛马,近不及古”之叹。这种状况在南宋时有所改观,当时的院体画家中有不少善画仕女者,并且在情趣、意境上寻求突破,确立了一套画仕女的标准,并成为明代仕女画家效仿的对象。
从现存宋代的仕女画来看,画风沉稳工致,线条法度严谨,人物形象娇小端丽,身材造型摆脱了盛唐和中晚唐壮硕丰肥的型制,开始过渡到瘦削的身材和轻盈的体态,结构严谨准确。身材娇小是宋代仕女造型的基本特征。面型上,与唐代“曲眉丰颊”的形象也已有明显区别,面型虽也比较圆润,但已经偏长圆。宋佚名《四美图》中除一女子脸型偏圆,其他三位女性脸型都偏长圆。到了南宋,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南宋苏汉臣《妆靓仕女图》中的仕女、南宋佚名《合乐图》的仕女,以及南宋刘松年《天女散花图》中的散花天女,面型都偏长圆,且向瘦削发展。
在服饰上,宋代仕女画中的人物装束与唐代仕女画中的人物装束区别很大,唐代服饰开放夸张,前胸半露,薄衣轻纱,轻纱透体;宋代仕女画中人物服饰拘谨保守,里三层外三层,层层包裹,不使有一点外露,唐代袒胸露臂的装束已经荡然无存,难怪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不无叹息地说:“……在宋代和宋以后,(妇女)胸部和颈部都先是用衣衫的上缘遮盖起来,后来用内衣高而紧的领子遮盖起来。直到今天,高领仍是中国女装的一个显著特点。”刘宗古《瑶台步月图》中的仕女形象服饰严谨保守,甚至衣角、裙边都规规矩矩,没有半点飞动、褶皱。宋代的女装通常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着长裙,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长袖小褙子,褙子有点像今天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一般都绣上漂亮的花边作为装饰,宋代佚名《蕉荫击球图》中仕女的服饰就是如此。这种保守拘谨、但又儒雅化的服饰,一方面是宋代礼教深化、儒学复兴、理学兴盛所导致的封闭、保守的社会风气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宋代“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滋生的文化氛围所致。宋代服饰对后世,尤其是明代服饰,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观念上,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在妆饰上,唐代浓艳、热烈、张扬的妆饰也已经无从寻觅,而代之以自然朴实。在髻式上,宋代女性发式承晚唐五代遗风,也以高髻为尚。此种髻式须加假发,在福州南宋黄升墓中曾发现高髻实物。也有直接用别人剪下的头发编结成各种不同式样的假髻,需要时直接使用的,与今天的假发套有异曲同工之妙,时称“特髻冠子”或“假髻”。另外,宋代还有许多不同的髻式,如朝天髻、包髻、双蟠髻、三髻丫、飞天髻等等。朝天髻在五代就十分流行,《宋史·五行志·木》载“建隆初,蜀孟昶末年,妇女竞治发为高髻,号“朝天髻”,宋代承此流风,这种髻式也很普遍,今所见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宋代彩塑就可见此种发髻的典型式样。包髻是颇具宋代特色的一种髻式,在山西太原晋祠彩塑中,也可见到,其具体做法是在梳好发式后,用绢、帛一类的布巾加以包裹,包裹之物可以包成各式花形,或做成一朵浮云等物状,装饰在发髻上,并佩以鲜花、珠宝等饰品。《蕉荫击球图》中的一位仕女以及《四美图》中的一位仕女就是这种发型,显得干净利落,又简洁大方。又有双蟠髻,双蟠髻又名“龙蕊髻”,苏轼词有“绀绾双蟠髻”之句,髻心很大,有双根扎以彩色之缯。这些发式在宋代仕女画中都可以找到踪迹。
宋代的面饰承唐代遗风,化妆步骤与唐代基本相同,只是唐代的“斜红”妆饰在宋代已不多见,贴花钿之风犹存,宋代·佚名的《宋仁宗皇后像》中的仁宗皇后就面贴花钿。宋代整体妆饰风格已没有唐代那样浓艳,而是倾向于淡雅自然。宋代的眉式却有后来者居上之势。宋代名妓莹姐“画眉日作一样”,宋·陶谷《清异录》载:
莹姐,平康妓也。玉净花明,尤善梳掠,画眉日作一样。唐斯立戏之日:西蜀有十眉图,汝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图;更假以岁年,当率同志为《修眉史》矣。
这位叫莹姐的名妓虽创造了近百种眉型,但最擅长的还是“倒晕眉”,眉型呈宽阔的月形,眉端用笔晕染,由深及浅,逐渐向外部散开,别有风韵。总的说来,宋代比较流行的还是以长眉为主,远山眉是经久不衰的眉式之一,秦观在《生查子》中曾专写当时引领妆饰时尚的名妓李师师之色容:
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妆罢立春风,一笑千金少。归去凤城时,说与青楼道。看遍颖川花,不似师师好。
这也正是宋代仕女画的形象特征,远山眉、细柳腰。
宋代仕女画的这些特征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风气的必然反映。
二、礼教的强化和对女性的拘束
宋代的文治所导致的国家的内向性,在宋代文化中有非常明显的反映。同日益加强的完备的宗法政治制度一样,宋代文化的发展与哲学体系,在内向封闭的境界中,实现着从整体到细节的不断修正和自我完善。这种变化,既是宋代文治社会的反映,也是宋代政治制度的需要。这一时期,最显著的文化现象之一就是理学的出现和发展。
理学产生于北宋,周敦颐是开山鼻祖,由程颢、程颐兄弟开始真正创立,其后经过二程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与发展,到南宋朱熹完成,二程和朱熹是这一派的最突出代表。因此,又称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中最引人注目也是影响最大的理论是礼教,对女性毒害最深的也是礼教。宋理学的开山人物周敦颐对孟子的寡欲论加以发挥,提出完善人格必须做到“无欲”、“主静”,先治家后治国,妻子必须绝对服从丈夫。这种理论到了程颢、程颐兄弟那里,更向前推进了一步,将天理与人欲完全对立起来,在他们的哲学范畴中,“天理”或“理”是最高统帅,是指自然的、普遍的、公共的准则或道理,一切事物必须服从于天理,人欲则是指一己私欲,明确提出“明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从下列引述中可以看出宋明理学中天理与人欲关系的发展过程:
孟子曰:养心莫于寡欲。……予谓,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周敦顾《周子全书·养心亭说》)
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周敦颐《周子全书·通书》)
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之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弗知,则至于天理灭而不知返。”(《二程集·遗书
卷二十五》)
养心莫善于寡欲,不欲则不惑。(《二程集·遗书卷十五》)
凡人欲之过者,皆本于奉养,其流之远,则为害矣。(《二程集·程氏易·损卦》)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程颐《遗书》(卷二十四)。
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道,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朱子语类》卷十三)
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朱子语类》卷十三)
从周敦颐的“无欲”,到程氏兄弟的“明天理,灭私欲”,再到朱熹的“明天道,灭人欲”,完成了这一理论系统化的过程,这种反自然、反人性的理论与封建统治的思想禁锢是相一致的,这种理论的存在和盛行更多地依赖于政治的扶持,所以,理学中的道德伦理明显地掺杂了政治伦理的因素,而且,政治伦理明显地凌驾于道德伦理之上,为封建统治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依据,这也是统治者极力提倡和扶持的原因。理学在南宋朱熹之后大行其道,并为宋元明清历代封建王朝所推崇,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体系。理学体系最具杀伤力的还不是其为封建社会提供的政治伦理,更具毒害性的是其对女性贞节的鼓吹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朱熹、吕祖谦编选之《近思录》记载了程颐对女性贞节观念的看法:
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
“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是程氏理论中最具毒害性的,朱熹对此理论加以附和,甚至公然写信劝人守节。朱熹之友陈师中的妹妹新丧夫,朱熹遂写《与陈师中书》劝其妹守节:
朋友传说,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之节。此事更在丞相夫人奖劝、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没为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计老兄昆仲,必不惮赞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君子现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伏况丞相,一代元老,名教所宗,举错之间,不可不审。熹既辱知之,厚于义,不可不言。未敢直前,原因老兄而密白之,不自知其为僭率也。
陈师中之父陈俊卿曾做过宰相,因此,信中有“丞相夫人”、“丞相”之语,出身豪门在朱熹眼中也成为守节的理由之一,因为其所起的表率作用更具奇效。程朱的这一理论在南宋之后,影响极为广泛,成为封建道德规范女性最严苛的枷锁和最严酷的教条,其流毒之深,使得历代女性前赴后继地践行着从一而终的教条,无数鲜活的生命死在贞节的祭坛上。正如胡适所说:
理学家把他们冥想出来的臆说认为是天理而强人服从……他们认人的情欲为仇敌;所以定下许多不近人情的礼教,用理来杀人,吃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分明是一个人的私见,然而八百年来竞成为天理,竞害死了无数无数的妇人女子。
程朱理学的贞节观念在宋代已有不小的影响,《宋史·列女传》中收录的贞节妇女有55位,在清人辑录的《古今图书集成》中宋代贞节妇女达274人,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前代。至元代,贞节观念影响更甚,《元史·列女传》收录列女187位,这也只是当时守节者中的突出者,未被记载的更是不计其数,这不能不说是程朱理学的“功劳”所在。不过,好在程朱理学的影响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程朱理学的禁欲主义在宋代提出之后并没有立即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宋代除了禁欲观念,还有与其不同导向的其他封建伦理,宋初的李觏在其《礼论》中强调礼应该是“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者也”,又提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的观念。在此类观念的影响下,宋初的贞节观念并不是很严苛。当时的名臣如范仲淹就有将儿媳再嫁的举动。范仲淹的母亲就曾经改嫁,范仲淹丝毫不以此为讳。范仲淹的儿子病死后,儿媳在范仲淹的安排下改嫁其门生王陶。宋代中期时,贞节观念依然比较松弛,宋·王辟之在其《渑水燕谈录》中记载了王安石嫁媳的故事:
宋王荆公之次子名雾,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庞氏女为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类己,百计欲杀之,竟以悸死,又与妻日相斗哄,荆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妇无罪,欲离异之,则恐其误被恶声;遂与择婿而嫁之。
这种开放的举动出现在宋代,委实令人庆幸。宋代的宫廷妇女也有再嫁的权利,并没有成为贞节标本的牺牲者,《宋史·宗室传》记载汝南王允让曾特地为限制妇女改嫁奏本,请求取消此制:“宗妇年少丧夫,虽无子不许嫁,非人情,请除其例。”这一请求得到了皇室的准许。宋代朝廷曾多次下诏宗室妇女可以再嫁,条件是不能嫁人为妾。这说明当时的世风对女性贞节并不是特别严苛,相反,倒有几许温情脉脉的人情味。而且,当时的男女交往也还比较多,妇女的社交也比较广泛,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描绘了当时元宵灯会上男女交往的风俗:“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贞节观念日益加强的南宋,妇女再嫁、改嫁也还比较多,宰相贾似道之母胡氏曾先后三次嫁人,死后依然被朝廷追谥为“柔正”。这时社会舆论并没有完全被贞节的教条湮没,女性的生活还有一定的自由度。但是应当看到,这种自由是夹缝里的自由,自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奇谈怪论出炉之后,宋代的贞节观念日益严苛,至南宋朱熹之后,理学被扶植为封建正统思想,贞节观念遂被广泛接受,成为世人公认的女性应该遵守的教条。到元代,虽然为蒙古族统治,但贞节观念依然被当作规范女性的基本准则。
与日益严苛的礼教相矛盾的是,宋代社会从上到下弥漫着及时行乐的艳雅之风。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再加上统治者又以财富笼络官员,使朝野上下纵情享乐风气盛行一时。这种享乐自然少不了舞榭楼台和轻歌曼舞的歌妓舞娘,因此,宋代妓院经济空前发达,歌台舞榭和歌儿舞女成为士大夫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北宋还出现了两位以奢侈风流著称的宰相寇准和晏殊为此风助焰。寇准生活穷奢极欲,耽于声色之娱,蓄养歌妓舞女无数,其侍妾蓓桃曾作诗劝诫,寇准不以为然,依然故我,并作诗回日:“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尊前听艳歌。”晏殊也是一个声色宰相,其宠妓被其妻赶出之后,晏殊怀念不已,叹息曰:“人生行乐耳,何自苦如此!”遂将遣出歌妓赎回。其子晏几道的词《鹧鸪天》更是将这种颓废生活描绘地颇为形象:“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这种奢靡之风遍及朝野,皇帝也是此风的主导者。皇帝狎妓恐怕亘古以来未之有也,宋徽宗和李师师的风流韵事在坊间里弄广为流传,这种“模范”的树立在朝野上下发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皇帝尚且如此,宋代享乐之风的盛行就不难找到原因了。这种风气的盛行也成为宋代文艺的主题。纵观宋词,“流连光景惜朱颜”的基调几乎是宋词的主旋律之一。他们把人生的意义,贯穿在花间月下,留连于
粉腮樱唇,往往从享受生活的欢娱中完成个体生命的体验。横刀跃马、建功立业只是在南宋特殊的情境中偶尔出现的个别情调,伤春悲秋、莺歌燕舞依然是宋代文艺的主题。李泽厚对文艺风气从中唐以来到宋代的改变做了精到的总结:
中唐的审美趣味和艺术主题已完全不同于盛唐,而是沿着中唐这一条线,走进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色彩的捕捉追求中。……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所以,这一时期最为成功的艺术部门和艺术品是山水画、爱情诗、宋词和宋瓷,而不是那些爱发议论的宋诗,不是鲜艳俗丽的唐三彩。这时,不但教人膜拜的宗教画已经衰落,甚至峨冠高髻的人物画也退居次要,心灵的安适享受占据首位。不是对人世的征服进取。而是从人世的逃遁退避;不是人物或人格,更不是人的活动、事业,而是人的心情意绪成了艺术和美学的主题。如果再作一次比较,战国秦汉的艺术,表现的是人对世界的铺陈和征服;魏晋六朝的艺术突出的是人的风神和思辨;盛唐是人的意气和功业;那么,这里呈现的则是人的心境和意绪。与大而化之的唐诗相对应的是纤细柔媚的花间体和北宋词。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的诗正是过渡的开始。胡应麟说,“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形容景物,妙绝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斩然。故知文章关气运,非人力。”区别到底何在呢?实际上仍是:盛唐以其对事功的向往而有广阔的眼界和博大的气势;中唐是退缩和萧瑟,晚唐则以其对日常生活的兴致,而向词过渡。这并非神秘的“气运”,而正是社会时代的变异发展所使然。
宋代这样一个整体社会趋向内省的时代,文化艺术也由向外拓展转到向纵深的内在挖掘,其所表现出的精致细腻程度是汉唐无法企及的。宋代的仕女画在风格上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唐代的雍容大度一变而为宋代的阴柔婉约,丰满壮硕也代之以孱弱纤细的清癯之美。
正是由于产生于既倡礼教又耽享乐的社会情境中,决定了宋代仕女画的表现必然遵从于这样的社会情境,因此,宋代仕女画中的仕女皆严装妍雅、规规矩矩,但又绚丽精致,讲究细节,充满情调。元代社会礼教风气的盛行度过于两宋,但也没有密不透风,女性也尚有一定自由度。且因为文人人朝为仕道路的断绝,文人隐居修道享受生活的风气也与宋代有些相似,因此,元代仕女画风比宋代仕女画除了加入了几许飘逸,其他与宋代区别并不是特别大。
三、世风影响下对女性的审美理想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唐代社会文化精神的昂扬向上、意气风发已不复存在,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劝诫大臣“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这已经为宋代的文化精神奠定了基调,追求现世享乐和精致生活是宋代自上而下的文化导向。这种文化导向和理学的兴起互相矛盾,但又同时并行,共同穿梭于社会的角角落落,构成了宋代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这种多元文化形态使宋代对女性的审美习俗也为之一变,女性美由雍容丰满走向清雅内敛。
宋代礼教风行造成了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女性缠足逐渐风行。关于缠足的起源有数种说法。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缠足》云:
(南唐)李后主宫嫔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令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形,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唐镐诗曰:“莲中花更好,云黑月常新”,因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纤弓为妙。以此知扎脚自五代以来方为之。
还有一说认为缠足起源时间更早,应在南北朝时,《南史-废帝东昏侯纪》记载,东昏侯荒淫无度,“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六朝乐府《双行缠》云:“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可为佐证。不管缠足起源于何时,在宋以前都还只是在宫廷中流行,到了北宋中晚期渐及贵族妇女,南宋初年,张邦基所著《墨庄漫录》一书,叙述缠足之事时,云缠足“近代兴起”。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则云“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者少,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可见,到了元代,缠足已成为流行,其流毒已成,从社会舆论“以不为者为耻”来看,此时缠足已相当普遍。宋代许多文人论及缠足,多为此鼓吹,以此为美,苏轼《菩萨蛮》词日:
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临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秦观《浣溪纱》则曰:
上鞋儿四寸罗,唇边朱粉一樱多。见人无语但回波,料得有心怜宋玉。只应无奈楚襄何,今生有分共伊么?
在以脚小为美的风气下,缠足成为对女性审美的一个重要条件,于是缠足之风愈演愈烈,流毒遂及民间。
在这种拘禁女性的风气下,对女性美的其他要求也有了明显变化。从当时最为盛行的文学形式——宋词中,可以看出当时对女性的审美要求。
晏几道的《鹧鸪天》云:“楚女腰肢越女腮,粉圆双蕊髻中开”,《浣溪沙》云:“腰自细来多态度,脸因红处转风流”,“香靥凝羞一笑开,柳腰如醉暖相挨”。秦观《满江红》云:“绝尘标致,倾城颜色,翠绾垂螺双髻小,柳柔花媚娇无力”,《生查子》云:“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妆罢立春风,一笑千金少”。可见,在身材上,与唐代的丰满壮硕已完全不同,而以纤柔瘦弱为美。甚至身材壮硕还会被讥笑,苏轼就曾做诗讥笑一位身材高大的舞妓:“舞袖翩跹,影摇千尺龙蛇动,歌喉宛转,声撼半天风雨寒。”元代,这种以娇弱为美的倾向更加明显,《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是当时文人心目中典型的美女形象:“裙鸳绣金莲术,红袖鸾销玉笋长”,“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这种瘦弱窈窕的纤弱形象来自于当时世俗的塑造,又得益于文人墨客的渲染鼓吹,以至于到明清已是恹恹病态,一至于斯了。
在身材形体上是这样,与此相匹配,在神态、情绪上则是慵懒忧郁,这在宋词中同样有许多表现。刘学箕《贺新郎》日:“午睡莺惊起,鬓云偏,鬓松未整,凤钗斜坠。宿酒残妆无意绪,春恨春愁似水”。这种百无聊赖、萎靡不振的情态为历代文人咏歌不已,遂成潮流。这种情态加上闲愁简直就成了宋代文艺的情绪了。欧阳修《踏莎行》云:“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张来《青玉案》则云:“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李清照《醉花阴》云:“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宋代积贫积弱的国势造就了这种文艺之风,加以文人的广为渲染,成为封建社会走向下坡路时的一路挽歌。正如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所云:
近代文学家写女性,大半以多愁多病为美人模范……以病态为羡,起于南朝。适足于证明女学界的病态。唐宋以后的作家都汲其流,说到美人便离不了病,真是文学界的一件耻辱。
这种忧郁症在宋代仕女画中的表现也非常突出,那些揽镜、奏乐、梳妆的女性无时无刻不满怀忧郁、满含闲愁。元代仕女画也未能幸免,即使描绘的是仙界神女,也哀怨愁闲。
总之,总结宋代对女性的审美标准,无出乎几个关键词:端庄娴静、娇小瘦弱、慵懒闲愁,这是礼教控制下的必然的审美形态,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世风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