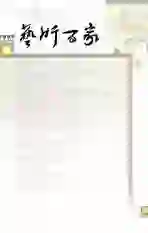武氏祠汉画像石中的吉祥文化内涵
2010-05-10杨大伟
杨大伟
摘要:山东嘉祥的武氏祠汉画像石所体现的吉祥文化,流露出对人情人性的理解,构建了汉代人的艺术精神和人文气质,成为一种对神的信仰和内心观照双方交流所获得的精神旨趣,标示着人生的情趣意象。武氏祠汉画像石的出现和传播,不仅体现了汉画及汉画以外吉祥文化的成型,而且促进了后期各种吉祥文化的发展,对人类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武氏祠;汉画像石;吉祥符号;吉祥文化;美学特征
中图分类号:J5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09)07-0032-02
“艺术品是将情感呈现出来供人观赏的,是由情感转化成的可见的或可听的形式。它是运用符号的形式把情感转化成诉诸人的知觉的东西……”——苏珊·朗格
古时祭祀天地、祭祀祖先、为亡魂引路、敬神占卜等活动,留下了许多吉祥图纹,这些图纹与文字的区别在于,它们不是语言的记录,有的象形,有的表意,但都是为了供奉祖先和神灵,驱邪除魔,达到消灾赐福的目的。图纹频繁出现,也是因为古人认定它们是吉祥之物,它可以让人多福,象征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汉代人用画像石装点墓室,暗含了墓主希望死后升仙和享受仙境的强烈愿望。而汉画像石所反映的仙境实际上就是墓主生前现实生活的延伸和继续。一派和谐的天国风景,自由、快乐的氛围,人与动物或动物与植物的混体,神怪往来飘荡,龙腾风翔等,传达了汉代人的魂梦。中国吉祥文化凝结着人们的伦理情感、生命意识、审美趣味与宗教情怀。中国吉祥文化源远流长,追求美好幸福,祈望吉祥平安的吉祥意识产生于古人对生活的不安定感。吉祥意识又决定了古人对吉祥符号的选择两汉时期,是我国吉祥文化的鼎盛时期,因而,在山东嘉祥武氏祠汉画像石中出现了大量的祥瑞图型,如武氏祠画像中出现的山神海灵、奇禽异兽、蛇尾怪兽、骑鱼仙人等等。
武氏祠画像,系东汉画像石,是武氏家族墓葬的双阙和四个石祠堂的装饰画。其中以武梁的祠堂为最早,从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开始,数十年间陆续营造,亦称“武梁祠画像”所刻画的历史人物故事、神仙怪兽和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画像,艺术风格浑朴雄健。祠内遍刻画像,东西中三壁上部,罗列40余则历史故事,有从伏羲至夏商古代帝王,有蔺相如、专诸、荆轲等忠臣义士,有闵子骞、老莱子、丁兰、梁高行等孝子贤妇;三壁下部为祠主的车马出行、家居庖厨等画像。东西壁山尖刻东王公、西王母等灵仙故事,内顶刻布神鼎、黄龙、比翼鸟、比肩兽等各种祥瑞图像。武氏祠汉画像石中的吉祥图型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天上的神仙世界,描写的是墓主人死后祈求步入的仙境;一类是人间的现实图景,描写的是墓主人生前的享乐生活。在神话传说的题材中,常见的有神兽、神鸟、水生奇异动物类、神人类、有东王公、西王母、等。为求得墓主人在阴间平安元事,画像石墓中常刻有铺首衔环、朱雀、青龙、玄武、白虎等吉祥动物。
武氏祠画像中许多图型如东王公、西王母被认为是天界掌管生死祸福的最高神;北斗星君则是掌管生死、消灾免祸的大神;风雨雷电之神是主宰这四种自然现象的神灵;伏羲女娲的形象是人头蛇身,两尾相缠,有交媾之意。“凡人之所以为人,礼义也。”(《礼记·冠义》)阴阳男女是延续生命的力量,人性里都有善的一面,爱美即是人之天性,礼义则是表现善与美的保障。汉代人以夸张的方式叙写着人性之善,展示出自己的潜力、才华、抱负和能达到的心理高度。伏羲和女娲或作蛇躯或作龙躯,或许表明中国古代常常视龙蛇为一体,以蛇为象征帝王的神物。传说汉高祖刘邦在秦末为亭长时,曾行经丰西大泽中,路遇大蛇挡路,乃拔剑斩杀大蛇,随后经过该地的人看到有一老妪对蛇悲哭,她说大蛇是白帝子,刚被路过的赤帝子杀害,说完后老妪就不见了。西汉时流行的上述传说,为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涂上了神异的色彩,同时说明当时人们习惯用蛇象征帝王。诸多吉祥图型的出现,是有其一定的历史渊源的。如玄武,又称真武,民间俗称真武大帝,荡魔天尊,北斗星君,元代被晋封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是由星辰信仰发展而来的方位神之一,主治北方。由于民间信仰以为龟雌蛇雄,便以龟蛇的组合作为玄武神的象征,这就出现了汉画中玄武的图型。古代有“南斗主生、北斗掌死”的说法,加之其又有荡魔除妖之能,就成为人们所尊崇的增福增寿、消灾免祸的吉祥大神。故汉画像石中出现了大量的玄武、北斗星君的形象。汉代以后,全国各地所建真武庙也随处可见。汉代人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些神人异兽、嘉禾灵器等,是因为人世间帝王将相、贤人高士的行为感动了上天,上天即降下这些表示祯祥福祉的东西以回应,究其思想渊源,无外乎是对福祉的企盼,对美好的憧憬,对邪恶的诅咒,对灾难的逃避,还有统治者对臣民的愚弄。这就是上述祥瑞画中祥瑞思想在汉画像石上的艺术表现。画像石中阴阳系列的日月、男女、都是主宰人的生命、繁衍、变化的象征系列,借助象征达到转变自然及命运的目的,寄托着人追求幸福、生命、理想的浓厚情感。因此,自然动物的形态就发生了变化,鸟类为三足鸟,稳步于太空象征太阳;五头鸟居墓室顶镇墓避邪;凤为展翅的朱雀,虎为有翼的白虎,马为飞翔的天马,它们都变成了神兽呈祥御凶。在人神合一的武氏祠汉画像石中,蕴含的信息就是:人是世界的主宰,人是汉代社会的主体。吉祥意识、吉祥文化已深深地植入中国人的生活中,以至于具有凡物皆可为吉祥的特点。吉祥对于中国人而言,就像水之于鱼、天空之于鸟、空气之于人。因此了解了吉祥文化,也就了解了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武氏祠汉画像石中最具有特点的,即出现了专题的“祥瑞图”,雕刻了二十余种祥瑞图型,并皆刻有榜题。蓂荚:《宋书·符瑞志》说:“萁荚,一名历荚,夹阶而生,一日生一叶,从朔而生,望而止。十六日,日落一叶,若月小,则一叶萎而不落,尧时生阶”。狼井:《宋书·符瑞志》说:“狼井,不凿自成,王者清则应。”六足兽:《宋书·符瑞志》说:“六足兽,王者谋及众庶则至”。玉英:《宋书·符瑞志》说:“玉英,五常并修则见。”银瓮:《宋书·符瑞志》说:“银鹿,(当为瓮)刑罚得共,民不为非则至。”比目鱼:《宋书·符瑞志》说:“比目鱼,王者德及幽隐则见。”白鱼:《宋书·符瑞志》说:“白鱼,武王渡孟津,中流人中王舟”。比肩兽:题榜曰:“比肩兽,王者德及矜寡则至”。比翼鸟:题榜日:“王者德及高远则至”。玄圭:题榜曰:“水泉流通,四海会同则至”。壁流离:题榜曰:“王者不隐过则至”。木连理:题榜曰:“木连理,王者德泽纯洽,八方为一家则连理生”。赤罴:《宋书·符瑞志》说:“赤罴,佞人远,奸滑息,则入国”。玉马:《宋书·符瑞志》说:“玉马,王者精明,尊贤者则出”。泽马:《《宋书·符瑞志》说:“王者劳来百姓则至”。白马:《宋书·符瑞志》说:“白马朱鬣,王者任贤良则至”。巨畅:题榜曰:“皇帝时,南(原题榜此处缺损一字)乘鹿来巨畅”。畅当为鬯之讹,鬯为古时一种美酒。《宋书·符瑞志》
说:“巨鬯,三禺之禾,一稃二米,王者宗庙修则出”。
武氏祠汉画像石产生的时期,是祥瑞思想发展到最兴盛的时期。信奉祥瑞的人数,在社会上达到空前的数量。祥瑞思想也深入到人们的思想生活深处。甚至官方修的史书中,专门列出祥瑞的篇章。如《宋书·符瑞志》、《魏书·灵征志》、《南齐书·祥瑞志》就是在狂热的祥瑞思想下的产物。《本纪》和《志》中,关于祥瑞的概述,多有记录。盛行期的祥瑞思想不像早期那样零碎和不系统,而是几乎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构筑这种思想体系的大师,当然首推董仲舒。他在《春秋繁露》一书中,开始把祥瑞思想整理成一种体系。东汉时,班固撰《白虎通义》(即《白虎通》或《白虎通德论》),其祥瑞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其后,萧梁时沈约撰《宋书》。此书中的《符瑞志》之详尽,为史书中所仅见。《孙氏瑞应图》为孙柔之所撰,是专门记述祥瑞的名著,并附有图画,可称集祥瑞之大成。至此祥瑞思想达到了高峰。唐代成玄英注春秋时代的《庄子》一书日:“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喜庆之征”。吉祥文化,以民间艺术为主要载体,旨在营造吉瑞环境,寄托人们的美好理想与愿望。寓意吉祥的图像称之为“吉祥纹祥”或“吉祥图案”,其题材浩如烟海,涵盖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贯穿于百姓的生产劳作、人生礼仪的方方面面。“福、禄、寿、喜、财、吉”是吉祥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彼此关联而又各具特色的吉瑞主题。后期相继出现了比如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羊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同心、十全十美、百事亨通、干事顺遂、万事如意、马上封猴、鸳鸯戏水、鲤鱼跳龙门、麒麟送子、岁寒三友、天地长春、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等新的吉祥语、吉祥图型和石雕作品。
武氏祠汉画像石所体现的吉祥文化,流露出对人情人性的理解,构建了汉代人的艺术精神和人文气质,成为一种对神的信仰和内心观照双方交流所获得的精神旨趣,标示着人生的情趣意象。明显感受到汉代人的审美感悟已经进入了对意蕴世界的发掘。吉祥文化,包含着传统文化的众多内容和人文主义精神,它是传统文化精神的镜子,是传统民俗文化的主要内容,涵括了人生的方方面面。武氏祠汉画像石中的祥瑞图型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它的出现和传播,不仅体现了汉画及汉画以外吉祥文化的成型,而且促进了后期各种吉祥文化的发展,对人类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