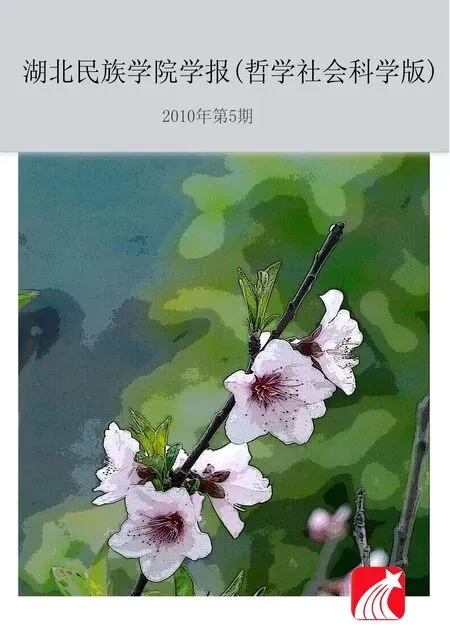清代鄂西与川边改土归流之比较研究
——以容美土司与德格土司为例
2010-04-10岳小国
岳小国
(三峡大学长江三峡发展研究院,湖北宜昌 443002)
清代鄂西与川边改土归流之比较研究
——以容美土司与德格土司为例
岳小国
(三峡大学长江三峡发展研究院,湖北宜昌 443002)
土司制是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种民族政策,它是一种过渡性的管理策略,因而改土归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清代的改流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其实施存在着地域、民族间的差别。从鄂西、川边地区的改土归流运动来看,二者同为少数民族聚居区,但改流的背景、目的及影响却大不相同。以史为鉴,鄂川两地改流的比较研究或可为我们当前民族地区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鄂西;川边;改土归流;容美土司;德格土司
改土归流是清代社会一项意义深远的政治改革,也是民族史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重点集中在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原因、目的、措施、影响与评价等方面,并产生了一批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①。然而,我们在肯定以往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存在的不足之处。比如,以往的研究偏重于某一区域、民族土司的改土归流,而对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比较研究则关注不多。事实上,这类主题也同样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以清代为例,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前后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改流运动,但是两次改流的动机和目的、采取的措施以及效果、影响等却大相径庭。以史为鉴,通过梳理、对比历史事件,为我们当前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制定、执行或可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笔者不揣浅陋,以清代鄂西与川边地区改土归流的对比研究为视角,并对二者的差异进行了阐释,以期能起抛砖引玉之效。
一、鄂川两地的土司制
“土司为封建之遗型”,古者“要荒夷落,修职贡者,皆给名爵”[1]71,西汉经略西南夷、唐宋行羁縻政策是为土司制之滥觞。作为一种行政体制,土司制正式形成于元,完善于明,而衰亡于清代。从地理区域上看,该制度主要推行于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这里以清代鄂西、川边两地为例,对土司制作以概要性地介绍。
鄂西土司地区在今天的行政区划上主要包括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大部、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的大部,以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西部[2]1。鄂西土司的设立始于元代末期,面对全国各地的农民大起义,元政府为了稳定鄂西的局势,遂设立施南道宣慰司一个,散毛誓崖等军民宣抚司5个,忠孝等军民安抚司4个。鄂西土司制在明代经过罢废与恢复两个阶段后,在制度上日趋完善,到清代中期开始走向衰落。在雍正改流前,鄂西有大小土司二十余个,除容美外,其余土司都比较小。容美土司最富强,它是湖广五大土司(永顺、保靖、桑植、容美、施南)之一,是湖北境内最大的土司[2]96。鄂西的改土归流结束于雍正十三年(1735)四月二十八日[3]83。整个土司制在鄂西历时四百余年。
川边①川边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包括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西藏昌都地区。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设立“川滇边务大臣”一职,管理移民垦殖事务,北洋政府于1914年置有川边特别区。地区早在元宪宗时已归附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宪宗二年(1252),命忽必烈讨西南夷,其“自中路大渡河出金沙江,西康诸部概于此时受抚。”[1]72元在吐蕃故地设置的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吐蕃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三个宣慰司中,川边地区受吐蕃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管辖。由于该司辖地广泛,所设置的朵甘思哈答李唐鱼通等处钱粮总管府可能驻牧于德格[1]75。明代册封朵甘卫都指挥使司,赏竹监藏为朵甘宣慰司,即后世之德格土司,所辖区域包括今德格、石渠、白玉、甘孜、江达、贡觉等县。清袭明制,设置德格宣慰司,德格土司在清初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西康诸土司部落,以德格为最大……”[4],该土司也成为康区四大土司(明正土司、理塘土司、巴塘土司、德格土司)之首。后因内部矛盾起,德格土司遂走向了衰落。清末,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赵尔丰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奏陈改流事宜。宣统元年(1909)对德格土司实行改流,迁土司多吉僧格于巴安(今巴塘县)。未几,辛亥鼎革,已废川边诸土司卷土重来,整个民国时期,土司在各辖区内仍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直至新中国成立。
可见,鄂西、川边所立的容美、德格两土司,发展轨迹有一些类似之处:历经唐宋羁縻统治、土司职设立于元代、发展壮大于清代,是区内首屈一指的大土司,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然而,相对于两土司的产生、发展来说,清王朝在两地推行的改流运动却显示出较大的差异性。
二、两地改土归流之比较
(一)改流背景
在有清一代,共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运动。第一次发生在雍正时期,第二次发生在清末的光绪、溥仪时期,从地域上看,前者以鄂西地区为代表,而后者发生在川边。不同的时空条件,暗含着两次改流之路的殊异性。
雍正朝正处于大清帝国“康乾盛世”的中期,大规模地开疆辟土工作已结束,台湾收回,来自边疆的威胁已基本解决。为此,雍正帝开始致力于国内政权的稳固,强化中央集权,结束区域内土司据地自封的割据局面。这一时期的改流主要以云、贵、湘、鄂等省为重点,主要是因为南方民族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日益密切,由于经济上的要求,各族人民希望打破一个个的独立王国,实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5]。此外,土民与土司以及中央政权与土司的矛盾也是促使雍正朝改流的一个方面。
鄂西的改流紧随湘西永顺、保靖、桑植等几大土司之后。通过改土归流,加强了中央王朝和土家族地区的联系,革除了“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旧规。
如果作一个历史的横向对比的话,可以发现:当大清王朝在湘鄂西地区进行轰轰烈烈地改土归流之时,在另一条战线上,清政府对西藏的经营亦在强化之中: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朝出兵击败了准格尔部策妄阿那布坦对西藏的入侵,并成功护送六世达赖进藏;雍正二年(1724)平定了罗布藏丹津在青海发动的叛乱;此外,清政府在成功解决卫藏战争之后,于雍正五年(1727)设立了驻藏大臣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对西藏的治理。中央王朝对西藏积极经营,与其在川边地区推行、维持土司制度同是治理藏区的重要措施,康区(川边)的稳定是成功经营西藏的基础。这时的清政府无力也无需废除川边的土司制。然而到了清末,川边地区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逐渐复杂起来。1888年,英国侵略军攻占西藏的亚东等地,强迫清政府相继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印藏条约》和《印藏续约》。一些有识之士,如四川总督鹿传霖等提出,“英、俄交窥藏地,蓄意已久”[6],“西藏地方与四川唇齿相依,关系甚重”[7]。这些人明确主张,为抵制帝国主义侵略,巩固国防,必须将康藏进行一体经营,川边的改流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04年,英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侵略西藏的战争中,血洗江孜,进军拉萨,迫使西藏地方政府订立了《拉萨条约》。同年,清政府任命凤全为驻藏邦办大臣,着手处理藏务。次年三月,凤全在巴塘遇害,这一事件成为了川边地区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导火索。因此,川边的改流一开始即和抵御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等特殊使命联系在了一起。
对比两次改流的背景可以看出,它们处在大清帝国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鄂西的改土归流处于清朝的鼎盛时期,主导改流的雍正皇帝是一位勤政而有远见的开明之君;而川边改流之际,晚清政府已是外忧内患、国势颓废,整个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而,前者是以积极的姿态主动实施改土归流,而后者则是迫不得已,借改流以图自保。
(二)改流原因和目的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鄂西与川边改流的原因及目的存在着重要区别。清王朝在鄂西实行改土归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从全国而言,清王朝正处于盛世时期,当权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改变分散割据的格局,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第二,鄂西诸土司接近中原腹地,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土司制的存在无疑是区域间交往的一种障碍;第三,从战略位置上看,鄂西是通往西南的咽喉之地,要想实现对西南的控制,必先将鄂西置于直接统治之下;第四,基于由近及远、先易后难的原则,率先在鄂西改流,也是为后期川边等地的改流扫除障碍、积累经验。
川边大规模地改流发生在清末,是清政府应对国内外危机的被动举措。
当时整个藏区正处于多事之秋:在国外,英、俄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妄图吞并西藏;而在国内,喇嘛教上层和土司势力顽固地保持农奴制度,拒绝任何社会改革。帝国主义采取收买喇嘛教上层,阴谋挑起汉藏纠纷,离间藏族地区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妄图煽动西藏独立。内外交困的危机,促使清政府认识到“西藏则川、滇、西宁、新疆、蒙古藩篱”[8],帝国主义倘得手西藏,势必危及中国西部的安全。赵尔丰改土归流的川边地区实际上是与西藏政权争夺汉区和藏区之间的缓冲地带,经营川边实际也是巩固西部国防问题。因此,赵氏在陈述川边改土归流的原因时曾说道:“自门户开放以来,强邻环伺,皆骎夕以辟地殖民为务,中国遂日受侵夺矣!从前属地未经编籍者,外人即指为彼之所觅殖民地,强为占据。”[9]“筹边保藏”,加强边藏地区的建设以保卫西藏的策略,“惟筹边乃能保藏,后路若不布置,中间隔绝,藏为孤悬。”[10]“稳藏必先安康”,川边的稳固对安定西藏局势,抵御国外侵略势力的干涉,维护国家的领土与主权至关重要。
(三)改流措施
鄂西、川边两地改流的原因和目的迥然相异,但二者改流措施上的差异不甚显著。
雍正朝,在南方几省掀起的第一次改流运动中,“鄂尔泰督云贵,建策改土归流,迈柱亦行之于湖广”[11]。迈柱改流之法和鄂尔泰大体相同,“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12]。在具体实施上,湘西及其相邻的鄂西地区,和平式改土归流,“斩首”式迁徙土司到异地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3]5。
在湘鄂西部,自雍正四年(1726)始,桑植、永顺、保靖、东乡等土司相继进行了改流。这些土司中,“有的是呈请纳土,有的是呈请改流,有的是直接‘裁废’,但对宣慰级的土司则主要采取‘拟罪改流’的政治手段”[3]85。在和平改流运动的背后,依然有“军事”、“武力”的威慑。在对容美土司的改流中,清王朝首先通过地方官员连篇累牍地弹劾容美,从外部制造舆论,向土司施压,比如,《容美司改土纪略》中所罗列的土司罪状有,“居设九间五层,坐向子午,私割阉人,妄制炮位,构怨邻司,……”[14];继而,夷陵镇总兵冶大雄调动五营兵丁,向容美领地进发,形成大军压境之势;在军事部署完毕后,迈柱等进一步策应边民叛逃、暴动,并瓦解统治阶级的内部力量;随着末代土司田旻如的自杀,标志着此次改流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接下来,雍正帝对田旻如“妻妾子女父母祖孙兄弟……照例分发陕西、广东、河南三省安插”[14],对土司属下的大小头目亦调离原籍,以免土人情恋故主。这样做是为了防范土司以后东山再起。当容美土司遭到打击而改流后,其他各土司也受到震慑,随即分化瓦解,积极呈请改流。鄂西改土归流对相邻的湖南、四川东南部诸土司的影响很大。他们看到清王朝推行改土归流的决心及执行方针政策的力度,同时也认识到这是大势所趋,乃纷纷申请改流。
清代前期在鄂西等地的顺利改流也成为后期改流的“摹本”。在鄂西土司改土归流约一百八十年后,一场规模更大的改流运动在川边地区执行开来。
德格土司是在赵尔丰的“兵威”下接受改流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德格土司家族内部发生纠纷,昂翁降白仁青在达赖集团的支持下争袭土司职位。赵氏先用武力于宣统元年(1909)六月击败昂翁降白仁青。并使土司自请“改流”。多吉僧格在军事压力之下,“情原将德格全境人民土地纳还朝廷”[15],在没有多大变动的情况下,将德格宣慰司改为徒拥虚名而无实权的世袭花翎二品顶戴都司,年给赡养银三千两,徙居巴塘。改流后的原土司之地分置邓科、石渠、德化、白玉、同普五县。德格土司的改流与康区多数土司类似,主要是以和平手段推进的。不过,清政府对德格土司的改流,虽也采取了迁徙的办法,但地点仍在原土司领地附近,并未从根本上重创其政教统治体系,加之时局动荡,设置的流官所发挥的影响非常有限,这就为后来川边土司的卷土重来埋下了隐患。
两地改流运动的顺利推行,并非预示着一种理想的结果,其后果与影响并未完全达到统治者的初衷。
(四)结果与影响
清王朝对湖广土司的改流,从实质上看,仍然是一种强制同化的民族政策,但这一改革打破了湖广土司据地自封的割据局面[16]。它加强了中央王朝和土家族地区的关系。伴随着改土归流的实施,清政府对土家族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这种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多方面的开发,大大推动了土家族地区的发展,促进了土家族的进步和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17]。因此,总体上看,雍正朝对鄂西地区改流是必要的,且意义深远。然而,当我们从地方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时,这一时期的改流运动尽管顺应了历史潮流,但是在部分区域,改流之后的社会反而比以前更加动荡了。客观而言,改流后当地的社会问题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社会危机、社会动荡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有学者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湘西改土归流前后各220年社会危机全过程分析后得出,非土司时期危机系数比土司时期的大,民国社会秩序比清代社会秩序混乱[13]1。造成这一现象固然有民间组织频繁活动、选官制度受到严重挑战,以及现实政策等方面的原因,但不容否认,土司制度中本身存在着与其社会文化相适应的一套体系。这是因为,鄂西地区土司的兴起,通常是土家族强宗大姓的形成与中央王朝推行土司制度相结合的历史产物。土司多依赖宗姓统治,它在广大土民中形成了一个重要而严密的社会结构,维持着社会秩序。宗族势力和土司的军队、法规等相比,是一种隐性的、有效的统治力量。因此,当土司制及土司宗族被消灭、迁徙后,在流官治理不力的情况下,社会秩序往往会比土司时期更为混乱。清、民国以来鄂西一些地方流管统治下的土司地区实际上比原来更动荡了。
在川边土司的改流中,由于所处时代、地域不同,其影响和意义也大不相同。此次改流的范围广泛,“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18]。它在一定程度上对西藏、康区局势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对抵制帝国主义势力染指西藏事务、打击西藏分裂势力、坚固我国国防和领土主权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川边地区改土归流,以土官取代原来的土司统治,将内地科教理念、生产技术等[19]输入到改流区,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进程,也“奠定了后来西康建省的基础”[20]。
川边与鄂西的改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立足于“兵威”,但不同之处在于:川边土司在赵尔丰的武力打击和胁迫下,虽一度废除,但后来又出现了大批的复辟。民国时期,多吉僧格乘内地混乱,中央政权对康区控制不力之机,于1915年由巴塘返回德格,恢复土制,废除改流设施,仍统治原有领地。当然,在德格土司复辟区,与土司统治机构并存的还有民国政府的县级政权机关,呈现出双重政权局面[21]69。因此,川边的改流较之于鄂西地区更为不彻底。
造成川西土司复辟,继续发挥影响力的因素很多,除去时局的影响、流官统治力量薄弱外,川边土司政权组织的特点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地土司的政治格局具有明显的政教联盟统治的特点。在德格,当地不是把政权与教权合二为一,而是政权支配神权的一种政治与宗教的集合体——“政教联盟”[22]。土司为密切同寺庙的关系,更方便、更直接地利用和控制各教派的寺庙,相继建立了五大家庙,予以重点扶持。土司也赋予上层喇嘛一定的政教特权,如在特殊情况下,遇有重大事件才召开的土司最高级会议,其参加者就有五大寺的活佛。并且,依照惯例,若一时无人承袭土司职位,可由当地威望最高的活佛任摄政。如1942年土司泽汪登病逝,其子乌金夏年仅四岁,八邦寺的司笃活佛即被选为摄政,代行土司职务[23]。这种政教联盟统治的途径,政教双方是互相支持的:寺院在宗教活动中,将土司歌颂为“正义”和“神”的化身;土司则支持寺院的经济收入,和喇嘛的来源。遇有重大事务,双方加强联合,以维护共同的利益,巩固统治[21]65。在川边土司的改流中,土司统治受到削弱、废除,被迁徙他地,但其势力及影响并未受到重创。尤其是与之结成联盟的宗教力量仍在当地发挥着影响,这些家庙的活佛对群众的号召力是巨大的。虽然土司被革去了名号,但宗教领袖无疑是土司家族的忠实代表。这也是川边土司得以复辟,而且仍能发挥影响的重要原因。
三、历史启示
土司制是一种广泛实行于我国西南、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对于锐意推行政治上大一统的封建君王来说,实行这种制度不过是权益之计。于是,分封土司与改土归流这两大主题始终贯穿于土司制发展的脉络之中。
改土归流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同样也存着历史局限性。从清代鄂西、川边地区发生的改流运动来看,二者同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同样实行土司制,然而整个改流过程及影响却大不相同。鄂西的改流是统治者主动实施的一场政治运动,它的推行相对彻底,但结果并未完全实现区域内的长效和平与和谐发展;清末川边的改流是应对国内外时局的被动举措,改流进程相对顺利,但随后土司迅速复辟,并在较长时期内影响着当地的局势,此次改流的结局亦可谓惨淡。两个区域、两次改流存在共同的问题:在军事压力下,仅仅依靠政治手段,而忽略了当地的社会结构及文化基础,改流的成效往往事与愿违。
以史为鉴,鄂川两地的改土归流或可为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当前民族地区政策的制定与推行,不仅要考虑区域、民族间在自然生态、历史条件等方面的区别,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其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等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
[1] 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M].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
[2] 胡挠,刘东海.鄂西土司社会概略[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3] 祝光强,向国平.容美土司概观[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4] 傅崇林.西康建省记—德格改流记[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
[5] 李世愉.试论清雍正王朝改土归流的原因和目的[J].北京大学学报,1984(3):68.
[6] 陈家进.筹瞻奏稿[M].卷上,十一.
[7]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上海:中华书局,1958.
[8] 吴丰培.联豫驻藏奏稿[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49.
[9] 赵尔丰奏议[M].卷三(手抄本).
[10] 赵尔丰函电续编[M].(手抄本).
[11] 清史稿[M].卷二百八十九,列传七十六.
[12] 清史稿[M].列传七十五,鄂尔泰.
[13] 成臻铭.改土归流与社区危机——主要以1505年—1949年湘西土司区危机事件为例[J].怀化学院学报,2005(1).
[14] 毛峻德.容美司改土纪略.鹤峰州志[M].(乾隆本),上卷.
[15] 德格土司纳还全境土地改土归流折[M]//赵尔丰康藏奏议公牍全集:卷十.
[16] 张雄,彭英明.湖广土司制度初探[J].江汉论坛,1982(6):59.
[17] 段超.试论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的开发[J].民族研究,2000(4):95.
[18] 清史稿[M].赵尔丰传.
[19] 徐铭.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初探[J].西藏研究,1982(2):118.
[20] 陈一石.赵尔丰与四川藏区的改土归流[J].四川师院学报,1981(3):83.
[21] 陈贤敏.改土归流与康区社会(下)[J].中国藏学,1988(4).
[22] 杜永彬.德格土司辖区的政教关系及其特点[J].中国藏学,1989(3):95.
[23] 德格地区的农奴制度,四川省甘孜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杨光宗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and Reform Policy between Western Hubei and Sichuan Bordering Areas in Qing Dynasty——A Case Study of Rongmei Tusi and Dege Tusi
YUE Xiao-guo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Three Gorges Area Development,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Yichang 443002,China)
Tusi system is a national policy implemented by the feudalism ruling class in the southwest and northwest minority region,which is a kind of transitional management strategy,thus land reform is the necessity of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Land reform in Qing dynasty was of certain progressive significance,and geographical and national differences existed in its implementation.Comparing land reform in Western Hubei and Sichuan bordering areas which are both minority regions,but their backgrounds and purposes vary a lot.With history as a mirror,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land reform in Hubei and Sichuan can provide some useful inspirations to the current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in national regions.
Western Hubei;Sichuan Edge;land reform;Rongmei Tusi;Dege Tusi
D691.72
A
1004-941(2010)05-0001-05
2010-09-30
岳小国(1976-),男,湖北襄樊人,博士,现主要研究方向为南方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