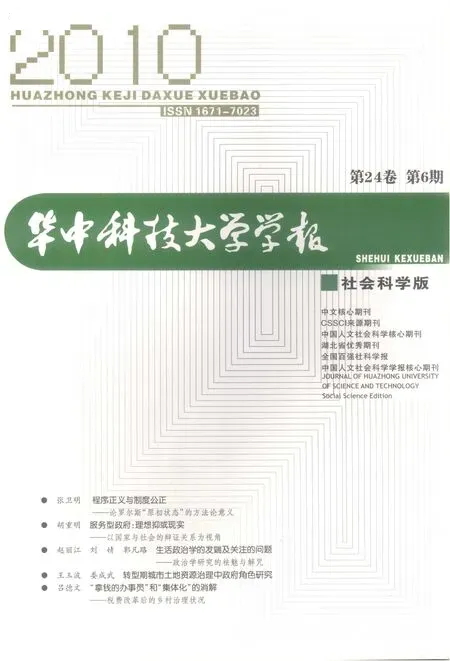罗马诉讼制度的演变与功能——追问实体法之生成史
2010-04-08宋旭明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上海201306
宋旭明,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 ,上海 201306
罗马诉讼制度的演变与功能
——追问实体法之生成史
宋旭明,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 ,上海 201306
罗马诉讼制度伴随着罗马社会发展而经历了法律诉讼、程式诉讼和非常诉讼的历史演变。在程式诉讼时期,为因应社会变革之需,裁判官运用司法自由裁量权,通过创设诉讼程式解决新型纠纷,间接地催生出大量的实体法规范,为后世实体法与程序法分离创造了条件。但是,作为实体法之生成的母体的,并非罗马诉讼制度,而是存在罗马人心中的抽象的实体正义观念,以及他们在个案中对具体的实体正义的追求。
罗马法;诉讼;实体法;程序法
在现代法上,人们习以为常地将法律之整体划分为程序法和实体法两大部分,并且一般认为程序服务于实体,尽管程序也有其独立价值。同时,人们也已经认识到,几乎在每个民族的法律进化过程中,都曾经历过一段诸法合体的早期历史,并且往往是程序法在其间占据着绝对主导性地位。显然,由古而今,各个民族的法的整体构成发生了一个根本性转变,实体法从弱到强,直至取代了程序法的显赫地位。其间的缘由曲折恐难籍一言以蔽之,但又颇具研究价值。本文拟选择人类早期法律的典型代表罗马法,并从最能体现其程序法之作用的诉讼制度出发,就实体法之生成史作一探究,以期有助于对现代法上程序法与实体法之关系诸问题的理解。
一、罗马诉讼制度的演变
罗马人虽然尚未正式发展出如同近现代法那样极受倚重的权利概念,①关于罗马法上是否既已存在权利概念,学界还存在争议。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贯穿罗马法之始终,占据其法律概念金字塔之顶点的,显然不是权利概念,因为这一点直到 16世纪的法国人文主义法学派的法学家胡果·多内鲁斯 (Hugo Donellus)那里才得以实现。Cfr.Orestano.Azione,Diritti Soggettivi,Persone Giuridiche.Bologna,1978.119.Cfr.Luigi Orsi.Pretesa.Enciclopedia del Diritto(ⅩⅩⅩⅤ).Prerogative-Procedimento,Giuffrè&Milano:GiuffrèEditore,1962.364.关于罗马法上是否既已存在权利概念,参见 Brian Tierney,The Idea ofNatural Rights:StudiesonNaturalRights,NaturalLaw and Church Law 1150–1625,EmoryUniversity Studies in Law and Religion 5,Atlanta,Georgia:Scholars,Press,1997,pp.16-17;James H.Huston,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Concept of a Right in America:The Contribution ofMichelVilley,39 Am.J.Juris.185(1994),pp.189-190;方新军:《权利概念的历史》,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 4期;李中原:《Ius和 right的词义变迁:谈两大法系权利概念的历史演进》,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 4期。但是却从来不妨碍他们本着对正义的追求来建构自身的法律救济制度。在近现代法的观念中,权利是先在的,救济手段则不过是权利的程序外衣。但是,诚如英国法学家巴里·尼古拉斯(BarryNicholas)所指出,“罗马法学家的看法并非如此。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更注重于救济手段,而不是权利”。[1]21对于救济的重视,贯穿于整个罗马法之中。随着罗马平民与传统世族贵族之间等级斗争的展开,规范罗马社会的主要依据由罗马人所称道的“先祖礼制 (MosMaiorum)”在《十二表法》制定以后转为罗马共和宪政制度,罗马总体上说进入了法治国家。[2]11与此相应,正如马可·奥勒留在他的敕令中所称,“当你请求获得信任,那么你最好使之在法庭上有效,而不是通过自助的方式。”[3]456换言之,在纠纷解决方面,私力救济也逐渐从主要领域之中退隐,代之以以诉讼为主的公力救济,诉讼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之中肩负救济的功能。①当然,罗马法中的诉讼制度,其目的并不仅仅限于救济,诸如拟诉弃权之类的制度中所规定的诉讼,则是以“救济”之名,行“创设”之实,因为这种诉讼的主要作用在于给付,而不是判决。参见 (英)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黄风,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66.本文所论的“罗马法中的诉”,均不涉及诸此类别,而仅限于具有救济功能的诉讼。特予说明。罗马法对于作为主要救济手段的诉讼的重视,也早可见之于《十二表法》将其前置的体系结构。[4]2-5而在这种制度背景之下,罗马实体法何以反而能够生成并且最终崛起,实值研究。
不过,虽然都是救济,但是在罗马法的不同历史时期,诉讼制度的救济功能却有其不同的表现方式。在笔者看来,这些不同的救济方式又深刻地反映并进一步推动着罗马社会的历史变革,包括其中的法律制度的变革。我们不妨先来对这一演变过程来一番回顾。
罗马法中的诉讼制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法律诉讼 (Legis Actiones)、程式诉讼(Processo per Formulas)和非常诉讼 (Cognitio extra Ordinem)。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诉讼程序有所不同。
早期的法律诉讼被分为两个阶段,即“法律审 (In Iure)”和“裁判审 (Apud Iudicem)”,其中的法律审,任务是在执法官面前确定当事人的身份、争议的事项以及诉讼请求,审查起诉是执法官的职责。而决定执法官是否应当受理的,是法律对于原告所提起的诉讼及其程式是否作了明确规定。凡法律没有规定的,纵然其正当利益受到侵害,执法官也无权受理,反之则不得拒绝受理。[5]932
法律诉讼仅仅适用于法律有规定者,这导致了诉讼相对于不断发展的现实需要的严重滞后。[6]426加之这种诉讼在严格的形式要求下导致“一种无益的风险”[7]95、不实用的繁琐程序等方面的缺陷,法律诉讼“逐渐引起人们的厌恶”②Gai.4.30.[8]302,在经历了《十二表法》时期的广泛存在之后,随着罗马国家司法权力的扩大以及与此相应地公元前 367年专司执法活动的裁判官的创设,③关于这一官职的“创设”及其职权,学界尚有争议,详见陈可风.罗马共和宪政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70-72.它受到了实践中逐渐出现的一种诉讼程序的补充乃至挑战。裁判官“这个新的执法官开始采取越来越直接的行动介入法的制定和适用。他取代法的真正渊源,允许在市民法未规定的情况中提起诉讼;但是,在某些纠纷中,他不把问题提交给审判员,而是撇开既定的制度自己来做决定”。[7]95这一套诉讼程序就是程式诉讼。立法对于诉讼程序的这一司法改革的肯定开始于公元前 2世纪的《阿布兹法 (Lex Aebutia)》,该法规定如果罗马市民约定在发生争议的情况下采用程式诉讼,则对该争议不得适用法律诉讼。[9]49笔者认为,这一规定的意义在于将此前存在的以法律诉讼为主、程式诉讼为辅的实际做法转变成了程式诉讼为主、法律诉讼为辅,从而大大提高了程式诉讼的地位。至公元前 17年,随着《关于私人审判的尤利法(Lex Iulia Iudiciorum Privatorum)》和《关于公共审判的尤利法 (Lex Iulia Iudiciorum Publicorum)》的颁布,除针对潜在损害的诉讼和将进行百人团审判的情况下,法律诉讼被废止,代之以程式诉讼④Gai.4.30;G.ai 4.31.[8]302。
程式诉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裁判官通过审判造法的权力扩大。[9]50裁判官的职能不是去对诉讼进行审判,而是仅限于使诉讼能够按照他告示中的程式加以表述,或者在特殊情况下,为处理新的案件事实提供新的程式。[1]25正如英国学者巴洛 (R·H·Barrow)所称,裁判官由此而“高踞于法律之上。他虽不能废除《十二表法》的现存律条,但可以通过拟定他的告示,通过其日复一日的裁决,来补充它,或者,他可以以矫正性补救方法对其进行修订;法律持续不变,但他可以迂回行事。”[10]230而巴洛在此所谓的“迂回行事”,是指裁判官“可以在认为适当的任何时候,根据某一具体案件的事实,或者根据较为一般的原因,提供新的救济手段。”[1]23而所谓“新的救济手段”,即表现为程式。程式是对诉讼形式的表达,裁判官可以为每个诉讼原因规定一套程式,由于这些程式的结构使它能够很容易地适应任何可由裁判官创造的新诉讼,显然,通过对诉讼形式即程式的创造,裁判官也就创造出了新的具有司法意义的诉讼原因。[1]22更有甚者,裁判官“每年任命一次。由此,只要愿意,他可以方便地承袭其前任的告示;但他也可以一上任就修改它,也可以在其任期内扩充或修改它。它存在于一个持续成长的国家之中,它生气勃勃:‘告示法是民法的充满活力的喉舌 (Viva vox)’。鲜活的思想不断作用其间。”[10]230-231因此,裁判官形式上只是在创设救济手段,实质上是在制定法。[1]27
“程式诉讼程序持续存在于罗马法学的整个古典时期,然而,‘以非常方式 (extra ordinem)’裁决纠纷的习惯 (即不再把案件交审判员处理),在帝国时期越来越成为常事。”[7]97这种诉讼开始仅实施于新征服的领地,后来也实施于罗马城内。及至优士丁尼主政,他宣称,在他的时代,所有的审判均为非常审判。①I.4.15.8;D.3.5.46(47).1.[7]97而所谓非常诉讼的“非常”之处,主要是指罗马国家司法权力的进一步扩大,表现在,一是取消了盛行于法律诉讼和程式诉讼时期的法律审和裁判审的阶段划分,整个诉讼活动统由公职的执法官主持,而不再将裁判审付诸私人审判;二是司法裁决不再是对有关诉讼请求的简单肯定或否定,而是由执法官根据公平原则比较具体地确定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三是判决的强制执行交由专门的机构负责。[9]62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执法官造法的权力也同样扩大,相反,随着公元 130年哈德良 (Publius Aelius Traianus Hadrianus)皇帝委托尤里安编辑修订的《永久告示(Edictum Perpetuum)》的颁布,执法官的衡平立法权被剥夺,自由裁量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11]228这一改变尽管由于法律渊源的多元化而不至于导致罗马法从此陷入僵化,[11]228但是裁判官法作为法渊源的生涯至此结束,它能得到发展的途径仅剩下法学家对《永久告示》的字面解释或者皇帝给予新的“裁判官法”以救济手段。[1]24
从罗马诉讼制度的演变可以看出,“形式”在诉讼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法律诉讼”又称“严法诉讼”,正是以其严格的法律形式而著称的,这种形式上的严格,不仅仅体现在诉讼必须有明确的程式规定才能受理,甚至还体现在今天看来纯属私法关系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商品交易上,要式买卖和拟诉弃权正是在那个时期大行其道。至于其间的实体正义,则如同普罗透斯的脸一样难以捉摸,远非程序那样易于把握,以人类当时的智识水平,通过主要将其委诸神明,求得一个绝大多数人皆能接受的结果,从而实现定纷止争的目的,无疑是一个合乎时宜的选择。正如德国法学家耶林所指出,从我们今天法律的角度来看,或许会对此类神明裁判的时代提出谴责,然而这些制度在它们各自所处的时代里,也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对那些时代而言,它不仅仅是必要之恶,更是正当合法的、最佳的途径,就好像春天的蓓蕾与花苞,在结出果实之前,必须先有它们的出现。[12]151不过,随着人类社会理性的不断发育成长和对正义的不懈追求,人们对于实体正义及其表现在法律领域中的实体法律关系越来越重视,以至发展出了罗马法学家这种职业法学家阶层,并由这一阶层发展出了日成系统、日见规模的“对神和人的事务的认识,关于正义和不正义的科学”②I.1.1.1.[13]11——法学,而法律诉讼时期那种初民社会的调整手段必将因其日益显示出时代局限性而终遭扬弃,通过裁判官之手对诉讼程式加以扩充成为这种发展趋势的结果。尽管在后来的非常诉讼时期,裁判官造法的权力受到极大的限制,但是,抛弃自由裁量,回到严格规则,这种肇因于伟大皇帝的过度自信的做法,后来终究为历史证明是行之不远的。[11]233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在罗马诉讼制度演变的三个历史阶段,最合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从而使其实质功能远远超出了诉讼本身,乃至最终催生了实体法并奠定后世实体法与程序法分离之基础的,是程式诉讼。
二、罗马程式诉讼的功能
实际上,罗马程式诉讼的特殊性,早已为法学家们所认识。颇具代表性的说法是,“如果不对程式诉讼至少作一番大概的了解,是难以解释诉讼的;诉讼的问题很大程度地受到了它的影响。”[14]212而我们在这里所要进一步考察的罗马程式诉讼的功能,指的自然不是诉讼本身具有的定纷止争功能,而是其对实体法催生功能。而程式诉讼之所以具备这一功能,得益于当时的裁判官制度。正如德国学者乔治亚德斯(Apostolos Georgiades)所称,“古典罗马法中的诉的核心意义应当首先从程式诉讼中裁判官的地位中得到理解。”[15]25
具体说来,在程式诉讼时期,Actio在发挥其救济功能方面,表现出了较法律诉讼和非常诉讼远为突出的灵活性,即通过裁判官的造法来实现救济功能。每一种新的程式表达着一个新的诉讼类型,而每一种新的诉讼类型又在表达着一个新的诉讼原因。而程式与诉讼原因之间的关系,从后世的观念来看,正是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关系。每一个新型的 Actio,所创造的不只是程序法,无疑同时也内含着实体法,因为它们直接指向的,并非审判,而是实体上的“应得之物”。这是因为,罗马法学家杰尔苏(Celsus)明确将Actio界定为“通过审判要求获得自己应得之物的权利”,①D.44.7.51.(意)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黄风,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85.英文版译文可参见:TheodorMommsen&Paul.The Digest of Justinian(Ⅳ).Translated byAlanWatson.Pennsylvan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5;http://www.constitution.org/sps/sps10.htm,2008-8-17.AdolfBerger.EncyclopedicDictionary of Roman Law.Transactions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New Ser.,Vol.43,No.2,1953.341;E·Metzger.A Companion to Justinian’s Institutes.London&New York:Duckworth&CornellU-niversity Press,1998.209.并且这一定义被优士丁尼(Iustiniani)皇帝几乎直接照搬进了他的《法学阶梯》。②I.4.6pr.[13]455尽管人们对其属概念 Ius本质上是否应当理解为权利尚存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应得之物”是 Actio所指向的目的,而审判只是获得这一利益的手段。因此,这里的Actio针对的是实体意义上的“应得之物”。当然,审判即便是作为获得应得之物的手段而存在,其本身也可以是一种利益,因此针对审判这种利益,用现代法学术语来说,仍可成立我们今日所称的“诉权”,由于它所针对的是“人们意图借以证明自己权利的存在的诉讼程序”,[7]85这在我国被称作“程序意义上的诉权”。但是,就罗马法中的Actio而言,审判仍然只是被当作获得应得之物的手段,被当作一种服务于应得之物这一核心目的的手段性利益,故而该 Actio实质上乃是针对实体利益,套用我国学界的说法,罗马法中 Actio概念的本质,乃是一种“实体意义上的诉”。退一步说,即便我们不对审判的利益和应得之物的利益在相互关系上作手段与目的的区分,而如同我国一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将二者的重要性等同视之,仍不妨碍我们根据前述Actio的定义认为,要求获得应得之物,至少是罗马法中的诉的部分内容。正是这种“实体意义”的存在,使裁判官在创造出一个一个的Actio程式的同时,也创造出一个一个的实体法律。
而更加重要的是,如果在一个制度中,法律实质性部分每年都在变化,这个制度显然将是难以操作的,因此,理论上说每一任裁判官告示均独立于前任,但实际上它们的主体部分却逐年延续了下来。[1]22-23这就使得程式的数量越积越丰富,最终使得在尤里安《永久告示》颁布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尽管禁止裁判官造法也基本上足以满足现实的需要成为可能。不过,当包括《永久告示》在内的各种法律的内容多到让人们在使用之时感到吃力时,面对着经由数百年发展而形成的纷繁芜杂的罗马法之整体,如何更高效率地在法律教学中讲述法律和在法律适用中寻找法律,开始成为考验罗马法学家们的智商的一个现实问题。人们需要找到一种更为科学的方式来组织法律,并且逐渐发现,“介绍法律的一个更加深思熟虑的方式是将相似的规则集中到一起,从整体上考虑每一个规则的实质性成分——‘谁’以及‘什么’。这将让人们更好地将给定的一系列事实划分为一种特别类型的法律事件。”[14]215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根本的实体性观念更加频繁地被作为区分于程序的主题得到讨论和表达,这样就产生了更为精细的分类方法。”[14]215盖尤斯的人、物、讼三分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应运而生,并最终被优士丁尼《法学阶梯》所采纳,程序法与实体法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划分,尽管这种划分在技术上还远远谈不上成熟。并且,正如梅因 (H·S·Maine)所认为的,法律规则的早期、粗糙的分类和现代、精致的分类的基本区别在于,后者涉及诉讼程序的规则被降到从属的地位,并且变成如边沁 (Jeremy Bentham)所称呼它们的程序法。就此而言,罗马法的设计者们正是如是提出的,因为他们将诉讼法放在了体系的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一个部分。这不是一个容易而自然地浮现在脑海里的安排。因为,在司法的幼年时期,诉讼法的优势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实体法一开始呈现出被逐渐隐藏于司法的缝隙之中的样子;而早期的法律家们也只能通过法律的技术形式外观来看待法律。[16]389由此也可以说,从《十二表法》时期到优士丁尼时期,罗马法从幼年时期走到了壮年时期。①不过,也存在与梅因不同的看法,如艾伦·沃森即坚持认为,罗马法甚至早在《十二表法》中即谨慎地将实体法与程序分离开来了。See AlanWatson.The Law ofAc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bstantive Law in the Early Roman Republic.LQR,1973,(89):387-92.而其间最大程度地推动了罗马法迅猛成长的,正属罗马的程式诉讼制度。当我们承认从《永久告示》到《国法大全》之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各个年度的裁判官告示之间某种实质内容的延续性时,并从《国法大全》中发现“裁判官的告示也拥有不小的法律权威”②I.1.2.7.[13]19时,我们怎么能够抹杀当年裁判官所创设的各种诉讼程式对于后来在《法学阶梯》中占据大半壁江山的实体性规定的催生作用呢?同时,跟随着作为一个整体的实体法之生成接踵而至的,是它与诉讼法的关系问题。从罗马法史来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诱发了此后诉讼法在罗马法上的地位的深刻变化。实际上,“后古典时代的诉讼体系已经失去了它的初始含义”,[15]25因为,正如德国学者卡塞尔·马科斯(KaserMax)所指出,“诉讼请求的原理从此以后建立在实体法律规定之上,而不再建立在一个适当的诉的存在之上。原告必须向法院提出他的请求,而不需要指明一个特定的诉讼程式。”[17]171因此,有学者称“诉讼法很大程度上具有将实体法与程序法逐渐分开的功能”,[14]215可见是颇资赞同的。
不过,笔者同时要说的是,对于罗马法上诉讼法对实体法乃至整个法律体系之形成的意义,也不宜被过分夸大,应当有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前述古罗马诉讼法对于实体法之生成的重要影响,曾被一些诉讼法学者作为论证诉讼法先在于实体法的一个极为仰赖的依据。例如,日本诉讼法学家谷口安平即有“诉讼法乃实体法发展之母体”的著名论断,他以古代英国法和罗马法为例,认为在这些法的发展初期,为了对付由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的事态,不断有新的诉讼程式、诉被追加进来,是最终促成实体法生成的根本原因,因此并非先有实体法,而是先有诉讼法。[18]69甚至他并不将这一论断局限于古代法,认为这不仅是久远的过去时代的事实,作为新的实体法或新的权利形成的母体,诉讼以及诉讼法的创造性功能在今天仍然不会丧失,只是变得不可视了而已,例如法院通过判决认可日照权的存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8]69
然而,笔者认为,不必说实体法发达如斯的今天,即便是在古代罗马法上,也难谓诉讼法作为母体而对实体法具有孕育作用。理由是多方面的。一方面,诉讼以实现实体正义为最终目的。诉讼缘于纠纷,而纠纷归根结底缘于诉争双方对一定的实体利益的争夺。很明显,诉讼的最终目的就在于通过解决纠纷,在当事人之间恢复和确保和平秩序,并且最终实现实体正义。虽有“迟到的正义非正义”一语强调程序的重要性,但此语强调程序的同时须臾没有离开实体,反而更进一步说明了程序的设置应当以尽可能实现实体正义为宗旨。因此,罗马裁判官每创设出一个新的诉讼程式之前,实际上已经基于他对案件中的实体正义问题作出了一个初步的基本的判断;而当诉讼程序启动之时,在裁判官心中也既已存在一个应当由他去加以探究的实体正义,而正当程序的作用仅在于帮助他尽可能地去发现和接近实体正义。因此,与其说裁判官的判决是在创造实体正义,不如说是在寻找和确认实体正义,孰先孰后,不言而喻。另一方面,实体权利的创设从根本上来说缘于实体正义而非诉讼。以谷口安平所举日照权的创设为例,该实体权利固然是通过诉讼程序创设出来的,但就此启动诉讼程序,只是在“提出问题”,并且根据公认的起诉权法理,针对这一程序之启动所设立的审查,仅限于程序性审查,不及于实体性审查。换言之,任何自认为有正当利益受到侵害的法律主体,具备法律规定的程序要件,均可以提起诉讼,至于诉讼请求是否得到支持,就起诉阶段而言在所不问。然而,对实体法之发展作出关键性贡献的,恰不在于诉讼被提起,而在于诉讼请求在法官的裁判中得到支持,正如“日照权”被裁判确认为受法律保护。而法官对基于案中实体法律关系是否应当支持这一诉求的的“分析问题”阶段,以及最终决定创设日照权以支持诉求的“解决问题”阶段,程序可谓全无作为,因为在实体法无具体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判决的实体内容所依据的,是实体法上的诸如“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如果还要进一步追问这些基本原则的依据,那就是基于伦理价值判断的实体正义了。有鉴于此此,笔者认为,裁判官创设的一套套程式以及根据这些程式所作的一项项判决,固然同时间接地逐个创设出了一条条实体法律规定,并最终催生出了堪与程序法并驾齐驱的整体意义上的实体法,但起到的只是一个“导火索”的作用。真正导致实体法与程序法如同“炸弹”“爆炸”一般分离的,是实体正义这一“炸药”。如若谓之罗马诉讼制度具有实体法的孕育功能,则是言过其实的。
三、结论
罗马诉讼制度的演变,既是罗马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又构成了这一进程的组成部分。在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的时期,诉讼制度也随之稳定,司法的严格规则主义大行其道,这正是法律诉讼和非常诉讼曾在罗马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盛行的原因,尽管非常诉讼与法律诉讼相比诉讼制度仍有着极大的差异。相反,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之中,由于新鲜事物不断出现,司法的自由裁量主义成为解决立法滞后问题的必要手段,这就是裁判官制度逐渐形成于罗马政制由共和转向帝政的时期的原因。裁判官在此过程中所彰显的自由裁量主义的优势,至今为人们所认可,甚至被明文写进了现代民法典。①《瑞士民法典》第 1条第 2、3款规定,“如本法没有可以适用的规定,法官应依据习惯法裁判,无习惯法时,应依据其作为立法者所提出的规则裁判;在前款之情形,法官应遵循公认的学理和惯例。”更为重要的是,裁判官藉由对他们所促成的程式诉讼制度的实施运用,催生出了大量的实体法规范,为后世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区分奠定了基础。
罗马诉讼制度的演变,尤其是从其中的程式诉讼中引发出程序法和实体法分离的结果,对于我们今天理解程序法和实体法之关系非常重要。我国数千年来深受儒家人性本善思想的影响,在由此形成的中华法系中,习惯于仰赖圣君贤相以其高尚的品德来在个案之中主持公道,实现正义的结果。至于法律程序,并不严格要求,调查取证甚至也可以不择手段,由此而形成了重视实体正义而轻视程序正义的法律文化。然而,这种做法已经被证明对人性本质的期待过高,极易导致公权力的滥用和对私权利的侵害。时至今日,虽然中华法系已经在我国被废弃,但其所根植其中的法律文化的重构却不是一朝一夕即可完成的。在此过程中,在法律意识上提高程序法之重要性的认识,在法律制度上优化程序设计并加重程序违法的处罚力度,尤其是在这个新生事物不断涌现的时代善用程序法对实体法发展的积极意义,是罗马诉讼制度给我们的最大启发。
不过话说回来,“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的论点,却在将我们从“程序工具论”的长期禁锢之下解放出来的同时,矫枉过正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实际上我们也应当清楚地看到,罗马诉讼制度并非孕育实体法的母体,罗马裁判官允许程式诉讼赋予给他们的能动司法权“造法”,首先还是在于现实生活呼唤对一些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利益进行保护。罗马诉讼制度从法律诉讼走向程式诉讼,也是这一发展趋势在制度保障方面的必然要求。所以说,是先有了个案当中对实体正义的追求,才有了裁判官运用程式对该实体正义的落实,进而将此类体现实体正义的裁判原理抽象而为实体法。因此,实体法的生成,最终应当归结于既存在罗马人心中的抽象的实体正义观念,以及他们在个案中对具体的实体正义的追求。这一点不仅适用于罗马法,也完全可以解释现代法上的程序法与实体法之关系。程序正义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法律价值,并被认为具有独立的意义,但这种独立意义主要在于对尊重人权、限制公权的宣示意义。程序正义之所以重要,更多地是因为它必将影响到实体正义,倘若不是如此,人们也不会如此孜孜不倦地进行强调。实体正义的实现有赖于良性的实体法,而实体法,其实施全然仰赖于程序法,而其生成和发展也在相当程度上如此。“谦卑的实体法目的论”,或许是对笔者在程序法与实体法之关系问题上的观点的恰当概括。
[1](英)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黄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2]陈可风:《罗马共和宪政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3]Affolter.Die celsinische Actio und der Anspruch des buergerlichen Gesetzbuchs.ZZP,1901,(31).
[4]徐国栋、阿尔多 ·贝特鲁奇:《 <十二表法 >新译本》,纪蔚民译,载《河北法学》2005年第 11期。
[5]周枏:《罗马法原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年版。
[6]丘汉平:《罗马法》,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年版。
[7](意)彼德罗 ·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出版社 1992年版。
[8]盖尤斯:《法学阶梯》,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9]黄风:《罗马私法导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英)R·H·巴洛:《罗马人 》,黄滔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11]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以诚实信用原则的法理分析为中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12](德)冯·耶林:《法学是一门科学吗》,李君韬译,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 2期。
[13]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徐国栋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14]E·Metzger.A Com panion to Justinian’s Institutes.London&New York:Duckworth&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
[15]Apostolos Georgiades.D ie Anspruchskonkurrenzim Zivilrecht und Zivilprozeвrecht.München: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1967.
[16]H·S·Maine.D issertations on Early Law and Custom.London:Henry Holt and Company,1883.389.
[17]Kaser·Max.Das r¨om ische Zivilprozeвrecht.Müchen: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1966.
[18](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The Evolvement and Function of Roman L itigation System——An Exploration to the History of Substantive Law’s Confor mation
SONG Xu-Ming
(Law school of ShanghaiMaritime University,Shanghai201306,China)
The roman litigation system had experienced the historical evolvement of legis actiones,processo per formulas and cognitio extra ordinem following its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period of processo per formulas,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cessarity of social reforms,the praeturs created for mulas to resolve the new-borned disputes according to using their discretion,indirectly brought about many substantive legal norms,and framed the conditions of the subsequent separation of substantive law and procedure law.However,it is not the roman litigation system but the idea of abstractive substantive justice of romans and their chase to the concrete substantive justice in individual cases,that had been the matrix of substantive law.
roman law;litigation;substantive law;procedure law
(1978-),男,湖南长沙人,法学博士,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罗马法、民商法。
教育部人事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YJC820072);上海海事大学校基金项目 (02009187)
2009-12-01
DF971
A
1671-7023(2010)06-0056-07
责任编辑 吴兰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