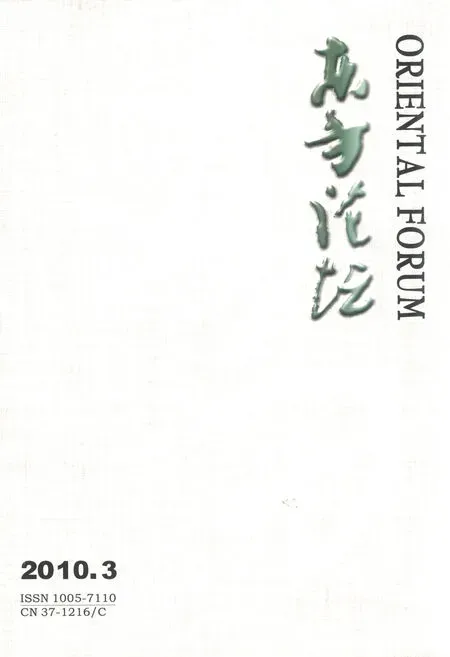塑造自我文化形象
——中国对外翻译现象研究
2010-04-05马士奎
马士奎
(中央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1)
塑造自我文化形象
——中国对外翻译现象研究
马士奎
(中央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1)
对外翻译行为的主要意图是在异文化中塑造出本文化的自我形象。这种翻译形式在大多数国家都得不到重视。但在中国,较长时间内,对外翻译一直是文化输出和对外宣传的重要手段。
翻译;对外翻译;异文化形象;自我文化形象
一、引言
人们常常会忽略翻译的方向问题,想当然地将其看作单一由外语到母语的行为。实际上,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信息转换,这种传递并非是单向的。就方向而言,翻译的形式有三种,可以由外语或非惯用语言到母语或惯用语言,也可以是由母语或惯用语言到外语或非惯用语言,而对掌握两种或数种外语的译者来说,其所从事的翻译也可以是由一种外语到另一种外语。
对外翻译是一种文化的自我协调行为。当某一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出现明显入超,翻译不平衡现象达到比较严重的程度时,自然会采取一些措施,去影响并且进入异文化,以图消解所存在的逆差,达到或接近翻译和文化交流的相对平衡状态。
对外翻译与一般翻译是方向相反而又相呼应的两种文化交流行为,通常都以服务翻译行为所发生的社会为目的。一般翻译可以在本文化中塑造出异文化形象,对外翻译则致力于在异文化中塑造出本文化的自我形象。
二、对外翻译与自我文化形象的塑造
对外翻译是指由译者所从事的将本文化作品译入其他语言的翻译活动,亦即从母语或惯用语言到外语或非惯用语言的翻译,以异文化的读者为主要对象。一般情况下,人们对母语和外语的掌握程度是不对称的,作为非母语写作形式的对外翻译常常被视作非典型的翻译,其可靠性、合理性和存在的意义受到许多人的怀疑,因而在大多数地区都得不到重视。早在18世纪,赫德尔(Johan Gottlieb Herder,1744-1803)即认为这种翻译现象不值得考虑。当代法国学者拉德米劳(J. Ladmiral)也认为对外翻译只适于充当语言教学中的一种练习手段;如果作为职业,这种要求是荒唐的,也是无法完成的任务。[1](P64)英国学者纽马克(Peter Newmark)也认为“只有在译入惯用语言时才有可能译得自然、准确,取得最令人满意的效果”。[2](P3)1976年发布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通过法律保护译者和译作权利及提高译者地位的建议(《内罗毕宣言》)也指出:“译者应尽可能将作品译入其母语或其有同等程度掌握的语言”。[1](P64)
在世界各地,绝大多数人都主张翻译作为一种职业只能是单向的,对外翻译方式则得不到重视。像英语在当今世界上处于国际语言的地位,英美文化的影响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入其他文化;而有些国家虽有这种需求,但受制于对外翻译人才匮乏等因素而难以实现。由于对外翻译的特殊性质,在世界范围内,这种方向的翻译难以成为翻译活动的主流;同样,在翻译研究领域,对外翻译现象向来难以进入人们的视野。
但对外翻译行为毕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根据Margret Grindrod在1985年所做的一项调查,在英国,有百分之八十四的译者单纯从事译入母语的翻译活动,在整个欧洲,这一比例为百分之六十五,在德国则为百分之三十五。[3](P9-10)这说明实际上有相当数量的译者在从事与一般翻译方向相逆的活动,只不过这种翻译现象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进入20世纪后,英语逐渐成为国际性语言,随着英语在全球的迅速普及,许多非英语地区人士的英语水平达到相当的程度,同时,各国又有被外界特别是英语世界了解的要求,在英语本土译者不足的情况下,非英语国家对外翻译现象的存在也就顺理成章。对外翻译在个别地区比较普遍,尤其在芬兰等少数国家,从事“对外翻译”的翻译家甚至占大多数。[1](P65-66)
对外翻译现象自有其存在的理由。主要原因在于各文化和语言地位的不平等、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局限以及由此产生的翻译不平衡现象等。如果两种文化和语言处于大致平等的地位,两种文化之间素有渊源,彼此关系比较密切,双向互动频繁,可以轻易在对方找到译者,如英法或英德之间等,对这种翻译的依赖性便不明显。就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文化而言,异文化中掌握其语言的人不多,其作品缺少被翻译的传统,对外翻译的重要性便会凸显出来。对外翻译是对现实中“翻译不平衡”现象的一种弥补。
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对外翻译的需要和依赖程度也各不相同。如果某一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在一段时间内难以为外界所接受,处于相对孤立的局面,对该文化来说,对外翻译的意义往往更显突出。例如,前苏联、中国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都设有专门的对外翻译出版机构,①和中国的“外文出版社”一样,苏、朝等国对外出版机构也先后出版了多种本国文学作品的英语等译本,尤其是相当数量的苏联文学名著都通过本国翻译家和出版机构之手进入西方社会。如朝鲜“外国文出版社”(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曾出版了“The Fate of a Self-defence Corps Man :Revolutionary Opera Based on the Immortal Classic Play of the Same Title”(1976)等文学作品,苏联的外文出版社更是对外翻译出版了大量本国文学作品的英语等译本,如《静静的顿河》(And Quiet Flows the Don)、《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等。担负面向国外尤其是英语世界的宣传任务,苏、中两国还曾分别创办以英、法等语言出版的《苏联文学》和《中国文学》刊物,作为对外介绍本国文学状况的主要窗口。
对外翻译的主要功能在于主动向外界传递本文化的信息,是原文化在目的语文化中有意识的渗透。译者将本文化中的部分作品译介到异文化中,作为本文化的代表,充当其参照,试图使目的语读者据此形成对原作、原语文化和原语社会的印象。因此这种翻译过程也是在异文化中塑造本国文化“自我形象”的过程。对外翻译时常承载着原语社会的某种期望。翻译主体有时还希望译作在目的语社会中起到示范作用,并试图使目的语社会发生自己所期待的某种改变。同一般翻译相比,对外翻译往往具有更强的政治功利性。
与一般方向的翻译相比,脱离目的语文化背景的译者在对外翻译中遇到的困难无疑会更多。通常情况下,人们对外语的掌握和运用能力都低于母语,其表达效果往往会与译者设定的目标有更大偏差。同时,对外翻译的目的能否实现还要取决于其他诸多不确定因素。只有译者的选题原则及文本处理策略与目的语读者的取向相符时,译作才会在异文化中得到积极反应。而实际上对外翻译常常与目的语文化的需求相脱节,译者常对异文化读者的审美情趣和阅读习惯缺乏足够考虑,原语文化的意图与目的语文化的需求之间往往难以协调。虽然有些作品的对外翻译是为了迎合目的语社会某些读者的要求,但更多情况下译作都是强加于异文化读者之上。这些通过对外翻译方式进入异文化的作品相对更难以在目的语社会引起共鸣。
但对外翻译方式也自有其优势。翻译主体在选择文本时可以有更大的余地;而且由于译者与原作者处在同一文化环境中,可以比较充分地把握原作,对当代作品来说甚至可以通过译者和作者及相关人员或机构之间的直接沟通来避免或减少理解上的误差,以保证信息传达的可靠性;对外翻译多是典型的以原语文化为出发点的翻译(source-oriented translation),将本文化的声音通过译作传递到其他文化中,可以更充分地体现本社会官方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意愿。
对外翻译过程也是对本文化进行自我过滤的过程。翻译主体可以从本文化的价值观出发去选择和处理文本,尽可能避免有损原语文化形象的内容流传出去。如上世纪50年代后期巴金名著《家》的英译本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时,译作与原著面貌有了很大差异,为了对外宣传的需要,一些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内容都给删去,包括书中人物随地吐痰、缠小脚等细节;[4](P17)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无双传》中有关报应的内容也被删略。②在Joseph S. M. Lau看来,当时的当权者决定删除有关报应等方面的内容,不是担心外国读者脆弱的神经,而是为了保全中国的面子。(It is not the concern for foreigners’ fragile nerves but the need to preserve China’s “face” that must have dictated the cut by the authorities.)Joseph S. M. Lau, “More Than Putting Things Together the Anthologization of Chinses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Ed. Eugene Eoyang, and Lin Yao-fu. pp225-226.这种翻译可以尽量避免或减少翻译过程中对本国文化形象的歪曲,以使异国读者获得的对原语文化的印象更接近主流意识形态的期望。这对异文化的译者和出版机构来说一般是难以做到的。
对外翻译的过程常常也是对本文化进行自我包装和自我修饰的过程。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翻译也是对异文化中既往翻译行为和既有翻译文本的修正,因而也是对目的语社会中业已形成的本文化形象的匡正和改善。有些作品在异文化中已存在译本,但如果翻译文本不符合原语文化的要求,对外翻译依然具有必要性。韩国首都中文译名的变迁即是一例。韩国方面主动将沿用多年的中文译名从汉城改为首尔,并提请中方使用,这主要是因为在许多韩国人看来,原中文译名容易让人联想到汉人、汉族,不适合用来称呼其国都,也会影响其在中国的形象。异文化中缺少译本并非对外翻译行为存在的惟一前提。
三、对外翻译与中国形象
中国的对外翻译即是指由中国本土译者(也包括以“外国专家”身份久居中国的外籍人士)所从事的将本国作品译成各种外语的翻译活动,而且译作也主要由国内相关机构对外出版发行。这种翻译常常与其他文化输出手段,如文化团体出访、对外广播等一起,致力于在异文化环境中塑造出中国文化的形象,增进外界对中国的了解,并试图通过译作影响外国人的“中国观”;同时,这种翻译也常常承载着向世界推广本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使命。
与其在西方所处的尴尬地位形成鲜明的对比,较长时间内,对外翻译在中国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这在国际翻译界也属罕见。零星的对外翻译现象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唐朝玄奘曾将《道德经》等著作译入梵文;清末民初亦曾出现辜鸿铭、苏曼殊等外译汉语著作的名家;到民国时期,对外翻译更进一步,译作包括《三国志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老残游记》、《镜花缘》等经典著作;①马祖毅,任荣珍的《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对此有详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对外翻译的重视程度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负责对外宣传报道和出版工作的外文局与新中国在同一天成立,[5]外文出版社的成立和英文版《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杂志的创刊标志着有组织的对外翻译出版工作步入正轨,对外翻译从此成为整个翻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翻译活动陷入空前低潮的“文革”时期,对外翻译仍然保持一定规模;“文革”结束后,外译作品的数量和对外传播的途径都远远超过了以往。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外交流日益密切,异文化中通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国外译者翻译中国作品的数量不断增加,但这一数量与中国的地位远不相称。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对外翻译仍将在一定规模上存在。
中国学者文人素有对外译介本国文学作品的传统,这是国际翻译界一道颇为独特的风景。勒菲弗尔等外国学者也曾注意到这一现象:
过去中国学者曾不屈不挠地把本国文学作品译成英语,有些还译成其他西方语言。世界上较少有人自豪地将作品译入其他语言,中国人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突出。[6](P70)
一段时间以来,对外翻译在中国始终以一定规模存在,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与外界特别是与西方各国之间“翻译不平衡”现象的存在。汉语言文字与西方各语言差异巨大,西方人学习汉语的难度远大于另一种西方语言。西方翻译中国典籍的历史虽然比较悠久,如《赵氏孤儿》和《好逑传》等作品早在18世纪就被译入英法等语言并且引起轰动,但从总体上说,西方翻译中国作品的数量有限。近代以来,各类作品的“入超”在中国始终是一个突出现象。据统计,上世纪80年代前期,在全球所出版的翻译作品中,译自中文的作品每年只有100余种,排在前10名之外,列日语和阿拉伯语之后。[7](P14)对外翻译是减少这种翻译“逆差”的一种重要手段。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拿来主义”占上风的情况下,始终有一些人致力于通过对外翻译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化,这常常也是中国文人学者文化责任感和文化自省意识的表现。辜鸿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将部分儒家经典作品译成英语,其翻译《中庸》一书的目的是使欧洲人“更好地理解‘道’,形成一种更明白更深刻的责任感”,并且在对待中国和中国人时“抛弃那种欧洲‘枪炮’和‘暴力’文明的态度,代之以道”;[8](P513)他还希望通过《论语》一书使“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英国人”读后“能引起对中国人现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对于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9](P346-347)老舍向来重视对外译介本国文学作品特别是当代文学作品的意义,认为“一部小说与一部剧本的介绍,其效果实不亚于一篇政治论文”,而将国内新创作的话剧介绍给美国“一定会比宋瓷、康熙瓷瓶更有价值”。[10](P213)当代著名学人季羡林一向强调中国传统文化西渐对世界文化的意义,认为在当今背景下大力张扬“送出主义”是必要的。①季羡林先生曾多次阐述中国文化的“送出”在当今世界的意义。见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第5页;《东学西渐与东化》,《东方论坛》,2004 年第5期,第1页。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将对外翻译视作“中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对世界文化应尽的责任”,认为有必要把“把一部分中国文化的血液,灌输到世界文化中去,使世界文化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光辉灿烂”。[11]对外翻译的从事者和倡导者都希望以此扩大中国文化在国外的影响。
中国在不同时期都有一批兼具很高本族文化修养和外语水平的翻译人才,尤其在建国后更是出现了一大批专事对外翻译或以其为主业的著名翻译家, 这在国际翻译界是不多见的,也是对外翻译得以开展的前提。同时,就对外翻译方式而言,集体翻译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常常需要各种背景人士的参与,这在举国体制下的中国更具可行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对外翻译也是对异文化中相关翻译行为的纠正和补充。由于文化观念和审美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中西方对中国文学作品有不同的评价和选择标准,异文化译者所选择的中国作品常常并不能代表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如《好俅传》这部才子佳人小说在中国古典作品中并不非常突出,但在相当时间内在欧洲被广泛看作中国最好的小说;另外,西方译者往往对中国古代经典作品情有独钟,对现当代作品则普遍缺少兴趣。萧乾曾在上世纪30年代向欧美读者译介部分中国现代作品,主要动因即在于“现代作品出关难”的局面。②参见符家钦的《记萧乾》,第13页,时事出版社,1996年出版;萧乾的《未带地图的旅人》,第331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在当代中国,虽然莫言、余华等作家拥有较多的国外读者,但大多数作家作品难以为西方所了解。为使世人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需要由中国本土译者将更多真正有代表性尤其是反映中国社会新貌但却为外界所忽视的作品推介出去。
中外之间的文化误读和异文化中既有中国作品译本的缺陷也是对外翻译行为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汉语言文字自身的特点及西方译者对中国文化和语言把握能力的欠缺,中国作品西译的难度远甚于其他西文作品,再加上相当一段时间内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在通过翻译等手段塑造对方文化的形象时常出现有意或无意的误解甚至歪曲。《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英译本的出版即是一例。建国初期由国内译者翻译(经英籍专家润色)的《毛选》(第一至四卷)英文版最早由英国一家出版社出版。由于双方观点差异,尤其是英共对暴力革命持反对态度,英方出版社对《毛泽东选集》中的敏感内容作了删节,毛泽东著作中的一些核心内容在译作出版时被删去。这也是1960年代国内组织精干力量对毛选英译本重新修订并且由国内的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重要原因之一。③著名翻译家程镇球先生在接受本文作者访谈时曾作如是介绍。另外,程镇球先生在《翻译问题探索——毛选英译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等著述中亦曾提及修订《毛选》的背景。辜鸿铭翻译《论语》等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理雅格翻译此作品时“文学训练还很不足,完全缺乏评判能力和文学感知力”,其“在译著中所展示的中国人之智识和道德装备”会使英国人产生“稀奇古怪的感觉”。[9](P345)老舍旅居美国时目睹自己的作品在外国译者笔下面目全非,愤而自己动手将《四世同堂》、《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译成英语(与他人合作)。④美国人伊文•金在翻译《骆驼祥子》即曾擅作改动,为作品设计了大团圆的结局,书名则采用了包含种族歧视意味的“Rickshaw Boy”。后来此人在翻译《离婚》一书时,更是率性发挥,在许多方面偏离原作,结尾尤其与原著完全不同,而且置老舍笔名的英译名“Lau Shaw”和“Lao Sheh”不用,意译为“Venerable House”,令老舍大为震怒。参阅老舍的《老舍自传》第213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因此,中国的对外翻译与外国译者塑造中国形象的翻译行为可以并行不悖,是对异文化中翻译行为的必要补充,意在改变目的语社会对原作和原语社会的认识,并且匡正异文化环境中产生的译作所塑造出的不真实的或不符合原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本国文化形象,消除或减少文化误读。
外译作品的走向也昭示了这种翻译行为的动机。对外翻译多以一个时期内的“国际语言”及其他影响和使用范围较广的语言为目的语,作品进入异文化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影响。早期中国的外译作品也基本符合这一规律。建国后对外翻译的目的语即开始呈现出多元化, 以英语为主,包括几十个语种,其中有法、俄、德、西班牙、日等相对重要的语言。同时,也有相当多的作品,特别是部分取材于中国革命历史或反映国家建设成就的作品进入一些使用人数少、影响较小的语言,尤其是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的语言,如亚洲的朝鲜语、越南语、泰语、缅甸语、泰米尔语和非洲本土语言豪萨语及斯瓦希里语等。在一些历史阶段,部分外译作品中所描述的中国现状及所走过的道路对目的语社会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译作进入异文化的方式也显示了中国对外翻译行为的目的性。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的作品及各种外文书刊主要面向“爱好和平愿意了解新中国的各国人民”,[12](P485)包括在华工作或来华访问的外国人,不以帮助中国读者学习外语为主要目的。长时间内,对外翻译首先不是作为一种经济行为而存在。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类译作通过贸易和非贸易(赠送和交换)方式相结合的途径进入异文化;在一些阶段,非贸易方式占主要地位。①参见《出版工作文件选编》(1949-1957),第423-424页,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办公室编印,1982年出版;罗俊,《回顾四十年中的十五年》,《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回忆录》,第68页,新星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种局面在“文革”结束一段时间后才有所改变。
四、结语
对外翻行为发生在原语文化中,是一种常常与目的语文化需求相脱节的文化输出形式,这种主动“送出”的译作获得认可的难度相对更大。只有在翻译主体的选择与目的语读者的需要相符合或巧合时,译作才会受到欢迎。中国古典文学的成就在全世界广受推崇,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外翻译出版的《儒林外史》、《红楼梦》和《水浒传》等作品大都受到好评,而多数当代生活题材的作品则难以在异文化中引起大的反响。
对外翻译方式本身的缺陷也会影响译作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处境。一方面,译者对非母语的把握和运用能力总是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就使得译作文本的语言难免有不符合目的语表达习惯的现象;另一方面,译者常常对目的语社会缺少足够的了解,翻译行为缺少针对性,这也会影响译作的接受。
由于这种翻译方式的局限性,一些人对中国译者所从事的对外翻译活动持否定态度。曾于上世纪70年代以“外国专家”身份在外文局与中国翻译家共事的英国汉学家詹纳尔认为,尽管中国本土译者的英语水平很高,但对他们来说,将本国文学作品移植到其他语言中的工作是“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an almost impossible task),其中的困难也是“几乎无法克服的”(almost insuperable)。在他看来,中国作品的英译应由英语本土人士承担(The job is really one that we Anglophones should have been doing for ourselves.)。[13](P187)著名汉学家马悦然(Goran Malmqvist)也认为“一个中国人,无论他的英文多么好,都不应该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14]
中国的对外翻译自有其存在的必要,其在文化输出和对外宣传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但由于这种翻译方式的特殊性,许多外译作品难以在异文化中充分发挥翻译主体所希冀的作用。为此,我们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译者水平和外译作品的质量;与此同时,也应该通过一些渠道吸引、鼓励更多外国人翻译中国的优秀作品,为其提供便利和必要的帮助,或者采用国内译者与目的语社会人士合作翻译的形式,这样可以促进外译中国作品的接受,进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塑造出中国文化的形象。
[1] Allison Beeby Lonsdale.“Direction of Translation ( Directionality)”. Routledge Encyclopa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M]. Ed. Mona Baker. NewYork: Routledge, 1998.
[2] Peter Newmark,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New York: Pri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UK) Ltd, 1988.
[3] Margret Grindrod. “Portrait of a Profession——The Language Monthly Survey of Translators”[J]. Language Monthly 2 (1986).
[4] 巴金.一篇序文[A].病中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5] 杨正泉.序言[A].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回忆录[C].北京:新星出版社,1999.
[6] 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 as the Creation of Images or ‘Excuse me, Is this the Same Poem?’”. Translating Literature. Ed. Susan Bassnett..
[7] 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8] 辜鸿铭.英译《中庸》序[A].辜鸿铭文集(下)[M].黄兴涛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9] 辜鸿铭.英译《论语》序[A].辜鸿铭文集(下)[M].黄兴涛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10]老舍.老舍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11]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12]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关于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的报告[A].出版工作文件选编(1949--1957)[Z].北京: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办公室,1982.
[13] W. J. F. Jenner. “Insuperable Barriers? Some Thoughts on the Reception of Chinese Writing in English Translation”.Worlds Apart Recent Chinese Writing and Its Audience. Ed. Howard Goldblatt. p187.
[14] 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称中国人不应翻译本国作品[N].南方都市报,2006-07-17.
责任编辑:冯济平
Creating the Self-image—A Study on the “Outward Translation ”in China
MA Shi-k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China.)
This paper intends to conduct a relatively systematic research into the “outward translation”, or the translation out of the native language. This kind of translation aims at creating the self-image of the native culture in the other cultures. For a long time, the “outward translation” has played a far greater role in China than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translation; outward translation; image of the other culture; image of the native culture
G125
A
1005-7110-(2010)03-0033-05
2008-11-26
马士奎(1967-),男,山东费县人,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翻译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外翻译理论和翻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