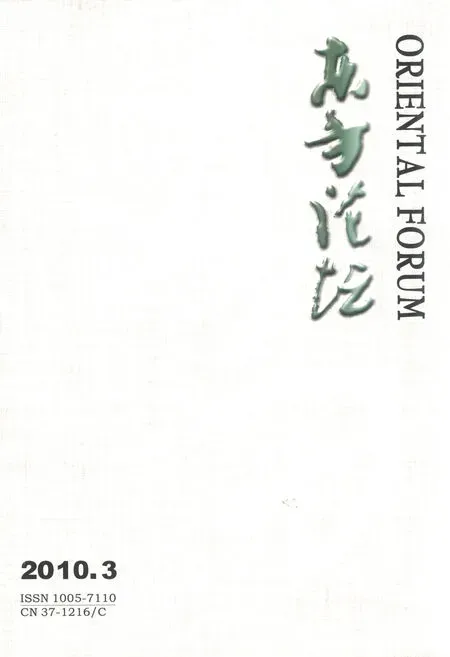杂取百家 集合群说
——《水经注》注释体例探析
2010-04-05张鹏飞
张鹏飞
(广东警官学院 公共课部,广东 广州 510230)
杂取百家 集合群说
——《水经注》注释体例探析
张鹏飞
(广东警官学院 公共课部,广东 广州 510230)
成书于元魏中后期的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一书,在为《水经》作注的过程中,博采群书,以丰富多样的文献资料来注释经文,将文献典籍、民间传闻与实地考察互相印证,尤其是运用文字学知识,把地理名称的文字辨析(包括音、义、字形)与地理考证结合起来,形成《水经注》一书独特的注疏方法。
《水经注》;注疏方法;杂取百家;实地考察
成书于元魏中后期的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一书,在为《水经》作注的过程中,博采北朝以来的经史典籍、野史碑录、地记故书、神话异闻、民间歌谣谚语等,模山范水、溯流穷源、访迹寻图,杂以神仙鬼怪,遂集斯学之大成。历代治《水经注》所引文献的,不乏其人,如:明人钟惺、谭元春、黄省曾,清人何焯、杨守敬,近人储皖峰、胡适、郑德坤、吴天任、马念祖、陈桥驿等;著作如:储皖峰《水经注引用书目》、胡适《水经注引用书类纂》、马念祖《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郑德坤《水经注引书考》、吴天任《水经注引书考》、陈桥驿《水经注文献录》等,但这些著作大多注重研究所引文献,而对《水经注》本书的注疏方法、文献考证特点关注甚少。本文拟就注疏条例、杂取百家、稽核群说、实地考察等方面探讨《水经注》一书独特的注疏方法,以期拓展郦学之范畴。
一、 注疏条例
(一)注疏之义界
清人顾炎武《日知录》言:“先儒释经之书,或曰传,或曰笺,或曰解,或曰学,今通谓之注。《书》则孔安国传,《诗》则毛苌传、郑玄笺,《周礼》、《仪礼》、《礼记》则郑玄注,《公羊》则何休学,《孟子》则赵歧注,皆汉人。《易》则王弼注,魏人。《系辞》则韩康伯注,晋人。《论语》则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则杜预注,《尔雅》则郭璞注,《谷梁》则范宁集解,皆晋人。《孝经》则唐明皇御注,其后儒辨释之书,名曰正义,今通谓之疏。”[1]其中提及传、笺、解、学、注、正义、疏,而将先儒释经之书通谓之注,将后儒辨释之书通谓之疏,并点明了二者区别之所在:注是早期(汉魏以来)儒生对儒家经籍的注解,而疏则为后世(唐宋以来)儒生对先世注解的进一步辩解注释。如《诗经》有毛传、郑笺,还有孔颖达的正义,其中毛传、郑笺即为注,孔颖达的正义即为疏。且自古以来,疏不破注,后人之疏必须在前人之注基础上进一步阐释,注与疏必须在总体上相一致。而与注疏相近的还有训诂、故、解故、训、训纂、章句等,但今世之注疏学与训诂学实为两大不同的学科。
吾国注疏之学,肇始于孔子为《周易》做“十翼”,其后七十子之徒,特别是子夏在注疏学史上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后汉书•徐防传》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2](P1501)后世汉魏以来六经注疏之学,皆源于子夏。至两汉之世,注疏之风盛行于世,并形成不同的流派和传承系统,于《诗》则有齐鲁毛韩四家,于《春秋》则有《左氏》、《公羊》、《谷梁》三传,于《礼》则有《周礼》、《仪礼》之分等等。至东汉末年,这种注疏之风进一步发展,并形成合流之势,贾奎、马融、郑玄等人打破传统的专注儒家一经之风,遍注六经,并综合了今文、古文学派之学说,使注疏之学在汉末形成一大颠峰,即后世所谓汉学。
可见,注疏学自产生之日起即依附于儒家经学,自周秦至两汉,几乎未有变化;至东汉末年注疏的范围始开始延及其它学科,首先是魏晋以来庄老玄学思想的兴盛,使玄理入注疏,比如王弼的《周易注》、《老子注》;南北朝时期,注疏之学的范围进一步延及史学、佛学、地学、算学、小学、医药学等学科,如裴松之《三国志注》、郭璞《山海经注》、祖冲之《九章算术义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郦道元的《水经注》等,其中在注疏方法与注疏体例上创新最多的,尤以南朝刘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为典范。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的过程中,博采群书达140余种,保存了大量史料,其注文甚至超出原文三倍,其注以补史、考史为主。而郦道元之《水经注》则更进一步,其以大量的各种文献资料来注释经文,且在为经作注的过程中每一条都是引用多种文献记载,这与以往的单纯的以扫清语言障碍揭示义理为主且仅引用单条文献的注疏方法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这种注疏方法与《左传》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并开创了南北朝以来义疏之注疏体例。
(二)《水经注》之注疏条例
“注大于文”是传统注疏中遵循的一个较为普遍的原则,郦道元在为《水经》做注过程中不仅遵循了这一原则,而且加以突破。《水经》一书原文只有三卷,一万多字,简要地记载了当时全国137条重要的河流与水道,而《水经注》一书以河流水道为纲,综述流域内水文、地貌、地质、土壤、植物、动物之分布,以及物产、交通、城邑建制沿革等地理状况。据今人赵永复统计,《水经注》中记载的河流水道达2596条[3],殆过《水经》所记载之水道数十倍。《水经注》全书四十卷共计32万字,其篇幅较《水经》达三十余倍矣,这种注文比原文多出几十倍的现象,在中国古代注疏史上,极为罕见。因此,“注大于文”构成了郦道元《水经注》重要的编辑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过多的注疏如无明确的注疏体例则必然杂乱不堪,郦道元对于此有清醒的认识,其于《水经注序》云:“自献迳见之心,备陈舆徒之说……所以撰证本经,附其枝要者,庶备无误之私,求其寻省之易。”[4]由此可知郦道元在撰述之初,必当有所条例,以使其注疏严谨周密。然而,除了郦道元在其《序》中所言:“经有谬误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载,非经水常源者,不在记注之限”,其余则未见言及注疏条例,加以《水经注》中所引众多典籍的亡佚,至北宋时又残缺数卷,且经注混淆,故后世读者往往望洋兴叹,难以卒读,以至多指其荒谬,病其旨晦,如:
郦盖借经而见已博该者也,然偏该而旨未洽,横萎而词未修,以备稽考,则优孟志怪以耀世,引遐搜僻以示异,将使人应接不暇,莫知所以根据,然宏富瞻给,而靡所取裁,以之钻味弗堪矣。[5]
《水经注》千年以来无人能读,纵有读之而叹其佳者,亦只赏其词句而为游记诗赋之用耳,然亦千万中之一二也。[6](P21)
郦氏之病,在立意修辞,因端起类,牵连附会,百曲千回,文采有余,本旨转晦。[7](P21)
山川形势之变迁,郭邑兴废之频繁,古今名目之殊异,以及典籍之亡佚或讹传,都为注疏《水经》带来极大困难。清人崇尚博雅,考据炽盛,遂多潜心素称难治之《水经》者,由此兴起郦学。赵一清于《水经注释》中首先釐清《水经注》之经注并标明其注疏条例:
经访禹贡,总书为过,注以经字代之,以此例河、济、江、淮诸经注混淆,百无一失……凡经文次篇之首,有某水二字,皆后人所加。盖汉人作经,自为一篇,岂能逆料郦氏为之注,而先于每卷交割处增二字,以别之哉?或郦注既成,用二字为提掇则可耳,然非经之旧也。此卷首例河水二字,谓重源之再见也。其义例如此。[5]
赵一清在作《水经注释》中即以此二条例为刊正《水经注》中经注之准则,如《水经注》卷十六漆水注“出扶风杜阳县俞山东北入于渭”条,其中注文“又东过漆沮入于河”赵一清刊误曰:“笺曰:克家云:东迳,《史记》作东过。按《尚书》本作东过,不独《史记》也。且郦道元注例用迳字,以别于经文之过。” 其后,全祖望于《五校水经注题辞》论及经注之别云:
经文与注文颇相似,故能相混,而不知熟玩之,则固判然不同也。经文简,注文繁,简者必审择于其地望,繁者必详及于渊源,一为纲,一为目,以次思之,盖过半矣。若其所以相混者,其始特抄袭之厉耳,及板本仍之,而世莫之疑矣。[8](P3)
“经文简,注文繁,简者必审择于其地望,繁者必详及于渊源”,全氏此说实为首创,在整个郦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虽未标明为注疏条例,然亦得郦书之篇旨。
清人除全、赵以外,治郦学者以戴震成就最为卓著。戴震以《永乐大典》本为底本,费十余年而校成武英殿聚珍本,基本解决了《水经注》原书自北宋以来的经注混淆情况,大致还原了其书的原貌。而且戴氏在总结前人之说的基础上,对《水经注》注疏条例总结为三则:
凡水道所经之地,经则云“过”,注则云“迳”;经则统举都会,注则兼及繁碎地名。凡一水之名,经则首句标明,后不重举,注则文多旁涉,必重举其名以更端。凡书内郡县,经则但举当时之名,注则兼考故城之迹。”[9]
戴氏以此条例为准则,将《水经注》中的原有混淆不清的经与注彻底分开,从而为今人治郦学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今人陈桥驿则从水文地理学的角度阐释《水经注》的注疏条例:
《水经注》首先根据河流的干支关系、长短大小、独流入海抑是汇入大河等指标,为河流的各种称谓,制定了它们的定义,卷一《河水注》云:水有大小、有远近,水出山而流入害者,命曰经水;引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出于地沟、流于大水及于海者,又命曰川水也。这一段注文真实开宗明义,它不仅是河流各种称谓的定义,而且也是郦道元撰写《水经注》的规范。在卷首所制定的撰写规范的,这就是《水经注》体例严密之处。[10]
综观赵一清、全祖望、戴震、陈桥驿等人为《水经注》所立凡例,有以分辨经注为准则的,如赵一清、全祖望、戴震;有从水文地理学角度而立的,如陈桥驿。从数人之论可知,无论从何角度去探讨,郦道元在注《水经》之时必制定有注疏条例,才能使《水经注》这样一部内容博杂且篇幅庞大、洋洋数十万字的鸿篇巨著显得严谨周密、条理清晰截然可读。本文认为,将文献典籍、民间传闻与实地考察互相印证,并运用文字学知识把地理名称的文字辨析(包括音、义、字形)与地理考证结合起来,这即是《水经注》一书主要的注疏条例,也是郦道元在为《水经》作注的过程中所采用的基本考证方法;而书中大量的山水景致描写、神话异闻、歌谣谚语,也正是在这样的注疏条例下加以裁略引用的。
二、杂取百家,稽核群说
郦道元好学,自幼博览群书,在为《水经》作注之时,杂取百家之言,稽核群说,征引极为丰富。其注疏特点与《春秋左传》相近,又与刘昭《后汉书》八志注、裴松之《三国志注》极为相似,其引文遵从其注疏条例,立足于补述、考辨的需要,不仅仅是对引用材料的简单罗列抄录,而是将引文与注疏行文融合在一体。其引书之丰富,据近人郑德坤统计共引用文献436种[11],不下刘孝标《世说新语》注、裴松之《三国志》注、《文选》六臣注;且遍及经、史、子、集,其中引及经传、谶纬、小学典籍约40余种,史书约140余种,子书20余种,诗赋杂文作者约40余家;碑刻也随处可见,还有许多文献典籍如《京房易传》、《尚书大传》、《韩诗》、《三仓》等等,多已不见于隋唐志略,赖此书而得以保存。《水经注》一书真可谓杂取百家、稽核群说。
(一)考诸地记典籍
郦道元在大量引用文献典籍的同时,并不仅仅迷信于传世文献记载,其判断地理之变迁、地名之演变时,多考诸地记典籍。本文所言地记典籍,系指成书于《水经注》之前的古代地理著作。《水经注》中引用了大量的此类典籍,如辛氏《三秦记》、东晋袁山松《宜都记》、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南朝宋郭缘生《述征记》、南朝宋雷次宗《豫章记》、南朝宋孔灵符《会稽记》等,用以资证地说。如卷十浊漳水注“又东北过曲周县东”条云:
郑玄注《尚书》,引《地说》云:大河东北流,过绛水千里,至大陆,为地腹。《地理志》曰:大陆在钜鹿,绛水在安平信都。如《志》之言,钜鹿与信都,相去不容此数也。水土之名变易,世失其处,见降水则以为绛水,故依而废读,或作绛字,非也。今河内共北山,淇水出焉,东至魏郡黎阳入河,近所谓降水也。降读当如郕降于齐师之降,盖周时国于此地者,恶言降,故改为共耳。
郑玄以为“降水”的“降”不当作“绛”,当读做投降的“降”,并为此说引经据典:“盖周时国于此地者,恶言降,故改为共耳”。作为东汉大儒,郑玄之论颇具权威性,而郦道元《水经注》中共引用其解说十八条,指出其谬误的就有四条,此处亦然:
余按郑玄据《尚书》有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推次言之,故以淇水为降水,共城为降城,所未详也。稽之群书,共县本共和之故国,是有共名,不因恶降而更称。禹著《山经》,淇出沮洳,《淇澳》,《卫诗》,列目又远,当非,改降革为今号。但是水导源共北山,玄欲因成降义,故以淇水为降水耳。”
对“降水”一名的来源,郦道元认为,郑玄依据《尚书》的记载“以淇水为降水,共城为降城”的推论无充足的理由,过于牵强附会;进而稽查群书,依据《尚书•禹贡》与《汉书•地理志》等地学典籍的记载发现,“共县本共和之故国”,是本有“共”名的,不可能因避“投降”之恶名而将“降城”改作“共城”,而淇水导源于共城附近之共北山,郑玄因以共城为降城、进而以淇水为降水的推论是完全错误的。由此可见郦道元治学之严谨,类似例子还有许多。
(二)杂取百家
郦道元在注疏之中除以地记典籍等地学知识为基础外,还稽核群说,参校诸多史志典籍、经书文集及诸子百家之言,以指正谬误。如卷五河水注“又东过成皋县北”条:
汜水又北流,注于河,《征艰赋》所谓步汜口之芳草,吊周襄之鄙馆者也。余按昔儒之论,周襄所居在颖川襄城县,是乃城名,非为水目。原夫致谬之由,俱以汜、郑为名故也,是为爽矣。又按郭缘生《述征记》、刘澄之《永初记》,并言高祖即帝位于是水之阳,今不复知旧坛所在。卢谌、崔云亦言是矣。余按:高皇帝受天命于定陶汜水,又不在此也,于是求坛,故无仿佛矣。
此引用卢谌之《征艰赋》“步汜口之芳草,吊周襄之鄙馆”以阐释汜水注入黄河之地理情况,然参校昔儒之论,则周襄王所居之地在颍川襄城县(今河南省襄城县),故此“汜口”非为汜水北入黄河之滨,而实为城名。进而参用郭缘生《述征记》、刘澄之《永初记》所载汉高祖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之史实,指明此汜水非为“汉高帝受天命”之“定陶汜水”也。又如卷九沁水注“又东过野王县北”条云:
邘水又东南,迳孔子庙东,庙庭有碑。魏太和元年,孔灵度等以旧宇毁落,上求修复。野王令范众爱、河内太守元真、刺史咸阳公高允表闻,立碑于庙。治中刘明、别驾吕次文、主簿向班虎、荀灵龟,以宣尼大圣,非碑颂所称,宜立记焉,云,仲尼伤道不行,欲北从赵鞅,闻杀鸣犊,遂旋车而返。及其后也,晋人思之,于太行巅南为之立庙,盖往时回辕处也。余按诸子书及史籍之文,并言仲尼临河而叹,曰:丘之不济,命也夫!是非太行回辕之言也。
此处以太行巅南孔子庙碑之记载,言孔子因伤道之不行,欲北从赵鞅,闻杀鸣犊,而于庙立之处回辕,郦道元考之诸子之书及史籍文献记载,认为仲尼临河而叹之言非太行回辕之言。
《水经注》一书中,还有“证诸史传”、“与经史诸书全相乖异”、“稽之群书”、“考诸地记”、“考寻兹说”、“稽之故说”、“稽故老之言”、“推旧访新,略究如此”、“考古推地”等言,皆为郦道元引用各种文献典籍用以注解《水经》的明证。此客观谨慎、宁缺勿滥之治学态度,亦可证明郦道元稽核群说之无所偏颇。
三、实地考察
郦道元在大量引用文献的同时,并不仅仅局限于文献典籍,而是注重实地考察,故能将文献典籍、民间传闻与丰富的实地考察成果互相印证。郦道元首先是一位地学家,其足迹所至,遍及大半中国。郦道元生长于北方,祖籍为北魏时范阳郡涿县(今河北涿县),出生地为其父郦范之任所青州(今山东),自幼随父宦游,到过北魏的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一带)和洛阳(今河南洛阳),二十余岁随北魏孝文帝北巡北方六镇(今甘肃、内蒙一带),先后任职于冀州(今河北冀县)、长社、颍川(今河南许昌)、鲁阳(今河南鲁山)、东荆州(今湖北北部),又因平息战乱而到过淮扬一带,最后因萧宝夤之乱而被害于阴盘驿亭(今陕西),足迹遍及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中上游一带,最北至阴山,最南至湖北北部一带。凡其足迹所至,必留心于当地河流山川景观以及郡邑之地貌、变迁,并注意收集当地的民间风俗见闻和歌谣谚语,从而作为其布广《水经》之实证材料,使《水经注》之实证性至千载以后依然辉耀于世。此一如太史公之“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12](P3293)
从《水经注》一书可以看到,凡是郦道元足迹所及地域,即卷一至卷三十二的《河水注》、《汾水注》、《济水注》、《清水注》、《洛水》、《巨洋水注》等,记载极为详细。如卷二十六淄水注“淄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云:
(石井水)北流入阳水。余生长东齐,极游其下,于中阔绝,乃积绵载。后因王事,复出海岱。郭金紫惠同石井,赋诗言意。弥日嬉娱,尤慰羁心,但恨此水时有通塞耳。阳水东迳故七级寺禅房南。水北则长庑遍驾,回阁承阿,林际则绳坐疏班,锡钵间设,所谓修修释子,眇眇禅栖者也。
这段文字描写了海岱境内之景致,海岱为青州之古地理名(《尚书•禹贡》)。据《水经注•巨洋水注》“又东过临朐县东”条云:“先公以太和中坐镇海岱,余总角之年,侍节东州”,东州即青州,可见郦道元在此度过了童年时光。步入仕途之后,郦道元又于北魏宣武帝景明四年(503)出任青州,曾与友人郭祚同石井赋诗言意,故对于当地地理格外熟悉,其记载亦细致真实,一草一木,极富情趣。而平城、洛阳是北魏王朝的旧、新都城,郦道元曾先后在此两地任职,因而卷十三对于北魏旧都平城一带的记载和卷十五对新都洛阳之盛况的描写都尤为详尽。
郦道元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为尚书主客郎,随高祖北巡六镇途中对北方边境之地里风俗多有见闻,其见闻即成为河水注中之材料。如卷三河水注“又东过云中桢陵县南”条云:
芒干水又西南,迳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萦带长城,背山面泽,谓之白道城。自城北出有高阪,谓之白道岭。沿路惟土穴出泉,挹之不穷。余每读《琴操》,见《琴慎相和雅歌录》云:饮马长城窟,及其扳陟斯途,远怀古事,始知信矣,非虚言也。
郦道元之前读《琴操》,对其中“饮马长城窟”一句感到不解:北方干旱,如何“饮马于长城之窟”呢?在北巡经过长城一带时,郦道元见沿途“土穴出泉,挹之不穷”,始恍然大悟。将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两相印证,实为郦道元注《水经》之基本方法,亦可见其治学之严谨不懈。同卷注文还有这样一段实录:
芒干水又西,塞水出怀朔镇东北芒中,南流迳广德殿西山下。余以太和十八年,从高祖北巡,届于阴山之讲武台。台之东有《高祖讲武碑》,碑文是中书郎高聪之辞也…… 魏太平真君三年,刻石树碑,勒宣时事。碑颂云:肃清帝道,振摄四荒。有蛮有戎,自彼氐羌;无思不服,重译稽颡。恂恂南秦,敛敛推亡。峨峨广德,奕奕焜煌。侍中、司徒、东郡公崔浩之辞也。碑阴题宣城公李孝伯、尚书卢遐等。从臣姓名,若新镂焉。
此乃郦道元每至一处有闻必录、且广辑碑文之一例。这样的碑铭、摩崖造像等石刻文献记载在《水经注》全书中还有三百余处。太和中,郦道元年方二十有余,正值如日中天之际,而随同孝文帝北巡的良机,使郦道元有机会实地考察北方地区特别是长城、边塞地带的地理环境、民风故俗,并形成随处登录见闻之习惯,从而为其以后为《水经》作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而卷三十三《江水注》、《湘水注》、《漓水注》、《渐江水注》、《庐江水注》等文主要涉及到长江中下游、钱塘江流域等南朝统治区,因无法前往亲身考察,郦道元只能依据南朝刘宋、齐梁以来的山水地志诸如裴松之《荆州记》、盛弘之《宜都山川记》、刘澄之《永初山川记》等的记载。像《江水注》中描写长江三峡壮丽景致的语句:“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柽柏,悬泉瀑布,飞潄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即为化用盛弘之《宜都山川记》之语。诸如此类还有许多。[13](P33)
《水经》所布水道遍及全国各地疆域,虽然由于南北分裂、政治军事对峙、个人游历经验有限等等原因,郦道元的足迹无法遍及各地,逐条实地考察,但校之以当时大量山川地记、方志之书,兼之以其累月积年、随时随地的勘察笔录,加之以其补正经籍之实证精神,均益使《水经注》弥足珍贵矣。
综上所述,郦道元在为《水经》做注过程中不仅突破了传统“注大于文”的注疏原则,而且形成严谨周密之注疏条例,即将文献典籍、民间传闻与实地考察互相印证、并运用文字学知识把地理名称的文字辨析(包括音、义、字形)与地理考证结合起来的注疏条例,开创了南北朝以来义疏之注疏体例。其路之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不囿于原著,以翔实文献资料对原著进行了一番增补的工作,表现了“有能自立于所注者之中,而又游乎其外”的精神;二是在注疏之时能够广收博采,认真鉴别考核,合理剪裁去取。其客观谨慎、实事求是、宁缺勿滥的治学态度,表现出一种求真、务实之风,即其在《水经注序》中所言“撰证本经、备忘误之私”的注疏之道,为后世注疏之学开辟了一条新路。
[1]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 范晔. 后汉书•徐防传[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3] 赵永复.水经注通检今释[M].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4] 郦道元.水经注[M].陈桥驿校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5] 赵一清.水经注释[M].[清]乾隆五十一年毕沅刊刻本.
[6] 刘献廷.广阳杂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7]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8] 全祖望. 水经注七校本[M].成都: 巴蜀书社,1985 .
[9] 戴震.序言[A].水经注校[M].武英殿聚珍本.
[10] 陈桥驿.水经注记载的水文地理[A].水经注研究[C].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
[11] 郑德坤.水经注引书考[M].台北: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
[1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13] 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潘文竹
A Study of the Scholium Methods in Commentary to the River Classic
ZHANG Peng-fei
(Dept of Common Courses, Guangdong Police College, Guangzhou 510230, China)
In adding notes to his Commentary to the River Classic, which was completed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386~534), Li Daoyun adopted a unique method by using abundant literature, classics, folk stories,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and geographical research.
Commentary to the River Classic; method of commentary; draw on various resources;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206
A
1005-7110-(2010)03-0044-06
2009-03-31
张鹏飞(1979-),男,湖北武汉人, 广东警官学院公共课部讲师,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