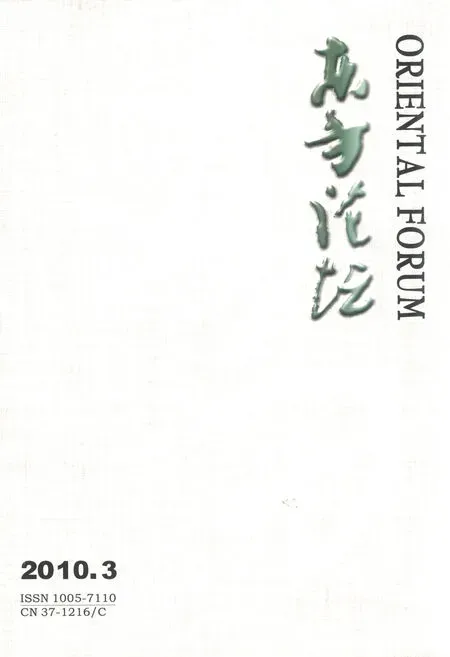西方汉学先驱罗明坚的生平与著译成就考察
2010-04-05郑锦怀
岳 峰 郑锦怀
(1.福建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2.泉州师范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西方汉学先驱罗明坚的生平与著译成就考察
岳 峰1郑锦怀2
(1.福建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2.泉州师范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罗明坚是最早获准进入中国内陆传教的耶稣会士,他在西学东传与中学西传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是西方传教士汉学的奠基人。他译述并出版了《祖传天主十诫》与《天主圣教实录》,并与利玛窦合编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本《葡汉词典》,还独立将《三字经》与《大学》等中国古典文献译成拉丁文,并且绘编了西方第一本专门的中国地图集。
罗明坚;汉学;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经典;翻译
一、引言
想要研究西方汉学史,想要考察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儒家经典的译介史实,罗明坚肯定是我们绕不过去的先驱人物之一。
据著名学者张西平的划分,汉学(Sinology)经历了“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与“专业汉学时期”这三个发展阶段。张西平认为,元、明期间的“游记汉学时期”仅仅是西方汉学的萌芽期,西方人仅通过一些游记与不确记载如《马可波罗游记》等来认识中国,所知肤浅。而到了明清之际,由于来华的耶稣会士中出现了不少精通汉语、熟悉中国文献、了解中国文化之人,著名的有利玛窦(Matteo Ricci)、艾儒略(Giulio Aleni)等人。他们出于传教的需要,对中国文化展开了广泛的译介与深入的研究,使得汉学渐渐发展成为一门真正学科,并由此进入了“传教士汉学时期”。[1](P101)
此前,中西文化交流领域的研究者常以利玛窦作为中学西传的鼻祖或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比如,有学者称:“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2](P6921)另有学者称:“明清之际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是西学东渐。它始于1582年利玛窦的来华,迄于1773年耶稣会的解散……利玛窦是西学东渐的开创者……”[3](P1)。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以耶稣会来华作为“传教士汉学时期”开始的标志,并以利玛窦来华那年作为其起始时间,但关于这个起始时间的具体说法却不完全一致。比如,詹杭伦在谈到“海外汉学发展简史”时袭用了张西平的划分方法,却称:“耶稣会1583年入华以后,开始了‘传教士汉学时期’。”[4](P516)蒋印莲亦称:“随着1583年基督教传入中国,‘传教士汉学时期’随之开始,成为欧洲研究中国的基础。”[5](P235)
我们自然无法否认,利玛窦确实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人物之一,也是名气最响、影响最大的一位耶稣会士,为中学西传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我们必需注意到,利玛窦既非最早来华亦非最早向西方译介中国文化的耶稣会士。
首先,比利玛窦更早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大有人在。据费赖之所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利玛窦于1582年8月来到当时为葡萄牙殖民者占据的澳门[6](P32),而在他之前来华的耶稣会士至少有九人之多,按来华时间之先后分别是方济各•沙勿略(Francois Xavier)、巴莱多(Melenior Nunez Barreto)、培莱思(Francois Perez)、黎伯腊(Jean-Baptiste Ribeyra)和黎耶腊(Pierre-Bonaventure Riera)、加奈罗(Mgr Melchior Carneiro)、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罗明坚(Michel Ruggieri)与巴范济(Francois Pasio)[6](P1-31)。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罗明坚于1579年7月就来到澳门[6](P23),至1580年又获准在广州定居[6](P24),1582年底又至肇庆[6](P26)。
其次,利玛窦绝非最早译介中国古典文献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其写于1594年11月15日的一封信中提到:“几年前我着手翻译著名的中国‘四书’为拉丁文,它是一本值得读的书,是伦理格言集,充满卓越智能的书。待明年整理妥后,再寄给总会长神甫,历时你就可以阅读欣赏了。”[7](P32-33)据考证,利玛窦在信中所称的“几年前”即为1591年。由此可见,利玛窦在1591年就开始要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但到1594年11月11日仍未最终完成该译本,必须等到1595年才能整理定稿。这样看来,利玛窦很可能是在1595年才将其《四书》拉丁文译本寄回罗马供耶稣会总会长参阅。遗憾的是,我们目前仍未能得见该译本的真面目。
而在利玛窦之前,罗明坚就已经于1581年底到1582年间曾将某种中文文献(可能是《三字经》)译成拉丁文,并在1582年将其寄回欧洲[1](P106);1589年,在回到欧洲之后,罗明坚又把《四书》中《大学》的部分内容译成拉丁文,后来于1593年正式刊印[1](P107)。可见,罗明坚比利玛窦更早从事中国文献的西译活动,而他的《大学》拉丁文译文也要比利玛窦的《四书》拉丁文译本要更早问世,可谓中国儒学经典的第一种西文译本。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应当以利玛窦来华时间1582年作为“传教士汉学时期”的起始时间,亦不应仅将利玛窦列为传教士汉学的奠基人,而应当改写汉学史,转而称罗明坚才是西方传教士汉学的奠基人,并对其展开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二、罗明坚生平简介
罗明坚(Michel Ruggieri)于1543年出生在意大利南部的斯品纳佐拉城(Spinazzola, Italy),该城当时受那不勒斯王国(Kingdom of Napoli,又译为“那波利王国”、“拿坡里王国”等)统辖。他早年勤奋学习,获得了民法与教会法博士学位(utroque iure, 即 civil and canon law),此后从政,仕途显赫。1572年10月27日,罗明坚在他二十九岁时辞去官职,进入设在罗马的耶稣会(the Society of Jesus)修院学习神学,但不等自己完成神学课程,他便申请前往印度传教[6](P23)。罗明坚来到葡萄牙里斯本(Lisbon, Portugal),当时那里是欧洲传教士前往东方的大门。在等待前往印度果阿(Goa,India)的船只出发期间,罗明坚于1578年3月被按立为神父。其后不久,罗明坚同利玛窦(Matteo Ricci)、阿奎维瓦(Rudolph Acquaviva)、巴范济(Francois Pasio)等一行十二位传教士乘船离开欧洲,于1578年9月到达印度果阿。在印度,鲁伊兹(Vecent Ruiz)派罗明坚到佩切利亚(Pecherrie)传教[6](P23)。罗明坚马上开始学习印度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居民使用的语言,过了不到六个月,罗明坚就基本能够听懂当地人使用土著语言进行的忏悔。可能正是由于罗明坚所展露出来的这种语言天赋,鲁伊兹认为他是前往中国传教的最佳人选,便命他去柯枝乘船前往澳门。1579年7月20日,罗明坚到达澳门。
此前,同样来自那不勒斯王国、从1574年起开始担任远东耶稣会传教团监理神父的范礼安神父(Alexandre Valignani)于1578年9月6日来到澳门,呆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直到1579年7月7日在罗明坚到来之前才离开澳门。在澳门逗留期间,范礼安详尽考察中国,主动与中国人交往,了解中国各个方面的具体情况,认为“这样一个聪隽而勤劳的民族决不会将懂得其语言和文化的有教养的耶稣会士拒之于门外”[8](P326),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应该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了解中国文化习俗等的要求。
罗明坚看到范礼安留下的指示,尽管“大惊骇”,但“忆及服从之义”,“严守之”[6](P23)。但是,在澳门的大多数耶稣会士并未理解范礼安提出的要求。他们悲观地认为中国的大门难以打开,也不支持与帮助罗明坚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罗明坚在澳门的“诸友识辈以其虚耗有用之光阴, 从事于永难成功之研究, 有劝阻者, 有揶揄者”[6](P23),但他始终毫不气馁。
据费赖之介绍,罗明坚请了一位中国画师来教他,后者用毛笔教罗明坚中国文字形义。罗明坚学得比较快,不久就觉得自己所学已经足够他到中国大陆与各级官史接触,并开展传教活动。当时,在每一年的某些日子里,葡萄牙人可以到广州郊外与中国进行贸易,但一到晚上就不得留在陆地上,必需回到船上过夜。罗明坚就借这些机会跟一些中国官吏接触,并请求在陆上定居,而中国官员在1580年允许罗明坚“居陆”,住在广州一处款待暹罗贡使的驿馆中。[6](P24)
关于罗明坚到广州与中国官员接触并获准在陆上过夜的时间,其他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张西平则认为:“1581年期间罗明坚曾三次随葡萄牙商人进入广州, 并很快取得了广州海道的信任,允许他在岸上过夜,……”[1](P102)。不过,从整体上来看,张西平所论值得商榷,因为他采信的罗明坚生平活动几个重要事件发生的时间均出现错误。比如,张西平认为罗明坚在“30岁时从里斯本出发到达印度的果阿”[1](P101),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个时间即1573年,但罗明坚其实是在1578年9月到达印度果阿。再如,张西平又称罗明坚在“31岁时抵达澳门”[1](P101),这个时间即1574年,但罗明坚其实是在1579年7月20日到达澳门。因此,张西平提出的罗明坚在1581年曾三次进入广州并获准在岸上过夜之说似乎有待查考。但不管怎么说,罗明坚是明清之际第一个获准到中国大陆岸上居住的天主教传教士当无疑义。不过,此时罗明坚还仅仅是获准在中葡贸易期间在广州过夜,而不是获准在中国大陆定居传教。
明万历十年(1582年),明朝新上任的两广总督陈瑞召见葡萄牙殖民者与传教士。据费赖之所称,“时两广总督狡而贪,命人至澳门谕澳门长官及主教,用欧罗巴商人首领之名义来肇庆晋谒。”[6](P25)葡方让罗明坚以代主教的身份与巴范济等人携带重礼前往陈瑞驻节地肇庆。大概是由于罗明坚等人的礼物对于眼界闭塞的中国人来说很是奇特珍异,收受了重礼的陈瑞正式允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9](P102),同时也准许罗明坚居留内地[6](P25)。
应罗明坚所请,经范礼安批准,利玛窦于1582年8月7日来到澳门。这时,范礼安正第二次来到澳门巡视。他让罗明坚与利玛窦二人不再承担其他事务工作而专事学习中文,并为他们两人提供了专门的教师等条件。[8](P326)由于利玛窦随身携带了一座自鸣钟,为陈瑞闻知。陈瑞便写信给罗明坚,让他带上自鸣钟去肇庆。1582年12月18日,罗明坚携同巴范济等人从澳门出发,到同年12月27日到达肇庆。[6](P26)收到礼物的陈瑞很高兴,让罗明坚等人在郊外与天宁寺相通的一座房子里安顿下来,并给予厚待[3](P12)。1583年2月5日,罗明坚等人向陈瑞请求让利玛窦到广东定居,得到批准[3](P12)。可惜的是,陈瑞不久便因依附张居正而被褫职。由于害怕自己与罗明坚等人的交往会加重他的罪行,陈瑞让他们前往广州。罗明坚等人乘船前往广州,但甚至都没被允许上岸,只能默然返回澳门[10](P152)。
与此同时,接任两广总督的莆田人郭应聘开始查处传教士进入中国内陆之事,澳门耶稣会当局便派罗明坚与利玛窦去交涉。1583年7、8月间,两人抵达广州,历经周折,郭应聘终于在8月15日派人通知他们,称准许外国传教士到肇庆定居。至此,中国地方政府才首次准许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居住。[3](P12-14)
1583年9月5日,罗明坚与利玛窦在总督侍卫官的陪同下来到广州,9月10日又抵达肇庆,受到肇庆知府王泮的接见。9月14日,罗明坚等人得到通知,获准在崇禧塔附近建造居所,为中国式样,包括一厅两厢房,另有两间小屋作寝室、会客室与图书室,即为“仙花寺教堂”。[3](P14-16)从此,耶稣会在中国拥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活动场所,其在华传教事业正式开始。
1583年冬天,罗明坚返回澳门募款,次年四月重回肇庆。他与利玛窦在肇庆努力开展传教事业,效果相当显著。据统计,“在一五八四年中,天主教信友,只有三个。一五八五年,有十九,或是二十个;一五八六年,有四十个;一五八九年,有八十个;……”[11](P60)到了1586年1月,罗明坚在新任肇庆知府郑一麟的协助下经江西到达浙江绍兴,但很快就重返广东[12](P24-25),后又曾到广西活动,亦不成功[6](P28)。1588年,罗明坚奉范礼安之命,由澳门登舟回欧洲,以便请罗马教廷派遣使节来华。1589年,罗明坚回到达里斯本,面见葡萄牙国王腓力二世(Felipe II)。1590到1591年,罗明坚先后面见了四位天主教教皇,但罗马教廷遣使往华之事一拖再拖,无法成行。罗明坚精力憔悴,只得回到意大利西南部的萨莱诺城(Salerno,又译为“萨勒诺城”)居住,最后于1607年5月11日在那里逝世。[6](P29)
三、罗明坚与西学东传
罗明坚一生在西学东传和中学西传两个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西学东传方面,罗明坚的主要功绩是向中国信徒译介天主教教义,译述并出版了《祖传天主十诫》与《天主圣教实录》。
1. 译印《祖传天主十诫》
据台湾学者张奉箴研究,罗明坚在1582年就在广州译完《祖传天主十诫》一书,并于次年在肇庆印行。他还认为《祖传天主十诫》是目前所知在华天主教的第一篇经文。[13](P161)该文较短,故全文转录如下:
“一、要诚心奉敬一位天主,不可祭拜别等神像。
二、勿呼请天主名字,而虚发誓愿。
三、当礼拜之日禁止工夫,谒寺诵经,礼拜天主。
四、当孝亲敬长。
五、莫乱法杀人。
六、莫行淫邪秽等事。
七、戒偷盗诸情。
八、戒谗谤是非。
九、戒恋慕他人妻子。
十、莫冒贪非义财物。
右诫十条,系古时天主亲书,降令普世遵守。顺者则魂升天堂受福,逆者则堕地狱加刑。”[13](P161)
张西平进一步指出,《祖传天主十诫》首次用中文表述基督教概念,在中西早期宗教、哲学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祖传天主十诫》的文体较为成熟,说明到了这个时候,罗明坚的中文应用及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都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14](P150-151)
2. 编译《天主圣教实录》
罗明坚在西学中传方面的另外一大成就是编译了天主教在华的第一部中文教义书《天主圣教实录》(又名《西竺国天主实录》、《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天主实录》等)。根据裴化行的研究,《天主圣教实录》根本就不是罗明坚自己的创作成果,而应当是一本拉丁文教理讲义Vera et brevis divi narum reru erposition的中文编译本。但罗明坚并未完全依照原文进行翻译,而是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天主教思想,对原文做了不少改动。[15](P264)
关于该书的完成时间,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比如,耶稣会史研究专家德礼贤(Pasquale d'Elia,1890-1963)认为,罗明坚在1581年10月25日至11月12日之间就已经完成该书的初稿[1](P111),而费赖之则称该书“于一五八四年十一月杪刻于广州。”[6](P29)其实,罗明坚在其写于1584年1月25日的一封信中提道:“我已经完成于4年前开始用中文写的《天主圣教实录》。”[16](P262)据此推断,罗明坚应当是在1580年前后就开始编译《天主圣教实录》一书,但直到1584年1月左右才最终定稿。在1582年,范礼安曾指示罗明坚印行该书,却未能如愿;到1584年夏天,经利玛窦与一位旅居肇庆的福建儒士润饰修改,该书改名为《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于1584年11月在广东肇庆刻印传播。[3](P211)
据张西平介绍,《天主圣教实录》有多种刻本,罗马耶稣会档案馆里即藏有四种。其中一种藏本包括《天主实录引》、《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目录》、《新编天主实录》,书后附有分别用黑体与蓝体印刷的两种《祖传天主十诫》及《拜告》,而其他三种藏本与其大同小异。[1](P111)查阅收入《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二册的《天主圣教实录》,我们可知该书正文共包括十六章,分别是:“真有一天主章之一”、“天主事情章之二”、“解释世人冒认天主章之三”、“天主制作天地人物章之四”、“天神亚当章之五”、“论人魂不灭大异禽兽章之六”、“天主圣性章之七”、“解释魂归五所章之八”、“自古及今天主止有降其规诫三端章之九”、“解释第三次与人规诫事情章之十”、“解释人当诚信天主事实章之十一”、“天主十诫章之十二”、“解释第一靣碑文章之十三”、“解释第二靣碑文章之十三”、“解释天主劝论三规章之十五”、“解释圣水除罪章之十六”。[17](P763-764)
此外,张奉箴认为罗明坚在1583年底便将他自己所撰《天主实录》重校完毕,又请利玛窦和一位在肇庆居住的福建儒者润饰,到次年旧历八月十八日写好序文,同年十一月全书印刷完毕,刻印了1200本。张奉箴还认为该书不久之后重版,到那时才改名为《天主圣教实录》。[13](P163)
四、罗明坚与中学西传
在中学西传方面,罗明坚的主要成就是与利玛窦合编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本《葡汉词典》,独力将《三字经》与《大学》等中国古典文献译成拉丁文,并且绘编了西方第一种专门的中国地图集。
1. 与利玛窦合编世界历史上第一本《葡汉词典》
1584年在肇庆传教期间,罗明坚与利玛窦开始合作编写了一本葡萄牙语-汉语词典,直到1588年仍未编写完毕,也未能正式印行,但其手稿目前存放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
德礼贤在1934年最早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发现了这组编号为“Jap.-Sin.,I,198”的未署名手稿。这份手稿总共189页,其中“第32至65页”为葡萄牙语与汉语对照的辞典。不过,德礼贤却认为它是利玛窦与郭居静(Lazaro Cattaneo)合编的
成果。[13](P103-104)
1986年以后,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教师杨福绵多次发表文章介绍藏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这组手稿。杨福绵指出,该组手稿内容并不一致,只是因为纸张、墨迹相同而被编为一组,而其中的第32-165页为一部葡萄牙语与汉语对照的辞典,并称之为《葡汉辞典》。《葡汉辞典》前后附页内容零散,包括学习汉语用的笔记、词汇、天干地支、十五省的名称、天文知识及天主教教义、简介等杂项,其中第3a至7a页的罗马注音标题为Pin ciù ven tà ssì gnì,其中文名称应为《宾主问答辞义》,是一本会话小册子。[18](P35)杨福绵认为《葡汉辞典》是罗明坚与利玛窦的共同作品,并介绍了辞典的体例,如辞典分为三栏,分别是葡萄牙文词句、罗马注音与汉语词条,自32a至34页第三栏后还附有意大利语词条。据杨福绵的初步统计,整部《葡汉辞典》共有6000多个葡萄牙语词条,却只有5460个汉语词条只有5460个,有540多条葡语词条未见对应的汉语词条,这可能是由于有些葡萄牙语词汇一时找不到恰当的汉语译法,只能暂时空置。[18](P37-39)杨福绵还深入讨论了《葡汉辞典》采用的汉语拼音方案,并以该辞典为证据指出明代官话是以南京话为基础。
此外,张西平于1998年夏到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访问,亲自查阅了手稿,从而根据手稿的其他部分内容进一步指出这部葡汉辞典是罗明坚所编,而利玛窦则只是他的助手。[1](P105-106)
罗明坚与利玛窦的这部《葡汉辞典》被中西交通史研究学者方豪称为“第一部中西文字典”[19](P201),当然也是最早的葡萄牙文-中文词典。具体而言,它采用拉丁化注音模式,即应用包括“26个声母,43个韵母,4个‘次音’,5个字调符号”的罗马拼音,在每个汉字旁边注有声母、韵母,并标明清平、浊平、上、去、入五声符号,使得西方读者看见其罗马拼音即能知晓该汉字的读音,这是以西文拼读汉字之始,对西方人学习中国语言乃至汉语的拼音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20](P349-350)。
2.首次将《三字经》译成西文
罗明坚可谓是最早将中国古典文献译成西方文字的欧洲人。他在1583年2月7日写的一封信中说道:“去年我曾寄去一本中文书,并附有拉丁文翻译。”[1](P106)而据裴化行所言,“在一五八一年九月及十月里,罗明坚和他的同伴第三次入广州城……把中国儿童所用的一本‘研究道德’的小册,给会长送去。在送这本书的时候,他写了这一句,‘时间仓促,拉丁文译文也很不通顺。’”[15](P191)综合两种文献,可以推断,罗明坚应当是在1581年底至1582年之间译完了这本小册子,并于1582年的某个时候将其中文印本与拉丁文译本一同寄给耶稣会总会会长。
那么,这个小册子的源本为何呢?对此,学界说法各异。裴化行在注释中猜测这个小册子就是《三字经》或《千字文》的拉丁文译本[15](P200)。张西平则直接认定它是《三字经》的拉丁文译本[1](P106)。亦有学者认为该小册子节译的是《四书》中《大学》的部分内容[21](P23)。不过,根据裴化行所言,它是“中国儿童所用的一本‘研究道德’的小册”[15](P200),而《千字文》与《大学》的内容均与该描述不同。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罗明坚当时翻译的是中国古代蒙学经典《三字经》。可惜的是,这个小册子并未公开出版,未在西方留下什么影响,而我们也无法得见其真实面目。
3. 首次将《大学》译成拉丁文
1589年,在回到欧洲之后,罗明坚把《四书》中《大学》的部分内容译成拉丁文。当时罗明坚常去跟曾任耶稣会总会会长麦古里安(Mrecurian)秘书的波赛维诺(Antonio Possevino)交流,向对方讲述他自己在中国的见闻经历。于是,波赛维诺就在其百科全书式巨著Bibliotheca Selecta qua agitur de Ratione stucliorum in historia, in disciplines, in Salute omnium procuranda(中译为《历史、科学、救世研讨丛书选编》)的第九章中介绍了罗明坚在中国的部分经历,并附上罗明坚节译的《大学》拉丁文译文。波赛维诺的这本书1593年由罗马的Ex Typographia Apostolica Vaticana印行,后来又于1603年和1608年分别在威尼斯和科隆两次重印。虽然得以公开发表的只是罗明坚译稿的一小部分,而他的全部拉丁文译稿现存于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中[1](P107),但这是《大学》西文译文首次获得公开发表,且其问世时间要比利玛窦在1595年才完成并寄回意大利的《四书》拉丁文译本要早,意义极其重大。
据美国爱荷华州柯尔大学历史系(History Dept., Coe College, Cedar Rapids, Iowa, USA)编印的China Mission Studies (1550-1800) Bulletin 1(1979年刊印)第9页,索默尔沃热尔(Carlos Sommervogel)等人编的Bibliothèque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中译为《耶稣会藏书目录》,1890年在布鲁塞尔与巴黎出版)补编第九卷第826栏(suppl. IX. col. 826)指出罗明坚的译稿首页印有“China, Seu Humanae Institutio…”(中译为“中国,成人的教育……”)字样。费赖之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也称索默尔沃热尔的“《书目》补编(卷九,八二六栏)著录有罗明坚神甫抄本一部,现藏罗马维托利奥-伊曼纽尔图书馆[耶稣会士手稿,1185号(3314),标题作《中国的人事机构》]。”[6](P30)但冯承钧在翻译“China, Seu HumanaeInstitutio…”时显然出现了误译。
张西平指出,波赛维诺书中所载罗明坚《大学》拉丁文译文仅是《大学》的第一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1](P108)
张西平还据China Mission Studies (1550-1800) Bulletin 1第11页抄录了罗明坚的《大学》拉丁文译文,并加以分析,认为其翻译质量较高。比如,他通过对比多位译者的译文,认为罗明坚将“大学”二字译为“Humanae institutions ratio”(回译成中文即为“教育人的正确道路”),比较符合“大学”二字的原意[1](P108)。但他同时也指出,罗明坚还未能很好地理解中国哲学的伦理特征,因为他将“格物致知”译成“Absolutio scientiae posita est in causis et retionibus rerum cognoscendits.”(回译成中文为“知识的圆满在于认识事物的根源和规律”),未能领会宋明理学“不在乎科学之真,而在乎明道之喜”的“格物致知论”本质[1](P109)。
尽管波赛维诺之书曾两次重印,流传颇广,但罗明坚将《大学》译成西方文字的功绩却长期不为人所知。据丹麦学者龙伯格所说,17世纪西方最著名的伦理学与政治学著作都未曾提到罗明坚的这个译文[1](P110)。但不管怎么说,罗明坚首次将中国儒家经典译成西方文字,在中国文献西传史上开风气之先,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值得我们关注。
4. 绘编西方第一种中国地图集
回到欧洲后,罗明坚除了翻译儒家典籍,还绘编了西方第一种专门的中国地图集。该地图集当时也未正式印行,而是深藏在罗马的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中,直到1987年才为人发现,并经尤金尼奥•洛•萨尔多(Eugenio Lo Sardo)整理编辑,于1993年由罗马的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与Libreria dello Stato出版,书名为Atlante della Cina。
据介绍,该地图集共包括37页地理状况描绘与27幅地图,其中有的只是草图,有的则绘制得十分精美细致。罗明坚在其地图集中首次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十五个省份的地理位置、河流、农业、矿产、教育、宗教等情况,还首次向西方介绍了中国从省到府、州、县乃至卫、所的行政建构,并突出了中国南方的重要性。[1](P114-115)这是西方第一种专门的中国地图集,尽管它未获得广泛的传播,也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但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它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五、结语
罗明坚较早来到当时已被葡萄牙殖民者占据的中国澳门进行活动,并最早被中国地方官员允许到中国大陆居住与活动,是耶稣会在华传教先驱之一。他主要在广东肇庆传教,成果显著,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传教之外,罗明坚还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西学东传方面,他主要译印了《祖传天主十诫》与《天主圣教实录》等书,促进了天主教教义的在华传播。在中学西传方面,他不仅与利玛窦合编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本《葡汉词典》,绘编了西方第一种专门的中国地图集,更首次将中国古典文献《三字经》与《大学》译成拉丁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罗明坚是在1589年回到欧洲之后将《大学》的部分内容译成拉丁文,后来被收入波赛维诺的《历史、科学、救世研讨丛书选编》一书中,于1593年在罗马首次出版,到1603年和1608年又分别在威尼斯和科隆重印。而利玛窦在1591年才开始要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但到1594年11月11日仍未最终完成该译本,到1595年才整理定稿,并将其寄回欧洲。由此可见,罗明坚才是最早将儒家典籍译成西方文字之人,是名符其实的传教士汉学时期的开启者,是西方汉学的重要先驱人物。
[1]张西平.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J].历史研究,2001,(3).
[2]方豪.中西交通史[M].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
[3] 林金水.前言[A].林金水.利马窦与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詹杭伦.国学通论讲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 蒋印莲.国际汉语教学与汉语教学的国际化[A].云南省高等教育学会编.云南高教论坛(第三辑)[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6]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
[7]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8] 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二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9]邓开颂等主编.粤澳关系史[M].北京:中国书店,1999.
[10]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1583-1610)[M].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2] 林金水,邹萍.泰西儒士利玛窦[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13]张奉箴.利玛窦——来华前驱[J].辅仁大学神学论集,1983,56.
[14] 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
[15] 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M].萧溶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6] 霍•林斯特拉英译,万明译.1583-1584年在华耶稣会士的8封信[A].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2辑)[C].郑州:大象出版社,1998.
[17] 罗明坚.天主圣教实录[A].翁同苏等.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2)[C].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
[18] 杨福绵.罗明坚、利马窦《葡汉辞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J].中国语言学报,1995,(5).
[19] 利玛窦.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20] 方汉文主编.东西方比较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1] 岳峰.儒经西传中的翻译与文化意象的变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冯济平
A Survey of Michel Ruggieri’s Life and Works
YUE Feng1ZHENG Jin-Huai2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 2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00)
Michel Ruggieri, the first Jesuit allowed to live and preach in the inland of China,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Though many articles and monographs have dealt with his life events as well as his Sinological achievements, there are still quite a few points that need further consideration. In consideration of this, this paper endeavors to clarify Michel Ruggieri’s important undertakings in an effort to rectify some doubtful viewpoints of previous research and to present his achievements in introducing Catholic works into China. Finall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Michel Ruggieri compiled with Matteo Ricci the first Portuguese-Chinese dictionary in history, and that he translated San Zi Jing (the Three-Character Classic) and Da Xue (the Great Learning) into Latin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all by himself, and finished the first specialized version of Chinese atlas in the West.
Michel Ruggieri;Sinology;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ion
G119
A
1005-7110(2010)03-0026-07
2010-03-26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西方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翻译与传播》(项目编号:2009B2047)阶段性成果;福建省高校服务海西建设重点项目“构建翻译产品审核保障体系,改善海西跨文化交流环境”系列成果之一。
岳峰(1966-),男,福建泉州人,福建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翻译与中外关系史研究;郑锦怀(1981- ),男,福建德化人,泉州师范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中西文献交流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