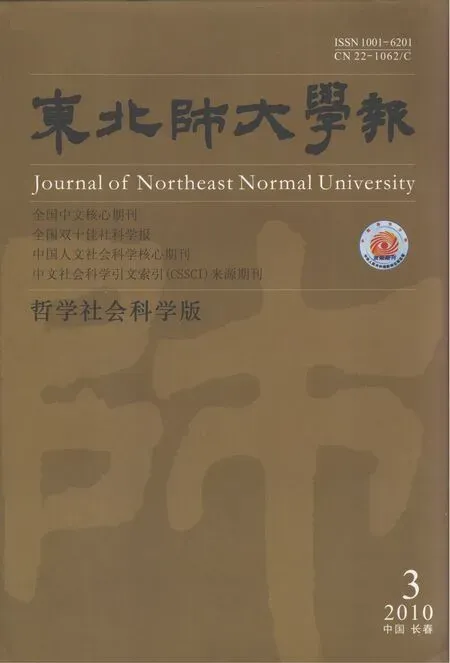左翼文学的发难:贫弱的实绩与历史的光影
2010-04-03陈红旗
陈红旗
(嘉应学院 文学院 ,广东 梅州 514015)
左翼文学的发难:贫弱的实绩与历史的光影
陈红旗
(嘉应学院 文学院 ,广东 梅州 514015)
20世纪30年代初,刚刚发难不久的左翼文学不但遭到了国民党御用文人充满敌意的贬斥、攻击和诬蔑,还受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求“看货色”的强烈质疑。发难期的左翼文学之所以备受质疑是因为其创作实绩比较贫弱,而造成这种贫弱的原因在于:文学对政治的依附和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侵蚀,国内外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偏颇的影响,尤其是左翼作家自身薄弱的才艺的限制。发难期的中国左翼文学是世界左翼文艺思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尽管它还不成熟,但它具有鲜明的介入社会、政治、人生的意识形态性质,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其自身的文学价值,也使它获得了与其艺术成就并不相匹配的历史光环。
左翼文学;发难;实绩;历史光影
1928年前后,中国左翼知识界为左翼文学的发生直接发难,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了一种不同于“五四”新文学并强化马列主义革命现代性追求的文学形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这一过程中,左翼作家力求新文学的变革和鸿篇巨著的创制,但左翼文学在一段时间内并未能显现出与新锐的世界无产阶级文学未来或辉煌的中国古典文学历史相称的艺术潜质和艺术水准,这是发难期中国左翼作家颇为苦闷和困惑的所在。
一、“拿出货色来看!”[1]
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代表着新的价值取向的左翼文学形态——“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文坛上开始逐渐流行起来。1930年,国民党御用文人提倡“三民主义文学”,同时大肆贬斥、攻击“普罗文学”,他们的言论中充满了诬蔑、构陷和敌意:“所谓新兴文学完全被一般盲目的作者戴着新的假面具借来宣传他们的主义或受某一阶级的利用。……俄国共产主义的一种革命政策,一种企图获得政权的运动——绝不是大公无私,本着研究文艺的宗旨而提倡起来的。”[2]在他们看来,“那一般创造社太阳社的狗们,受了赤色帝国主义的收买,受了苏俄的卢布的津贴,就甘心做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工具,鼓吹在中国不能适用的阶级斗争,和杀人放火式的暴动,而来破坏中国三民主义的革命。”[3]除开这类带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偏见的评论,最令当时左翼文艺界头痛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带有挑衅意味而提出的“我们不要看广告,我们要看货色”[4]的要求,这种要求包含着对左翼文艺创作水准的质疑、揶揄甚至嘲弄,而糟糕的是左翼文艺界徒然光火却难以辩驳。
对于这些贬斥、否定和质疑,30年代的左翼文艺界一直力图通过文学创作和理论建构予以反击。1933年,左翼文学发生了质的飞跃,左翼文艺界终于可以自豪地说:“我们这面”有《子夜》,“是他们所不能及的”[5]。此外,左翼文学的其他领域,如杂文和戏剧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无产阶级文化理论的译介同样显示出了一定的规模和质量。1934年,上海《中国论坛》(ChinaForum)杂志主编伊罗生(HaroldR.Isaacs)计划编辑《草鞋脚》(Straw Sandals)(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1918-1933),并请鲁迅和茅盾协助提供有关材料。鲁迅和茅盾为这部小说集收入了23个作家的30部作品,其中除了鲁迅、茅盾、郁达夫、冰心等几个成名作家之外,剩下的作者几乎都是无名的左翼文艺青年。这里,编选者希望提携左翼文艺新人的意图和殷切之情可谓呼之欲出。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该书迟至1974年才出版问世。从结果上看,它根本没有对左翼文学的发展产生什么质的影响,但在当时,对于鲁迅、茅盾乃至整个左翼文艺界而言,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很喜欢听的消息”,或曰一件充满“希望”的事情[6],这意味着中国左翼文学不但可以给批评者“拿出货色来看”,甚至可以对外国文艺界进行“文学输出”了。然而,回顾《草鞋脚》的选题目录及作家作品介绍,我们不得不承认,鲁迅和茅盾的“喜欢”与“希望”,实则突显了左翼文学发难时的低起点和创作实绩的贫弱。
与此同时,左翼文艺界的理论主张问题更多,不断受到反对者的冲击,新月派“人性论”对“文艺阶级斗争论”的挑战,“三民主义文学”倡导者对左翼作家的人身攻击,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倡导者对左翼文艺界的诋毁,“自由人”、“第三种人”对文学政治化倾向的指责,都令左翼文艺界忙于抗争和辩驳。1932年瞿秋白在反驳苏汶对左翼文艺理论界的批评时,虽然对后者的“唯心论”进行了充分有力的批驳,为文学的阶级斗争等功能进行了正名,但他在开展自己的论述之前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新兴文艺理论的发生和发展——到现在还不上三年,这里所发生的错误,而且有些是极端严重的错误,实在是多得很。”[7]事实上,进步的文艺青年所见到的多是一些左翼作家从日俄理论界抄译过来的、夹生的、断章取义的马列主义或苏俄无产阶级文论,他们所体会到的多是无谓的对骂、意气之争和宗派情绪等负面感受,所以沈从文将这些文坛纷争视为丑角、木偶戏的互相纠打,他断言这些纷争除了养成读者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以外,一无所有,文坛的“争斗成绩”不过是“把读者养成欢喜看戏不欢喜看书的习气”,他认为:“争斗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8]事后看来,沈从文指出了文坛论争中“无聊”的一面,也透视了左翼文艺界一些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左翼作家才艺的限度:“普罗文学”贫弱的本根
左翼文学发难期实绩薄弱的原因很多。多数文学史家将之归因于文学对政治的依附和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侵蚀,这是有道理的。淡化文学的审美特性,认为文学应当成为政治实践的一部分,认为文学能够完全转化为宣传和阶级斗争的工具,将文学设置在依附于政治的地位上,这些理念势必使文学的审美本质在被侵蚀后遭受无情的消解。结果,政治化思维、残酷的生存境遇、国民党的文艺统制和左翼文艺界的内耗一起,将左翼作家的文韵、灵气、美感不断功利化、简约化和粗鄙化。不过,须注意的是,仅仅将左翼作家创作实绩不高归因于政治因素的制约并不能令人完全认可,因为至少鲁迅是个例外。求证于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经典,很多作品都有清晰的政治视阈,所以将文学经典性的缺失全部归因于政治因素的制约未免将问题简单化了。
顺延寻找外在因素的思维方式,有诸多学者进一步将之归结为日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产生的偏颇的附带影响,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样难以令人完全信服。周扬说:“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无论在理论上或创作上,都还很幼稚,这是事实。然而也正就是因为幼稚,所以我们要向已经有了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的欧美各国,特别是苏俄去学习。”[9]的确,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是“幼稚”的,中国左翼文艺界也确实是以日本、苏俄等世界无产阶级文学为标尺来进行学习和创作的。可实践者为什么没有取得期许中的成就,却把那些偏颇性的东西当作真理引进中国并大肆宣扬?经过研究可以发现,左翼作家在研读外国文学名著(尤其是苏俄文学经典)和某些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过程中,经过对比、学习、揣摩、探索,发现了一些伟大作品的精神印记和美学底蕴,确立了全新的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尺度——真实性和阶级性,可惜的是,当他们借用异域的价值观念深入中国社会生活和工农生命世界时,当他们希望自己能够达到相应的精神高度时,当他们希望自己成为中国的高尔基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时,问题出现了。原来,他们在学习和模仿的过程中,捕捉到的乃是文学观念、技艺上的形似,而非对象的文化内涵上的神韵。在混乱的中国文坛和社会中,他们一方面急迫地书写庞大的国家、现代化、革命主题,另一方面也急切地把自身内在的精神感悟变成单纯的战斗情绪释放出去。结果,他们留下了不计其数的文艺半成品,这些“半成品”见证了左翼文学发难的艰难性,也见证了他们可怜的艺术才情和文学修养。有学者说:“即使处于文学历史的转折关头,即使面临着感知方式与表达方式的变化,作家本身所具有的气质、才情和修养依然是决定其文学成就的关键因素。”[10]这启示我们,左翼作家有限的“气质、才情和修养”,加之他们在构建无产阶级文学和追求异域文化价值理念在中国实现的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偏误,才是制约左翼文学成就走低的关键性要素。
左翼文学发难期的创作实绩不佳,对于这一问题,当时的批评家已经做了较为深入的究因和探源性工作。1932 年阳翰笙[11]、瞿秋白[12]、郑伯奇[13]、茅盾[14]、钱杏邨[15]以《地泉》为范本展开的对1928到1930年间“普罗文学”的批评就是例证。从这些左翼理论家的批评话语中可以看出,在肯定“普罗文学”存在意义的前提下,他们已经深刻认识到了“普罗文学”的诸多缺点和“应然性”等问题,指出了造成“文学难产”的多重原因,如作家恶劣的生存环境、认识社会现象不够全面、创作方法上选择不当、题材选取上有错误倾向、理论不够正确等。值得深思的是,这些批评家唯独没有提及作家的才情和修养问题,这并非是他们有意忽视,而是他们在思想意识里认为这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但事实表明,他们的无意忽视恰恰反衬了作家文学才能、艺术修养乃至想象力的重要性。
由于文学与政治纠葛的复杂性,左翼文学发难的艰难性及其内容形式上的时代局限性是很难避免的。问题仍在于,众多左翼作家何以如此自觉地“抛弃”文艺的诸多审美特性而将文学领域视为阶级斗争的一个“角斗场”:政治化思维方式?意识形态斗争的必然性?机械复制时代商业化后遗症?出版商要求作者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和期待视野?都有可能,但这些都是非决定性因素,因为作家主体完全可以凭借艺术才能和文化修养超越这些限制。因此,将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思、批判和“由于对马克思主义过于简化的公式的信仰”[16]233作为早期左翼作家创作实绩薄弱的原因,是没有道理的。左翼文学的发难来自于太阳社、后期创造社成员和瞿秋白等先驱者对“文学革命”的反思、批判,来自于他们将文学与革命结合起来的文化理想,来自于他们的无产阶级文化想象,来自于他们力图通过文学进行革命启蒙、阶级斗争的现代理念,也来自于他们追求马列主义革命现代性的精神诉求。在《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拓荒者》、《萌芽》等刊物上刊载的许多革命文学作品中,确实有一些概念化、宣传说教的痕迹,但左翼作家后来对这些偏颇现象有所纠正和超越,他们不再教条地宣讲大道理,而是将之内化到作品的精神深处。左翼作家要处理好阶级斗争意识和文学艺术性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困难,可这并非难以逾越的鸿沟。何况强烈的阶级意识、政治热情和主题先行未必就会阻碍作者的成功,否则,何以政治意识鲜明、“主题先行”的“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17]《子夜》会在艺术成就上远远高出同时代的其他作品?
如果将原因归之于左翼作家的文体写作技巧落后而导致他们无法真正实现对“五四”新文艺界的超越,这同样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事实上,左翼作家都或多或少地从“五四”新文学或外国文学中汲取精神营养和现代的文学技巧,他们在这方面非但不弱,相反还保有非常明显和自觉的“先锋性”追求,例如,殷夫的诗“十分注意剪裁意象,锤炼语言,兼具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的艺术风格。”[18]小说方面则更为明显,蒋光慈的《最后的微笑》、《冲出云围的月亮》,华汉的《女囚》,洪灵菲的《流亡》、《转变》、《前线》,都采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心理分析手法。当然也有例外,华汉曾在自我批判中强调自己在创作方法上没有“走唯物辩证法的现实主义的路线”。但话又说回来,“走”了又怎么样?“走”得进来,深刻认识客观现实,也只能写出小说的“新”而未必能写得出“精彩”。1933年国际和国内左翼文艺界开始批判、清理“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转而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此后,创作方法不是问题了,但留名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左翼文学经典作品仍然寥寥无几。这说明左翼文学的艺术成就与先进的创作方法并不成正比。
茅盾在《子夜》发表前后,依据他的现实主义主张,曾多次撰文批评左翼作家创作中问题“严重”,认为左翼作家选材“公式主义”,“精彩”、“个性”不够,缺少对生活的全面认识,等等。显然,茅盾的批评是有的放矢的,但这种逻辑概括并非没有漏洞,中外优秀作家的事例证实:缺少现实生活实感与题材的逼仄未必就写不出优秀的作品来,“写得怎样”归根结底在于作家精神视野上是否丰富,思想境界是否高远,艺术才能上是否突出。考察早期的左翼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们的选材是很宽泛的:从闭塞的内陆到开阔的海洋,从欲望化的都市到日渐骚动的乡村,从天灾人祸到悲欢离合,从革命启蒙到情爱绞缠,从才子佳人到英雄儿女,从改造国民劣根性到挖掘民众本性的良善,从民族国家关怀到批判个人主义……可以说,左翼作家所写的都是当时文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这种题材上的丰富性和时效性仍然不会改变我们阅读中生成的那种粗陋感或促狭感。左翼文学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模式化也被有的文学史家所定性。有趣的是,被国民党文人称之为“嚣张”的“普罗文艺”[19]就是由这些简单浅显的作品组成的。彼时,每一个左翼作家都在努力进行创新求变,左翼文学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在审美意识、思维方式上都有被拓展的机遇,但创做主体们没有做好这一点,蒋光慈、华汉、洪灵菲、郭沫若、阿英等创作的革命文学“残次品”都是例证,而根源就在于他们自身艺术才能上的欠缺。
毫无疑问,在30年代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左翼文学的“否定性”激进力量需要更加成熟的审美维度才能够被充分传递,但由于受文学才能上的局囿,在当时能够达到这一点的作家太少了。要知道:“艺术遵从必然性,然又有其自身的自由,这种自由并非革命的自由。艺术与革命在‘改造世界’即解放中,携起手来;但是,艺术在其实践中,并不放弃它自身的紧迫性,并不离开它自身的维度:艺术总是非操作性的东西。在艺术中,政治目标仅仅表现在审美形式的变形中。即使艺术家本人是‘介入的’,是一个革命家,但革命在作品中也许照会付诸阙如。”[20]这意味着要处理好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很难的,因此,瞿秋白仅只在鲁迅的杂感里发现了革命文艺的成功结构,他还进一步强调说:“革命的作家总是公开地表示他们和社会斗争的联系;他们不但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一定的思想,而且时常用一个公民的资格出来对社会说话,为着自己的理想而战斗,暴露那些假清高的绅士艺术家的虚伪。”[21]可问题在于,鲁迅的成功是以其超出常人的智慧和艺术才能作为支撑的,这不是其他左翼作家靠勤奋努力就能够实现的。
三、意识形态性与历史光影的彰显
在左翼文学发难之初,左翼文艺青年的创作很不成熟,对此,进步文艺界颇为理解。诚如鲁迅先生所言:“因为在我们还算是新的尝试,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可以看见它恰如压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虽然并不繁荣,它却在曲曲折折地生长。”[22]鲁迅的这番话是说给英语世界的读者听的,可谓意味深长、充满期望。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幼稚的左翼文学不但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还在迥异的评价机制下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和浓重的历史光影。
具体而言,在中国的现代学术体系中,对左翼文学的评述往往是两极分化的:一极是将左翼文学主流意识形态化,使其以“进化者”的姿态不断建构自身获得正义、公理、胜利的历史镜像;另一极是将左翼文学“妖魔化”,单纯地强调其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宗派主义等负面色彩。这两种叙述也是在“二项对立”思维模式下不断进行加减法的过程,前者进行的是加法,将左翼文学的细节完善并经典化;后者进行的是减法,将左翼文学肢解、弱化、抽象化乃至完全否定。很明显,这两种论述都有意无意地扭曲了左翼文学的存在本相。左翼文学作为一种“载道文学”,它固然没有那么耀眼的光环,同样也没有那么“可厌”[16]111的面孔。
实际上,左翼文学自发难之时起就有着鲜明的介入社会、政治、人生的意识形态性质。“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以后,中华民族仍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民主、自由被极权统治阶级所践踏,社会严重不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受困于物质层面,而社会、文化价值权威继续空缺,封建主义、复古思潮、虚无观念依然捆缚着时人的精神。在这个历史、文化转折的关头,“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成为激励进步青年走出困境的一种精神力量,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幼稚单薄的革命文学作品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风行和畅销。再者,“左翼文学”是“青年文化”[23]的重要载体,左翼作家有着独特的生命风度和对待人生的积极态度,如他们对健全社会的理想追求,他们将“革命”和“恋爱”结合起来的浪漫情怀,他们恨不得与旧社会一起灭亡的牺牲精神……当然,如是说并不等于美化左翼文学的缺点,而是强调我们要在特定的思想文化历史背景和民族国家关怀的宏大叙事基础上认识其不足,这才是正确把握左翼文学的前提。
从世界文学范围来看,中国左翼文学无疑是世界左翼文艺思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在中国传播的介体,它的发难有其必然性,它的产生是一种国际现象[24]。从中国国内情形来看,左翼文学是在“文学革命”口号力量衰竭后逐渐发展起来的,30年代的左翼作家们“能达到五四新文学的早期实践者们未能达到的观察深度和高超技巧”[25];左翼文学是在与通俗文学的互动互为中发展起来的,曾吸引大量的“现代”读者;左翼文学是在国民党的文艺独裁和文艺统治下艰难生存下来的,当时的作家倡导左翼文学需要巨大的勇气,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左翼文学在发难之初曾存在宗派主义、“左倾幼稚病”等诸多问题,但它能够和其他进步的文艺力量一起汇成30年代的文学主潮,这意味着它具有迥异于其他文学形态的独特精神内质和顽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的根源就在于它能够从底层民众的利益出发,以实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解放和幸福为现实目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以“五四”新文化(文学)运动和国外进步文艺活动作为它必要的实践语境和资源准备,并在艺术形式上保持一定的探索性、革新性[26]。更值得尊敬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发难者根本不企望自己的作品“不朽”,而是希望它们与黑暗的时代、社会一起“速腐”,这才是左翼文学最可宝贵的精神追求的向度[27]。
至此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发难期的左翼文学以其强韧的生命力、受众的广泛性和历史光影的驳杂性,成为一种颇具矛盾绞缠意味的存在:它既为中国文坛提供了大量半成品的文本和复杂多样的论争,也给后来者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无论好坏,都已经远远超出了其自身的文学价值,也使它获得了与其艺术成就并不相匹配的历史光环。
[1]鲁迅.汉字和拉丁化[A].鲁迅全集:第5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57.
[2]陈穆如.中国今日之新兴文学[N].民国日报,1930-05-14.
[3]管理.解放中国文坛[N].民国日报,1930-05-14.
[4]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J].新月,1929(9):10.
[5]鲁迅.致曹靖华[A].鲁迅全集:第12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48.
[6]鲁迅、茅盾关于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的书信和资料手稿[J].文献,1979(1):12.
[7]易嘉.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J].现代,1932(10):781.
[8]沈从文.谈谈上海的刊物[A].沈从文文集:第12卷[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177.
[9]周起应.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读《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J].现代,1932(10):796.
[10]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20.
[11]阳翰笙.《地泉》重版自序[A].阳翰笙选集:第4卷[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71-77.
[12]易嘉.革命的浪漫谛克——《地泉》序[A].阳翰笙选集:第4卷[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77-81.
[13]郑伯奇.《地泉》序[A].阳翰笙选集:第4卷[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81-83.
[14]茅盾.《地泉》读后感[A].阳翰笙选集:第4卷[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83-88.
[15]钱杏邨.《地泉》序[A].阳翰笙选集:第4卷[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88-92.
[16]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编译.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
[17]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172.
[18]程光炜.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72.
[19]陶愚川.如何突破现在普罗文艺嚣张的危机[N].民国日报,1930-08-06.
[20][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64-165.
[21]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A].瞿秋白文集:第3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978.
[22]鲁迅.《草鞋脚》小引[A].鲁迅全集:第6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0.
[23]王富仁.创造社与中国现代社会的青年文化[A].王富仁自选集[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93.
[24]孔海珠.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是一种国际现象[J].学术研究,2006(8):125.
[25][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478.
[26]姬蕾.论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的影响[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155.
[27]杨卓.新文化运动中舆论领袖引领方向的启示[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125.
The Left-wing L iterature Rising in Revolt:Poor and Weak Achievement and Historical L ight and Shadow
CHEN Hong-qi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College of Jiaying University,M eizhou 514015,China)
A t the beginning of 1930's,the left-w ing literature just rising in revolt not only encountered the Kuomintang hired scribblers to fill with hostility to demote,to attack,and to slander,but also had
the intense question by Chinese liberal intelligentsia requesting“to look at the goods”.The reason w hy the left-wing literature rising in revoltwas intensely questioned was because of its poo r and weak creation actual accomplishments,but created this kind of poo r and weak reason to lie in:the literature to the political attachment and the political ideology to the literature co rrosion,the biased influence of domestic and fo reign proletarian literary and art movement,particularly left-w ing w riters'weaknesses in talent and skill.The Chinese left-w ing literature rising in revoltwasan o rganic partof the left-w ing trend of thought in literature and art of the wo rld,although it was not mature,but it had the bright ideology nature to involve the society,the politics,and the life,its influence had already far exceeded itsow n literary value,also caused it to obtain the historical glo ry w hich the artistic achievement did notmatch.
left-w ing literature;rise in revolt;achievement;historical light and shadow
I206.6
A
1001-6201(2010)03-0112-05
2009-12-0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09YJC751035);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青年项目(08YJ-04)
陈红旗(1974-),男,吉林双辽人,嘉应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张树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