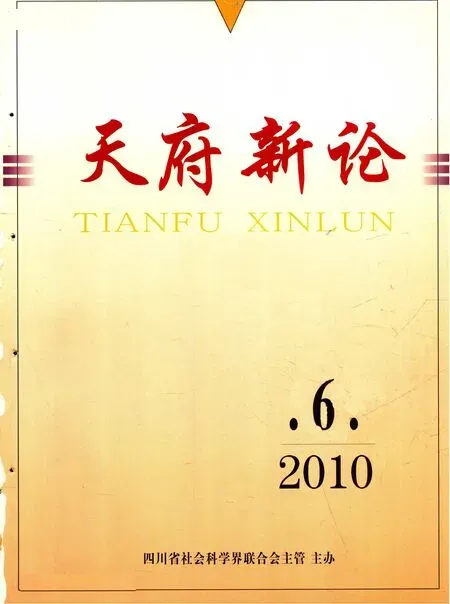巴蜀文学奇特、虚幻的审美精神及其思想渊源——以司马相如辞赋创作为例
2010-03-22李天道
李天道
巴蜀文学奇特、虚幻的审美精神及其思想渊源
——以司马相如辞赋创作为例
李天道
由于巴蜀地域文化的影响,巴蜀文学审美思想极为注重内心体验,强调于空明澄澈的审美心境中营构审美意象,在一种永恒超远的时空结构中“苞括宇宙”,“总揽人物”,以穷极宇宙的微旨。正是这种虚静空灵的审美态势,使巴蜀文人在审美创作构思方面形成“架虚行危”、凌虚翱翔的极具地域特色的审美想象活动方式,并突出地呈现出一种奇特虚幻的审美精神。
地域文化;架虚行危;奇特虚幻;奇特虚幻
受巴蜀地域文化心理的影响,巴蜀文学审美思想极为注重内心体验,强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司马相如语,见《西京杂记》卷二)的心灵感悟,要求审美创作者应在一种“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1〕的空明澄澈的审美心境中营构审美意象,在一种永恒超远的时空结构中“苞括宇宙”,“总揽人物”①据《西京杂记》卷二记载:“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以穷极宇宙的微旨。正是这种虚静空灵的审美态势,使巴蜀文人在审美创作构思方面形成“苞括宇宙,总览人物”与 “架虚行危”、“气号凌云”、凌虚翱翔等两种主要的、极具民族地域特色的审美想象活动方式。前者强调“应物斯感”、“联类无穷”,要求,“睹物兴情”,重视由所见而生发开去,认为审美创作者必须感物起兴,以当下的观物为审美创作构思的契机,并由此以展开审美想象活动。而“架虚行危”、“气号凌云”的审美构思则强调“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虽然生在当世,却可以悬想千载,洞古察今,尽管身居斗室,却可以臆测宇宙,上天入地,“凭虚构象”,“心生言立”,“穷于有数,追于无形”,“我才知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要求从心灵出发,而起浩荡之思,生奇逸之趣,是一种偏重于心灵构想的审美想象方式,并突出地呈现出一种奇特虚幻的审美精神。
(一)
应该说,奇特虚幻是以司马相如的创作为主要代表的巴蜀文人及其文学创作审美精神的一种突出呈现。据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其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这就是说,司马相如喜欢运用“虚言”,“空藉” “乌有其事”和“无是人”来“推”想“事”“义”,熔铸审美意象,表现审美意旨,营构审美境域。同时,从其赋作也可以看出,司马相如主张辞赋创作构思应充分发挥创作者的审美想象力,去“下峥嵘”、“上寥廓”、“视眩眠”、“听惝恍”、“乘虚无”、“超无友”(见《大人赋》), “视之无端,究之无穷” (见《天子游猎赋》),以架虚行危,凭虚构象。如他的《大人赋》就通篇都是想象之辞,其辞为,“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弥万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轻举而远游。垂絳幡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浮。建格泽之长竿兮,总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为幓,抴慧星而为髾。……”于是,这位大人“邪绝少阳而登太阴兮,与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转兮,横厉飞泉以正东。悉征灵圉而选之兮,部乘众神于瑶光。使五帝先导兮,反太一而从陵阳。”“历唐尧于崇山兮,过虞舜于九疑。”“遍览八紘而观四海兮,朅度九江越五河。”入帝宫,登阆风,“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咀噍芝英兮叽琼华”。从这种审美观念出发,因此,他在辞赋创作中喜欢将神话、历史融合到描写对象之中,虚实结合,在一篇 (一段)语言摹写中有铺陈,而更多的则是夸饰和架虚行危、凭虚构象的想象。如《子虚赋》对楚王校猎场面的描写:“于是乃使专诸之伦,手格此兽。楚王乃驾驯驳之驷,乘雕玉之舆,靡鱼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阳子骖乘,纤阿为御。案节未舒,即陵狡兽,辚蛩蛩,蹴距虚,轶野马而轊騊駼,乘遗风而射游骐。”这里,专诸是古代吴国刺客,阳子是秦穆公臣,纤阿是传说中的善御者;干将、乌号、夏服分别是传说中的宝戟、名弓、劲箭;蛩蛩、距虚、野马、騊駼、遗风、游骐,都是神话或传说中的兽名。足见作者想象力的丰富。即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夸饰》篇中所指出的:“相如凭风,诡滥愈甚。”又如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所指出的:“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对其《大人赋》,扬雄曾批评说:“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飘飘有凌云之志。”(见《汉书·扬雄传》)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中也指出:“相如赋仙,气好凌云。”当然,从传统讽谏的原则出发,“相如赋仙,气好凌云”,正应了“劝百讽一”这句话,可谓适得其反。不过,若转换一个角度,能使人“飘飘有凌云之志”者,则正是相如赋仙之作善于想入非非,凭虚架危,规矩虚位,刻镂无形,抟虚成实,从而才给人以思逸神超、亦真亦幻、飘飘然生凌云之志的审美感受。
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形容东方虬的《咏孤桐篇》诗云:“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听,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长期以来,人们只在这段话中所谓的“兴寄都绝”处寻找微言大义,却忽略了其后半段的文辞意义。认真分析起来,这里所谓的“骨气端翔”,与刘勰所指出的“相如赋仙,气号凌云”就有那么一些神秘而密切的联系。如果说“端”可以理解作刘勰所谓“结言端直”之“端直”的话,那么,“翔”就是对司马相如创作“赋仙”一类辞赋,任想象自由驰骋,“架虚行危”、“气号凌云“、凌虚翱翔的生动摹写。
司马相如认为:“赋家之心,苞括宇宙。”“苞括宇宙”,显然是极言艺术想象的审美包容性,具象的描述了艺术想象时空的巨大,以及艺术想象的自由驰骋。即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所指出的:“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神妙的艺术想象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一任心灵的羽翼,在辽阔无垠的宇宙中自由飞翔。刘勰以后,想象丰富奇特的巴蜀诗人李白则用“俱怀逸兴壮思飞”来表述诗歌创作中想象的自由驰骋。李白“俱怀逸兴壮思飞”和另一位巴蜀诗人陈子昂所谓的“骨气端翔”,都是用飞翔的意象来描述艺术想象的自由驰骋。可见,从“相如赋仙”始,到陈子昂之作“方外十友”和李白被称为 “诗仙”,在中国古代特定的巴蜀地域文化背景下,飞翔的意象因此而必然反映着道家或道教文化的信仰及心理,这一层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以飞翔意象来描述或解说艺术想象的超时空现象,最终都出自一种原因,那就是“文以气为主”的基本观念。
曹丕在《典论·论文》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深入分析这段话,则不难发现,在文学审美创作与“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气”之间,曹丕引进了一个具有中间性的艺术表现形式,即“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 “音乐”。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魏晋时期的文学创作理论之所以喜欢以“音乐”为喻,追溯起来,其根源还在上古时期声音分“清”分“浊”之说。相传黄帝时,由伶伦截竹为筒,以筒之长短,分别声音之清浊,高下,乐器之音,乃据以分阴阳各六,阳为律,阴为吕,合称十二律。《左传·齐侯二十七年》载:“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梁丘据不然,君所谓可,梁丘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梁丘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这就是说,创作一首歌和煲制羹汤一样,也应该“和而不同”,把不同的音乐元素结合起来,作到:控制气息,把握阴阳,懂得风雅颂三类,使用金石丝竹五种乐器,使宫商角徵羽五声 (即阴阳上去入五声)相变相化而相辅相成,和谐完美地融合为一体。这样:声音有清浊,有大小,节奏有短促和绵长,速度有急速和徐缓,情感有悲哀和快乐,有柔弱和刚強,呼吸有出入,速度有长短,音调有高低,节奏有疏密,声音变化取长补短,把不同音乐要素巧妙地安排搭配。君子听了这美妙的声音,可以使心情愉悦,心情愉悦就有了平和的德性。
据《黄帝内经》记载,人的五脏各有不同的声音,其声音也有清浊之分。据此,《荀子·正名》云:“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对于声音有 “清浊”之分的现象,《礼记·乐记》解释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于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之所以这样,是由于“音”生于人心,感情生于心中,从而才发出 “声”。由于 “声”有清浊,表现出来则有文采,就才是“音”。“音”既生于心,因此审“音”就可知政治。所以国家安定其乐则安静而欢乐,说明治理得好;国家混乱,其乐则怨怒,说明其政治乖僻;将亡之国,其音悲哀而思旧;人民生活困苦,声音情绪是与政治相通的。以此对照于曹丕之说,所谓“引气不齐”,显然是就“声音清浊”,即完全个体化的“声音清浊”而言的,也正由于此,所以“文以气为主”。
审美创作中,作用于创作者之 “气”的氤氲、薄靡、凝滞,从而生成“骨气端翔”而“俱怀逸兴壮思飞”的奇特、虚幻审美想象。的确,在古代宇宙论中,“气之清浊有体”就意味着“道集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 (扬)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淮南子·天文训》)这种元气混沌而清浊分异为天地的宇宙生成观念,原是人们所熟知的,而正是这里的“清扬”与“重浊”之分,从深层观念上确定了元气清扬而飞翔的思维定势。完全可以这样说,轻扬而飞翔,高引而升腾,但凡所有指示向上一路者,都将与 “清”之概念有缘了。意气峻爽,是向上一路,慷慨激昂,也是向上一路,凌虚飘渺,也还是向上一路,在这个意义上,奇特、虚幻审美想象的超时空性,最终也只能概括为令人振作奋发而使意气飞扬的审美体验。一言以蔽之,“风清骨峻”之“风清”就是精神之自由翱翔。具有独特个性的审美创作者,其最为难能可贵的精神,就是在审美创作活动中往往采用超现实的构思方式以营构审美意象。所谓超现实,就是在审美意象营构中不随同于现实,也不屈从于现实,当然,也不因个人意气而嫉恨于现实。作为具有独特个性的审美创作者的超越意识要求他决不因循于既定之审美诉求,这里因此就有了创造性意义上的情景、心物、意象的统一。尤其重要的是,司马相如之作为独立的审美创作者,又是与其人格清浊的辨别意识相同一的。即如庄子一样,在对“怨邪非邪”“是邪非邪”的难题表示了其怀疑性的思考之后,他的辞赋创作虽以类相从而丰富多样,但其审美想象的超迈,最终还在“虚廓”之“生气”上。
(二)
“架虚行危”、“气号凌云”、凌虚翱翔的想象活动与“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想象活动是不同的,后者的“宇宙”与“人物”等,偏向于形象的显现,而“架虚行危”、“气号凌云”、凌虚翱翔的想象活动中的“架虚”、“凌云”、“凌虚”则象虚而物实,偏重于心灵的表现,追求在飘逸的用思中创造意与象融的“金相玉式,艳溢锱毫”的杰作。它要求在不思不想、“寂然”“悄焉”中,以“虚静”空明的心境洞见宇宙生命真谛,在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神思方运中直视古今,达到无所不想其极的审美境域。“通”不是思绪的具体展开,而是心灵的自由飞跃,自致广大,自达无穷;也是深层生命意识的涌动,“枢机”方通,“关键”畅开,在无意识中让自我情愫飘逸到最渺远的所在,在追光蹑影,蹈虚逐无,“规矩虚位,刻镂无形”(《文心雕龙·神思》)中完成审美创作构思活动。司马相如在写作《上林赋》、《子虚赋》时,就出现“意思萧散”,“忽焉如睡,焕然而兴”的精神状态。受到这种诗情的鼓荡,他便快捷地完成了该诗的创作。
“架虚行危”、“气号凌云”、凌虚翱翔的想象活动和夸饰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认为,想象是一种思维过程,夸饰是一种修辞手法。夸饰有时离不开想象,例如说甘泉宫如何如何高峻,以至鬼魅不能自逮,半途下颠,鬼魅云云就是借助于想象。但想象又不完全是夸饰,夸饰是以现实为基础的夸张增饰,想象则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文心雕龙·神思》)。《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里的“象”就是虚灵的。所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惟恍惟惚”。《淮南子·天文训》说:“古未有天地之时,唯象无形。”有象但是却没有形,可见“象”实际上是没有其物,没有其形的,而是“心意”突破景象域限所再造的虚灵、空灵境域。正因为它是虚灵的,所以通于审美境域。庄子就继老子“大象无形”说而提出“象罔”这个哲学概念。庄子认为仅凭借视觉、言辩和理智是得不到“道”的玄奥境域的,必须 “象罔”才能得之。所谓“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庄子·天地》)。庄子标举的“象罔”境域在有形无形、虚与实之际。成玄英《疏》云:“象罔,无心之谓。”“象则非无,罔则非有,不缴不昧,玄珠 (道)之所以得也。”宗白华进一步加以阐释说:“非无非有,不皦不昧,这正是艺术形相的象征作用。‘象’是境相,‘罔’是虚幻,艺术家创造虚幻的境相以象征宇宙人生的真际。真理闪耀于艺术形相里,玄珠的皪于象罔里。”〔2〕“虚幻的境相”可以说正好是“架虚行危”、“气号凌云”、凌虚翱翔的想象活动中“象”的最恰当的解释。和“苞括宇宙,总览人物”不同;“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是依附于视听等感知觉的直观体验,是 “宇宙”与“人物”,即自然天地与社会生活给创作者提供一个“联类不穷”的场所,一个“文思之奥府”,创作者在此 “意思萧散”,“忽焉如睡,焕然而兴”向 “物沿耳目”、“物无隐貌”、物我陶然相融、氤氲满怀的审美境域升腾;而 “架虚行危”、“气号凌云”、凌虚翱翔的想象活则已经超越了这种境域,是在激荡中心灵自由飞跃,向更高层次上的升华,是心与象通,心灵与意象融贯,意中之象与象外之象凝聚,审美心态到宇宙心态贯通。庄子把这种审美境域创构活动称做“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刘勰则称此为“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独”是就心而言,它是指一种超越概念因果欲望束缚,忘知、忘我、忘欲、忘物,“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胸中廓然无一物”,以“遗物而观物”的纯粹观照之创作者;“天地精神”与“意象”相同,就“象”而言,都是指超越一般客观物象的永恒生命本体,是自然万物所具有的共通的自然之“道 (气)”;共通的创作者意识和共通的自然之“道”又具有深层的共通;即宇宙意识与生命意识的同构。也正因为这样才促使了物我互观互照的共感运动和心灵飞跃,即刘勰说的“神用象通”。
由此可见,具体说来,司马相如辞赋创作中的“架虚行危”、“气号凌云”、凌虚翱翔的想象活动,就是指审美创作者“疏瀹五藏,澡雪精神”,通过 “驰神运思”的心灵体验,神游默会以体悟宇宙万物间的生命内涵与幽微哲理。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说:“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在《文心雕龙·隐秀》篇中又说:“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在《文心雕龙·养气》篇中说:“纷哉万象,劳矣千思。”从这些论述中也可以看出,司马相如“架虚行危”、“气号凌云”、凌虚翱翔的想象活动,其“架虚”“凌云”“凌虚”中所凭借的就是刘勰“神用象通”中所谓的 “神”,是指一种自由的精神。有时刘勰也用“神思”,或者用“神理”、“神道”、“神明”、“神气”、“千思”、“心术之动”等来表述。而所谓“神用象通”,就是指审美创作者于“从容率情,优柔适会”的空明虚静的心境中,一任自由平和之心灵跃入宇宙大化的节奏里,以“穷变化之端”,去“穷于有数,追于无形”、“源奥而派生”,“神道阐幽,天命微显”;在刘勰看来,“神用象通”,是去体悟“道 (气)”这种自然万物的生命本原,领悟宇宙天地间最为神圣、最为微妙的 “大音”、“大象”也即“大美”,从而表现为达到“万物为我用”、“众机为我运”、“寄形骸之外”、“俯仰自得”、“理通情畅”的审美境域的一种心灵体验方式。这种心灵体验方式的最大特色是“规矩虚位,刻镂无形”,追虚捕微,抟虚为实。即如桓谭《新论》所指出的:“夫体道者圣,游神者哲,体道而后寄形骸之外,游神然后穷变化之端。故寂然不动,万物为我用,块然之默,而众机为我运。”又如嵇康《赠秀才参军》诗所云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在我们看来,所谓“游神”、“游心”,也就是:“神用象通”的“神通”。
在中国古代哲人看来,作为宇宙万物生命本原的“道”,是不可能通过感知觉以把握到的。《文心雕龙·征圣》篇说:“天道难闻,犹或钻仰。”《文心雕龙·夸饰》篇说:“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创作者要在创作构思活动中把握并领悟到深藏于自然万物深层内核的“道”这种生命真谛,则必须借助于心灵。《文心雕龙·知音》篇说:“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了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人凭借感知觉能把握客观事物的形状。而对蕴藉于形状之内的“理”也即生命本原“道”的把握,则只有依靠心灵之光的映照。“心敏则理达”,“神用则象通”。佛教教义云:“神道无方,触象而寄。” (慧远:《万佛影铭序》)在佛教看来,法身 (佛的性相)是超乎物外,无形无名,无所不在的,所以如来佛显迹于各种各样的场合,冥寄于非有非无之间。佛教所揭示的人生真谛就有如道家所谓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可得而不可见’,“可传而不可受”。“神道无方”。它是宇宙自然生命节奏和旋律的表现,故不许道破,不落言诠,而是将这种“神道”也就是人生真谛、宇宙之美,也即佛理即“神道”与佛象浑融一体,借助佛象以表现佛理即“神道”的庄严、崇高,及其生命奥秘,从而把佛教具象化、生动化,以产生其巨大的感染人的力量。因此,这种佛教效应并不仅仅限于对佛教塑象的敬畏,以及由此而来的顶礼膜拜;也不仅仅限于对佛理的图解。就佛理所揭示的人生直谛与宇宙之美来说,它还要指向更高处,即取“象”外之义。这是因为,佛家以超脱为旨归,不执着于物象,而认为“四大皆空”,“一切如如”,故贵悟不贵解,以“求理于象外”。这种象外之理,能启人深悟,但不易为言语所表边,人们只有凭借心灵的俯仰去迫寻与体悟,于空虚明净的心态中让自己的“神”与象外之理汇合感应,从而始能心悟到这种象外之理,也即宇宙间无言无象的“大美”。相传当年佛祖释迦牟尼在灵山聚众说法,曾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而笑,默然神会。此即佛在心内,不在心外,故不假外求,不立文字,世尊拈花,迦叶微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求理于象外”、假象以通神的典型事例。这种假象以通神,而神余象外的审美观念,在六朝绘画美学思想中较多。如宗炳强调“神超理得”;谢赫则提出“取之象外”;刘勰则吸收这种思想到文学审美创作中,提倡“思表纤旨,文外曲致”、“文外之重旨”、“义主文外”、“情在辞外”(《文心雕龙·隐秀》),并提出审美创作体验应“神用象通”,凭虚构象。正是受此影响,遂形成后来唐代诗歌美学思想中的“象外”说。如贾岛的 “神游象外”、皎然的“采奇于象外”、司空图的“象外之象”、“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等等。
〔1〕李天道.司马相如辞赋美学思想的现代阐释 〔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5,(4).
〔2〕宗白华.艺境 〔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59.
I207.22
A
1004—0633(2010)06—150—04
2010—07—22
李天道,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四川成都 610066
(本文责任编辑 刘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