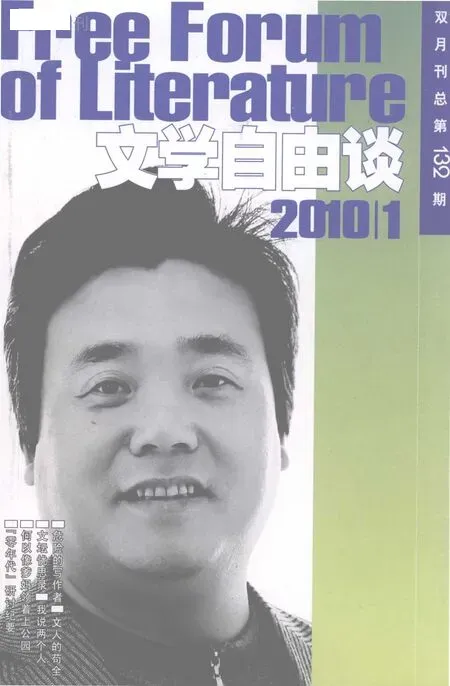有"光"的文学
2010-03-21张浩文
●文 张浩文
奥古斯丁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奠基者,和所有虔诚的基督徒一样,他对宣扬世俗激情的文学作品深恶痛绝;一般基督徒只把这种憎恨保留在腹诽或者口头谴责的份上,可奥古斯丁是非洲大主教,他的愤怒更加深刻,口诛已不足泄愤,因此必须笔伐——他觉得必须把世俗文艺的罪恶公诸天下,这样才能避免更多纯洁的灵魂受其玷污。大概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有幸看到了一部在世界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控诉世俗文艺罪行的檄文——《忏悔录》。
这真是一个悖论:骂文学的书是用文学的形式写成的,恰恰因为是骂文学的,所以才在文学史上有特殊的价值。我们一般都知道卢梭的《忏悔录》很有名,可很少有人注意到无论是在文体还是内容上它其实都是模仿奥古斯丁的。如果我们认为卢梭的《忏悔录》是文学名著的话,那么我们也就无法否认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也是经典——它不光是文学经典,而且还是哲学和神学经典。
奥古斯丁创造了一种文体,这种文体把叙述、描写、抒情、议论兼容并包,把激情、哲理、信仰、直觉熔为一炉,我们今天把它叫做随笔,叫做跨文体写作,而且我们今天已经把它操练了20个世纪了,可如果回头去看看,把自己经常自鸣得意的那种也叫做随笔的东西跟奥古斯丁比较一下,无论是技法和境界,自知之明的人都会感到脸红的。
在《忏悔录》里,奥古斯丁对自己少年时期沉溺于希腊文学作品、特别是那些描写爱情的神话和史诗之中不能自拔悔恨不已,那时候他单纯幼稚,被文学作品魅惑得废寝忘食、失魂落魄,经常为主人公的命运担忧、哭泣。可是成年之后他终于醒悟了,识破了文学骗人的把戏:一切都是虚构的,更可恶的是它把人卑劣的情欲强加在神身上,为人的堕落开脱罪责。
我们不能责怪奥古斯丁,以为他不懂文学,只要是读过《忏悔录》的人,无不为其充沛的激情、宏博的气势、形象的比喻、犀利的辩驳而折服,没有高超的文学造诣的人是不可能写成这样的美文的。其实奥古斯丁和柏拉图一样,都是文学大家,是文学的道德至上主义者,他们正因为爱文学所以才恨文学——文学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和社会影响力,所以没有道德内涵的文学作品才贻害无穷!奥古斯丁所面对的现实要比柏拉图糟得多,希腊文化尽管有尽情享乐的原欲型一面,但毕竟有苏格拉底、狄奥根尼、亚里士多德等圣人的理性节制,它坏不到那里去;但可怜的罗马人基本上都是一些武夫和建筑工,他们除了没完没了的厮杀就是到处盖房子,然后把俘虏来的异族男人投入角斗场或者采石场,把那些漂亮的女俘虏藏在他们富丽堂皇的宫殿里尽情享用。他们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征服了希腊,却敬畏地拜倒在希腊文化的脚下,他们懒于进行文化创造,就借坡骑驴把希腊文化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可一帮粗人眼中的希腊文化就是感官享受——神人狂欢、美酒美女、偷情纵欲,他们把希腊文化里原欲的一面酿造到了极致,以至于罗马后来真成了酒池肉林、淫窟艳园,不要说偷情滥交,就连同性恋也成了时尚,后来的许多电影,如《埃及艳后》、《角斗士》、《斯巴达克斯》等对此都有真实的描绘。罗马人与其说是亡于蛮族入侵,不如说是亡于自己的骄奢淫逸。这真有点文化诅咒的味道: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人,却被希腊的文化摧毁了。希腊文化的原欲在希腊人自己是生命的动力,对罗马人而言却是致命的毒药。
奥古斯丁面对如此糜烂的罗马现实,他不从罗马自身寻找原因,却认为这一切都是希腊文学惹的祸,所以他的怒火喷向了荷马及其同伙。在诅咒完充斥情欲和物欲的希腊文学之后,奥古斯丁提出他心目中理想的文学:超越感官,皈依灵魂,从有限达到无限,从杂乱达到整一,从此岸引升彼岸;一句话,从世俗生活仰望天堂,那里才是真善美的统一。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把这样的文学称做有“光”的文学,“这光,不是肉眼可见的、普通的光……这光在我之上,因为它创造了我;我在其下,因为我是它创造的。谁认识真理,即认识这光;谁认识这光,也就认识永恒”。
这“光”实际上就是上帝之光,精神之光,灵魂之光。
一部《忏悔录》最有价值的就在这里,判别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不仅仅看它形式的华美,还要看它道德的取向,不仅仅看它激情的畅酣,还要看它理智的节制。奥古斯丁几乎是用泣血的呐喊完成他的论题的,我们可以质疑他的宗教立场,但我们无法不感动于他诚挚的态度和焦灼的激情。
在我今天重读这一不朽的经典时,我耳边呼啸的是我们社会欲望的喧哗,这种骄奢淫逸的氛围日甚一日;而我们所谓的文学又在做着什么事情呢?这种文学还有没有灵魂的“光”?
当年罗马的欲望马车正在狂奔时,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似乎来得晚了一些,罗马人还没有来得及借“光”看见自己的灵魂时,帝国的马车就栽进了万丈深渊;可入侵的蛮族却是幸运的,日耳曼人与奥古斯丁的相会正当其时,他们在罗马的废墟上选择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他们克制自己的欲望终于为日后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及资产阶级崛起积聚了强大的力量。
我们能有这种幸运吗?我们能有这样一本触及灵魂的书吗?即使万幸有了,我们有多少人愿意耐心地把它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