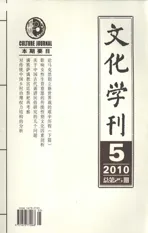关于中国古代谣谚民俗研究的几个问题
2010-03-21王凯旋
王凯旋
(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1)
谣谚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社会风俗研究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在古代社会众多领域的描述和研究中其功能又是多方面的,这当中既有史学的功能,又有文学的与民俗的、社会的、人文的等多种功能。如何看待、分析、研究和应用中国古代谣谚资料,以便在更为客观真实的基础上诠释和复原古代社会历史和社会风俗的自然面貌,因而对古代谣谚的重新认识和挖掘便显得尤为重要。学术界对于古谣谚的认识与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成果,但应当说就谣谚与古代社会历史与古代社会风俗的整体研究而言,其不足仍然是十分明显的,对于与其相关的学术认识仍然是不完整的,其学术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仍然是较为薄弱的。有鉴于此,本文拟就相关的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学术界的相关同道。
一、如何看待谣谚的史料价值及其史料应用
长久以来,许多学者都十分重视对谣谚的分析和研究,并为此发表了数量不等的学术论著和学术文章,但相关的论著和文章则大多数是从文学艺术的视角对古代谣谚加以研究,诸如对古代谣谚的文学价值、创作手法、地域特点、歌咏形式等方面的比较探讨,而少有对古代谣谚所反映社会历史与民俗民风的综合系统的研究。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在对谣谚史料的价值认识上的偏差所造成的,以民歌谣谚的版本与分类为例便可看出,著名民歌谣谚专家薛冰先生说:“从现存民歌版本的实际看,不说明代以前,清代以至民国版本也难得一见,我搜集二十余年,所得四百余种中,旧本也不过十分之一。所以需要解决的就是数量巨大的当代出版物分类问题。这些出版物,固然有相当一部分由正规出版社正式出版,更多的则是由各地区、机构、团体以至个人自行印制的非正式出版物。这种情况,仅见于民间文学和艺术类图书,在其他各类出版物中,是看不到的。”[1]可见,将民歌谣谚仅作为文学艺术门类的单一研究现象是十分突出的。
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判定历史资料的价值种类一为文献材料,二为考古资料,也包括诸如甲骨文金文和简牍帛书一类的古文字资料。这样的划分不是狭义的,更不是绝对的,比如从秦汉史研究的角度说,汉代的符玺、封泥本不在通常的史料范围内,但对研究汉史者来说,符玺和封泥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类似的情况如汉代出土的画像砖刻与画像石刻也是如此。因此,就谣谚所反映的社会历史情况的真实性而言,它无疑是价值珍贵的历史资料。清代学者杜文澜辑有《古谣谚》一书,将散见于各朝各代正史与其他文献的谣谚材料汇于一书,可见杜氏已深味其中的史料价值,《古谣谚》也成为目前有关古代谣谚最为详瞻、最为权威的辑本,且有些谣谚已在原始文献中佚失,因而愈显其弥足珍贵。
我们说古代谣谚之所以成为价值珍贵的史料,一是它的真实性,杜文澜在《古谣谚》一书中记载反映汉代选举情况的谣谚:“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2]汉代选举的真实情况是否如民谚所说呢?《后汉书·梁冀传》记载说“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梁冀失利后,“其他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外戚操纵选举之滥由此可见一斑。汉代宦官左右选举,史称宦官“割裂城社,自相封赏,父子兄弟,被蒙尊荣,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3]东汉时,政府竟公开卖官,汉灵帝时“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4]汉代选官如此之滥,所以当时人葛洪才说:“灵、献之世……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5]可见,这则谣谚是对汉代选举最为真实并最具鞭挞力的写照,其理论概括在所有关于汉代选举文献的史料记载之上。反映汉代选举的谣谚也是刻画得入木三分,如“头白皓然,食不充粮。裹衣褰裳,当还故乡。圣主愍念,悉用补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黄”。[6]所述汉代士人追逐功名,以读书为进身闻达之途是汉代历史的真实写照。谣谚的真实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其史料价值的准确性超过了已有的古文献记载,因而谣谚本身不仅仅是民人的口头传唱和吟诵,而恰恰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借助谣谚对古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民风习俗做广泛深入的研究不但是可能的,也是可行和必要的。其二,古谣谚之所以成为价值珍贵的史料,还在于它的客观性。我国传统的正史文献因其政治的和历史的原因,常常有曲笔回护之载,因而许多文献记载本身并不能客观地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记录和评论,由此而使文献本身的可依据性大打折扣。古代谣谚集于众口,其记载不须隐匿,更无巧饰曲笔之过,其写实特征十分突出。如东汉顺帝一则童谣直斥当时世风“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7]“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免治生。何以孝悌为,财多而光荣。”[8]这样的谣谚正是对汉代世风最为直观的写照。而在同时代的汉代文献中却几乎看不到这样的文字记载。谣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备着“实录”以及“秉笔直书”的特点,只不过直书的作者不是官府,不是哪一个人,而是社会中的民人,是大众。
谣谚的史料权威性决定了这种史料完全应当应用于历史、社会和民俗民风的学术研究中。就谣谚的主要特点而言,其社会民俗性是基本的和主要的内容,因而在社会民俗史研究中,谣谚便成为支撑社会民俗史研究的最为坚实可靠的史料来源。同时谣谚史料的多样性也传递着民俗史研究的目标信息,可以为民俗史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课题,这一点也往往是正史和其他史料无法提供的。
二、谣谚的民俗研究、文学研究与史学研究之关系
谣谚同时具有文学性、史料性和民俗性,这是由谣谚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因而对古代谣谚的考察和研究就不应当是孤立的和片面的,而应当是综合的和多视角的。这样说,并不是没有侧重,也不是不讲专业和学科特点,而是要说明谣谚不单单是文学概念中的种类,也不单单是世井乡俗中的传诵和散曲,谣谚本身更是一部社会史,正如《诗经》反映先秦时期社会历史和社会民俗一样,谣谚的功能也是社会的和民俗的。
我们说研究民俗离不开谣谚,因为谣谚的内容恰是民俗的和大众的生活,但反映民俗事象和民风民情的谣谚并不等同于乡间俚语,其表现形式很多时候则至为优美,谣谚词语很多情况下可以入曲也正是这个道理。由于此,谣谚便常常成为人们口头传说传唱的重要形式,除了其本身内容足以吸引人们之外,其表现形式的优美多样也是谣谚得以流传的重要原因。因而谣谚在事实上成为中国古代民间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可以说,作为民俗民风传播载体的谣谚,其传播方式便是文学的。所以说,民俗谣谚的研究既是民俗的,又是文学的。
谣谚民俗研究应当也必须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的民俗都是社会历史的民俗,所有反映民俗事象的谣谚也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谣谚。社会史研究在更大的理论层面上讲是对社会生活史(也有说社会风俗史)加以研究,社会的风俗事象自然是社会风俗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因而谣谚所反映的民俗事象是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民俗事象。离开了一定条件下的社会历史环境,所谓的民俗谣谚也是无法理解的。可见,谣谚民俗研究不能只就民俗来研究民俗,不能只就谣谚来研究谣谚,更不能只关注谣谚的文学特征而忽略了它的民俗性和历史性。谣谚民俗研究应当也必须充分关注民俗与历史的结合,关注在民俗表象背后的深层社会历史环境,把握民俗文化变化发展的历史脉搏。如此,谣谚民俗才可能达到更高的研究水平。
正确处理谣谚的民俗研究、文学研究和史学研究之关系,并不是要机械地和教条式地强调它们的结合,而是说明在侧重点和学科专业不同的情况下,对谣谚民俗的研究应当有所不同。问题在于,不能将这种学科专业的要求与对谣谚民俗的研究对立起来。我们认为,在学科方向明确的前提下,对谣谚民俗的研究充分兼顾到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能够做得到的。事实上,谣谚本身的特点也在客观上要求研究者们应该并且必须这样做。以谣谚文学研究为例,古代谣谚属文学史的范畴,而文学史上所发生的文学现象又是在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它就必然要和当时当地的社会和历史发生关系。因而也就不可能抛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去做所谓的纯而又纯的谣谚文学研究。如果有这样的研究,也大多是价值不高的。我们所说的整体研究和有机联系并不是要面面俱到,而是一个研究宗旨和原则,只有用整体的观点、联系的观点来看待和实践谣谚民俗研究,才有可能达到更有深度和广度的学术研究目标。
三、谣谚地域与民俗地域之特点
中国民间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之说,它充分反映了民俗的特性,即民俗的地域性,而谣谚也正是在地域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前此我们说许多谣谚可以入曲,这个入曲实际上就是入的地方乡土的俗调民曲。今天大家所熟知的刘三姐的故事,其中的山歌对唱中的许多词句便是那一方乡土的民谣民谚。因此,就地域的特性而言,谣谚与民俗的源出与内容都是一致的。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谣谚与民俗的地域特点呢?这是因为作为民俗史料的谣谚所反映的民俗世风与民俗事象是有严格的地域不同的。在某些情况下,甲地之风俗与乙地之风俗不同,便导致了甲地之谣谚与乙地之谣谚的区别。这样的情形同样不是说各地风俗之间和各地谣谚之间没有联系、没有共性,但事实是,由于影响地域风俗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乃至某些社会环境的不同,民俗谣谚在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往往是明显和极大的。因而对民俗谣谚的研究就一定要关注到这种地域的复杂性所带来的民俗的与谣谚的差别。《史记·河渠书》记载治河的《瓠子歌》中说:“瓠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旴旴兮闾殚为何。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巨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延道弛兮离长流,蛟龙骋兮方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齿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兮浚流难。搴长茭兮沈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颓林竹兮菑石揵,宣防塞兮万福来。”[9]这则谣谚的地域就很明确,它讲述的是瓠子河的各种情形而不是别的什么河。正像可以入曲的民歌一样,其地域特点便十分鲜明,如汉代乐府曲“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10]所述为典型的江南采莲之景。以大家熟悉的北朝《敕勒歌》就更是如此,“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北国塞外的自然景色是与江南风貌截然不同的。可见,民俗谣谚的地域性是基本的特点之一。
由于民俗谣谚的地域性特征,便使得我们在从事谣谚民俗研究中必须充分重视地域文献和考古资料,也包括流传至今的民谣民谚,尤其应当重视各地各类方志、家书、文集、信札等官私文书。因为谣谚记载往往少见于正史文献,且专书记载就更是罕见,清代学者杜文澜辑其《古谣谚》一书,至今珍贵,道理也正在于此。大量的古代谣谚散见于各类记载,也使研究者在进行某一专题谣谚民俗研究时颇有披沙拣金之感。谣谚民俗史料的分散,特别是它的口耳相传特点以及地域相隔而使材料不易寻找等特点都对谣谚民俗研究增加了相当的难度。因而,对已有资料的分类、整理和分析鉴别,对将要搜集资料的梳理、查勘和汇集就成为从事谣谚民俗研究的最基础工作,这一阶段的工作常常很艰苦,但这是必须经过的基础工作,是谣谚民俗研究不能跨越的阶段。
四、谣谚之时代变迁与民俗之变化发展
同任何事物一样,谣谚民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容、形式与风格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这里所说的变化和发展是从民俗本身和谣谚本身两个方面来说的。这种变化和发展同时又有文学形式的变化发展,谣谚表现形式的变化发展,民俗历史的变化发展,记录手段的变化发展等等方面。如先秦时期文献《竹书纪年》记载的“帝载歌”说:“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顺径,百姓允诚。于予论乐,配天之灵。迁于贤善,莫不咸听。鼚乎鼓之,轩乎舞之。菁华已竭,褰裳去之。”[11]《韩诗外传》“夏桀群臣歌二则”记载“江水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趣归于亳,亳亦大矣。乐兮乐兮,四牡骄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从善,何不乐兮。”仅从形式上而言,便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谣谚无论就文字表现,还是语言使用上都较后代要艰涩得多。到了汉代,则有了很大变化,如《贾生引野谚》记载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12]《优孟歌》记载说:“山居耕田苦,难以得食,起而为吏。身贪鄙者余财,不顾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赇枉法,为奸触大罪,身死而家灭,贪吏安可为也。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廉吏安可为也。楚相孙叔教,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13]我们也是仅从谣谚的文字表现和语言使用上来看上面两则汉代谣谚的记录,从中不难发现,汉代谣谚比之先秦时期的谣谚更趋于平易,语言文字更少障碍,其谣谚格式也更为开放,不拘字数之限,散文化情形更易于大多数人理解并传播。经过数百年间的变化发展,谣谚逐渐脱离了先秦时代那种甚为艰涩的语言表现形式,而进入到了汉代更为优美平实的自然表现形式。这种变化的最终动力和缘由是时代的进步,时代的变迁也是社会的变迁,作为文学表现形式和社会民俗反映的谣谚的变化正是极其自然的现象。
宋代文献《曲洧旧闻》记载当时社会卖官鬻爵的谣谚比照汉代则更为通俗明了,“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14]《老学庵笔记》记载宋代当时官府之职的谣谚写道:“吏勋封考,笔头不倒。户度金仓,日夜穷忙。礼祠主膳,不识判砚。兵职驾库,典了袯袴。刑都比门,总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见鬼。”[15]这一则谣谚将吏职的黑暗描述得淋漓尽致。同书卷六以同样的方式做了一个更为辛辣的嘲讽,兹一并录之下,“吏勋封考,三婆两嫂。户度金仓,细酒肥羊。礼祠主膳,淡吃菲面。兵职驾库,龄姜呷醋。刑都比门,人肉馄饨。工屯虞水,生身饿鬼”。不难看出,谣谚的文字形式与语言表现到了宋代又呈现为一个更为活泼有趣,更为尖锐深刻,同时也更为民俗化大众化的趋势。
谣谚民俗的与时俱进,也正是谣谚民俗在历史发展各阶段的积累、完善、充实和提高的过程,因此,谣谚民俗研究应当了解和关注不同时段、不同历史时期的谣谚民俗的比较研究,这对认识和理解谣谚民俗的历史演进着实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五、谣谚民俗的广泛性与大众性
反映民俗事象的古代谣谚是丰富多彩的,其所涉及的对象和描述内容包含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的方面,这是谣谚民俗至今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谣谚民俗的广泛性表现在谣谚所传达的民俗事象与社会生活的宽广层面上。如记载汉代水渠灌溉之利的《郑白渠歌》:“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水流龟下,鱼跃入釜。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16]记载汉孝文王与其弟的《民为淮南厉王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17]记载评论人物的《引谚论人物》:“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18]记载古代列女的《陶婴歌》:“黄鹄之早寡兮,七年不双。鹓颈独宿兮,不与众同。夜半悲呜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独宿何伤。寡妇念此兮,泣下数行。呜呼哉兮,死者不可忘。飞鸟尚然兮,况于贞良。虽有贤雄兮,终不重行。”[19]记载时令的《芒种占雨谚》:“雨芒种头,河鱼泪流。雨芒种脚,鱼捉不著。”《夏至占雨谚》:“夏至无雨,碓里无米。夏至日个雨,一点值千金。”《四月占麦谚》:“小麦不怕神共鬼,只怕四月八月雨。”《重午占年谚》:“端午晴干,农人喜欢。”《中秋上元谚》:“云罩中秋月,雨打上元灯。”记载有关气象预报的《占气候谚》:“河东西,好使犁。河射角,好夜作。水成田,衣成人。无衣不成人,无水不成田。黄梅天,日多几番颠。黄梅天气,□向老婆头边,也要担了蓑衣箬帽去。夏至日,莫与人种秧。冬至日,莫与人打更。霜降了,布衲著得。暴寒难忍热难当。大寒须守火,无事不出门。腊月廿四五,锥刀不出土。”记载总结人生悲喜之事的《得意失意语》:“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心。”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古代谣谚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领域之广,范围之宽是其他文献记载难于相较的。我们这里所举的例证限于篇幅是十分有限的。而大量的谣谚所覆盖的领域则是很难用几篇文字可以承载得下的,诸如渔夫樵夫谣,诸如歌颂为官清正廉洁与抨击贪官恶吏的谣谚,诸如讴歌妇女勤劳与贬斥懒惰之人的谣谚,诸如描绘自然景色的千姿万点与山川秀美的壮丽景观的谣谚,可以说谣谚的广泛性几乎涉及到了可能涉及到的所有方面。
谣谚民俗的大众性则在于谣谚反映民俗事象的通俗性与平实性上。如前所述,谣谚语言文字的平易和直白是其基本特点之一,这种平实更多地源自于谣谚的口头创作,口耳相传。故谣谚才被当做民间文学与大众文学的主要形式。谣谚民俗的大众性除了语言文字方面的特点之外,其记叙的内容贴近大众民人生活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如《陈彦修侍姬梦少年歌》:“人生开口笑难逢,富贵荣华总是空。惟有隋堤千树柳,滔滔依旧水流东。”[20]如《引谚论择师》:“三岁学,不如一岁择师。”[21]如《文臣武臣谚》:“文官宜不爱钱,武官宜不惜死。”[22]如《赵甤引谚》:“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士不必贤也,要之知道。女不必贵种,要之贞好。”[23]这些谣谚从语言文字风格到行文内容都贴近世俗生活,其大众化的特点十分鲜明。谣谚民俗的千年流传也正是古谣谚本身极具大众化的最真实体现。
谣谚民俗的广泛性与大众性使得利用谣谚资料对民俗进行研究成为新的重要的研究视角,我们应当加紧努力地为它的成果添砖加瓦。
六、谣谚民俗需要综合研究
所谓谣谚民俗的综合研究,是由谣谚民俗的相应特点决定的。谣谚民俗带有民间文学的特征,尤其与民俗相关联的地域特点,使我们不能不充分关注到谣谚民俗在各地、各个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的文字表现形式与民人社会风俗的变化和差异。在搜集和整理有关谣谚民俗的历史文献和历史资料时,对于谣谚民俗在各阶段的史料鉴别、史料真伪的考察、相关谣谚民俗史实的考证、谣谚本身与其他材料的比勘、谣谚记载与民俗历史文献记载的异同等等,在从事这些工作时,所应用的研究方法和利用手段便更多地采用了历史学、考古学乃至于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即是说,谣谚民俗研究强调着各个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而不是单一的偏重于某一学科领域。
谣谚民俗强调和需要综合研究,强调和需要多学科的比较研究和交叉互动,是因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单纯从某一学科出发而忽略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和比较,是很难从一个角度能够将谣谚民俗所反映的真实情况说清楚的。在很多情况下,对某一谣谚民俗在某一研究视角上出现了障碍甚至不得解时,换一个学科视角或采用另外一种研究方法,则这一问题就极有可能获得突破性的成果。同时,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综合研究又十分有利于为谣谚民俗研究提供更多的信息资料。以民俗史为例,反映某一时代民俗历史的某一现象在正史和其他相关的野史、杂史和文集笔记中不一定有记载的情况下,在说唱形式的乡谣乡谚中就极有可能出现这一方面的资料,因而也就解决了资料无征的问题。这种情况正好应验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学术研究心境。过去学术界对于谣谚的研究更多侧重于文学领域,特别是民间文学方面的研究上,很少关注到谣谚所反映的民俗事象与历史文化方面,应当说,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缺失。将谣谚与民歌山曲近乎画了等号,使得对谣谚研究的视角显得较为狭窄。同时,由于这种只顾及某一方面的研究现状而使对于谣谚本身的研究也很难达到更高的水平。
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工作者也需要不断加强自己的学术积累,加强读书治学,努力拓宽自己的知识和研究领域,既是专家,又是杂家。当然,这个“杂”要做到通,要做到懂,不是一知半解,不是望文生义,更不是主观臆断、信口开河,在今天,尤其要反对那种空疏的学风。研究者首先要有综合研究的意识,搞民俗的要懂文学、懂历史,搞文学和历史的也是如此。不能搞外行充内行,不懂装懂。对研究者的要求,既是专业能力、专业素质和专业基础的要求,也是学风品德的要求。因为谣谚民俗的综合研究是靠研究者们来做的,人的认识及相关问题不解决,综合研究就是一句空话。
谣谚民俗研究正当方兴未艾,还有许多课题可做,也还有许多问题值得商榷和探讨,特别是以往的某些研究仍然有深化和拓展的必要,我们完全可能在已有的基础上将谣谚民俗的研究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探索而达到一个新的学术水平。
[1][10]从民间来[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115—116.3.
[2][6][7][8][9][11][12]杜文澜.古谣谚[M].北京:中华书局,1958.95.
[3]后汉书·曹节传[M].
[4]后汉书·灵帝纪[M].
[5]抱朴子·审举[M].
[13]史记·滑稽优孟传[M].
[14]曲洧旧闻·卷十[M].
[15]老学庵笔记·卷五[M].
[16]汉书·沟洫志[M].
[17]史记·淮南厉王传[M].
[18]史记·货殖列传[M].
[19]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二[M].
[20]陶朱新录[M].
[21]太平御览·卷四百四十[M].
[22][23]古谣谚·卷三十六[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