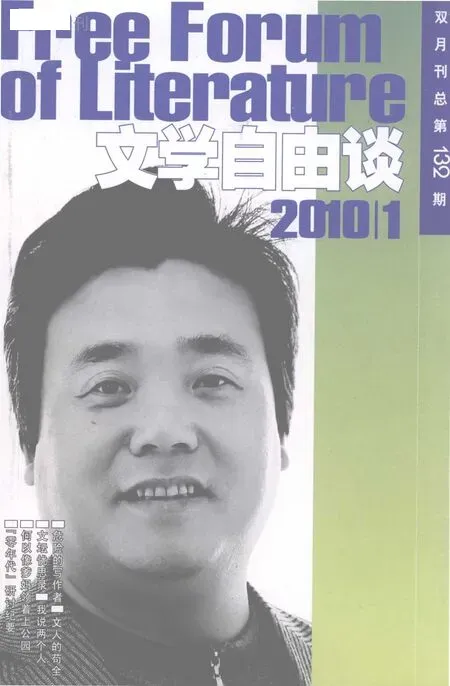关于金人先生
2010-03-21李建军
●文 李建军
我喜欢俄罗斯文学,像喜欢《史记》和“杜诗”一样喜欢,像喜欢《红楼梦》和鲁迅一样喜欢。第一流的俄国文学作品,凡能读进去的,我都读了。一个不懂俄语的人,能用自己的母语,毫无窒碍地阅读俄国大师的作品,这得归功于那些翻译家。在我国的文学翻译家中,俄文翻译家贡献大,水平也高。如草婴、汝龙、满涛、刘辽逸、力冈等,都是第一流的俄语文学的翻译家。他们的译文,“信”、“达”与否,不敢妄断,但从汉语的角度看,清通流丽,风神秀逸——一个“雅”字,实在是当之无愧的。
在所有的俄罗斯长篇小说中,最让我觉得平易亲切的,是《静静的顿河》。二十多年前,我初读这部巨著,就被它吸引。肖洛霍夫对顿河草原的诗意描写,对人物不幸的命运的完美叙述,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种心醉魂迷的体验,至今想起,仍然令人激动和快乐。尤其是译者的文笔,自然而优美,既有外语的绵密和气势,又有汉语的凝练和韵致。厚厚的四卷本小说,仿佛不是从别的语言翻译过来的,而是直接用典雅的汉语写出来的。
《静静的顿河》的译者,是翻译家金人先生,一个人们知之甚少的翻译家。那么,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很少有人在文章中提起他?他还健在吗?生活得好吗?每当回味《静静的顿河》,我就会想到它的译者,就会想到这些与他相关的问题。
让我意外的是,再次与金人先生相遇,竟然是在鲁迅先生的著作里。那时,我正像朝圣一样,一行一行细读《鲁迅全集》,读到第13卷的时候,忽然看到了“金人”二字。在1935年,从1月29日开始,到8月24日,鲁迅在给萧军和萧红的信中,曾13次提到金人。
在1935年1月29日致萧军、萧红的信中,鲁迅第一次提到了作为“您的朋友”的金人。金人想翻译屠格涅夫的《前夜》,大概是想通过二萧,得到鲁迅的指导和帮助。鲁迅告诉二萧:“您的朋友要译,我想不如鼓励他译,一面却要老实告诉他能否出版很难预定,不可用‘空城计’。因为一个人遇了几回空城计后,就会灰心,或者从此怀疑朋友的。”后来,鲁迅对金人有过切实的帮助,曾把他翻译的左琴科的《滑稽故事》,推荐给了《新小说》月刊,并在当年的7月刊载了出来(事见1935年3月1日鲁迅致二萧信)。
在1935年3月13日致二萧的信中,鲁迅除了继续推荐金人的译作,还评价了他的“文笔”:“金人的译文看过了,文笔很不差,一篇给了良友,一篇想交给《译文》。”六天后,在单独写给萧军的信中,鲁迅又评价金人《滑稽故事》的译稿“是很流畅的”。1935年3月25日,鲁迅又在给萧军的信中评价金人的“译笔是好的”。
此后,鲁迅还帮过金人不少忙,但都是通过萧军这个中介,似乎从来不曾直接与金人有过联系。我们据此可以推测金人的性格:他似乎是一个不很善于与人交往的人,即使对自己敬仰的鲁迅先生,他也不曾产生直接接触或者联系的冲动。
根据《鲁迅全集》第13卷第71页的寥寥数语的介绍,我知道,金人生于1910年,河北南宫人,卒于1971年,活了仅仅61岁。而1971年是一个不祥的年份,但愿他不是死于非命。
关于金人先生,许多年前,我能得到的信息,就是这些了。
1999年,我博士毕业,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人文社是金人先生离开人世前的单位,对他的生死来去,这里的老编辑应该是了解的,然而,我向好几个年高德劭的前辈打听,都说不知道金人的情况,有的甚至不知道社里曾经有过这个人。
那么,金人先生到底因何而死?死于何地?葬于何处?很长一段时间,我常常会想到这些问题,很想找到答案,虽然我知道,于死者,于他人,这答案并无太大的意义,但对我来讲,却成了一个难以释怀的牵念,有一种了却心愿的意思。
天下的事情,常有不期然而至者。有一天,读韦君宜先生的《思痛录》,忽然看到了金人先生的名字。我屏住呼吸,紧张地读完了那段并不长的文字。
金人先生原来死在干校!而且死得无声无息,仿佛一片落叶飘向大地。
韦君宜《思痛录》第十四章写了十个在干校劳改的死者。这一章的标题是《抹不去的记忆——忆向阳湖畔十个无罪者》。“向阳湖”位于湖北咸宁,是“文革”期间的一个条件非常恶劣的“干校”,是作家协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的“坏分子”劳改的地方,冰心、韦君宜、阎纲、周明、王莹等作家和编辑家,都曾在这里干过又苦又脏的活。在晚年的韦君宜的回忆中,“向阳湖”仍然是一个可怕的死亡之地:“当年我们一起来到向阳湖,我们这个不过二百人的小小单位,竟有八个忠骨埋在这里。其他单位(连队)也有。加上邻居中很熟悉的两个,我记下了十个完全无罪的葬身于此的人的名字。我本人是个活着回去的‘走资派’。”(《思痛录·路莎的路》(最新修订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
关于金人先生的获罪和死亡,韦君宜的叙述,拢共不到300字:“第七个是金人,这一位翻译家,本来并无什么罪状,在社里又和大部分群众水米无交。他之所以作为‘反革命’被揪出来,是由于造反派普查人们的历史,查出了他当年原是共产党员,还是沈阳市的负责人。苏联部队和国民党部队进沈阳时,把他找出来,不知叫他办了个什么手续,这下子把党籍弄掉了。他自己对此从不隐讳,本无可斗,但还是循例斗了,戴上帽子,赶到向阳湖。他年龄既老,身体又坏,造反派手中没材料,本来就对他没多大兴趣,于是让他跟一群老弱病残去丹江。丹江是我们干校丧失劳动力的人的收容处,免了这群老弱病残的生产任务,却让他们自己种菜、拉煤、做饭。中年人都不去。谁知道他们怎么干的?反正金人就死在那里了。”(同前,第146-147页)
刚六十出头,实在说不上老;但体弱,多病,无论对于老者,还是年轻人,都是苦难,如果还得不到宽恕和照顾,还要被强制劳动,那实在等于置之死地,断无活路。而作为“人民的敌人”,如金人先生者,活着有罪,死有余辜,一条命贱得与蝼蚁无异。所以,金人如何死的,他人自然无须萦怀,韦君宜也无法得知更多。
那么,在网上查查如何?看看,关于金人先生,是否能得到更多的信息。点击谷歌的搜索引擎,关于他的经历,倒是有一条信息,比之纸媒上的介绍,稍微详细了些:
金人(1910-1971),原名张少岩,后改名张君悌,又名张恺年,笔名金人。文学翻译家。直隶(今河北)南宫人。哈尔滨特区法学院肄业。金人曾任上海培成女子中学教师,苏北《抗敌报》、苏中《苏中报》编辑,苏中行政委员会法制委员会主任,东北文艺协会研究部副部长、出版部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司法部秘书处处长。建国后,历任出版总署编译局副局长,时代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译有(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潘菲洛夫《磨刀石农庄》、柯切托夫《茹尔宾一家人》、茹尔巴《普通一兵——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等。
1933年起,始见哈尔滨《国际协报》、《哈尔滨公报》等报副刊。后见《国闻周报》、《译文》、《鲁迅风》等。田风(见1937《光明》)、近仁(见1938《申报.自由谈》。出版《第二年》亦署)、高曼(抗战前在哈尔滨用)、GM(见1934哈尔滨《国际协报.文艺》)。抗战前在哈尔滨法院任俄文翻译。1937年初,从东北逃亡到上海。1942年到苏北,任职于《抗战报》,后任苏北行政公署司法处处长。1946年到东北文协,任东北司法部秘书处处长。解放后参加中国作家协会。译有《克里姆·萨姆金》、《列宁的童年》等等。
其实,关于他的译作,这里的介绍,并不完整,因为,我手头上就有他翻译的一本契诃夫的小说集,是三卷本中的一本,光明书局出版。不过,在他的四个笔名里,“近仁”尤其耐人寻味——“金人”是“近仁”的谐音。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第十三》)意思是说:意志刚强、性格果决、秉性朴实、言语谨慎,这些接近仁。金人先生的道德理想,是作一个心性温厚、谦光自抑的仁者。然而,他不幸生活在一个时时处处与好人为难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做一个于人有益、与世无争的人,竟然成了一种奢望,而运交华盖、客死异乡,则是一种在劫难逃的命运。
在《静静的顿河》里,被子弹射中的阿克西尼亚,死在葛利高里的怀抱里。葛利高里用马刀挖了一个坑,把自己心爱的人埋葬了:“太阳在热风阵阵的晨雾中升到沟涯上空。阳光照在葛利高里没戴帽子的头上,照得他那浓密的白发银光闪闪,滑过他那苍白的、呆板、可怕的脸。仿佛是从噩梦中惊醒,他抬起头,看见头顶上黑沉沉的天空和一轮闪着黑色光芒的太阳。”天空和太阳一瞬间都变成了黑色的,但是,肖洛霍夫的文字,却发出了照亮世界、温暖人心的光芒。
我不知道,临死的时候,金人先生是否想起了不幸的阿克西尼亚,是否想起了命运多舛的葛利高里,是否想起了那轮可怕的黑色的太阳;但是,我可以断定,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只要还有人阅读《静静的顿河》,金人先生就会像阿克西尼亚和葛利高里一样,活在一个宁静而永恒的世界里,在那里,没有残酷的斗争,没有无情的折磨,只有无边的爱和无尽的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