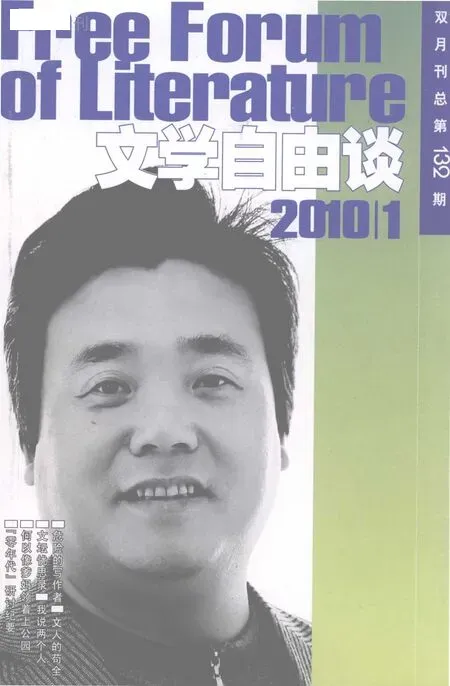文人的苟全
2010-03-21李国文
●文 李国文
一
毛奇龄是清初文坛的一位怪人,说他怪,就是此人好抬杠。
两个人,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但偏要将对方说服,争得面红耳赤,声高八度,甚至捋袖掏拳,口出恶言。老百姓管这种争辩过程,叫作抬杠。凡抬杠者,通常都是输了也不认输的坚硬派,有理要抬,无理也要抬的,人们对这些“死了的鸭子嘴硬”者,戏称为“杠头”。我们在生活中都有遭遇到此类“杠头”的体验,理他吧,一肚子气;不理他吧,照样还是一肚子气。
抬杠,常见于市井大众,知书识礼者不屑为,但毛奇龄例外,抬杠成癖,顶牛上瘾,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中国文学史三千年,像他这样总是非难一切,总是质疑一切,总是驳倒一切的“杠头”;甚至,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本来大家都认为正确的一切,纯系为杠而杠的“杠头”,可谓独此一家,天下难寻。而且口气之大,足以噎你一个跟头。他说:“元明以来无学人,学人之绝斯三百年矣!”所以,有清一代,对毛奇龄的学术评价,褒者贬者不一,说好说坏都有,但对毛奇龄的做人评价,其不可理喻的别扭,其无理取闹的争拗,其不肯服输的倔强,其彻底否定的逆反心理,咸持负面看法。
其实,毛奇龄之杠,成为当时和嗣后的争议话题,是那个尴尬的历史时代所决定的。
毛奇龄活到九十多岁,可谓长寿。第一,作为一个有学问,更有争议的文人,脑袋大过常人,当局很容易就摸得着;第二,作为一个反清没门,复明更没门的志士,头顶长过棱角,政府更不会将他忘怀。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康熙本人未必知道他是老几,但康熙身边的那些智囊,那些文胆,肯定知道他是老几。面对满清统治者那愈来愈严酷的思想箝制,面对异族主子日甚一日的文字狱恐怖政策,面对诸多文人动辄获咎一劫不复的政治打击下,他采取这种活着一天,抬杠不已,健在一日,杠头如故的生存方式,未必不是精神解压的途径。尽管很招人非议,很令人讨厌,可老先生一直到死,毫无悔意。
因此,据我私忖,估计这位老夫子,对这种自我心理调适,大概很自得,甚至还窃喜他终于形成的招牌形象。
说白了,中国皇帝收拾中国文人的手段,虽然很多,但是中国文人应付中国皇帝的招数,似乎更多。毛氏的杠,旨在宣泄,意在排解,其实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行为。他最为脍炙人口的抬杠,莫过于发难苏轼的七律《惠崇春江晓景》了。
明眼人看得出来老头子是负气之作,谁都当作一则笑话,毛奇龄却正经八百地抬,得意洋洋地抬。也许中国人对于名人,通常很宽待,便纵容得这班名流信口胡嘞,不知收敛,高谈阔论,不着边际。你就看当下电视讲座上这班货色的瞎说八道,走火入魔,而居然被容忍,居然不抗议,说明中国观众多么有涵养。顶多换一个频道,不看那张肉脸,免得夜间做恶梦,也则罢了。要放在外国,不知该有多少电视机被愤怒的群众砸掉。所以,大概也只有在我国,害似毛奇龄“鹅不知耶”的屁话,竟然有好事者认真地记录下来。
苏轼这首诗,尽人皆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好在清新淡雅,好在平白如话,尤其好在诗中的第二句,堪称神来之笔。西方人好说,“魔鬼在细节”(Devilsareinthedetails),在文学创作中,一个精彩的细节,往往决定作品的成败。毛奇龄当然懂得,感知到春水温润的鸭子,是这首诗中的精彩所在,也就是所谓的魔鬼细节。可他偏要强词夺理;鸭子知道,鹅就不知道吗?
事出陈康祺的《郎潜纪闻初笔》,卷十二:“汪蛟门比部懋麟,尝诵东坡‘春江水暖鸭先知’句。西河在座怫然曰:‘鹅讵后知耶?’人遂谓西河不知诗。余谓是句之妙,西河何尝不知,特其崛强本色,不辩不快。此老生平著述,全是一时火气,不许今人低首古人,何尝为解经讲学起见。”袁枚在《随园诗话》的卷三之九中,也述及“鹅不知耶”这句毛氏屁话,并大不以为然:“东坡近体诗,少蕴酿烹炼之功,故言尽而意亦止,绝无弦外之音,味外之味;阮亭以为非其所长,后人不可为法,此言是也。然毛西河诋之太过,或引‘春江水暖鸭先知’,以为是坡诗近体之佳者。西河云‘春江水暖,定该鸭知,鹅不知耶?’此言则太鹘突矣。若持此论诗,则《三百篇》句句不是:在河之洲者,斑鸠、 鸠皆可在也,何必‘雎鸠’耶?止丘隅者,黑鸟白鸟皆可止也,何必‘黄鸟’耶?”一直到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时,对毛西河的抬杠犹耿耿于怀,干脆斥之以“卑鄙”,可见其义愤填膺之状。“此乃本集上上绝句,人尽知之,而固陵毛氏独不谓然。凡长于言理者,言诗则往往别具肺肠,卑鄙可笑,何也?”
“何也?”回答很简单,不拿鹅来杠鸭,就不是毛西河的风格了。不过,陈康祺的“全是一时火气”,倒是点中了毛西河的软肋。
在明末清初的文人群落中,毛奇龄(1623-1716))是毫无疑义的大学问家,在解《易》这一门经学研究上,其一家之言,具有扛鼎的权威性。然而,与他基本上为同龄人的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2-1682)、王夫之(1619-1692)、李 (1627-1705)、吕留良(1629-1683)、徐乾学(1631-1694)诸人相比,他们无一不是铮铮佼佼,众望所归,出类拔萃,有口皆碑的饱学之士,而他却是属于剑走偏锋的野狐禅,半路杀出的三脚猫,加之在志节上,不及黄、顾、王之铁骨忠贞,磊落豪横,在人望上,不及李、吕、徐之高超俊逸,风格迥出。而在那个讲气节的年代里,人格的考量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这个极自负,极计较,极介意的西河先生,很不被人视为这个大师行列中的一员,使他郁闷,因此,这也促成他不甘雌伏,不想认输,不愿落败,不肯费厄泼赖的性格,而变得不可理喻的别扭。
《清史稿》称他:“淹贯群书,所自负者在经学,然好为驳辨。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词。”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那部伪《古文尚书》,自宋以来,都疑其作假。阎若璩专书疏解,力证其假冒伪劣,可毛偏要作《古文尚书冤词》力辨为真。《清史稿》说这个抬杠专家,“又删旧所作《尚书广听录》为五卷,以求胜若璩。所作经问,指名攻驳者惟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博学重望,足以攻击。而余子之下,不足齿录,其傲睨如此”。毛奇龄,不但杠同时代的顾、阎、胡等同辈,隔了好几百年的苏轼,因为这句“春江水暖鸭先知”,照样挑动了他的逆反心理。
如果毛氏的“抬杠”,竟止于口角之争,也只罢了。此公岂但动口,脾气上来了,还会动手。据方浚师的《蕉轩随录》,有一次毛奇龄与李因笃论古韵,以博闻强记、名重于时的关西夫子,与顾炎武被视为当世可师之文宗,自然不甘示弱,于辩诘中竟使西河先生一时语塞。这位老人家哪经过这等挫折,始则恫喝,继则大怒,最终甚至施以拳脚,武力相峙,这简直大辱斯文。在大家的排解下,老头子仍一脸愠色,咆哮不已,未肯罢休,那样子,在座的人,肯定是想笑而不敢笑,脸上不笑,心里却又乐不可支。
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十一《李天生之豪侠》条载:“李天生(即李因笃)检讨,性行 豪,尚气慨而急人患,一秉秦中雄直之气。生平与二曲交最密。天生宗朱子,二曲讲良知,各尊所闻,不为同异。亭林在山左被诬陷,天生走三千里至日下,泣诉当事,而脱其难。在都门,尝与毛西河论古韵不合,西河强辩,天生气愤填膺不能答,遂拔剑斫之,西河骇走。康祺窃谓天生古豪杰,其周旋亭林、二曲,不愧古人之交;其剑劫西河,未免稍失儒者气象。然以西河之利口,喋喋,滑稽不穷,非劲敌如天生,恐亦不足以折其骄横诡之气,宜当时传为快事云。”
全祖望在其《鲒 亭集外集》中,也说到这次先动口后动手的故事:“西河雅好殴人,其与人语,稍不合,即骂。骂甚,继之以殴。一日,与富平李检讨天生会于合肥阁学座论韵学,天生主顾氏韵说,西河斥以邪妄。天生秦人,故负气起而争。西河骂之,天生奋拳殴西河重伤。合肥素以兄事天生,西河遂不敢校,闻者快之。”
毛氏的这种活到老,杠到老,一息尚存,“抬杠”不止的精神,直至乾隆年间,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时,大概仍是文坛的热点话题。
作为主笔的纪晓岚,在《总目提要》里,对他敬之,畏之,又无可奈何之,因为此公无论做学问,写文章,无论考据经学,发表观点,都“好为驳辨”,遂作了一个极精譬的总结:“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辞。”你说东,他偏说西,而你一旦说西了,他又说东。纪昀在评介他的著作《诗话》时,对他这种非人之所是,是人之所非的文学批评态度,也是不以为然的。“奇龄以考据见长,诗文直以才锋用事,而于诗尤浅。”认为毛之“所论宋诗,皆未见宋人得失,漫肆讥弹”。认为毛之“所论唐诗,亦未造唐人藩篱,而妄相标榜,如诋李白,诋李商隐,诋柳宗元,诋苏轼,皆务为高论,实茫然不得要领”。
应该说,纪昀对他的评价,相当客观:“奇龄之文,纵横博辨,傲睨一世,与其经说相表里,不古不今,自成一格,不可以绳尺求之。然议论多所发明,亦不可废。其诗又次于文,不免伤于猥杂,而要亦我用我法,不屑随人步趋者,以余事观之可矣。”尽管如此,不能不郑重对待这位著作等身的学者,在他主编的《四库全书》中,收其著作达五十二种之多,作品被收《四库全书》,自然也是一种荣耀,以作家被收藏的数量计,他不数第一,也数第二。
在《四库全书》收藏古今书目中,名列前茅,也许是历史对他剖眼相看的一点。
我始终认为,他的抬杠,是他心理不平衡的结果。他的否定一切,一切否定的绝对态度,是他对自己期待过高,但在现实世界里,这些期待不仅难以落实,而且处处碰壁。他认为他应该受到世人的尊崇,然而他又做出不被世人尊崇的事情,也就难以得到众口一词的推誉,于是失落,于是恼火,于是动口加之动手,于是天下人不中他的意,同样,他也不中天下人的意。
我很钦佩这样于书无所不窥,学识博大精研,笔锋无所不涉,才气汪洋恣肆,能够一辈子“好为驳辨”,贯彻始终的怪人。当代文坛上“,好为驳辨”者,也有,但如毛西河淹古贯今的饱学之士,简直再也找不到一位。
二
毛奇龄,浙江萧山人。字大可,号秋晴,因郡望西河,又称西河先生。生于明天启三年,逝于清康熙五十五年,享年九十三岁。此人称得上腹笥丰赡,学识渊博,凡经学,文学,史学,乃至音韵,诗词,书法诸多方面,都达到了完善成熟的程度。应该说,钻研学问不难,而娴熟方方面面的学问,成为一个无不该洽的通才,那可不易。毛奇龄为清代初期的一位全天候的、货真价实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学问家,当是无疑的结论。
这位负才纵横,傲睨当世的文人,固然是狂狷一生,反弹一生,对传统质疑一生,对正统非议一生,对众所一辞的儒家定论逆反一生。可表面上的嬉笑怒骂,狂放恣意,别人眼中的无所忌惮,事必反弹,这一切,并不代表他活得很快乐。虽然,抬杠不止,可以取得口头上的一时宣泄之快;虽然,施以拳脚,可以得到肢体上的暴力发泄之快,但都不是他所追求的目标,更不是他所期盼的境界。
如果我们从他明清鼎革前后的人生轨迹,便知道他何以不快乐的由来。
一,“总角,陈子龙为推官,爱之,遂补诸生。”
二,明亡后,“哭于学宫三日,山贼起,窜身城南山,筑土室,读书其中。”
三,顺治三年(1647)陈子龙抗清殉难,毛奇龄追随其师大义,入南明政权毛有伦宁波抗清军中。“是时,马士英、方国安与有伦犄角。奇龄曰:‘方、马国贼也,明公为东南建义旗,何可与二贼共事?’国安闻之大恨,欲杀之,奇龄遂脱去。”(《清史稿》)
在中国儒家的传统精神中,师承,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信义,更是一种不可背约的担当。因为中国人相信,师生之间的文化联系,与父子之间的亲情联系,是应该划等号的,所以才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个太公遗训。因此,陈子龙对于旧国的眷恋,对于故土的忠贞,对于异族的抵抗,对于生死的豁达,以及他最后被俘不屈,杀身成仁的大义,如炬如火,燃烧起这位弟子对于江山社稷,不被腥膻的反抗意识;如光如电,指引着这位传人对于复我衣冠,还我故土的斗争道路。可以说,毛奇龄的一生,始终是在陈子龙精神力量的笼罩下,感召有之,激励有之,鞭策有之,镜鉴有之,而炯戒,则更有之。
一个大写的人,永远足以为人师范,而对早年受业于陈子龙的毛奇龄则尤其是,明崇祯八年(1636),才十三岁的他,以优异才禀,应童子试,恰陈子龙为主考官,见其稚气尚存,曾戏称:“黄毛未退,亦来应试?”毛奇龄答曰:“鹄飞有待,此振先声。”从此,遂为入门弟子。在所有关于这位西河先生的记载中,无不特别提到他受知于陈子龙这一点,可以断定,他以他的座师自豪,也曾经登堂入室,随侍左右,奔走往还,颇以其师那首《易水吟》中“昨夜匣中鸣”的“并刀”自许。
公元1664年,时年二十一岁的毛奇龄,与全体中国人一样,陷入了痛苦的抉择之中。是留发不留头,做明朝的忠烈,还是留头不留发,做清朝的顺民?对儒家子弟而言,改朝换代,也许不及衣冠制度的变换,更为触及灵魂,而 发留辫,要比胡服左衽,更是一种屈辱性的令其臣服的手段。所以,他与其师采取了与大清王朝为敌到底的态度。
当时,摆在知识分子面前,出路大致有四:
一,以死殉国;
二,武装斗争;
三,变节降顺;
四,苟且偷生。
毛奇龄既是抗清英雄陈子龙的得意门生,自然也当追随其宗师,转战江南,负隅顽抗。这段历史空白,已无从知悉,但陈子龙历经艰险,不折不挠,屡遭挫败,九死不悔,最后,不幸被俘,一死明志,殉忠前朝以后,作为陈子龙门生的毛奇龄,这位明末廪生,虽未能与其师同进共退,但迅即加入南明鲁王的军事活动,沿着他老师抗清足迹,游击于江浙一带,继续战斗。然而,崇祯朝所有的败象,在南明小政权再度重复,大势既去,败局已定,大厦之既倒,非人力之所能挽救,只好看它完蛋。鲁王败后,毛奇龄化名王彦,亡命江湖。这应该是公元1644年(顺治十七年)至公元1678年(康熙十七年)间事。明亡后的这三十年间,应该说,毛奇龄对他的入门老师陈子龙,在精神上的尊重,在感情上的缅怀,在反清复明事业上的传承,完全合乎儒家所要求的,“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可是,到了公元1679年(康熙十八年),西河先生五十六岁,已经是知天命的年纪,突然出现令人大跌眼镜的变化,竟要应博学鸿儒科,受招安。
在这个世界上,有勇敢者,也有不勇敢者。勇敢者,固可钦敬,不勇敢者,也不应苛责。毛奇龄不是绝对的不勇敢者,勇敢过,不成功,遂再也勇敢不起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完全没有必要一百八十度转向,放下武器也就够了,一定要去当伪军吗?这世界好宽广,这天地好辽阔,你四十年浪迹江湖,萍踪万里,满清政权不也未能伤及你分毫嘛?为什么要自投罗网?再退一步论,按师即父,父即师的儒家传统,你怎么能够向有杀父之仇而不共戴天的异族主子输诚纳款,俯首帖耳呢?近人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毛奇龄与钱谦益、李光地等辈,俱列入伪学者之流,很显然,公元1679年(康熙十八年),他被招安的这一步,是他头顶上这个“伪”字的来历。
康熙对汉族士人一手硬,一手软,剿抚并重的绥靖政策,最成功的一次,莫过于这年五月的博学鸿儒科了。第一,大清王朝江山坐稳,第二,大明王朝气数已尽,第三,最具有实力的三藩眼看完蛋,第四,康熙高规格地收买人心,于是这次“己未特科”,便成为一个表演的戏台,中国文人中最赖蛋的,最没起子的,最卑鄙无耻的,最下作最丧心病狂的,都跳了出来,群魔乱舞,丑态毕露,洋相百出,令人不齿。而在这个舞台上看不到身影的一群,却是中国文人中最精华的,最有骨气的,最信仰坚定的,最正直最光明磊落的精英,他们拒不从命,谢绝招安,守拙安穷,不求闻达的高风亮节,令人高山望止。那些与毛奇龄年纪相当的同辈文人,如黄宗羲,如顾炎武,如王夫之,如李 ,他们或逃入山林,或躲进洞穴,或绝粒成病,或誓死抵制。不买账,不上当,不应征,不受招安,与无法拒绝诱惑的西河先生相比,高下立见,瑕瑜不同。
此公兴冲冲从萧山北上,以布衣应博学鸿儒科,本想大显身手,谁知康熙志在安抚汉族知识分子,不在意才干识见,无所谓人品学问,只要你来应试,你就等于弃明投清,入吾彀中,只试一诗一赋,统统予以网罗。发榜后,毛试列二等,授翰林院检讨,任《明史》撰修官,充会试同考官。便在南城找了间小院,接来家眷,过起京官的衙门生涯。饮茶赋诗,品酒会友,三天一雅集,五天一堂会,倒也忙得不亦乐乎。此时此刻,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陈子龙,早抛在九霄云外。毛奇龄的这一“华丽”转身,由布衣而庙堂,由遗民而新贵,本以为会轰动,会叫座,会得到一个满堂彩,没想到却是很丑陋,很恶心的结果,因为中国人的记忆力,说来也有点奇怪,常常忘掉不该忘掉的,某些人自以为的伟大;但却常常记住不该记住的,某些人最忌讳的渺小。陈大樽,一代诗豪,末世奇雄,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你是他的门生,他是你的座师,阁下的这种背师行径,能不让人啐唾沫么?
作为《明史》馆纂修,并不安心于埋头史料,搜罗资证,却忙里偷闲,给康熙上了一本《平滇颂》。毫无疑义,这是一篇马屁文学。当时,康熙征讨吴三桂,尚未取得胜利,一方面对吴三桂讨伐之,粪土之,一方面对康熙吹捧之,神化之。也许康熙身边有的是阿谀奉承的御用文人,毛奇龄哪里拍得过高士奇这等马屁精,白忙活一场,什么也没捞着。那年的年终奖有没有倒在其次,这篇《平滇颂》引起的物议,却沸反盈天。第一,吴三桂对于大明王朝,虽万死不赎,但你毛奇龄也是降人一个,以同类为牺牲,作俎上肉,千刀万剐,以求取悦于新朝,在道德上先就站不住脚。第二,你毛西河本来“少年苦节”,“有古烈士风”的美誉,如今怎么也溜须拍马,不顾廉耻地下作起来。于是,给人留下“晚节不忠,媚于旃裘”的恶评。
终于,他明白了,这是一次投入太多,付出太大,而收获甚少的蚀本生意,不当遗民当顺民,不作孤忠作时贤,只是得到史馆中的一席位置。长年坐冷板凳下去,这实在太划不来了。呜呼,这样一个聪明人,怎么能不懂得物稀为贵的市场原则呢?当满清入关之初,抵抗者众,反对者多,不合作者遍地皆是时,第一个软骨头洪承畴表示降服,会被皇太极视若至宝。第二个软骨头吴三桂表示归顺,会让多尔兖受宠若惊。可后来,一个比一个赛着软骨头,一个比一个赛着王八蛋,你毛奇龄迟来的投诚,康熙就不会将你当香饽饽待了。于是,公元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因痹疾患足,借病隐退,长居杭州,既没有十分地堕落,为大清王朝鹰犬,也不敢公开地反抗,为大明王朝招魂。住在杭州竹竽巷他哥哥家中,专事著作,苟安求生。
这期间,康熙因政局渐趋稳定,遂加紧对汉族文人严密控制,遂有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这次文字狱,牵连方苞和安徽桐城方氏宗族,被绞,被杀,被关,被流,以及合家老小集体自缢、投塘者,足有数百条人命,这是公元1711年(康熙五十年)间发生的悲剧。时已米寿的毛奇龄,听到这个消息后,吓坏了。因为方苞为《南山集》写序,而成为同案犯,他很害怕为其师卢函赤《续表忠记》一书所作的序,是否会因都记南明政权的史事,招来杀身之祸。凡文字狱兴,最可怕的不是皇帝的震怒,而是会有无数的小人跳出来,鸡蛋里找骨头,文章里做文章,顺藤摸瓜,找缝下蛆。毛西河一生,因这抬杠,不知得罪了多少人?谁要趁此咬他一口,必死无疑。因此,他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茶饭不思,坐卧不宁。偶有动静,心惊肉跳,公人路过,魂飞魄散。一个八十八岁的老汉,哪禁得如此折腾,看来,即使没有小人收拾他,他自己也会在惊吓中,收拾了自己。
天才的最大不幸,首先是生错了年代,其次是生错了地方,再其次,居然活得很长很长,所谓“老而不死”,所谓“寿则辱”,其实就是拖得很长的痛苦。那些日子里,这位老先生,如坐针毡,如履薄冰,至此,作为一个苟全于世的文人,他所能做的,就是推得一干二净,嫁祸于人了。全祖望《鲒 亭集外集》中《书毛检讨忠臣不死节辨后》一文,对这位老先生为保全自己,推卸责任的卑污行止,大加谴斥。“已而京师有戴名世之祸,检讨惧甚,以手札属镇远之子曰,吾师所表彰诸忠臣,有干犯令甲者,急收其书弗出也。其子奉其戒惟谨。乃检讨惧未止,急作此辨而终之曰,近有《续表忠记》者,假托予序,恐世人之不知,不可无辨。呜呼,检讨不过避祸,遂尽忘平日感恩知己之旧。检讨所作底本并其手札,至今犹藏卢氏。其子尝流涕出以示予,予因而记之。检讨亲为之序而反覆如此,则可骇也。”
于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抬杠的毛奇龄萎琐,自私,庸俗,卑下的另一个侧面。他虽然有学问,但是,人格上并不完整,他虽然著书等身,但是,思想上并不高尚。当他汹汹然驳难这个世界时,他曾经是谁也压不服的强者;可当他面临利害选择,安危应对时,他却是一个进退失据的侏儒。
一个人,怎么活?是他自己的选择,好和坏,对和错,旁人是不宜置喙的。同样的道理,一个古人,他的一辈子,他走过来的路,印着自己无悔的足迹,别人是无法改变那段历史的。后人评价的好和坏,与本人感觉的对和错,也许并不总是划等号。因为时代不同,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受也不同。明白这一点,对于古人,应该尽量宽容一点才是,背离时代的求全责备,罔顾性格的过高期待,认为应该站直了活,宁死也不屈,而不应该低三下四,受嗟来之食的高调,都有缺乏辨证唯物和实事求是的不足之处。
所以,全祖望在他那篇文章的末后,说了这样一句话,给我很大的启发:“天门唐庶常建中曰,君姑置检讨弗问,盖谅其非本心耳。予大笑而颔之。”同样,法国汉学家戴廷杰(PIERREHENRIDURAND)在其所著《戴名世年谱》中,提到这件事,也表现出来一种宽容和厚道的精神:“文祸方震天下,股栗畏陷坑,伤义以避网,岂独毛奇龄一人而已哉?”
公元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西河先生终于寿终正寝。
死前,他留下遗言:“不冠,不履,不易衣服,不接受吊客。”这四不,也许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后一次的抬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