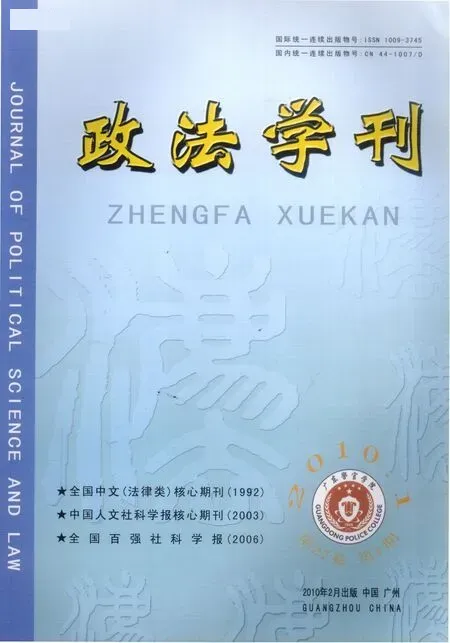多元法律文化的混合
——论英国普通法的“混合性”特征及其启示
2010-02-15谢红星
谢红星
(江西财经大学 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多元法律文化的混合
——论英国普通法的“混合性”特征及其启示
谢红星
(江西财经大学 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英国普通法是多种法律文化混合生成的,具有一种 “混合性”的特征。普通法的 “混合性”,既指其历史渊源的多样性,也指其法律内容的有机性。中央集权的强化是推动普通法 “混合性”特征形成的政治要素,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相通、深厚的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传统、实用主义的法律风格是影响这一特征形成的法律要素。借鉴普通法“混合性”特征及其形成的经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当混合现有的传统法、苏联法、欧美法等法律文化。在混合过程中,要重视政治权力的积极作用,珍惜传统法律文化,和采取实用的态度。
普通法;混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法律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是人类法律发展史上的常有现象。数种异质法律文化在某些因素的复合作用下、逐渐混合形成一种新型法律文化的现象,普通法在英国的形成正是这样一种情形。11-13世纪,英格兰境内的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诺曼底法和天主教教会法等法律文化在中央集权强化这一政治进程的推动下,逐步混合形成一种新的法律体系——普通法,因此,普通法是以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为基础、吸收了诺曼底法和教会法的诸多成分而形成的的混合性法律体系。本文将对普通法 “混合性”特征的具体涵义及形成要素进行初步解析,并尝试分析这一特征及其形成对我国现阶段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借鉴意义。
一、普通法“混合性”特征
普通法的“混合性”特征,指普通法历史渊源的多样性及法律内容的有机性:
(一)历史渊源的多样性。普通法直接的历史渊源,有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诺曼底法和教会法:(1)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自公元 5世纪起盎格鲁、撒克逊、裘特等日耳曼部落对不列颠的征服,不仅使上述部族成为不列颠的主要族群,也使上述部族的原有习惯成为岛上主要适用的法律规则,其后,受欧洲大陆日耳曼国家编篡法典的影响,盎格鲁 -撒克逊各王国也相继编篡了一系列的法典,原有的习惯得以规范化和体系化,逐渐发展成英格兰习惯法的主体。此后,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以其强大的传统力量,历经北欧人入侵和诺曼底人征服而不衰,成为普通法的主要渊源。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的许多原则和制度奠定了普通法的基础,例如,“国王和平”的法律观念是王室法院对刑事犯罪案件行使充分管辖权的主要依据,马尔克公社土地制是普通法上地产制的雏形; (2)诺曼底法。诺曼底法指欧洲大陆诺曼底公国的法律,它以管理有效而闻名。在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不列颠之后,英格兰诺曼王朝将诺曼底的法律引入不列颠,这一举措对普通法的形成意义重大,正如约翰·哈德森所言,“尽管盎格鲁 -撒克逊的法律传统相当深厚,像安茹王朝时期一样,对法律的发展而言,诺曼时期也是一个重要的开创时期”[2]33,可见,诺曼底法也是普通法的重要渊源。诺曼底法对普通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王室法院的各类机构源自于诺曼底时期即初具雏形的御前会议,陪审制被认为来自诺曼底的邻人调查团程序,巡回审判也被认为正式起源于诺曼底——虽然在此之前它有着更为古老的渊源,更为重要的是,诺曼底公国富有效率的管理制度被引入英格兰,英格兰诺曼王朝通过税收体制的完善和诺曼底特色封建保有制度的确立,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为普通法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3)教会法。在盎格鲁 -撒克逊时期,伴随着天主教教会势力的扩张,教会法对盎格鲁 -撒克逊诸王国法律的影响不断扩大:公元 600年前后编篡的《埃塞伯特法典》将保护基督教会及其神职人员的利益列于篇首,可见该法典受教会法的影响是何等之深!著名的阿尔弗烈德国王的法典,更是 “试图把摩西法典同基督教原则和传统的日耳曼习惯结合起来”[3]120。威廉对不列颠的征服虽加强了英格兰中央政府的权威,但一方面由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发起的“教皇革命”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因为威廉对不列颠的征服行为本身就是在当时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支持下进行的,因而在诺曼王朝统治时期,天主教会和教会法在不列颠的影响急剧扩大:亨利一世即位时,“教皇的地位强大到足以迫使国王亨利在教职的任命方面作出实质性的让步”[1]536;诺曼王朝的末代国王斯蒂芬执政时,罗马教廷对英国教会的掌控和对世俗政权的影响均达到颠峰。可见,普通法是在强大的教会法背景下形成的,普通法的形成是一个英格兰王室法与教会法竞争并逐渐获胜的过程,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王室法在教会法的影响和渗透下缓慢成长并最终生成为适用于整个英格兰王国的法律体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会法对普通法的塑造作用不可忽视。因此,教会法同样是普通法的重要渊源。教会法对普通法自由主义宪政原则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教会法对教皇权力的法律限制,罗马教廷在西欧包括英国构建的二元政治架构,以及在实践中它对世俗权力的抗争,对普通法自由主义宪政传统的形成影响深远。贝克特虽死,“贝克特的传统却遗留至今”[1];天主教会的势力在英国虽不复当初之盛,中世纪教会法对普通法形成的影响却不容忽视。总之,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诺曼底法和教会法是普通法的三历史大渊源。
(二)法律内容的有机性。普通法的历史渊源虽是多元的,但作为一种统一的、具有全新生命力的法律体系,它既不是原有法律体系的简单延续、移植或模仿,更不是多种渊源的相加,而是不同法律文化的有机混合:诺曼底法与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的混合,教会法与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的混合,甚至是三者的混合。正是这种有机的混合,使得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诺曼底法和教会法原有的一些制度得到改造,具备了新的生命力,并成长为普通法上的重要制度。以巡回审判制度为例,巡回审判制度虽起源于诺曼底人派遣法官主持地方法庭的做法,但英格兰诺曼王朝在把它引入英格兰的同时,将其与英格兰本土的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巧妙结合起来,具体措施是由巡回法官取代郡长主持盎格鲁 -撒克逊时期就已存在的、由日耳曼民众大会发展而来的郡法院,这样做的好处是:首先,借巡回法官之手将王室法适用于地方,加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法律统一;其次,承认原有的郡法院系统体现了中央政府对盎格鲁 -撒克逊地方自治传统的尊重,从而使巡回审判制度更容易为英格兰民众接受;再次,以郡法院为平台审判案件,巡回法官可全面掌握各地的习惯法,并将其中的合理部分吸收到王室法中,有利于王室法自身的发展完善。诺曼底巡回审判做法与盎格鲁 -撒克逊地方自治传统的有机混合,造就了普通法上的巡回审判制度。再以地产权制度为例,普通法上的地产权制度,是盎格鲁 -撒克逊时期的马尔克公社土地制度与诺曼底封建土地保有制度相混合的产物。威廉征服不列颠后,诺曼底封建土地保有制度随征服者一起进入英格兰,与原有的盎格鲁 -撒克逊马尔克公社土地制度相混合,形成了一种新的地产权制度。具体做法是:国王和各级领主取代了原有的马尔克公社,各级封臣取代了原来的公社社员,通过次级分封,建立起国王、大领主、中间领主、封臣顺序的金字塔式的封建体制。新的地产权制度既保留了马尔克公社土地制度基本传统——封建契约与封建权利的相对性,又吸收了诺曼底封建土地保有制度的重要特点,即封建附庸关系的直接化,从而既不同于欧洲大陆的封建土地保有制,也不同于盎格鲁 -撒克逊时期英格兰逐渐形成的采邑制。混合生成的普通法地产权制度,内容较以往的马尔克公社土地制更为充实:领主和封臣的关系更多依赖于书面的特许状或封赠协议,而非旧有的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领主权和地产权之间的争议由领主法院解决,而非盎格鲁 -撒克逊时期的民众大会,因此,也就更能适应大征服后英格兰政治和社会的现实需要。总之,多元法律文化的有机混合,造就了普通法不同于其历史渊源的新生命,为普通法在英格兰成长与繁茂奠定了根基。
综上所述,11-13世纪,英格兰本土的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与诺曼底法、教会法相混合,形成了一个以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为基础、吸收了诺曼底法和教会法诸多成分的法律体系——普通法。普通法的“混合性”,指其历史渊源的多样性和法律内容的有机性。
二、普通法“混合性”特征的形成
一般认为,普通法形成于 11-13世纪,即自威廉征服不列颠至爱德华一世即位这一历史时期。通过对这一时期英格兰国家与社会的分析,笔者认为,影响普通法“混合性”特征形成的要素,包括政治要素和法律要素两方面:
(一)政治要素。中央集权的强化是影响普通法“混合性”特征形成的政治要素。正如密尔松所言,“普通法是英格兰被诺曼人征服后的几个世纪里,英格兰政府逐步走向中央集权和特殊化的过程中,行政权力全面胜利的一种副产品”[4]3。在诺曼征服之前,英格兰王国中央政府权威有限,王室法适用范围很小,更不存在统一适用于整个王国的法律。诺曼征服改变了这一切,大征服之后相继建立的诺曼王朝和安茹王朝均积极谋求强化王权、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诺曼王朝通过诺曼底特色封建关系的建立、税收制度的完善和对英格兰教会的人事控制强化了对全国的统治;安茹王朝亨利二世统治时期,司法和兵役制度的成功改革使英格兰中央政府的集权程度达到一个高峰,虽然此后政局动荡,王权时有低落,但英格兰中央政府仍是同时期西欧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之一。中央集权的强化使法律统一成为可能,反之,法律统一也是强化中央集权的重要举措,诺曼王朝和安茹王朝通过拓展王室法院的司法管辖权,逐步扩大王室法的适用范围,使其发展成为统一适用于整个王国的法律体系。王室法院司法管辖权的拓展是通过争夺并挤压地方法院、领主法院、教会法院的司法管辖权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王室法院主要是通过法律途径、采取法律上的措施同其它法院争夺司法管辖权,即通过完善王室法的各项制度,使王室法展现出更多的优越性、更能满足人们解决纠纷的法律需要,从而把当事人从其它法院吸引过来,而非采用政治暴力强制取缔旧法院与废除旧规则,这一过程正如丘吉尔对亨利二世法律改革的形容,“强迫手段对于实现他的计划没有用处,他应该遵循的第一条原则,必须是把案件吸引到而不是强行拿到自己的法庭审理。要使诉讼人到国王的法庭起诉,就必须有东西吸引他们,国王断案必须比他们的领主公正”[3]201。因此,英格兰中央政府统一法律、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也是一个王室法自我完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王室法以英格兰本土的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为基础,充分吸收了诺曼底法和教会法的许多有益成分,实现了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诺曼底法、教会法的有机混合,发展成为一种新的适用于全国的法律体系——普通法。总之,中央集权的强化是促成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诺曼底法、教会法相混合的政治要素。
(二)法律要素。除了中央集权的强化这一政治要素的推动外,多种法律渊源之所以能混合形成一种新的法律体系,也是因为某些法律要素的积极作用,这些法律要素包括: (1)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相通。相通方可混合,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诺曼底法、教会法能相混合首先在于它们之间的相通。以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与诺曼底法而言,两者同属日耳曼法,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正如约翰·哈德森所言,“除了注重社会地位而不是注重民族出身这一倾向外,诺曼习惯和英格兰习惯之间相当大的一致性或许也对彼此的同化有所助益”[2]30。就教会法而言,尽管它被认为是日耳曼法的竞争对手,但从早期日耳曼社会开始,基督教就在不威胁甚至支持日耳曼法律制度的前提下,逐渐促成日耳曼法的实质性变化,这种变化可归为两点:基督教促进了日耳曼部落习惯的成文化;在促进习惯成文化的同时改变习惯,其中以提高王权的作用尤为重要。可见,盎格鲁-撒克逊习惯法和诺曼底法其实都是经过基督教改造的日耳曼法,它们与教会法的相通性自不待言;(2)深厚的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传统。英格兰民族向来尊重传统、推崇本民族固有的习惯法。诺曼征服并未触动这种传统,反而巩固了它。在征服不列颠之后,征服者威廉以英格兰王位的合法继承人自居,下令继续适用英王爱德华时期的法律,即旧有的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这一传统造成的后果是,任何法律变革都不能废弃旧有的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中央政府统一法律的努力必须尊重既有的法律规则,并到其中去寻求支持。正因为如此,当亨利二世进行意义深远的法律改革时,他声称他的改革是在维护其祖辈曾享有的权利和适用的习惯,然后在此旗帜下小心翼翼地改变传统,创造出新的规则。丘吉尔对此也形容道,“亨利巧妙地改变一个又一个惯例,并且给这些改革披上颇受尊重的保守主义外衣。他小心翼翼地尊重已有的形式,因而计划在旧原则的形式下注入新内容”[3]201。深厚的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传统使得普通法的形成必然是一个诺曼底法及教会法成分持续注入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并成长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对旧有的盎格鲁-撒克逊习惯法的尊重符合了英格兰民族的传统,从而使得三种法律渊源能够成功地实现有机混合;(3)实用主义的法律风格。英格兰民族尊重传统,同样也崇尚实用、注重行动,这种一特点体现在法律领域,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法律风格:法律因解决问题而生,规则为处理纠纷而设。法律统一的目的是强化中央集权,普通法只是这一过程的副产品,因此,就整体而言,普通法并不是出于某几位天才的精心设计,而是在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中为解决实际问题而逐步生成的:王室法院系统的完善是为了同教会法院、领主法院竞争司法管辖权,并通过更多案件的受理来增加王室收入;巡回审判最初是为了加强王室权威,其中对法律事务的处理还可增加王室的财政收入,因为处罚犯罪所得到的罚金是王室的重要收入来源;令状的出现为当事人寻求王室法院的救济开辟了途径,但考虑到寻求王室法院救济的人需要向国王支付一笔可观的费用,所以其目的不能排除是为了给王室开辟一条可观的收入来源。同样,不同法律渊源的混合也是出于现实的需要:为了巩固征服者对不列颠的统治,诺曼底法被引入英格兰;为了获得被征服者的认可与合作,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得以保留;为了换取罗马教廷的支持,对教会势力作出一定让步不是不可以的,某些不妨碍世俗政权统治的教会法的引用更不是问题。总之,一切皆为用,无用即为空,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诺曼底法、教会法为解决现实问题而混合,这种“实用”的混合使混合生成的法律制度更能适应英格兰的具体国情,并在实践中得到更多的适用。
综上所述,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推动了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诺曼底法、教会法之间的混合,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相通、深厚的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传统、实用主义的法律风格则为这种混合的成功实现提供了可能。普通法“混合性”特征的形成,既有政治要素的推动,也有法律要素的积极作用。
三、普通法 “混合性”及其形成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启示
普通法“混合性”特征及其形成,对现阶段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无启示,这是因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同样面临一个混合多种法律文化的问题。基于种种原因,我国现有的法律文化是多样的,有前苏联的,有欧美的,还有本土的传统法律文化。总起来说,新中国建国初期废弃六法全书、全面学习苏联,苏联法遂成为当时法律的主要渊源;改革开放后学习西方,欧美法于是重新成为我国法律的重要渊源;近些年来国学大兴,复兴传统成一时潮流,于是传统法律文化又成了法制建设不可忽略的“本土资源”。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过程中,面对如此多样的法律文化,我们应该作出何种选择?笔者认为,最佳的选择应该是混合三者。三种法律文化均存在于我国多年,其原则和制度不少已反映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为公众所熟知并接受,况且三种法律文化各有其优点,贸然放弃其中一种或两种,实属不智。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在选择苏联法的同时舍弃了传统法和欧美法,因为它们被认为是落后的、反动的;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我们重新选择了欧美法,批判了苏联法,因为它被认为是僵化的;后来,因欧美法的引入带来诸多问题,我们转而批评欧美法不合国情,传统法又开始受到追捧。偏重其一而舍弃其余,是法制建设中的一种偏执。唯有成功混合传统法、苏联法、欧美法这三种法律文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才能构建起来。中世纪英国普通法混合生成的经验,正可为此提供借鉴。
笔者认为,借鉴普通法混合生成的经验,混合我国现有诸种法律文化、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重视政治权力的积极作用。政治权力对法制建设有破坏的一面,但也有促进的一面。虽然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5]18,但在现实生活中,“是权力使法律具有了神圣的性质,是权力使法律具有了强制服从的力量源泉”[6],对权力的敬畏制造并维持着人们对法律心理及行动上的服从,而服从法律是信仰法律的前提。因法制建设屡遭政治权力干扰且破坏的惨痛教训,政治权力对法制建设的积极一面在今天往往被忽略,然而,普通法在中央集权强化的政治动力下混合生成的历史经验证明,一种强大适中的政治权力对法制的建立与完善是何等重要!若无强大的王权,地方官员及民众岂能服从巡回法官的判决,地方法院、领主法院、教会法院岂能甘心于其管辖权被王室法院蚕食,王室法又怎能取代盎格鲁 -撒克逊地方习惯在全国统一适用?故正如程汉大教授所言,11-13世纪英国强大适中的王权 “赋予国王政府以足够的力量,使它能够保持国家的政令统一,从而不但避免了同期欧陆各国那种封建分裂局面的出现,而且有能力在12世纪自上而下地发动和推行大规模司法改革,将分属于贵族和地方共同体的司法管辖权集中于中央,通过国王法院司法判决的积累,使各地分散的习惯法融为一体,形成通行全国的普通法”[7]。因此,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一种适度强大的政治权力尤其是中央政治权力是必需的,它是人们服从法律的基础,是消除各式规范各自为政的利器,更是混合各种法律文化、构建一个统一协调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保证。
(二)珍惜传统法律文化。虽然,我们不应在“固守国粹”的幌子下排斥外来法,但是,作为一种本土的、根深叶茂的法律文化,传统法理应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要渊源。传统法律文化中蕴含着许多有益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成分,曾宪义教授指出,“如果不带有偏见,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凝聚着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凝聚着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巨大智慧,因此在现实中我们不难寻找到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明的契合点,也不难发现传统法律文化对我们的积极影响”[8],因此,“在现代法治的形成过程中,从理念到制度,我们并不缺乏可利用的本土资源,我们理应对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法律文化充满信心”[8];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必须植根于传统法,以更新和复兴传统法为前提,张晋藩教授指出,“传统是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只能更新,不能铲除;失去传统就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特点,就失去了前进的历史与文化的基础”[9]1。马小红教授认为,“西方启蒙思想家对未来的信心是建立在传统的复兴和发展之上的”[10],相反 “我们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将历史和传统视为包袱”,结果是我国法制近代化的道路上充满了 “苦涩和失落”[10]4,因此,“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传统的重要,并有意识地、自觉地’激活’传统中有益于现实、有利于发展的成分,传统才能成为发展的动力而不是阻力”[10]68。普通法虽是混合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诺曼底法、教会法而生成的,但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始终是主要渊源,普通法的生成是一个诺曼底法和教会法持续注入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并成长为一个整体的过程,若无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为根基,这一混合能否成功实属难料。以此为鉴,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过程中,唯有珍惜传统法、依托传统法,对现有诸种法律文化的混合方能成功。
(三)尚实用,去浮躁。混合多种法律文化需要采取一种实用的态度,解决现实法律问题、促进纠纷的解决是混合的出发点,也是混合之目的所在。在混合的具体过程中,选取苏联法、欧美法、传统法的哪些制度进行混合,如何混合,应从现实的法律需要出发。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为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华丽目标而引入别国一些所谓的先进制度,或者为一种复古的臆想而意图全面恢复一些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的古董,全能不顾现实需要与否。相比之下,普通法生成过程中对盎格鲁 -撒克逊习惯法、诺曼底法、教会法具体制度的混合就完全是出于一种实用的考量,这种混合并不是刻意的、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的,也不是出于保障人权、促进法治之类的崇高目标,而是基于增加王室收入、强化中央集权、促进纠纷解决等现实的政治及法律需要而实施的,以亨利二世的法律改革为例,程汉大教授认为,“亨利二世司法改革并不是深思熟虑和精心策划的结果,更不是出自高瞻远瞩的先见之明。驱使亨利二世进行改革的原动力主要是现实政治需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出于君王之私的一己考虑”[11],实用的目的使混合生成的制度能满足现实需要,从而具备了持续成长的生命力。因此,在混合传统法、苏联法、欧美法的过程中,如能尚实用、去浮躁,混合生成的法律体系必定能适应我国的具体国情,并在此基础上成长、完善。
[1]伯尔曼.法律与革命 [M].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2]约翰·哈德森.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时期英格兰的法律与社会 [M].刘四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 (上)[M].薛力敏,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4]密尔松.普通法的历史基础 [M].李显冬,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5]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M].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6]卓泽渊.政治是法律的基础 [J].学习与探索,2005,(5):101.
[7]程汉大.政治与法律的良性互动——英国法治道路成功的根本原因 [J].史学月刊,2008,(12):76.
[8]曾宪义.从传统中寻找力量——《法律文化研究》(年刊)卷首语 [J].法律文化研究,2007.
[9]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 (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10]马小红.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1]程汉大.亨利二世司法改革新论 [J].环球法律评论,2009,(2):18.
责任编辑:林 衍
A bstract:The British Common Law System is a mixture of various kinds of legal cultures 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interfusion”.The characteristic of“interfusion”refers to the variety of its origin and the organic character of its legal content.The reinforcement of centralization of authority is the political factor that accelerates the for mation of“interfusion”characteristic.The communication among different legal cultures,the deeply-rooted tradition ofAnglo-Saxon unwritten laws and practical legal style are the legal factors.By referring to“infusion”characteristic of Common Law System and its experience in formation,the socialis m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allmix the culturesof current traditional law,SovietUnion law and Euro-American law.In the infusion of different legal cultures,we shall pay attention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political power,treasure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and adopt a practical attitude.
Key w ords:Common Law System;interfusion;socialis m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Interfusion ofM ulti-d imensionalLegal Cultures-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Interfusion in British Common Law System and its Enlightenment
Xie Hong-xing
(School ofLaw,Jiangxi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China)
DF07
A
1009-3745(2010)01-0016-06
2010-01-12
谢红星 (1978-),男,江西于都人,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史专业 2008级博士研究生,从事法律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