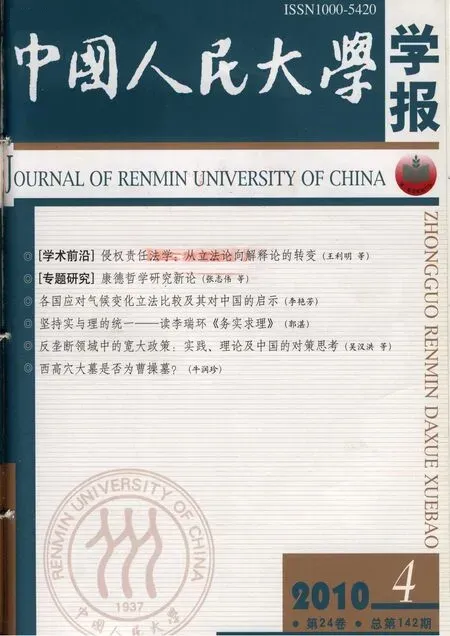康德的“形而上学”之思
2010-02-10张能为
张能为
(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230039)
康德的“形而上学”之思
张能为
(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230039)
人们不断去追问和进行整体性思考的形而上学传统源远流长,但是,伴随着近代科学理性的强势发展,形而上学日渐失去其原本含义而走上了科学化、知识化的实证历程,这引起了康德的高度警惕和深刻批判。康德在区分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实现了对知识性的“独断论的形而上学”的批判性扭转,重新恢复了形而上学的原有含义,确定了形而上学发展的真正方向。
一、科学与形而上学之异
康德关于科学与形而上学相区分的思想奠定了其形而上学批判与重建的基本理路和运思架构。正是在明确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根本相异之后,康德提出了对形而上学的重新理解,既批判了传统的作为知识性的独断论形而上学,又指出了真正的“一般的形而上学”和“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
亚里士多德将哲学与科学做了明确的区分。各门具体科学是指对具体事物的本质、规律予以研究的学问,哲学则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科学,是研究宇宙万物内在统一性的学问。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区分,指明了哲学就是关于存在的本质、关于宇宙整体的学问。康德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正是从认知的角度在没有认清理性能力的情况下混同了形而上学与科学认知,把形而上学问题当作科学问题来加以认识,所以,往往造成了相互矛盾、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康德意识到了重建形而上学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无论是独断论形而上学,还是怀疑论形而上学,在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上都是不正确的。它们或者将形而上学混同于科学,或者因科学的有限性而否定形而上学,这要么使哲学变成无休无止的争论,要么使哲学失去了追求真理的根本性质。正确的理解是:形而上学必须有,但又不能归属于科学知识领域;科学知识是有限的,但又因此而预示着形而上学存在的必然性。理性能力的有限性并不能阻止理性做无限的追求,而这却正是形而上学产生的总根源。
二、形而上学的理解与重建
依照康德的见解,形而上学的对象就是理性本身的纯原则,即理性永恒不变的规律,只有探明这些规律,哲学才会最终达到其完满的状态。形而上学就是这样一门科学,它所研究的是“纯粹理性本身不可避免的问题”,这门以全力解决这些问题为最终目的的科学,就叫做形而上学。
在康德看来,形而上学是存在的,对形而上学的追求是人类理性自发产生的、不可避免的自然倾向。“如果有这样一种科学,一些与它有关的问题已经由人类理性的本能向每个人提了出来,因为人们总是不免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了许许多多尽管失败的尝试,所以我们可以说,形而上学在主观上是(而且必定是)实在的 ……”[1](P104)而要改变形而上学的知识化发展路向,变原先的“坏的形而上学”为真正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就必须彻底放弃独断地用概念来构造关于上帝、自由和不死的科学。一旦我们从传统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中摆脱出来,指出形而上学从一种自然倾向变成可靠的确切科学的条件,那么,作为一门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存在就完全是可能的。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部分“方法论”中,勾画了一个未来的科学的形而上学体系内容的纲要。康德认为,作为“纯粹理性体系”的形而上学,就是指“它在系统联系中研究出自纯粹理性的全部(既包括真实的也包括虚假的)哲学知识”。[2](P536)其特性就是具有形而上学固有的一种特殊的先验性,即形而上学的知识从概念到原理都不是经验的,因为“它必须不是形而下的知识,而……应该是经验以外的知识”[3](P17);其来源就是纯粹理性,它不涉及具体客体,而只关乎理性;其分类是纯粹理性应用于思辨的形而上学(自然形而上学)和纯粹理性应用于实践的形而上学(道德形而上学),前者考察理性在事物知识上的纯粹原则,后者则探讨“先天地规定所为所弃并使之成为必然的原则”[4](P537);其方法是在纯粹理性基础上通过先天概念和先天原则研究知识的最高统一和人类道德行为的原理问题。康德对形而上学体系内容所做的概括就是:“形而上学的整个体系由四个部分组成:1.本体论。2.理性自然学。3.理性宇宙论。4.理性神学。第二个部分,即纯粹理性的自然学说,包含着两个分支,即理性物理学和理性心理学。”[5](P540)由此康德认为,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三大理性观念:上帝、自由和不朽。上帝是超自然的、无条件的最高的存在;自由是道德意志的主体无条件独立于经验规定的宇宙秩序;不朽是精神实体无条件地不可消灭。可以看出,康德这种对形而上学的全新理解和改革纲要的实质,就是将形而上学视作只与理性发生关系,因为理性自身蕴含着认识原则,它表现为一种独特的、完全的统一。不同于具体科学,作为纯粹理性科学的形而上学,它能对理性本身进行彻底的研究。
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必须认清知性“范畴”与“理念”问题之间的区别,因为“没有这种区别,形而上学就完全不可能”。[6](P105-106)按照康德的看法,范畴只是对有限东西的联系或者说关系的反映,它与经验对象相对应,而理念则不同,它以把握全体为目标,是一种超验性的东西,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是“条件的绝对全体”。范畴是与有限东西相关,而理念则与无限的全体相联。
康德通过考察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指明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制的,只能局限于现象世界,而对物自体的本体世界却无能为力,知性认识只能局限于有限范围之内的东西,而无法认知和穷尽无所不包的无限整体。不过,尽管物自体的存在不能被有限的知性范畴所表述、所认知,但却是可以信仰的。这个无限的统一整体是人类的理性所公设的东西,它确实存在,但又不同于我们日常所见的有限对象,作为一种超验对象,它只是一个理想、信仰,即是一个人类理性的“公设”。
三、形而上学的扭转与方向
与其说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的核心内容,毋宁说哲学与形而上学是同质性的概念。随着近代西方科学理性的突出和强调,那种强调知识、规律和本质的理论哲学逐渐占据了哲学的主导地位,理论哲学成为主流的哲学形态,形而上学问题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那种整体性意义的视角和理解,而日渐科学化、知识化,似乎成为一种具体的知识论问题,形而上学表现出一种必须对世界和事物的本质有所断定和认识的知识论形态,其最大的理论诉求变成了获取世界之最终本质的终极性认识。
面对形而上学发展的这种偏向,康德所要做的就是通过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实现形而上学的扭转,重新确定真正的形而上学的发展方向。“近代哲学十分注重知识理论的科学性、证明性。这一思想到了康德那里,则演变成重新思考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问题。”[7]康德通过对理性能力的有限性的分析,区分开科学与形而上学,告诉人们,作为知识论的形而上学必然是一种独断论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对象是无法成为知识论研究的对象的;而更要强调的是,不作为“知识论的形而上学”而作为“一般的形而上学”却必定是可能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形而上学才表现出其独特的理论价值和正确发展方向。形而上学的这一发展方向就是还没有人走过的“批判的路子”(康德语)。康德的批判与扭转就表现在实现了从追求本质、规律的“知识论的形而上学”向诉求意义、价值整体的设定和信仰的“一般形而上学”的转变,实现了形而上学从主要表现于理论哲学向主要表现于实践哲学的转变,实现了从一种“本质论的形而上学”向“意义论的形而上学”的转变。通过这些转变,形而上学回归到其本身的含义上来,它不再是一个事实性问题,而变成一个意义性问题,对于形而上学而言,关于世界和事物的不是认识不认识问题,而是意义的理解、诠释和建构问题。
可以说,正是康德完成了对西方形而上学科学化、知识化状况和局面的根本性扭转,重新理解了形而上学的含义与研究方式,确定了形而上学的真正方向。康德明确指出:“形而上学是对人类理性的一切教养的完成,这种教养即使撇开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对某些确定目的的影响不谈,也是不可或缺的。”[8](P641)康德对形而上学的这种重建在现代哲学发展中表现出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意义,整个现代西方科学主义哲学就是在科学、非科学与形而上学的总体思想框架中形成了对哲学本体观的理解并展开对形而上学的批判的。虽然形而上学被现代科学主义哲学不断地加以拒斥、消解和否定,但形而上学作为一种整体性意义和价值的学问却始终贯穿于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的理解和建构之中,即使是在现代科学主义哲学阵营之中,比如卡尔纳普等人后来还是非常明确地承认和肯定了形而上学命题不作为表述职能但作为表达职能的价值命题是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的。卡尔纳普就指出,“形而上学命题没有意义”只是就其在知识论或科学知识方面而言的,并非是指它没有任何社会生活方面的价值,因为它像“抒情诗”一样表达了哲学家们的内心情感、意志或愿望,因而是不具有意义但具有价值的“价值命题”。[9](P25-26)显然,历经现代哲学的荡涤和解构,形而上学却始终没有终结,似乎愈益展现出自身的魅力,这是形而上学真正含义的回归和显现,当然也是与康德在形而上学上的远见卓识、批判性扭转和创造性重建密不可分的。“我们只有回到康德,然后才能遵循着哲学通过他安然获得的基本认识的方向,继承着永恒哲学问题因他而深刻化的纯粹结果,进而向前迈进。”[10](P81)那托尔普的声音仍旧回响不息。
[1][3][6]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
[2][4][5]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3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7]张能为:《康德意义:经验主义视角的解读与新路径》,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9]Rudolf Carnap.Philosophy and Logical Syntax.London:K.Paul ,Trench,Trubner ﹠Co.,Ltd.,1935.
[10]那托尔普:《康德与马堡学派》,载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