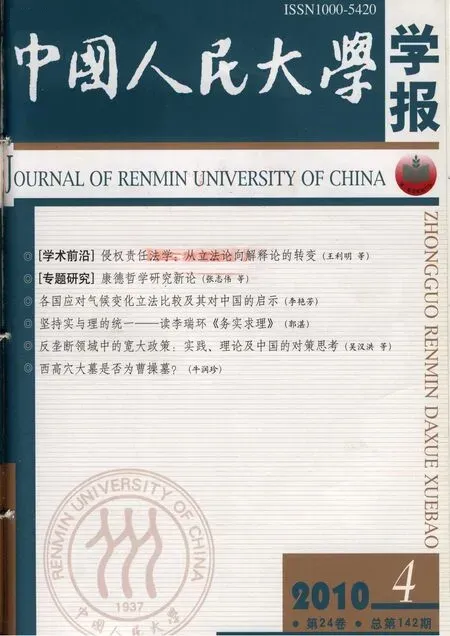《纯粹理性批判》对形而上学的贡献
2010-02-10张志伟
张志伟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众所周知,《纯粹理性批判》是有史以来对于形而上学批判最深入、系统、全面的著作。实际上,《纯粹理性批判》不仅包括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亦包括对形而上学的建设,而且这一方面与批判具有同样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形而上学(虽然他并没有使用“形而上学”概念)大致划分为三个相关的部分:一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科学;二是涉及“最高种类的存在”的神学;三是研究“第一原理”的科学。[1](P3)中世纪哲学家把这些不同的方面区分为“普遍形而上学”和“特殊形而上学”。对康德来说,前者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本体论即范畴体系,后者则相当于由笛卡尔的三条形而上学基本原理所确定的研究灵魂、上帝和宇宙的超越形而上学。如果前者可以称之为“本体论”,那么后者可以称之为“超越论”。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前言中康德谈到他的哲学革命时说:“这一尝试如愿得以成功,并且在形而上学探讨先天概念(它们在经验中的相应对象能够与它们相适合地被给予出来)的第一部分中,向形而上学许诺了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但是,从我们先天认识能力的这一演绎中,在形而上学的第一部分里,却得出了一个令人感到奇怪的、对于第二部分所探讨的形而上学的整个目的就一切迹象来看非常不利的结果,即我们不能凭借这种能力超越可能经验的界限,而这恰恰是这门科学最本质的事务。”[2](P17)康德认为他既证明了一种先天知识的可能性,也为作为经验对象之总和的自然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这就是所谓的“内在的形而上学”,当然与此同时也就证明了“超越的形而上学”在认识领域是不可能的。
毫无疑问,康德哲学具有二元论的性质,不过其目的却是克服笛卡尔式的二元论,纠正经验论与唯理论关于主体与知识相关,而对象则是外在的物的通常观念,以认识对象内在于主体之中来解决知识与对象的关系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康德是从二元论出发,并且将二元论推到极致,但放弃了“物自身”这一元而完全在主体之中来解决知识与对象的关系问题。所以,康德关于知性范畴的客观演绎意在解答范畴对于经验的客观有效性,亦即知性范畴应用于经验对象的客观有效性。由此,康德从根本上改变了认识对象的性质,使“内在形而上学”成为可能。
康德关于知性范畴的客观演绎围绕“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而展开,不过他的论证实际上有两个出发点:其一是感性与知性的区别,感性不能思维而知性不能直观;其二是杂多表象之联结即“综合”属于知性而非源自感性。先验统觉作为一切认识的最高根据和先验的条件体现为分析的统一性,所有表象必须以先验统觉为前提才能为我所知,才是我的表象。然而,由于先验统觉自身不能直观,因而杂多表象来自感性,所以当且仅当杂多表象中具有综合统一性的时候,我才能意识到自身的同一性。分析的统一(统觉)与综合的统一(直观)之所以能够沟通而相互联系起来,就在于知性范畴作为统觉的综合统一功能所架起的桥梁。至于知性如何能够应用于与之不同类的感性,康德通过先验想象力来解决问题:想象力在感性直观中盲目地发挥形成形象的作用,而形成形象所需要的综合则服从知性范畴的规则。先验想象力是“生产的想象力”,亦即“生产”对象的先验功能。所以,范畴对于感性之杂多表象的综合不仅是知识的先天条件,也是对象的先天条件。由此,我们就达到了先验哲学的最高成果:知性为自然立法。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往往从“知性为知识立法”的角度理解“知性为自然立法”,而康德所强调的实际上是“知性为经验对象立法”。
康德关于范畴的客观演绎使我们对于自然的看法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对于认识论以及本体论具有重要的意义。无论是认为外部世界自身具有逻辑结构(如亚里士多德),还是认为外部世界实际上是观念的世界(如贝克莱),都假设了由诸多属性所集合而成的对象独立于主体而存在,心物二元论成为不可克服的难题。“知性为自然立法”不仅保证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有效性,而且保证了经验对象的客观有效性,因为两者归根结底来源于知性范畴的综合统一功能。
总之,由感性直观提供感觉经验之杂多表象,由知性范畴提供综合统一杂多表象的规则,两者结合便形成了现象界。现象界不仅是可以认识的,而且可以形成科学知识。形而上学的第一部分即本体论作为“内在形而上学”由此而成为“科学”:本体论即先验哲学,先天认识形式作为现象界的先天条件亦即经验世界的逻辑结构。当然,形而上学的第一部分作为“内在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恰恰证明了形而上学的第二部分即“超越的形而上学”的不可能。先验分析论的重要结论是:“知性先天地可以做到的,永远无非是预先推定一般可能经验的形式,而既然不是显象的东西就不可能是经验的对象,所以知性永远不能逾越感性的界限,只有在感性的界限内部对象才被给予我们。知性的原理只是一些对显象做出说明的原则,自以为能够在一个系统的学说中为关于一般而言的物提供先天综合知识(例如因果性原理)的本体论,其自负的称号必须让位于仅仅一种纯粹知性的分析论的谦逊称号。”[3](P240)由此,康德以先验分析论之先验哲学取代了传统本体论的位置。康德的相关思想对于20 世纪哲学影响深远,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观点: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两者是重合的,也可以理解英美语言哲学对于形而上学(主要是本体论)研究的复兴。
如前所述,我们在康德的意义上将形而上学区分为两个方面,即“本体论”和“超越论”。在康德之前,这两方面都与认识论纠缠不清。在某种意义上,康德的工作是在两者之间作出区别,将本体论安置在合理的位置上,将超越论转移到伦理学的领域。这就涉及康德对于transzendental (先验)与transzendent (超越或超验)的区分。
transzendental 与transzendent 源自拉丁文,在中世纪基本上没有区别。康德着意在transzendental 与transzendent 之间作出区别,乃源于他对于形而上学两个部分的批判反思。尽管康德在概念的使用上往往并不严格,但是先验与超验之间的区别还是清楚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导论中说:“我把一切不研究对象、而是一般地研究我们关于对象的认识方式——就这种方式是先天地可能的而言——的知识称为先验的。这样一些概念的体系可以叫做先验哲学。”[4](P48-49)这可以看做transzendental 的基本用法。我们可以把“经验性的”、“先验的”和“超验的”(超越的)看做一组相关的概念:(1)“先验的”与“经验性的”区别,“先验的”所研究的是独立于经验同时构成经验之先天条件的先天认识形式。(2)“先验的”与“超验的”区别,“先验的”是经验的先天条件,而“超验的”则超越了经验,属于不可知的领域。(3 )“超验的”与“内在的”相对,“经验性的”与“先验的”都属于“内在的”:“先验的和超验的并不是一回事。我们上面所陈述的纯粹知性的原理只应当有经验性的应用,而不应当有先验的应用,亦即超出经验界限的应用。但是,一个取消这些界限,甚至让人逾越这些界限的原理,就叫做超验的。如果我们的批判能够做到揭露这些僭越的原理的幻相的话,那么,那些纯然经验性应用的原理就与后一些原理相反,可以被称为纯粹知性的内在的原理。”[5](P272-273)
虽然transzendental 与transzendent 这两个同源概念在中世纪时可能没有区别,康德第一个做了这个区别,但是这个区别在形而上学上是有其根源的。如前所述,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一般可以区别为“普遍形而上学”与“特殊形而上学”。由此而考虑康德对这两个同源概念的区别,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概念实际上相应于形而上学的两个部分。显然,康德之所以区别这两个概念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先验的观念性”(内在性),一方面证明形而上学第一部分作为内在形而上学或先验形而上学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则将超越或超验形而上学排除在了认识领域之外。
当然,康德的内在形而上学毕竟是“纯粹理性的体系”,仍然是一个封闭的意识的“宇宙”,传统认识论的二元论问题不可能由此而得到彻底有效的解答。康德之后,有些哲学家致力于将transzendental 与transzendent 重新统一起来,虽然他们在方向上可能完全不同,例如黑格尔和胡塞尔、海德格尔。黑格尔的《逻辑学》相当于将康德的内在形而上学与超越形而上学统一起来,或者说,重新赋予内在形而上学以超越形而上学的意义,而其“先验演绎”乃是《精神现象学》的工作。[6](P5)胡塞尔则从传统认识论之二元论难题出发,变物自体的超越性为意识的超越性(意向性),这似乎可以理解为唯有意识才是真正超越的。海德格尔(至少是前期的海德格尔)则将胡塞尔的“事情本身”从纯粹意识“深入”到了意识的“存在”(生存)。就此而论,意识的“宇宙”具有“开放性”,transzendental 重新获得了transzendent 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或许正是康德对于transzendental 与transzendent 的区别,为这些哲学家们将两者重新统一起来开辟了道路。从这个角度看,海德格尔将康德视为其基础存在论的唯一先驱,不能说没有道理。
[1]参见布鲁斯·昂:《形而上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2][3][4][5]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3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6]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