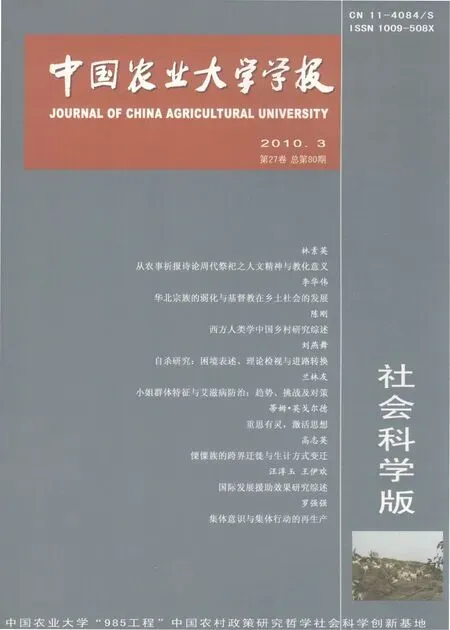国际发展援助效果研究综述
2010-02-09汪淳玉王伊欢
汪淳玉 王伊欢
国际发展援助效果研究综述
汪淳玉 王伊欢
国际发展援助作为发达国家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主要手段,自从其开始形成就受到各方的质疑。质疑的焦点一直集中在发展援助的效果方面。从不同学科视角得出的研究结论往往相互矛盾,甚至同一学科领域内的研究也不能达成一致。主要的观点大致上可以分为援助的有效性,援助的无效性以及援助有条件的有效性等三个方面。文章从分析路径、研究结论和相关建议三方面综述了国际发展援助效果的研究,介绍了发展话语之外的关于国际发展援助有效性的人类学讨论,并简要论述了发展研究效果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国际发展援助;援助效果;学科视角
国际发展援助在“二战”后伴随发展话语与理论的产生而蓬勃展开。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实践过程中,它对援助国与受援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围绕国际发展援助所带来的这些影响,不少学者试图通过大量的实证和理论研究来回答以下关键问题:援助究竟是有效还是无效,影响是积极抑或消极。一方面,这种对于援助效果的探讨关系到国际发展援助的合法性,即国际发展援助是否应该继续。这无疑牵涉到国际发展援助机构的未来走向。而另一方面,对援助效果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有助于双边和多边发展机构从经济安排、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积极反思和改善国际发展援助的效果。因此,国际发展援助效果研究逐渐成为了国际发展领域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热点领域。
尽管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对国际发展援助有效性的研究已日益增多,但这些研究常常相互问诘,得出的结论迥然不同。例如有学者认为国际发展援助是卓有成效的,它不仅是贫穷的国家摆脱贫困陷阱不可缺少的助力,也是灾后或战后重建的重要推动力量。但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国际发展援助的自利性本质,援助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受援国的状况,反而会加深受援地区人民的苦难。从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上来看,既有因为国际发展援助而取得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进步的范例,如韩国,我国的台湾;也不乏有接受了多年的发展援助,而国家依然积弱的事实,如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还有外来援助的数量和比例很小,而经济却迅速发展的奇迹,如中国,印度。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国际发展援助效果的研究进行整体梳理,以了解这些研究从何种视角出发得出了怎样的结论,而这些研究与结论对于国际发展援助,对于援助机构,对于受援国和援助国分别有怎样的启迪。本文将从分析路径、研究结论和相关建议三方面综述国际发展援助效果的研究。同时介绍部分人类学家对发展话语和国际发展援助的讨论与解构。
一、国际发展援助有效性的分析路径
国际发展援助有效性的分析路径与其定义和目标有紧密的联系。狭义的国际发展援助,又称“官方国际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指国家政府或多边发展机构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优惠贷款和赠款。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政府间的转移支付。[1]1OECD在1969年对官方国际发展援助设定了三个标准:由援助国官方承担;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促进其福利增长作为主要目标;援助资金以优惠条件提供,贷款中至少包括25%以上的赠款(以10%的折扣率计算)。[2]更为广义的国际发展援助还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优惠或无偿的物品、资金与技术。因马歇尔计划对战后欧洲国家的重建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通常被视为国际发展援助的正式开始。[1]23
国际发展援助旨在通过经济援助的方式来解决受援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政治等各种问题。因此,对国际发展援助效果的探讨便是考察国际发展援助的目标的达成情况:受援国的经济是否得到了增长,社会福祉是否得到了提高,政治与自然环境是否得到了改善等。从过程研究的角度来看,国际发展援助效果不仅体现为国际发展援助目标的实现,同时还体现了对国际发展援助过程的控制,体现为一组庞大的、涉及方方面面的目标和产出。[1]160
简言之,国际发展援助不仅仅是一种资源和服务跨国转移的经济现象,它也是涉及国内财政开支和纳税人利益以及国际关系尤其是南北关系的政治问题。[3]72此外,援助国带来的思想、理念和制度安排还延伸到受援国的社会、文化领域。因此,有关国际发展援助效果的研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多重视角。
(一)经济学视角的国际发展援助效果
国际发展援助从最初就具有浓厚的经济学的色彩,因为国际发展援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以往的国际发展援助效果研究可以说是遵循了从计量经济学到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逻辑。我们可以参考杜古利雅戈的做法,将经济学视角的国际发展援助效果研究大体分为三类:(1)援助对投资、储蓄的影响;(2)直接考察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3)一定条件的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4]227-254前两类研究主要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模型来考察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而得出有关援助效果的结论;后一类研究则主要考察经济政策与经济制度等因素对国际发展援助效果的影响,这已经具有发展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转向。
1.援助与储蓄、投资的关系
在国际发展援助的早期阶段,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该模型通过讨论经济增长与储蓄、投资以及人口增长、技术水平等因素,说明国民收入的增加是投资增量的函数,即经济增长来自于投资。由于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满足经济持续增长的储蓄和外汇收入,这在理论上就形成了“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因此,在早期的国际发展援助中,最重要的援助策略是为受援国提供急需的资金,以刺激投资和增加就业,从而带动受援国的经济增长。[5]19对国际发展援助有效性的考察就集中在援助是否能够增加受援国的储蓄与外汇,弥合缺口,改善受援国的经济状况。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研究者就根据当时可以获得的数据发现,援助的流入会减少同等数量的受援国的储蓄积累。[6,7]援助的可替代性(fungibility)意味着援助所激发的边际活动并不会使储蓄增加。如果说制约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资金积累,那么这一结论可以说是挑战了援助的合法性,因为外国援助更有可能被发展中国家用于消费,而不是用于投资。[8]289
杜古利雅戈等分析了29项关于援助与储蓄的研究和37项关于援助与投资的研究,并基于这些研究的结论分别建立了援助对于储蓄和投资的弹性系数图。他们认为,援助资金中约有25%能够促进储蓄,而剩下的75%只会导致公共开支(public consumption)的增加。而公共开支与增长的相关分析中出现了负相关系数,这说明公共开支对增长有负面的影响。[9]452
总体来看,这些研究中较为一致的结论是援助会导致公共开支和消费的增加。但关于援助和储蓄与投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矛盾的。部分学者认为援助并不能够导致储蓄的增加,而部分学者认为援助中有四分之一的资金能够促进储蓄。这些研究并没有回答,援助是否能够通过促进储蓄进而推动受援国经济的增长。确实,如果不考察资金的来源与走向而试图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解读国际发展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这样得出的结论即便是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也缺少学理上的支持。国际发展援助、投资和储蓄、经济增长这三者之间的因果链条并不牢固。
2.援助与增长的关系
另一类研究抛开了哈罗德-多马模型,直接关注援助与增长的关系。这类研究同样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通过回归分析探讨这两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不同学者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有些学者认为援助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米诺伊和瑞德区分了两种援助资金:针对经济发展的援助与针对地区政治的援助。他们发现如果单纯考虑针对经济发展的援助资金的影响,那么这种对外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面的、持续的,统计上显著的”。[10]1得出类似结论的还有克莱门等人。通过评估援助对于预算、收支平衡、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和工业的影响后,他们发现,投向这些部门的援助资金在短期内对经济有明显的影响。平均来说,每1美元的援助会带来1.64美元的收入的增长。[11]34对那些希望得到援助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中那些呼吁增加对外援助的个人或机构来说,上述研究无疑为他们的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然而,在分析了543份类似的研究结论后,杜古利雅戈指出这些研究的回归分析中存在多重共线性。如果只取前250个估计值,那么回归分析的结果将显示援助有明显的效果。但如果考虑所有的估计值,结论就会完全不同:援助对增长的影响几乎趋于零(0.02~0.04)。[9]451-453显然样本量过小所得出的结论具有误导性。此外,由于研究者不愿意发表具有负面影响的报告,这类研究的结论常常是有失偏颇的。
应当说,经济学的视角面临一个困境,即经济学家在将复杂的问题化约为经济问题的过程中,不得不舍弃众多重要的变量,例如政治、文化、社会等干扰因素。利用某些区域的经济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能够类推到其他区域之中。结论的矛盾与断层亦在所难免。
3.援助与经济政策、制度的关系
有鉴于此,许多研究者,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家,希望通过分析受援国的经济政策环境来解释国际发展援助在不同国家的表现。这类研究目前有三种不同的结论:(1)援助只能够促进拥有良政的国家的经济发展;(2)援助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与经济政策无关;(3)援助即便是在经济政策良好的国家也并不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本赛德和杜大伟利用OLS(正交最小平方)与2SLS(二阶最小乘法)研究了发展中国家1970—1993年的数据,发现援助在拥有良好的财政、货币和贸易政策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对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在缺乏良好经济政策的国家则无效,反而会驱逐私人投资。[12]这一结论得到了众多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的热烈欢迎。世界银行自身的调查报告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3]28-44即国际发展援助在良好的经济环境下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减贫和社会福利。克莱尔和杜大伟研究了59个发展中国家1974—1997年的数据,发现国际发展援助对增长的影响有赖于经济政策的质量。[14]1475-1500布归农和森德伯格同样认为,援助与发展结果之间存在某种尚未打开的黑匣子,这个黑匣子就是两组关系:援助国通过援助资金和技术援助影响受援国的政策决定者,进而影响政策的制定(援助国还可通过软贷款的条件间接影响到政策的制定)。[15]317因此援助的效果有赖于良政的实施。自此之后,援助界开始呼吁选择受援国,即只有那些有强烈减贫意愿、并开展了相关改革的发展中国家才可能得到某些援助,例如总预算支持(GeneralBudget Support,GBS)。
但也有学者发问,难道良好的政策真是援助有效的前提吗?这些学者的研究认为,首先,类似的经验研究取决于模型和特定的案例。[16]399其次,不难发现,援助即便是在恶劣的经济政策条件下也能够促进增长,即援助效果并不依赖于是否有良好的经济政策。[17]375
第三种论点是由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斯特莱等提出。他们在本赛德和杜大伟[12]的研究基础上使用相同的解释变量(援助额/GDP,预算赤字/GDP,通胀率等),唯一的差别仅在于分析中的面板数据比之前多了四年(至1997年),但结果表明前者的结论不能得到数据支持,“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如果认为外援能够有效促进拥有良政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就过于乐观了”。[18]779-780
诚然,从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再到新自由主义,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都有不同的解答。政府是否应当干预和调节市场?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介入市场?既然对这些经济学界都尚未有定论,什么是良好的经济政策就更难以有明确的答案。此外,一国的经济并非遗世而独立,良好的经济政策也应当与国际经济环境互为呼应。因此,剥离了外部与内部经济环境而开展的有关良政与国际发展援助的关系的探讨,本身就存在先天不足。
与着眼于经济政策的发展经济学不同,制度经济学探究的是影响经济政策的更深层原因——制度,他们试图发现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由此探索相应的提高援助效果的对策。
首先,在制度作为因变量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大量的外援进入受援国后对制度的影响之一是宏观经济失衡,这种失衡类似于荷兰病,即热钱的涌入会带来竞争力减弱以及出口、增长和就业机会减少。[19]372援助不仅侵害了受援国政府制定预算的能力,使长期规划复杂化,还导致政府支出过度并且不可持续。同时,高援助与低税收之间存在双变量关系,特别是在非洲国家。在短期内援助能够替代税收,但从长期来看,对非洲的援助并没有使非洲的纳税负担降低,[20]19-20对援助有依赖的政府的税收管理和制度能力建设还会被削弱。[21]6此外,援助还可能增加制度运行的成本。项目过多导致受援国疲于应付项目各环节的准备工作,行政成本增加[22]4。例如莫桑比克在2001—2003年间就接受了1 921个项目;而坦桑尼亚在同一时期有1 528个项目。在加纳,高级官员每年要花费44个星期来协调或参与援助国派来的指导代表团的工作。[23]261而且援助本身可能会延缓制度变革,甚至导致制度恶化。[24]77在考察了南撒哈拉地区的援助历史后,莫斯等[21]1认为,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来自国际社会的国家政府对其民众较不负责,在维持公共合法性方面的压力较小。他们也不太可能投入和发展有效的制度与机构。例如从1980年以来,非洲领导人平均在位时间是12年,是西方民选总统的在位时间的三倍。同样关注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布罗缇甘在调查了32个非洲国家1982—1997年的数据后发现,在较高比例的援助与治理恶化之间存在统计上的强相关。[23]255
更为重要的是制度也可能被视为自变量。这一类研究的出发点是承认优良的制度或善治能够帮助受援国更好吸纳和利用援助资金。世行的援助评估报告[13]60-78指出,如果制度和机构积弱,政府的开支就摇摆不定,而援助与援助对增长带来的影响也同样变得难以预料。这里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受援国的吸纳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即低收入国家吸收援助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援助的收益是趋于递减的。[14,25]有研究者认为,援助的边际影响的转折点,或说援助门槛,是受援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到45%。超出这一比例,受援国的吸纳能力就相当有限了。这也被称为援助饱和点。在这一点上,援助的增加对于促进经济的增长已然无效。[26]1133一般而言,政策和制度环境越优越,受援国的吸纳能力就越强,饱和点也越高。但哪怕制度再优越,援助的饱和点也是存在的。[27]1006大部分关注治理与发展结果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认为,善治能够带来更好的援助效果。[28]49-123虽然善治与良政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但可以跨过政策这一环节,直接分析善治对经济结果的影响,阿西墨格鲁指出,该影响是正面的。[29]2-5这便是以治理表现为基础的援助资金的分配体系背后的逻辑。
总之,援助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无统一的结论,难以断言良好的经济政策是否是援助的必要和(或)充分条件。而援助与制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大量援助可能会导致制度的固化或恶化。然而,本身良好的制度能够提高吸纳援助的能力,使援助能够发挥更为明显的效用。这类研究结论将发展援助机构推入了困境:援助国应当援助制度和政策环境已经良好的国家,但最需要援助的国家往往并不具有这些条件。上述制度经济学的面向意味着国际发展援助已然超出了计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非经济因素也成为考察援助效果的重点。至此,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成为探讨援助效果问题的必要选择。
(二)政治学视角的国际发展援助效果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国际发展援助的历史渊源和政治动因。国际发展援助发端于“二战”后以及冷战期间的国际政治环境。除人道主义与经济目的之外,通过国际发展援助影响受援国的政治倾向和国际关系格局也是国际发展援助的重要目标。因此,从政治学视角探讨援助效果问题,一方面可以考察国际发展援助是否实现了援助国及受援国的政治意图;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阐述国际发展援助的政治目的实现过程,来解释为何国际发展援助不能实现其经济目标。
国际发展援助是保护和促进国家安全、主权以及地域国际环境的一种有力工具。它是争取盟友和朋友的手段。[1]57-58因而任何官方发展援助的作用都具有双重性质:一是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二是为援助国自身的政治、经济战略目标服务。[5]19也有更为激进的学者认为,无论什么样的对外援助,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主要目标都是促进和保护国家利益,除此之外,没有更高的道德原则。[6]一位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官员这样坦白地描述了援助的政治性质:“我们基本的、广泛的目标是一系列政治上的目标,决不是为发展而发展……从而确保在国外的私人投资,特别是确保美国的投资受到欢迎和优待。问题在于要估量用哪种方式可以使发展项目给美国的总体利益带来更大的贡献”。[30]111关于德国对华援助的研究也表明,国际发展援助政策日趋实用化。实用化的关键之处是讲回报,或者政治的,或者经济的,或者战略的,至于消除贫困这一国际发展援助最根本的目标反而被淡化。[31]30G·凯和S·阿明在关于商业资本主义的讨论中指出,法国在西非国家的传统上层贵族和其附属集团之间制造不和,从而削弱上层集团的谈判优势。[30]44-45世界银行的政策倾向与发达国家的政策导向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32]38这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际发展援助的本质。
因此,国际发展援助过程中的一些奇怪现象就能得到解释,国际发展援助没有取得成效也就不足为奇。首先是捆绑性援助的问题(tied aid)。很多援助国在向受援国提供援助的同时,会指定援助项目的具体实施方。大约有70%的政府援助是直接施惠于援助国本身的私人公司与专家,因为这些公司接受政府的合同,负责提供第三世界某些发展项目所需的专利和技术,所以援助的款项实际上付给了这些私人公司。[30]113,121其次是援助资金的走向问题。援助并不一定是给予了最需要援助的国家,而是向更有偿还能力、更有经济振兴前景的国家,这些国家从长远来看更可能成为西方的稳定的市场。施奈德、胡克和泰勒[33]294-320通过研究流向非洲的资金,否定了有关援助国利他主义的说法。阿勒斯狄娜和杜大伟[34]33-63也发现,决定援助资金流向的更多的是殖民地历史和联合国的投票方式,而不是受援国的政治制度或经济政策。例如,并不民主的前殖民地获得的援助比民主的非殖民地国家多出了两倍。三大援助国,美国,日本和法国都有不同程度的援助偏好。美国将其三分之一的援助资金投向了埃及和以色列;法国投向了它的前殖民地;日本的资金流向则和联合国的投票方式有关:紧挨着日本投票的国家获得更多的援助。可以说,双边援助与贫困、民主和良政的关联相当微弱。第三,为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援助不能有效地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例如,56个国家1970—2001年的数据表明,占总援助的70%双边援助在冷战之前和之后对于受援国的效果都要优于冷战期间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援助在冷战时期服务于援助国的全球地理政治利益,而并非受援国的经济发展。[35]161-180鲍勃和鲍威尔比较了流向政治盟友和非政治盟友的援助效果,也发现对非政治盟友的援助能够促进受援国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而对于其盟友,援助则不起作用。[36]5-6
国际发展援助的这一本质决定了援助国与受援国在利益上的不连续性,双方必然在国际发展援助问题上产生分歧和摩擦。王伟认为,只要援助国与受援国所追求的发展议程不同,可替代性就会持续存在;当援助国增多时,援助可替代性就会增强。这对受援国而言是有利的,因为它可以从中选择条件更为优惠、更符合自身利益的援助。受援国在这过程中受援国获得的一个重大进展就是“非捆绑性援助”(untied aid)的出现,强调受援国在发展中的自主性(ownership)。[37]17-18
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从政治视角讨论国际发展援助的研究,更多揭示了援助国在援助过程中的政治目的和意义,忽视了受援国在其过程中的政治活动和外交意图。并非所有受援国都被动接受援助国在本国的活动,任援助国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受援国可能通过在多个援助国和援助机构之间的活动达成本国的政治利益,而针对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不多。
(三)发展社会学视角的国际发展援助效果
随着国际发展援助的开展及大量的援助资金投入,很多受援国收效甚微。援助过程中的非经济因素在经历了“发展等于经济增长”阶段后再度成为社学研究的重要讨论领域。
鲁兹等的研究所采用的虽然是计量经济学的方法(G MM,高斯混合模型;与3SLS,三阶最小二乘法),但他们考察的是援助与受援国的制度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政策改革在极大程度上受到制度的影响,而制度又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如社会资本等,这些是长期经济增长与收入的深层决定因素。但该文对于应当如何积累社会资本并未作深入的阐述。[38]510-525
此外,社会学家从国际发展援助项目失败原因出发,总结出一系列提高国际发展援助效果的方法,参与式发展因此成为国际发展援助中的热点之一,例如上世纪80年代,参与式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发展项目之中,即在发展干预过程中考虑农村本身的社会经济文化特殊性。世行发布了《把人民放在首位》,鼓励广泛使用参与式农村评估工具(PRA)。世行1998的报告主张援助国与受援国政府共同努力,摒弃了结构调整时期(杠杆理论)和冷战时代援助国向受援国附加种种援助条款的做法。这一方面是由于国际环境变化的压力,同时也与发展社会学中尊重本土知识、尊重当地人的选择等理念遥相呼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国际发展援助效果的讨论中,人的因素逐渐被纳入考察的视野。研究者发现,受援国当地居民和官员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援助国的项目,他们在项目周期的各个环节都可能发挥其能动性,不断形塑其他行动者的行为和项目过程,使其进入自己的“项目”,按照自己的意愿运行。[39]75-76因此,发展项目并非是从目标到结果的简单的线性过程。[40]1另外,由于项目性质不同,实施的环境迥异,在某地经过评估发现有效的项目可能并不能被顺利地移植到另一国或地区并发挥作用。不是所有的援助都会受到影响评估的制约。援助也并不是只提供给起作用的地区或部门。[15]316-320
发展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为国际发展援助在微观领域内的实施积累了大量有益的经验,参与、赋权、与穷人一起工作等理念是从国际发展援助项目实践中积累的,为国际发展援助的有效性做出了贡献。但同时,对发展的反思使很多发展社会学与人类学家意识到了发展更为深刻的内涵,对参与、赋权的质疑逐渐升温,这些将在第四部分进一步展开讨论。
二、国际发展援助有效还是无效
上述对于国际发展援助效果的研究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两种矛盾的结论。一派认为援助有助于受援国经济增长和发展,另一派则认为援助对于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而言,是低效或无效的,并且两派都有充分的证据支持。[41]40不同的国别与不同时期的数据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而微观上项目所取得的明显成就与宏观上的受援国经济并无起色并存,这些对立成为了现阶段国际发展援助有效性研究结论的主要特点。
(一)有效论
萨克斯[42]188-209对国际发展援助十分乐观。他认为非洲实在太穷,离开外界援助根本无力发展。非洲需要援助资金的大力推动,才能终结贫困。国际发展援助的成功案例众多,比如对河盲症的治疗[43]24-26。在这一发展项目中,26个援助国共同行动,挽救了30个国家中60万人的视力,开发了2 500万公顷土地。由于国际发展援助,马拉维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免除了初等教育的学费。当学生人数增加了120万人后,援助国进行了教师培训,到2001年为马拉维新增了27 000名教师。国际发展援助还消灭了天花,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在孟加拉和埃及推行了现代的避孕法,提高了乌干达和布基纳法索的入学率,帮助波斯尼亚、东帝汶和塞拉利昂等国家实现了战后重
建[44]142。
克莱尔等[26]1125-1145特别分析了17个战后国家在第一个十年里的重建情况。援助资金在这些国家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在调查了58个国家(包括23个非洲国家)1965—1999年的情况之后,肖维特[45]4指出,援助能够帮助脆弱性较高的国家抵御外部的政治和经济风险。这个结论有其独到之处,因为它指出外部援助如果用于经济动荡和地区局势不稳的国家,能够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她的结论也表明,尽管外来援助能够帮助国家抵御地区的政治动荡,但对于内政不稳的国家有效性较弱。
卡森[46]所作的经典的研究也表明,大约有一半的援助项目是有效果的,在剩下的项目中,即便是失败了,也只有极少数的项目为当地带来了危害。
有效论的背后实际上存在这样一个预设:发展中国家无力通过自身的力量获得发展,而需要外部的干预或支持。具体来说,因为发展中国家资金匮乏,融资能力弱,投资较少,经济无法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因此会陷入贫困与不发达的恶性循环之中。在外国援助的帮助下,它们可以利用援助资金投资,以此带动就业、消费和出口;甚至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后发优势”,大幅缩短技术进步所需的时间;或借助外资,通过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此外,援助可以减少落后国家因贫穷而死亡的人数,改善他们恶劣的生存和生活环境。有效论也是发展事业、发展机构、发展话语和理论生存的根基。
(二)无效论
实际上,国际发展援助的效果一直受到质疑和挑战。早在1969年,世行的皮尔森报告就承认了国际发展援助的低效,在经历了20多年的国际发展援助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加大,贫困人口不断增多。此后,有学者悲观地发现,发达国家在50年代许诺的富足之国迄今并未出现,相反,发展的话语和实践带来的是大规模的欠发达和贫穷,是难以言说的剥削和压迫[47]3。可以说,国际发展援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几乎为零[9]433。
伊斯特利[48]15-16对国际发展援助的效果心存怀疑。他认为,如果发展的目标是填补投资与储蓄的缺口,如果说增加投资将导致更高和更有持续性的发展进而导致人均收入的提高,那么显然国际发展援助就没有达到这一目标。以赞比亚为例,尽管国际发展援助进行了多年,人均收入仍不足500美元。而如果国际发展援助真的有效果,那么赞比亚的人均收入应当超过了2万美元。他对国际发展援助的悲观论调似乎在对整个非洲的研究中进一步得到了证实。尽管西方在过去的40年里向非洲注入了4 500亿美元,非洲的经济境况并未有长足的改观。20世纪80~90年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26次给予科特迪瓦结构性调整贷款。可这段时期,该国却陷入了历史上最长也是最糟糕的经济衰退,其人均收入也大幅下降。近年来几乎所有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国家,都曾接受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力干预[49]53。鲁斯[19]363-381通过比较1970年至2003年非洲GDP数据与ODA占非洲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后发现,截至1992年,援助占非洲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攀升,但非洲的经济增长一直持续低迷。1992至1997年,非洲经济呈现上升势头,而这段时期ODA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并没有显著增加。更为严重的是,大多数受援国,尤其是南部非洲的大部分国家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援助以后,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反而经济停滞甚至倒退,贫困人口不减反增,而且对援助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依赖[50]55。即如果没有外部援助支持,受援国国内公共服务机构就无法正常运转,其发展计划和政策措施就无法和难以付诸实践。在经过了长期外部“输血”以后,受援国自身的“造血”功能不但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还有可能遭到了破坏。孙同全认为,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受援国自身落后的经济技术基础和羸弱的管理体制,这使受援国往往不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需要建设经济体系,而只能接受援助国的安排。[50]58
在有效与无效之争中,最为常见的是国别研究。研究者试图解释的是同样接受了大量援助,为何有些国家借此获得了良好的发展,而有些国家深陷贫困的沼泽;或者,为何有些国家接受了大量的援助经济却没有起色,而有些国家接受的外援(总量或人均)较少却获得了经济的起飞和成功。在这方面,常被研究者作为例证的有中国①尽管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接受了大量的外来援助,但人均受援金额与外援占GDP的比重均很低。中国对外援的利用、管理和监督均有别于大部分受援国,而中国利用外援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受援国以及中国作为援助国提供参考。这些观点笔者将另有一文阐述。,越南,印度,墨西哥等。波萨尔比较了越南与尼加拉瓜在接受国际发展援助后的经济社会变化。[44]137-138越南尽管未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一员,却成功地开拓了出口市场,实现了经济的多样化,人均收入持续增长,贫困人口不断减少。同样接受了援助的尼加拉瓜尽管可以进入美国市场,但在克服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方面并无进展。相反,马来西亚,印度,智利等国,并未一直接受大量的国际发展援助,却取得了优于一般国家的发展。有趣的是,同一个国家可能被视为援助有效以及无效的例证。例如墨西哥。它属于北美经济贸易圈中的成员,进入美国市场无需关税,而且美国对墨西哥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并吸引了大批墨西哥劳动力,但墨西哥在90年代人均年收入增长不到百分之一,长期被视为援助失效的例证。而1994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向墨西哥的援助成功地缓解了墨西哥的债务危机,又常被引为援助有效的证据。
莫斯利将有效与无效之争概括为“宏观与微观矛盾”(micro-macro paradox),[51]即大量的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表明援助确实发挥了作用,特别是在卫生、医疗、基础设施等领域。但在宏观层面,尤其是国别的层面,援助的效果更为复杂。至今实证研究都无法在宏观层面得出统一的结论。
有些学者试图解释分歧产生的原因,这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方法论的层面,换言之,可能由于援助动机多样,外援与最终结果之间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而分析工具又有限,因此援助有效性的实证研究一般都不能得出清晰的结论。目前来看,不少研究将援助作为单一的变量,考察是否更多的援助会带来更好的结果。这种跨国的研究通常都会发现援助与发展结果之间的关系脆弱而且模糊不清。[15]316鲁兹等认为对援助有效性的研究之所以未能得出明晰的结论,一方面是因为缺少数据,另一方面是因为使用了不恰当的计量经济学工具和化约了的经验观察。[38]510
三、有关提高国际发展援助有效性的政策
很多研究者常提出的问题是“援助因何无效?怎样才能有效?”对此类问题的分析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从最初单纯的经济学探讨转向了政策、制度等领域,并形成了援助效果需要援助国和受援国双方共同努力的共识。
世行在皮尔森报告中反思了上世纪60年代国际发展援助的局限,认为只注重受援国的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公平是造成贫富差距不断增加,受援国民众生存环境恶化的根源,减贫因此在上世纪70年代成为国际发展援助的热点。但减贫在主要的受援国进行了多年,效果并不显著。发展机构和经济学家(例如华盛顿共识、世行1998年的援助评估报告等)开始将经济政策纳入考虑的范围,认为只有适当的贸易、金融和财政政策环境下援助才可能发挥效用。在后来的研究中,制度、社会资本等非经济因素被视为制约援助效果的重要原因,双边或多边的援助机构、非政府组织因此将制度改革、政策倡导等加入援助的条款。在这一过程中,蒙特雷共识(于2002年首次正式提出援助效果的理念)、巴黎宣言(2005)、阿拉克行动方案(2008)等国际性文件详细规定了援助国和受援国应当采取的措施以保证援助的效果。[52]
(一)对援助国的建议
波萨尔批判了援助国的错误做法,并将之归纳为影响援助效果的七宗罪:缺乏制度建设的耐心;不能也不愿从不成功的项目和国家撤离;失败的项目评估;认为参与就是自主权(ownership);同一受援国内不同的援助国之间缺乏协作;转移支付不足而且不可靠;对当地的公共投资不足等。[53]3此外,援助国认为严格的贷款条件就能够带来所期待的政策变化,进而推动受援国的发展。通过援助条款,援助国有关什么是正确的发展政策的种种观点得到了声张,但这些观点往往鲜有参考受援国的社会经济特点。[15]316-320
这些问题实际上在蒙特雷共识上就已经提出并制定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例如它强调,多边和双边金融及发展机构应加紧致力于按最高标准协调统一业务程序,以降低交易费用,并且更为灵活地使用和交付官方国际发展援助款项;国际发展援助要与受援国国民的发展需要和目标相结合;支持并践行所作出的倡议,取消援助附带条件;进一步努力解决因国际发展援助所造成的负担及其引起的各种限制问题;加强受援国的援助吸收能力和财务管理能力,以利用援助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采用最适当的援助手段交付可预测的资源;使用发展中国家已经形成的,包括减贫战略在内的发展框架作为交付援助的工具;增加受援国对技术援助方案设计的参与,包括采购和自主权,并更加有效地使用当地技术援助资源;提倡以广泛的国际发展援助促使外来投资和贸易和发展资金量增加;加强三方合作,包括经济转型国家间的合作和南南合作,以此作为援助的交付工具;改进广泛国际发展援助对不发达国家的目标导向、援助协调和成果监测评估等。
在蒙特雷共识的基础上,100多个国家在2005年签署了有关援助有效性的巴黎宣言,提出援助国与受援国需遵从的五项援助有效性监测指标:受援国自主权(ownership),受援国与援助国的协调(alignment),援助国之间的合作(harmonisation),管理援助结果(managing for results),对彼此负责(mutual accountability)。巴黎宣言认同需要提高贷款的协调性,提高援助国与受援国发展策略的吻合度,降低受援国对援助国的依从,按照受援国的表现(国家政策的力度与中期指标)来分配援助款项等。
2008年的阿克拉行动计划旨在加速与深化2005年巴黎宣言的实施。该行动计划的特征是强调受援国的自主权,即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当对自身的发展政策拥有更强的主导权,与本国的议会和民众共同决定发展政策。援助国应当尊重受援国的发展优先序,促进该国的人力资源与制度建设。
在西方学者的建议中,还一种方法是将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委托-代理关系,利用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设计种种可行的机制,使两者间的“目标”尽可能接近,努力解决其中的逆向选择、代理风险(fiduciary risk)等问题,从而有效地达到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的目的。在西方的援助体系中,援助国向受援国提出种种条款(conditionality)较为常见。这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发展援助最初就是为了保证“二战”后受援国国家的政治趋向和世界格局朝有利于西方援助国期待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量的援助贷款是通过受援国政府作用于该国,难免产生需要规避的代理风险。而事实是,很多受援国并不能兑现当初为获得贷款和援助而许下的改革承诺。即使双方选择了合适的“限制”,援助合同执行之后,监督成本会非常高,可行性因而也就成了问题。并且与传统的委托-代理问题不同,援助国并没有“剩余索取权”,它最多能做的就是在受援国不予配合的时候,拒绝提供进一步援助。因此斯多克区分了事前制约(ex-ante conditionality,在受援国做出某些承诺后提供援助)和事后制约(ex-post conditionality,在承诺兑现后提供援助),建议援助国根据最终结果和可观察到的政策的质量,来签订援助合同。[54]
(二)对受援国的建议
为帮助受援国实现经济的起飞和社会的进步,援助国、援助机构和经济发展领域内的专家们开出了一系列药方,但这些建议均遭受挫折。最初,对受援国的建议是大力加强经济建设,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但大部分受援国的经济并没有起色,不能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快速城市化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且经济增长的涓流效应也并没有发生。贫困因此成为上世纪70年代的主要问题。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和里根政府推动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此影响下,合适的财政、金融和货币政策成为提高国际发展援助效果的重要因素,结构调整理论成为华盛顿共识的指导思想。受援国被建议尽可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全面发挥主导作用。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甚至引发社会动荡。上世纪90年代晚期,受援国不民主、腐败的制度往往被视为影响援助效果的重要因素。因此,蒙特雷共识认为,援助国和受援国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以增加资金流动的透明度和信息交流。
(三)其他建议
也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更为具体的建议,如教育应该是国际发展援助的重点投资方向。[55,37]教育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本,加强社会的凝聚力,进而影响制度建设和政策改革,而这些是使援助产生效果的深层次的原因。安思铎和南瓦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援助、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关系。[56]631-639在低收入国家,致力于初等教育的援助能够有效推动经济发展;而在中等收入国家则需要更高层次的教育。而在战后重建方面,在动乱结束后的第一个四年内,援助资金应逐渐增加,以提高受援国的吸纳能力,并在第一个十年结束时恢复到一般的水平,以免形成援助依赖。并且援助的资金应当首先支持受援国的社会政策建设,其次是产业部门建设,这将对受援国的宏观经济产生更为持久的影响。[26]1125-1145
有些学者对提高援助效果十分乐观,认为尽管“有关跨国的对外援助效果的研究是经不起推敲的。但这绝不意味着所有的援助都是无效的,也不意味着我们无力使援助更加有效”。[15]320而也有学者认为,提高国际发展援助的有效性应该说是困难重重。首先,以国际发展援助的效果来决定下一次援助的方向和国家面临较多的问题。一是时间性。如果检验的时间太短,不利于长期规划的实施,而如果太长,受援国官员缺少努力实施援助项目的动机,因为其在位的时间是受限制的。二是公平性。因为它并不是根据受援国的需要来决定援助的配置,而那些“表现不好”的国家,可能正是非常需要外国援助的国家;而那些“表现较好”的国家,很有可能无需进一步的援助,经济也可以实现持续发展。[41]42其次,政治性的援助机构是多元的,分散的和多维度的。因为在同一个援助机构也有不同行动者发挥作用;援助者可能意见并不统一;同一个援助者可能同时追求多个目标。从崇高而目标远大的宣言到真正的行动与决策,往往有不同的政治过程、行动者和利益横亘其间,[57]577这些都增加了实施建议的难度。
四、对国际发展援助的反思与批判
在上述文献中,认为国际发展援助有效果的一方无疑是处于维护发展机构和事业的立场,而认为国际发展援助无效或效果不显著的一方也在竭力寻找效果不显著的根源:受援国的制度、政策环境,援助国的援助力度,选择受援国的标准问题,援助国之间的协调,援助国与受援国的合作障碍如此等等,以探讨如何才能使国际发展援助变得有效。但也有一批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发展和干预本身持否定态度,认为国际发展援助没有合法性依据,国际发展援助没有效果也是理所应当。
在自由贸易派的代表人物彼得·鲍尔看来,那种认为应当援助穷国的观点“可以休矣”。对外援助本身就是物质增长的障碍,它是对资本的无效利用,不利于竞争。援助带来依赖,给受援国上层权贵带来寄生生活。[30]119但鲍尔也承认援助这一“产业”看来已无法取消,所以只能尽量有效地利用援助。更为激进的海特①海特本人曾在世界银行下的一家援助机构任职。当时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海外开发署拒绝发表她向该组织提供的关于60年代拉美援助经费发放与使用情况的报告。后来这个报告以手稿的形式刊印出来,即《帝国主义的援助》。认为,援助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假面具”,其目的是要在新殖民主义时期继续保持资本主义渗透机制的作用,是西方资本主义攫取第三世界资源的又一种方式。援助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方针施加很大影响,使发展方针最大限度地符合资本主义的利益。其影响的途径就是发放贷款的各种附加条件,这些条件表面上是为了振兴受援国的经济,实际上却是要使其长期保持对外国资本的依赖。[30]119-121对于有些学者的观点——援助经费若管理得当,则可以收到较好效果——韦伯斯特认为不无道理,但所谓“好的管理”,对于受援国的上层利益集团而言,是有着社会与政治含义的。[30]125
所谓好的管理又是怎样呢?公开、透明地使用援助资金,以赋权、参与等方式选择发展的路径等是公认的良好的援助资金管理方式。但无论赋权还是参与,归根到底还要取决于社会强势群体在多大程度上容许农民的参与;多大程度上愿意赋予农民以权利,即农民的参与和赋权最终取决于其他社会行动者的权力滴流。其实这些理论不过是为了寻找一种更有效的话语解释和话语统治。[58]54
埃斯科瓦尔借助福柯对知识、真理和权力的分析,追溯了发展主义话语的历史系谱。他认为发展话语将纷杂多样的农民化约为“小农”,变为应该被管理、教育和规训的对象。[47]在国际发展援助机构的协助下,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与之相关的生产和权力系统得到了强化。弗格森也同样解释了为什么发展机构一定要把一个明明拥有市场的国家(莱索托)定义成一个应当实施社会发展项目的“欠发达”国家。[59]因为如果不这么定义,所有在莱索托的社会发展项目都会荒诞可笑。弗格森发现,原本去政治化的发展话语反而生产了一个无孔不入的官僚机构。
这些论述深刻地剖析了发展、发展话语、国际发展援助的本质。只有将第三世界国家定义为第三世界,发展机构与组织才有了生存的根基,国际发展援助才能够不断地影响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使其向援助国期待的方向发展。
五、国际发展援助效果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援助的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国际发展援助的思路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起初,在经济模型的指导下,人们以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最重要的原因是缺乏资本和技术,而这个问题是很容易通过援助解决的。但蔓延受援国的贫困与非受援国经济的起飞促使援助机构反思原有的援助的方式和路径。非经济因素被纳入了考虑的范围。人们开始认为,有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在援助下取得成功(如日、韩、台湾等)而众多的其他受援国不能,是与该国家特定的制度、政策、社会、文化因素有关。因此,援助国有足够的理由要求受援国进行一系列经济结构改革,以开放的市场和较少的政府干预为主要评价指标。但在一系列“结构调整”的援助项目失败之后,人们意识到,在很多情况下,援助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贡献,为了提高援助的效果,援助国与受援国应共同努力,包括给予受援国更多的自主权,加强受援国的制度建设,利用其本身的资源,减少由援助引起的制度和行政成本等。
当然,也有更为激进的人类学家从根本上反对发展话语统治下的对外援助。国际发展援助被认为是一种“新殖民主义”,是掠夺和侵占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资本和市场的新型手段。由于国际发展援助首先服务于援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因此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并不完全是温情脉脉的友好关系,而是存在利益与矛盾冲突的。对于国际发展援助的有效与否,也是这两类学者争论的焦点。
总体来看,对援助国而言,国际发展援助是实现政治、经济和外交目的的工具;对援助机构而言,是其赖以生存的根基;对受援国而言,是外来的可以利用的资金、技术、制度和理念。就此,笔者认为:
首先,国际发展援助效果的研究必须置身于宏观环境。这一环境包括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等,也包括当时学术界的主流思想(例如主张减少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际发展援助所侧重的目标、工具和理念,进而影响到援助的效果。
其次,我们不能用简单的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对外援助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然后断言对外援助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否起到了推动。因为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对外援助,都是多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累积的结果。多学科视角应当成为国际发展援助效果研究的科学态度和方向。
第三,不同国家,同一个国家在不同阶段由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差异,援助国的目标、理念和工具的不同,因此,援助效果也会大相径庭,研究数据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因此不可避免,我们对于国际发展援助的有效性也不必一概而论。
第四,对外援助是一个多目标的行为,因此,援助国与受援国的目标并非总是一致。一个未能实现受援国经济发展和减贫的对外援助活动,却可能已经达成了援助国的某些政治目标。援助的效果往往是援助国与受援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彼此博弈的结果。
第五,谁来评估援助的效果?因为评估机构的利益所属也影响着对援助有效性的判定。机构的评估框架、方法和效果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援助的评估结果。国际发展援助机构、不同层次的受援国官员或民众以及独立专家对同一个国际发展援助项目的效果评估在很多时候也会存在差异。对于不同援助利益群体或者社会行动者的研究应该成为今后援助效果研究的内容之一。
第六,对外援助的影响效果研究需要注意评估的时期分割。因为援助的影响有短期和长期之分。可以发现,某些对外援助项目的效果在短期内十分显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负面作用慢慢显现。也可能情况正好相反,一些投资于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援助的效果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体现。长、短期效果结合的评估有利于全面有效地认识援助效果。
第七,对外援助的影响效果也有微观与宏观之分。从微观来看,对外援助项目可能取得的效果是明显的,但整体上大部分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或社会进步并无改善又是不争的事实。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经济发展或社会进步会受多重因素影响。单个项目的成功并不能对经济或社会起到宏观上的影响作用。
第八,国际发展援助不是独立存在,因此考察国际发展援助的效果,还需考虑其与受援国自身的发展政策、措施如何互动。
最后,人类学对于发展话语与权力的追溯和批判令人耳目一新,然而,无论是援助国还是受援国,它们能否真正抵御国际发展援助的诱惑?人们是否可以天真地认为,国际发展援助这一庞大的系统产业能够被一笔勾销?必须承认的是,众多发展中国家无法拒绝国际发展援助提供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国与受援国利益已然彼此钳制与互锁。在此,讨论提高援助的有效性就具有了其特殊的意义。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如何使援助与接受援助的方案在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不同发展阶段实现相互匹配,使援助国与受援国能够真正互惠互利、取得援助共赢。
[1] 李小云等.国际发展援助概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
[2] OECD.(2003).Glossary of statistical ter ms,http:∥stats.oecd.org/glossary/detail.asp?I D=6043,latest access:2010-5-27
[3] 丁韶彬.国际道义视角下的发展援助.外交评论.2009,(4):72-82
[4] Doucouliagos H.,Paldam M.Aid effectiveness on accumulation.A metastudy.Kyklos2006,59:227-254
[5] 邹加怡.从“补缺”到“杠杆”——关于发展援助理论的评介与探讨.世界经济,1993(6):19-23
[6] Griffin K,Enos J.Foreign Assistance:Objectives and Consequences.Econom icDevelopm 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70,(18):313-327
[7] Weisskopf T E.The I mpact of Foreign Capital Inflow on Domestic Savings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 ics,1972,(2):25-38.
[8] Boone P.Politic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Foreign Aid.European Econom ic Review,1996,40:289-329.
[9] DoucouliagosD,Paldam M.The Aid EffectivenessLiterature:the Sad Results of 40 Years of Research.Journal of Econom ic Surveys,2009,23(3):433-461
[10] Minoiu C,Reddy G S.DevelopmentAid and Economic Growth:A Positive Long-Run Relation.I M F W orking Paper,09/118,2009
[11] ClemensM A,Radelet S,Bhavnani R.Counting ChickensWhen They Hatch:The Short-Ter m Effect of Aid on Growth.W ashington: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 ent,CGD Working Paper,44,2004
[12] Burnside C,DollarD.Aid,Policies,and Growth.Am erican Econom ic Review,2000,90(4):847-68
[13] World Bank.Assessing A id,W hatW orks,W hat Doesn’t and W h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14] Collier P,DollarD.Aid Alloc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European Econom ic Review,2002(46):1475-1500
[15] Bourguignon F,SundbergM.IS FOREIGN A I D HELPI NG?Aid Effectiveness—Opening the Black Box.American Econom ic Review,2007,97(2):316-320
[16] Lensink R,White H.Aid Allocation,Poverty Reduction and the Assessing Aid Repor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 ent,2000,12:399-412
[17] Hansen H,Tarp F.Aid EffectivenessDisputed.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 ent,2000,12(3):375-98
[18] EasterlyW,Levine R,Roodman D.Aid,Policies,and Growth:Comment.Am erican Econom ic Review,2004,94 (3):774-80
[19] Loots E.Aid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the Debate,the Challenges and theWay Forward.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 ics,2006,74(3):363-381
[20] Devarajan S,BajkumarA S,Swaroop V.WhatDoes Aid to Africa Finance?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World Bank,January,1999
[21] Moss T,Petterssonm G,van deWalle N.An Aid-Institutions Paradox:A Review Essay on Aid Dependency and State Building in Sub-Saharan Africa.W orking Paper74,Center for GlobalDevelopment,Washington,DC,2006
[22] Roodman D.Aid Project Proliferation and Absorptive Capacity.Center forGlobalDevelopment,W orking Paper,75, January,2006
[23] Bräutigam D,Knack S.Foreign Aid,Institutions,and Governance in Sub-Saharan Africa.Econom ic Developm ent and Cultural Change,2004,52(2):255-85
[24] Remmer KL.DoesForeignAid Promote the Expansion of Government?Am 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4, 48(1):77-92.
[25] ClemensM,Radelet S.TheMillennium Challenge Account:HowMuch is tooMuch,How Long isLong Enough? W ashington: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 ent,Working Paper,23,2003
[26] Collier P,HoefflerA.Aid,Policy and Growth in PostConflict Societies.European Econom ic Review,2004(48), 1125-1145
[27] McGillivrayM.WhatDeterminesAfricanAid Receip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Development,2005,17(8),1003 -1018
[28] Acemoglu,Daron,Johnson S,James A.Robinson,and Yunyong Thaicharoen.Institutional Causes,Macroeconomic Symptoms:Volatility,Crises and Growth.Journal of M onetary Econom ics,2003(50),49-123
[29] Acemoglu,et al.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Aghion P.Handbook of Econom ic Grow th,North Holland.http:∥elsa.berkeley.edu/~chad/handbook9sj.pdf,latest access:2010-02-23
[30] 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31] 林燕.20世纪90年代德国发展援助政策的特点.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1):28-30
[32] 邹加怡,莫小龙.从世界银行政策变化看全球化的矛盾和发展援助的职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1),36-41
[33] Schraeder P,Hook S,TaylorB.Clarifying the Foreign Aid Puzzle:A Comparison ofAmerican,Japanese,French and Swedish Aid Flows.W orld Politics,1998:294-320
[34] Alestina A,DollarD.Who Gives Foreign Aid toWhom andWhy?Journal of Econom ic Grow th,2000,5:33-63
[35] Headey D D.Geopolitics and the Effectof ForeignAid on Economic Growth:1970—2001.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 ent,2007,20(2):161-180.
[36] BobbaM,PowellA.Aid and Growth:PoliticsMatters.W orking PaperNo.601,2007,Washington: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Bank
[37] Wangwe SM.Aid Reform in Africa–the Conceptual Framework.Econom ic and Social Research Foundation, Dares Salaam,June,2002
[38] Baliamoune-LutzM,Mavrotas G.Aid Effectiveness:Looking at the Aid-Social Capital-Growth Nexus,Review of Developm ent Econom ics,2009,13(3):510-525
[39] 叶敬忠,王伊欢,李春艳.行动者为导向的发展社会学研究方法.贵州社会科学,2009,238(10):72-79.
[40] Wang Yihuan.How DiscontinuitiesBecome Continuities:the Dynamics of Participatory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PhD thesis.Wageningen University,2003
[41] 周宝根.援助促进受援国发展吗?——国外发展援助有效性的学理纷争.国际经济合作,2009(5):40-43
[42] Sachs J.The End of Poverty.How W e Can M ake it Happen in OurLifetim e.Penguin:London,2005
[43] Anon.Aid to Africa.The Econom ist,2005(2):24-26
[44] BirdsallN,Rodrik D,Subramanlan A.How to Help Poor Countries.Foreign Affairs,2005,84(4):136-152
[45] ChauvetL.Can Foreign Aid Dampen External Political Shocks?Paper Presented at the UNU-W ider Jubilee Conference,2005,June,Helsinki
[46] Cassen R,et al.(1986,1994)Does A id W 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7] Escobar A.Encountering Developm ent:the M aking and the Unm aking of the Third W orl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48] EasterlyW.The Ghostof the Financing Gap:Testing the GrowthModelUsed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 ics,1999,60(2),423-438
[49] 伊斯特利.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崔新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50] 孙同全.国际发展援助中“援助依赖”的成因.国际经济合作,2008,(6):55-58
[51] Mosley P.Aid Effectiveness:theMicro-Macro Paradox.Institute of Developm ent StudiesBulletin,1986,17:214-225
[52] OECD.(2008).The Paris Declaration and Accra Agenda for Action,http:∥www.oecd.org/document/18/0, 2340,en_2649_3236398_35401554_1_1_1_1,00.html,latest access:2010-02-01
[53] BirdsallN.Seven Deadly Sins:Reflections on Donor Failings.Center forGlobalDevelopm ent,W orking Paper,50, December,2004
[54] Stokke O.(ed.)A id and Political Conditionality.London:Frank Cass,1995
[55] EasterlyW,Ritzen J,WoolcockM.Social Cohesion,Institutions,and Growth.DR IWorking Paper 17,November,2005
[56] Asiedu E,Nandwa B.On the I mpact of Foreign Aid in Education and Growth:How Relevant is the Heterogeneity ofAid Flows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Aid Recipients?Review of W orld Econom ics,2007,143(4):631-49
[57] MolenaersN,NijsL.From the Theory of Aid Effectiveness to the Practice: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Governance Incentive Tranche,Developm ent Policy Review,2009,27(5):561-580
[58] 叶敬忠.发展干预中的权力滴流误区与农民组织.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30(2):50-55
[59] Ferguson J.The Anti-PoliticsM achine:“Developm ent”,Depolitic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University ofMinnesota Press,1990
Abstract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id has been questioned since its advent as amain approach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mpoverished countries.The focusof discussion has always been the aid effectiveness,accompanied by conflicting conclusions from different or even the same research perspectives.These conclus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lassifications:those arguing for its effectiveness,those against it,and those for conditional aid effectiveness.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aid effectiveness literature in three aspects:research approaches,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introduced a deconstructionis m view on aid effectiveness in anthropology,and briefly discussed the status quo and possible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aid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id;Aid effectiveness;Perspective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责任编辑:连丽霞)
L iterature Review on A id Effectiveness
Wang Chunyu Wang Yihuan
2010-04-06
汪淳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讲师;
王伊欢,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邮编:100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