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有灵,激活思想①
2010-12-20蒂姆英戈尔德
蒂姆·英戈尔德
重思有灵,激活思想①
蒂姆·英戈尔德
文章试图重新思考民族志中有关泛灵论的材料,目的是要理解生命的意义。西方传统理论和受其影响的现代科学理论被确证存在着转换的逻辑:这些理论倾向于认为个体生命是从世界中抽离出来的,是一个有边界的实体。作者试图从“生生不息”“生命存在的关系构造”以及“运动的首要地位”等方面重新思考生命世界的意义,并指涉现代科学的研究。通过区分“对世界感到惊奇”与“对世界感到震撼”来反思现代科学的不足之处,并提出理解世界的新视角——栖居。
泛灵论;生命;网络;生生不息;运动;震撼与惊奇
一、发现生命
对于即将发现火星生命这一愿景,西方媒体不时制造出一波又一波令人兴奋的气氛。这一预期如此的强有力,以至于满世界的领导者们都把自己的名誉赌在完成这项工程的承诺上——这样的理智真值得怀疑。那些“老谋深算”的天文学家,由于长期困扰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支撑他们昂贵的科学实验,因而很清楚维持这种“兴奋”的重要性。他们知道,只要政治家们把它看作是一个确保自己历史地位的机会,科研经费就会滚滚而来。不过对其余的人来说,认为另一个行星上也存在生命的想法一直是有吸引力的,我这样说可能有点天真,但并没什么嘲讽之意。我本人同样痴迷于这种想法,但是我却不清楚科学家们到底希望在那个星球上发现什么。生命是火星地表上存留的某种东西吗?如果是,当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应该怎样去识别它?答案可能是:我们用与识别地球生命完全一样的办法来识别火星生命。但是我依然不确定我们应该如何做。我能确定的是,根据我们从民族志中了解到的,人们对“什么是活的”和“什么不是活的”的区分通常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可能即使他们有相同的看法也出自完全不同的原因;我还可以确定的是,不是人人都会对“物”进行“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分类。这是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生命根本就不是物的特有属性;换句话说,生命并不是来自一个已经存在的、由这样的“物”组成的世界,而是内在于世界持续的生成(或形成)这一过程中。
对生命持有这种理解的人们 (很多已经被人类学家研究过,居住在亚马逊河、东南亚以及北极圈等多个不同地区)通常被研究文献称为泛灵论②泛灵论,也称万物有灵论。——译者注。者。按照既有的传统,泛灵论是一套信仰体系,它认为生命或者灵魂是被赋予到无生命之物上的。但是这个传统在两个方面有误导性:第一,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把世界作为对象来讨论一种信仰方式,而是要讨论存在于世界之中的这种状态。这也可以被描述为对世界敏感的状态,其特征是在感知和行动上,对总是一刻不停地变化着的环境保持高度的敏感和反应能力。那么,“有灵”(animacy)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投射在他们所感知到的存在物上的某种属性;恰恰相反——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二点——“有灵”是整个关系场域能转化新生的动力潜能,在这个关系场域中,所有的存在 (不论类人的还是拟物的)不断地、相互地把彼此带入存在状态。总之,生命世界的“有灵”不是把灵魂注入实物的结果,也不是某种中介进入物质体的结果,而是本体论上它先于这种 (灵魂与物质的)区别而存在。
肯定不是我第一个持有这样的观点:按照泛灵论者这个术语的传统定义,那些梦想着在火星上发现生命的人就属于真正的泛灵论者。他们笃信,存在着一条可能是物体内部固有的赋灵原理(animating principle),它使得这些物体能够成长和繁殖。19世纪的民族学家认为他们所了解的野蛮人所拥有的就是这种信仰,并且认为那些野蛮人对这种信仰用得太泛滥,不管物体事实上是不是“活的”,他们都认为是被赋了灵的。所以,把 21世纪早期的天文学家和他们的民族志前辈相提并论,对此不应该感到惊奇,因为前者希望发现生命潜伏在其他行星上,而后者打算发现万物有灵信仰潜藏在异文化的思维中,其实这两者是共通的。心理学家已经指出,这样的信仰建立在一种潜意识倾向的基础之上,这种倾向甚至是受过教育的成人也会有——大概和幼儿、原始人一样——习惯于把无生命的物体当作有生命的[1]。既然有这样的观点,那么如果你不知道一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活的”的时候,那么你最好认为它是,并预料到这种认定会带来的后果。如果弄错,那么所付出的代价要比弄对所带来的好处大得多[2]41。于是,我们都变成了不自觉的泛灵论者。凭直觉持非泛灵论观点的人已经被淘汰了,因为他们原先预计没有生命力的东西,结果却被证明是有生命力的。
二、生生不息
言归正传,一般的看法都遵循着同样的逻辑,我称之为“反转逻辑”(the logic of inversion),它深深地植根于经典的西方思想里[3]218-219。通过反转,涉入世界的东西 (物或人),其场域被转化成为一种内部架构,物或人的外观和行为仅仅是这一内部架构的外在表达。于是,沿着生命线成长而步入生命之网的有机体被重新编排成一种内部设计的外在表达。按照惯例这种设计被认为是基因型 (genotype)的,它可以保证显型 (phenotype)得以明显表现。同样地,人也是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行动和感知,于是被认为是按照头脑中的文化模式或者认知图示来采取行动。生命原本对世界开放,通过反转而逼近自身,被外边界或外壳封闭起来,避免其内部构造与周围环境发生交互作用。我的目的是反转这个“反转逻辑”。生命已经被从外到内 (outside in)地反转过了,我现在想把它从内到外地再反转过来,为的是恢复原本对世界的开放性,那些被我们 (也就是受西方训练的民族学家)称作泛灵论者的人们通过这种开放性发现了生命的意义。
加拿大北部威明基的一位克里族猎人向民族志学者科林·斯科特 (Colin Scott)这样讲述,他说:“生命就是连续出生 (continuous birth)。”[4]195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句话一语中的。具体而言:在“灵”的本体论中,生命 (life)不是生命存在 (being)的发射物 (emanation),而是生命存在的生产 (generation),总之这种生产不是预先注定的,而是初始的 (incipient),永远处于已然状态的边缘[5]113。人的繁衍连续不断,就是那种永远处于边缘时刻的证明,像波浪起伏一样,在那个时刻世界显露了它的本来面目。哲学家梅洛-庞蒂 (Maurice Merleau-Ponty)在他的文章《眼与心》中揭示出画家也具有同样的敏感性——对形成中的世界有着同样的开放性。梅洛-庞蒂写到:“画家之于世界,不是简单的物理-视觉的 (physical-op tical)关系。”也就是说,画家并不是要凝视一个有限的、完整的世界并把它表现出来。毋宁说,画家之于世界的关系是“连续的出生”(continued birth)的关系——梅洛-庞蒂也用了“连续的出生”这样的话——就好像每次画家睁开眼睛看世界都是第一次看。画家的眼睛看的根本不是世界中的事物本身,而是看物变成物、世界变成世界的过程[6]167-168,181。画家保罗·克利 (Paul Klee)在他 1920年的作品《创意 (Creative Credo)》中也有几乎完全一样的表达。他的著名论断是:“艺术并不是复制视觉的结果,而是制造视觉的效果。”[7]76
三、生命存在的关系构造
对于认为世界有灵的看法,我想强调两点:第一点涉及生命存在的关系构造,第二点涉及运动的首要地位。我将会依次讨论。先谈第一点,我需要回到“反转逻辑”,让我们设想一个有机体或者一个人,我可能会像这样来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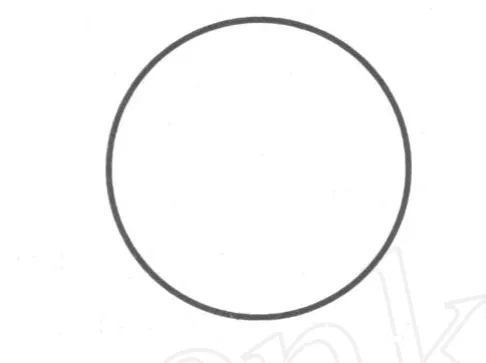
但是在这个显然很随意的描述中,我已经实现了一种“反转”。我把这个有机体折回它自身,由此它被一条圆形边界线围起来,与周围的世界分裂开来了,如果依照其本性,这个世界应该是它注定会与之发生交互作用的环境。这个有机体在“圈内”,环境在“圈外”。但是如果不画一个圈,我也可以画一条线来代替。那么我们重新画,是下面这样的一个有机体:

这样画没有内外之分,也没有被分界线分成的两个确定的范围,反而有一条运动或成长的轨迹。每一条这样的轨迹都描绘了一种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在一个物体与另一个物体之间,即不是“圈内”(物体)和“圈外”(环境)之间;这种关系是生命要活下去必须遵循的轨迹:就像织网中的一股绳,生命的轨迹把它编织到生命世界的纹理中。这个纹理就是我在谈及有机体在关系域中被构造时想表达的意思,这个域不是由连通的点所组成,而是由互相编织的线所组成;不是虚拟网络 (network),而是实在的网络组织 (meshwork)。
然而这种单线条的描述很显然是一种简化,因为有机体生命一般不是沿着单一轨迹,而是沿着多样的轨迹,从源头不断发展出来。那么我们应该这样来想象有机体:它不是一个像球一样可以自己滚来滚去的独立物体,而是由生长线构成不断分叉的网。哲学家德勒兹 (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 (Félix Guattari)[8]很恰当地把该网络比喻为植物的根茎,尽管我觉得更像真菌的菌丝[9]302-306。不管我们选择哪种比喻,有机体现在看起来像是下面的这个样子:

毫无疑问这种描述也适用于同样作为有机体的人类,他们也是沿着多样的路径发展,融入世界。
但是现在,又该如何看待环境呢?它肯定不是字面意义上包围着有机体或人的东西,因为除非在外面划一条线,否则你就无法包围一个网络。而那样就立刻会导致“反转”,把那些关系 (有机体—人遵循这些关系在世界上过活)转化为生命的内在属性 (生命只是内在属性的外在表达)。然而我们可以想象,那些从多种源头衍生出来的成长线错综复杂地缠绕在一起,就好像热带雨林中的一块地上长满了藤类和匍匐类植物,或者就好像你每次用铁锹挖起花园中的一块泥土时所看见的盘结的植物根须。那么我们平时习惯称为“环境”的东西也许更应该被视为一种纠缠物的领域,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断地这里打结那里松开的交错轨迹的纷乱状态里,生命沿着他们的关系线在成
长[9]305-306。
这种纷乱状态就是世界的纹理。在“灵”的本体论中,生命存在不是简单地占据 (occupy)世界,而是栖居 (inhabit)在世界中,这样一来——把自己的路径像穿线一样穿在在网络中——它们促成了网络不断演进的编织。因此我们一定不能再继续把世界看作是毫无生气的地方 (在那儿生物驱使他们自己有点像棋盘上的棋子或者舞台上的演员,在那里人工制品和场景分别取代了自然物和自然风光)。出于同样的原因,栖居在世界中的生命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确实是土著)就不是在世界的表面进行机械位移的物体。其实这个栖居的世界根本就没有表面。无论什么表面 (不管是陆地、水域、植被还是建筑),它们都在世界之中,而不是世界的表面[5]241。被编织进纹理中的是生长线和栖居者的运动。总之,每一条这样的线都穿梭于网络之中而不是从表面掠过。而生命正是作为运动的线条 (而非自我驱动的活动实体)展现在世界之中。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二个观点:关于运动的首要地位。
四、运动的首要地位
有灵的世界处在不断的变迁中,因为其中的每种生命都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这些生命不是存续在固定的地点,而是沿着不同的路径出现。例如作家鲁迪·维柏洱 (Rudy Weibe)介绍的住在加拿大北极圈的因纽特人[10]15:一个人只要一搬家他就立刻变成了一条“线”,留在身后的轨迹是认识和辨认他的依据。同样的,辨识动物也是靠它们的特有活动模式以及运动特征来区分,而且要感知到动物的存在就要亲眼看到它在活动或者亲耳听到它活动的声音。现在,从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 Nelson)对阿拉斯加的科尤康族人的精彩记叙 (《对乌鸦的祈祷》)中选取两个例子,如你所知,“像火光瞬间穿过灌木丛一样飞奔的”不是“狐狸”,“栖息在云杉树低低的枝杈上的”不是“猫头鹰”[11]108,158。这些动物的名字不是名词,而是动词。
这和太阳、月亮等天体没什么不同。我们可以想象太阳是一个巨大的圆盘,我们看到它每天自东向西掠过广袤的天顶。可以这样来描述:

但是在北美平原原住民象形文字的碑文中,它是像这样被描述的:

或是这样:

在每条线末端的短线表示日出或者日落[12]959。在这些描述中,太阳不是被理解成一个掠过天空的物体,而是被视作穿越天空的运动路径,每天由东向西运行。我们将要如何想象天空,尤其是想象天空和陆地的关系,这是我下面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运动。但是不是所有的运动都预示着生命。生命的运动特指形成的过程而不是存在的状态,是沿着某一路径的更新而不是空间的位移。每种生物在其成长并留下轨迹的时候都以独特的方式运动。太阳是活的,因为它在天空中运行的方式;树木是活的,因为它们的枝叶在风中摇摆并且哗哗作响。尽管西方科学家可能怀疑太阳是活的,但是一定会赞成树木是活的。不过理由是完全不同的:他可能会说“树木是活的,不是因为它的运动,而是因为它是由细胞构成的有机体,它的成长由光合作用提供能量并受到细胞核内 DNA的控制。至于那些运动,只不过是风的作用而已。”但是风的作用来自哪里?于是科学家们又解释说:“风由大气气压的水平和垂直差异产生,它也只是一种效果。”然而在大多数有灵的宇宙论中,风被认为是有生命的并且拥有主动的力量;很多时候风如同太阳、月亮和星星一样,被当作是“重要人物”,形塑和引导着人们栖居的世界。
一旦我们认识到在有灵宇宙中运动居于首要地位,那么这座“万神殿”里的生命存在——被现代科学分类称为气象现象 (不仅有风,还有雷电)——就变得容易理解了。我们不需要相信风是会吹的生命存在或雷电是会轰鸣的生命存在,毋宁说风在吹、雷电在轰鸣,就好像有机体和人类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生存一样。但是我想应该再多说一点这些与天气有关的生命特征,这些特征非常突出,这就引出了我下面要说的天空与大地的关系。
五、天空、大地与天气
我在前面已提到,我们倾向于假定死气沉沉的世界是被生命占据的表面。我们说,生命存活在地上,固着在坚实的土地中,而天气在头顶上环绕。在地表之下的是地球,地表之上大气。地球作为固体物质,为生命活动提供支持,为生存提供物质资料;空气作为气态介质,支持变动和感官知觉,当然也使陆地上的动物得以呼吸[13]16-22。然而,在很多理论家的表述中,地面不只是介质和实体的交界面,更根本的是中介性 (agency)和物质性 (materiality)领域的分界。这会产生一个非常奇怪的推论:会出现一个非物质的介质,有机体和人通过它进行活动。那么,又该怎样看待风和雨、光和云、雾和雪、雷和电呢?
物质守恒和地球固态的观点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生命存活在世界的外表面 (世界已经凝结成最终形态),而不是存活在世界的永恒变动之中。在心灵与自然、人与物、中介性与物质性之间,并没有一个概念空间来表达那些非常真实的现象和介质 (一般被称作天气)的转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没有涉及天气。这是反转逻辑的结果:一种占据先于栖居 (occupation before habitation),位移先于穿越 (movement across beforemovement through),表面先于介质 (surface before medium)的逻辑。就这种逻辑而言,天气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相比之下,在有灵的本体论中,不可想象的却是这样一种观念——世界是个了无生气的表面,生命在此衰竭。根据这种本体论,因为生物有机体要在一个不断生成的世界中穿越 (through)而非掠过 (across)事先形成的表面,所以生物有机体要穿越的介质的属性就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栖居的世界首先是由天气的气流,而非固定的陆地景观构成的。天气是动态的,总是不断变化,它的状态、气流、光影、色彩、干湿、冷热等等也会不断改变。在这个世界上,地球远非支撑存在物的实体基础,而更像一个由陆上生命编制而成的、易碎的、朝生暮死的木筏悬浮在空中。天空就是所有高级活动发生的地方,在那里有太阳发光、刮风,下雪,起大风暴。人类中的超群者不满足于将自己的意志停留在地面上,而是追求在天空中与鸟为伴,御风而行,共星长谈。比较而言,我们可以说,他们的雄心是朝向天空的,而非面向大地。
回到刚才提出的问题——天空的意义及它与大地的关系。参考《钱伯斯英语字典》的定义:天空“看起来是我们头顶的华盖”。这个定义揭示了两点:第一,天空被想象成一个表面 (surface),就像大地的表面 (当然只不过一个是头顶的遮蔽物,一个则是脚下的平台);第二,又不像大地的表面,天空的表面并非真实的,只不过看起来是 (apparent),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如果这样想的话,天空就是幻象 (在那儿有天使在走动)。那么按照熟悉的思路,地表就变成了实体和想象之间的交界面。位于下面的 (大地)属于实体世界,隆起的 (天空)升华成思想。人类脚在地上而头在空中,似乎天生就被分裂为物质和精神的二元。然而,在有灵的宇宙中,天空并不是一个真实或虚构的表面,而是一种媒介 (medium)。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这个媒介里栖居着各种生命存在,包括太阳、月亮、风、雷和鸟等等。这些生命存在把自己的行迹留在天空中,就像大地上的生命在地上留下了足迹。太阳轨迹的例子已提过了。同样,风通常也被认为是从它“居住”的地方跑出来的,并在空中留下轨迹[12]943。大地和天空也不是互相排斥的栖居领域,鸟儿会飞上天空,也会停在地上;而人类中的超群者,如萨满,也是如此。根据安妮·费纳普-瑞奥丹 (Anne Fienup-Riordan)[14]80的描述,爱斯基摩人承认有一类离奇的人,他们健步如飞,就像真的飞起来,以致身后留下风吹落雪的轨迹。
六、震撼与惊奇
总之,与真实有形和虚幻无形之间存在决绝的分割不同,大地与天空存在于同一个不可分的场域中,难解难分,沿着栖居者错综纠缠的生命线整合在一起。画家懂得这一点,他们知道要画习惯上所说的“风景 (landscape)”,就要既画地又画天,而且要把地和天融合在对世界“生生不息 (continuous birth)”的感知中。他们也知道,这种对天地的感知——不像对风景画中的物体的感知——首先是一种关于光的体验。在绘画的过程中,他们旨在重新获得那种看的体验所带来的全然的震撼(astonishment),在能看到东西这种平常状态的背后,是一种有能力去看的体验。这就是被梅洛-庞蒂[6]166称为视觉的魔法或癫狂 (magic or delirium of vision)的东西。我认为,“震撼”是对世界保持开放性的另一种方法(我在前面提到对世界的开放性是有灵存在的基础)。这种奇迹感来自于对世界生生不息的体验。然而与开放性相伴的是脆弱性,对不熟悉这种有灵的存在方式的外来者来说,震撼经常被看作是怯懦和虚弱,是一般认为的原始信仰和实践不够严格的证明。据说,要想通晓世界,与其让自己接受世界,不如用一套概念和分类体系把握住 (grasp)它。震撼已被驱除出概念驱动和理性审查的框架之外,它是科学的敌人。
因为科学家们谋求封闭 (的确定性)而非开放 (的任意性),所以他们经常会为他们的发现感到惊奇 (surprised),但从没有感到过震撼 (astonished)。当科学家们的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他们会感到惊奇。他们妄想世界是可以被精确计算的,他们据此进行预测。但是当然,世界无论怎样都只是按着照自己的方式行进。建筑设计师斯坦利·布兰德 (Stanley Brand)所说的关于建筑构造的话同样适用于科学的构造:“所有的建筑都是预测;所有的预测都是错的。”[15]178依照波普尔主义(Popperian)关于猜想与反驳的步骤,科学将惊奇变成了试错渐进原则 (p rincip le of creative advance),从而把一部不断累计的预测失败史转化为科学进步史。然而,只有那些已忘记了怎样对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感到震撼的人才会有惊奇,他们对控制和可预测已经变得如此习惯,以至于他们需要依靠意外情况的发生来使自己确信某些事件正在发生,历史正在被创造。相比之下,那些真正对世界开放的人是永远感到震撼却从不感到惊奇的。如果这种非惊奇的震撼态度留给人们的是脆弱,那么它也是带来力量、韧性和智慧的源泉。因为这种态度不是等着意外情况的发生,不是到结果来临时才发觉有错误,所以人们每时每刻会都带着谨慎、判断和敏感对世界的变迁做出回应。
泛灵论和科学因此不可调和么?泛灵论对世界的开放态度是科学的敌人么?当然不!我并不希望我的话被理解成对整个科学事业的攻击。但科学就现状来看却建立在一块荒诞的基石之上,因为为了把世界变成科学研究的对象,它不得不将自身放置于它宣称要理解的世界之上 (或之外)。使科学家获得知识的条件——至少按照官方的要求——是让科学家不可能处于他们从中探寻知识的世界中。然而一切科学都取决于观察,而一切观察又都取决于参与——换言之,取决于感知与行动的紧密联系,取决于观察者与所关注的世界各方面之间的密切关系。如果科学想变成一种连贯的知识实践,那么它必须在开放而非封闭 (openness rather than closure)、结合而非分离 (engagement rather than detachment)的基础上进行重建。这意味着要寻回已经在当代科学工作中明显缺失了的震撼感。认知 (knowing)与存在 (being),认识论与本体论,思想 (thought)与生活必须重新结合。通过对土著的泛灵论的这些重新思考,我们提议——我们要激活我们自己的、所谓西方的思想传统。
[1] Brown L B,Thouless R H.Animistic Thought in Civilized Adults.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1965(107):33-42
[2] Guthrie S.Faces in the Clouds:A New Theory of Relig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3] Ingold T.The A rt of Translation in a ContinuousWorld∥Palsson G.Beyond Boundaries:Understanding,Translation and Anthropological Discourse.Oxford:Berg,1993:210-230
[4] Scott C.Knowledge Construction among Cree Hunters:Metaphors and Literal Understanding.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s Américanistes,1989(75):193-208
[5] Ingold T.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Essays on Livelihood,Dwelling and Skill.London:Routledge,2000
[6] Merleau-Ponty M.Eye and M ind∥Edie JM.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and Other Essays on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the Philosophy of Art,History and Politics.Evanston,I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4:159-190
[7] Klee P.Notebooks,Volume 1:The Thinking Eye.London:Lund Humphries,1961
[8] Deleuze G,Guattari F.On the Line.Johnston J,trans.New York:Semiotext(e),1983
[9] Ingold T.Two Reflectionson Ecological Knowledge∥Sanga G,Ortalli G.Nature know ledge:Ethnoscience,Cognition,Identity.New York:Berghahn,2003:301-311
[10] Wiebe R.Playing Dead:A Contemplation Concerning the Arctic.Edmonton,Canada:NeWest,1989
[11] Nelson R K.M ake Prayers to the Raven:A Koyukon View of the Northern Forest.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12] Farnell B M.Ethno-Graphics and the Moving Body.M an(N.S.),1994(29):929-974
[13] Gibson J J.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Boston:Houghton M ifflin,1979
[14] Fienup-Riordan A.Boundaries and Passages:Rule and Ritual in Yup’ik Eskimo Oral Tradition.Norman,OK: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4
[15] Brand S.How Buildings Learn:What Happens to Them After They’re Built.Harmondsworth:Penguin,1994
Rethink ing the An imate,Re-an imating Thought
Tim Ingold
Thispaper tries to rethink thematerial about the animism in the ethnography,in order to interpret themeanings of life.It’s convinced that there exists logic of diversion in thewestern traditional theory and the affected modern theory:they tend to consider that life is apart from theworld and it’s an objectwithin a boundary.The author rethinks themeaningsof the lifeworld from different aspects such as“the continuous birth”,“the relational constitution of being”and“the primacy of movement”,and refers to themodern scientific study.By distinguishing the differencesbetween“the surprise to the world”which impulses the science and“the astonishment to theworld”which help s to understand the lifeworld,he rethinks the shortage of modern science and puts forward the inhabitation perspective to interpret theworld.
Animism;Life;Meshwork;Continuous birth;Movement;Astonishment and surp rise
2010-03-19
蒂姆·英戈尔德 (Tim Ingold),英国阿伯丁大学 (Aberdeen University)社会人类学系教授,1948年生于英国,1970年获得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学士学位,1976年获得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他曾任曼彻斯特大学格拉克曼讲座教授,著名人类学学刊《人类》(M an)的主编,早年的著作包括《人类学内的关键论争》(Key Debates in Anthropology)等,近年出版的《环境的感知》(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是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① 本文是作者于 2009年 5月在北京大学讲座的发言稿,摘要为译者所加。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王浩、本科生孙超初译,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谢元媛重新修订。
(责任编辑:常 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