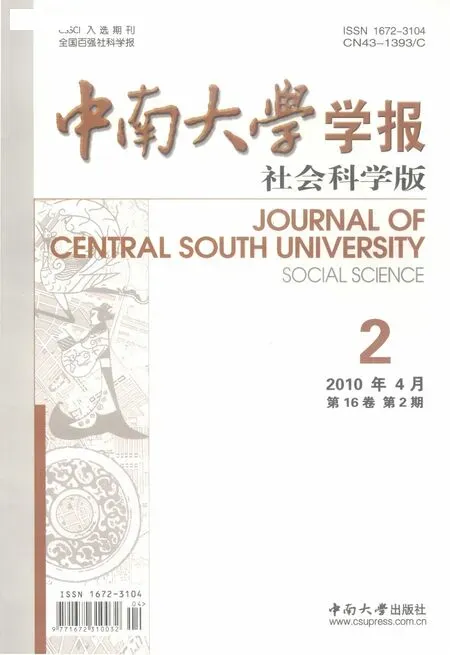“强奸转通奸”司法解释的困境与出路
2010-02-09陈罗兰
陈罗兰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200042)
一、由“庄志伟案”看有关“强奸转通奸”司法解释的问题
案情介绍:庄志伟、庄仁伟、张勤峰三位犯罪嫌疑人使用暴力手段分别强行与被害人李芳(化名)发生性关系。事后,李芳与庄志伟成为男女朋友,并自愿与其多次发生性关系。检察机关依据案情发展的特殊性以及司法实践惯例,未对犯罪嫌疑人庄志伟强奸行为的事实提起公诉,而其他两名共犯则因涉嫌强奸罪被提起公诉。上海某区人民法院采纳控方的意见,处理了该案[1]。法律依据为:1984年4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的相关规定。
本案三被告庄志伟、庄仁伟、张勤峰,同样实施了强奸行为,但为何针对他们所实施行为的法律后果却有如此大的差异?事后的补救行为能否与原来的犯罪行为互相抵消?此类轮奸案对个人行为认定方面是否可以完全不考虑共同犯罪这样一个情节的影响?《解答》中关于“强奸转通奸,一般不宜以强奸罪论处”的规定是否合理?该规定能否同样适用强奸罪的五个加重情形?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刑法该如何处理对社会关系稳定性的保护与对破坏这种稳定性的犯罪行为的惩罚之间的平衡?以上这些疑问都是亟待解决的。笔者将从强奸转通奸的一般情况入手,在深入分析该司法解释是否合理的基础之上,提出解决困境之道。
“强奸转通奸,一般不宜以强奸罪论处”已为司法解释所明确规定,但并不能等同于该规定一定是合理的。相反,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在法理上既有欠缺且有违伦理,适用中也存在困境。
(一)法理上的欠缺
强奸罪中所说的“违背妇女意志”是指在为强奸行为的当时与妇女性自由的意志相违背,而不涉及事前或者事后是否违背妇女意志。“强奸转通奸”,由违背妇女意志转变为不违背妇女意志,但后通奸行为并未改变先强奸行为存在的事实。只要在为强奸行为的当时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即构成强奸罪,这是以我国现行犯罪构成理论为基础得出的结论[2]。换言之,犯罪既遂后的行为不能反过来冲击犯罪的基本构成,作为阻却犯罪的依据。否则就存在一个困境:即上述司法解释与犯罪构成的关系以及二者如何协调,理论界或者实务界尚且没有对此作出有力回应[3]。与此同时,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虽在事后稍有弥补,但不能完全恢复,因此,需要对此类造成社会危害的行为进行惩罚,以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当前,有学者认为该解释是存在法理依据的,即“被害人承诺”理论。被害人承诺是基于被害人的承诺放弃法律对于其个人法益的保护,从而排除损害被害人法益之行为的违法性。“只有在违反被害人意志为前提的犯罪中,被害人的承诺才可能阻却违法性”[4](199)。强奸罪是以违反被害人意志为前提的犯罪,因此,“先强奸后通奸,一般不宜以强奸罪论处”可以基于“被害人承诺”原理,以获得其正当性。但笔者认为,被害人承诺原理能否作为该解释的法理依据还值得商榷。
“强奸转通奸”案件中,通奸情况发生时,强奸行为已经结束,若将“通奸”看成是被害人以行为表示的“承诺”,则被害人承诺时强奸行为已经完成,其侵害法益的后果已经出现,而被害人承诺适用的条件是被害人的承诺至迟存在于结果发生时。因此,从时间上来看,该承诺本身不能成立[4](199−200)。被害人承诺理论,依通说主要适用于犯罪行为前和行为中,或者结果发生前的情形[5,6],同时,本文所讨论的“强奸转通奸”类型犯罪,其强奸行为已经既遂并且发生了危害结果,因此笔者认为,司法解释合理性的证成不能通过“被害人承诺理论”来解决。
还有学者认为,《解答》的规定是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是为了防止对被害人的二度伤害,恢复被破坏之社会关系,符合构建社会和谐的要求。但是通奸本身就不合乎伦理,是对当前普适的伦理规则的背离,又何以用来构建和谐社会,恢复社会关系?“通奸”是指有配偶的男女双方之间或者已有配偶的一方与他人之间,自愿发生两性关系的行为。[7]通奸不被道德、伦理所接受,也妨害了一方或者双方正常的婚姻家庭关系。[8]如果在强奸犯罪后继续保持通奸,则必然有一方的正常婚姻受到侵害,如此还能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效果吗?与此同时,这种违背了伦理却仍然“逍遥法外”的现象,必然会伤害民众朴素的法感情,影响刑法的威慑作用。强奸行为是违反《刑法》的,通奸行为是违反《婚姻法》的,而一个犯罪行为与一个违法行为的结合,导致的结果是一个合法行为,这很荒唐。同时,这也可能成为法律规制犯罪的漏洞,被犯罪分子利用作为脱罪的手段,反而更加不利于对被害人的保护,导致放纵犯罪。行为人可以利用既成事实,软硬皆施,讨好、拉拢被害人,从而逃避法律规制。而在现实生活中,又常常存在有些被害人或者因为有损名誉、或者被金钱利益诱惑等,而委身于犯罪人的现象。这样不仅达不到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良好初衷,反而使得有些犯罪人成功逃避法律的制裁。因此,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是于法治、社会无益的。
综上所述,《解答》存在众多不合理之处,与伦理规则严重背离。通奸行为本身就具有违法性、危害性,在一些地区甚至认为通奸构成犯罪,如日本刑法第183条设置的奸通罪,要件有两条:第一,须为有夫之妇,而且必须是在民法上合法成立的婚姻。但婚姻无效者不在此列;第二,须与夫以外的男性为奸淫[9]。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239条规定,“有配偶而与人通奸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亦同。”从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状况看来,“通奸”既然被认为是犯罪行为,证明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虽然我国不认为通奸构成犯罪,但被认为是严重违背社会伦理的行为,有伤风化、违背公序良俗、不为公众所接受。在“强奸转通奸”的案件中,无论是强奸行为还是通奸行为都是对伦理规则的违反。可是,当前的法律规定却恰恰与公众认同的伦理规则相冲突。《解答》认为不构成犯罪,但伦理却认为不能容忍。二者分裂时,社会行为将无所适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刑权力不断向伦理观念靠拢,道德的权威在民间;同时又在不断地利用其权力的主动性对伦理观念做出改造以符合权力的运作要求”,“作为伦理规则,则是相对自在的、稳定的,尽管它不具有刑权力的强制力,但是国家刑权力的运行同样应该具有道德的操守,遵循其基本规律。”[10]
笔者认为在“先强奸后通奸”案件中,应当让国家刑权力向伦理规则靠拢,以民众能够普遍接受作为定罪量刑的考量。鉴于此考虑,笔者认为《解答》中规定的“一般不宜以强奸罪论处”是与伦理规则相背,缺乏合理性,应当废止该司法解释的继续实施,否则将对法治造成损害。
(二)适用中的困境
《解答》中关于“强奸转通奸”的司法解释在适用的过程中,存在诸多困境。
首先是“多次自愿”难以界定。《解答》中规定“女方又多次自愿与该男子发生性行为的”,这里的“多次”一般是指3次以上,那么,如果行为人被抓获时只与被害人发生一次通奸行为应当如何处理?如果出现虽然没有发生通奸行为,但是已经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又当如何处理?可见,若将自愿发生性行为3次以上作为阻却强奸罪成立的唯一标准,虽然较为明确,但有形式化、绝对化、僵硬化之嫌。[3]
第二,是《解答》尚未规定适用范围。《解答》尚未明确规定哪些强奸类型可以适用该解释,哪些不能适用,导致在司法实务当中出现适用上的混乱。如若轮奸、强奸多人等的情况都可适用,必然出现许多理论上的龃龉之处。例如在轮奸案件中的适用,导致实施同样行为的加害人,却受到迥异的法律评价,如有人不构成强奸罪,有人却构成强奸罪的加重犯,面临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重罚。差距如此之大的判决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有违一般的公众认同。更为极端的是,如果轮奸案件的所有加害人都与被害人保持通奸关系,按照《解答》规定认为不构成犯罪,如此判决公众能否认同?法律的威慑何在?对犯罪的惩罚何在?同时,如若是两人轮奸一妇女,其中一人与该妇女保持通奸关系,根据《解答》此人不构成强奸罪,那么另外一人是单独成立轮奸,还是构成一般强奸呢?再如强奸妇女多人的情况,行为人同时与被强奸的所有妇女都保持通奸关系,是否同样适用《解答》之规定?若同样适用,认定其不构成强奸罪,如此判决的合理性必将受到质疑。
第三,强奸转自由恋爱及合法婚姻的情况也未涉及。该解释是在论及强奸与通奸之区别时,提出“强奸转通奸,一般不宜以强奸罪论处”的。也即该《解答》适用的是强奸之后,两人发生通奸行为的情况。通奸是指一方或者双方已经结婚的情况下,男女之间发生婚外性关系。那么,在男女都是未婚的情况下,发生的合意性行为应当如何认定,对男女发生合法婚姻的情况应当如何处理,《解答》没有涉及。同时,无论采取何种方法,也不能将合意性行为及合法婚姻中的性行为解释为“通奸”。
二、解决问题的两条出路
要解决上述问题,可有如下两个办法。
(一)出路之一:废止现有司法解释,引入刑事和解制度
废止了《解答》中关于“强奸转通奸”之规定后,强奸转为通奸、自由恋爱、合法婚姻的案件一律认定为强奸罪,完全不考虑被害妇女的意愿,不考虑已破坏社会关系的修复,不考虑事实上加害人已经得到了被害人的原谅,那么法律将显得过于严苛,缺乏人性化。因此,应当在该解释废止后,为此类案件的处理寻求一条出路。
在解决该司法解释的困境及出路的问题上,有学者提出可以引入“亲告罪”的制度。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意大利、韩国等都将强奸罪定为“亲告罪”。根据《日本刑法典》第180条规定:“前四条之罪,待告诉而论之”①。再如意大利刑法第609条-7规定,强奸等性犯罪经被告人告诉才予以处罚,但是提前告诉的期限为6个月,一经告诉便不能撤销;芬兰刑法典第17条规定,强奸罪、滥用性权利罪等的受害人基于自愿不要求提起指控,则公诉人可以免予提起指控,除非由于涉及重大的个人和共同利益而要求提起指控[11];韩国刑法中规定有关强奸罪告诉乃论,“第306条(告诉)规定,第297条至第300条,与第302条至前条之罪,均须告诉乃论”[12]。虽然国外有相关立法,但对于我国是否在强奸犯罪中引入该项制度的问题,笔者持否定态度。亲告罪的引入,带来实惠的同时,却带来了更多的弊端。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强奸犯罪有着巨大的社会危害性,在我国属于国家公诉类犯罪,由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起诉,当事人之间不能通过非诉讼途径解决。若将强奸犯罪定为亲告罪,必将伤害公众的法感情,影响法律权威和尊严。特别在中国这样注重礼仪教化、伦理道德的社会环境下,将强奸罪定亲告罪可行性甚微。同时,还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强奸行为的定性处于极大的不确定之中。“刑事诉讼过程实质上是证据在不同阶段的认证过程,在司法实践中,几乎鲜有证据不发生变化的案件,尤以强奸案件最为突出”,因此,若将强奸罪定为“告诉才处理”,那么,人为因素和非法交易可能会致使一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3]
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制度诞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被害人保护运动的西方国家,主要功能在于恢复已经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使加害人能够复归社会,被害人心理创伤得到平复、物质损失得到弥补等。正因为刑事和解制度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殊途同归,故为我国当代法治所吸收借鉴。所谓刑事和解,又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亦即加害人得到被害人原谅之后,对加害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体现了对被害人选择权的尊重。
在许多西方国家,性犯罪中大量引入了刑事和解制度。如西班牙刑法第191条中规定,犯罪主体获得被害人宽恕的,可以免除诉讼或者免除已判的刑罚。西班牙刑罚性犯罪通则规定:“年满21岁未满23岁妇女之法律代表、保护人或看护人代为表达的原谅,需要法官听证,并由有关法院同意始可成立”[3]。芬兰刑法典第17条规定,强奸罪、滥用性权利罪等犯罪的受害人基于自愿不要求提起指控,则公诉人可以免予提起指控,体现了对被害人选择权的保护。德国刑事和解的适用案件类型则扩展到了重罪案件,包括强奸案件中的适用。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的,法院可根据第49条第1款减轻其刑罚。[13]在英国,刑事和解制度适用于强奸案件的情况也非常多。[14]国外在实行刑事和解制度时,不仅采用被害人谅解,还采取法官听证制度,处理该类案件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当前,在全国各地的司法实践中正在进行刑事和解制度的试点,刑事和解的范围从轻刑案件进一步扩大到重刑案件,直至一些地区已经开始了在死刑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的尝试。由此观之,我国的法治环境是允许刑事和解引入强奸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是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主动介入的情况下,强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尊重被害人的选择权,注重对被害人的安抚以及加害人的复归等。法官可根据不同的案件进行不同处理,结合被害人的谅解和加害人的补偿、认罪态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在法定刑基础上进行从宽处理。性犯罪本身就存在个体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法官在认定共性的同时,注重对案件个性的关注,能使得个案得到合理判决,从而达到能维护公平正义、保障法律权威的目的。
与此同时,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将规避《解答》在适用上存在的众多问题。例如对多次自愿的认定。妇女多次自愿与加害人发生性关系,才能作为适用该解释的条件。那么如果只发生了一次,第二次还没有来得及发生就已经案发的情况如何处理?同样的,妇女已经真心谅解了加害人,但是尚未发生性关系,只保持恋爱关系又当如何处理?司法实务中还存在加害人利用该解释作为法律的漏洞,使之成为脱罪的保护伞。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可回避。只有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才能合理解决这些问题。法官根据被害人的谅解行为及是否及时得到补偿、加害人的认罪等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虽然认定加害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对其进行否定性评价,但在量刑上可以给予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量刑上从轻、减轻的依据还在于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降低,以及社会危害性的减小。若按照《解答》的规定,一律不构成犯罪,这种做法过于绝对。绝对的确定性,必然导致法律对公平正义的偏离。若设定为亲告罪,排除公诉机关的介入,必将使得被害人的权益难以保障,其在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也将伤害民众法感情。强奸案在遵循法定刑的基础之上,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被害人的赔偿、心理的平复,也有利于案件的侦破以及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成本。同时,强奸案件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使得受众面更广,不仅仅局限于“强奸转通奸”的情况,还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强奸案件。如此做法有利于更多被害人的保护,更广泛社会关系的修复,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营造。
(二)出路之二:保留现有解释,加强科学适用
以上从立法论的角度提出应当废止该解释,只是一种倡导。那么,在当前该解释仍有效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应当如何科学适用呢?笔者拟从刑法解释学的角度提出如下建议。
1.强奸转自由恋爱及合法婚姻中也可适用《解答》之规定
未婚男子对未婚妇女实施强奸后又与其谈恋爱,发生“合意性关系(以下简称合奸)”[15]的,甚至发展为合法婚姻的,是否属于该司法解释适用的范围?如上所述,“通奸是指有配偶的男女之间以及有配偶的男女一方与他人之间自愿发生婚外性行为”[16],从文意来看,“通奸”不应包括未婚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那么,此司法解释能否适用单身男女之间发生的“先强奸后合奸或者转化为合法婚姻”的情况呢?笔者认为,虽然从“通奸”本身的字面意思来看,不包括单身男女之间发生的“合奸”或者“合法婚姻”的情况,但是从立法原意和刑事政策以及“举重以明轻”的刑法解释论入手分析,可以参照适用。通奸本身不合乎道德伦理,且具有违法性,却能阻却犯罪(根据《解答》的规定),那么单身男女之间发生的合意性关系,应当更具有去犯罪化的效力。我们进一步思考,合法婚姻不违背道德伦理且受法律的保护,则应更加优于通奸和合奸,更加具有去犯罪化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强奸转通奸”中的“通奸”扩大解释为包括通奸、合奸与合法婚姻。
2.“先强奸后通奸”中“强奸”概念范围之界定
《解答》中“强奸”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强奸包括强奸罪中的所有情形,而狭义的强奸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在广义的强奸中排除了“轮奸”“奸淫幼女”两种类型[17];第二种认为应当排除广义强奸罪中的五种加重情形及奸淫幼女的情形。笔者支持狭义说的第二种观点。
其一,强奸采狭义说是《解答》本身的应有之义。从《解答》本身的规定来看,“强奸转通奸”司法解释中的强奸行为并不是广义的。《解答》共分为七个部分,前面三个部分与后面三个部分的职能存在区别。第一、二、三描述了一般的强奸罪应当如何认定,其中包括暴力、胁迫和其他手段,分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等;第四、五、六、七部分主要讲述了加重情节及强奸的特殊情况和类型。也就是前面三部分应当是排除了加重情节和强奸的特殊类型的。这在关于奸淫幼女的规定中,可以得到印证。第六部分排除了奸淫幼女罪对于第三部分第二条第二项关于“先强奸后通奸”的司法解释的适用,“一般地说,不论行为人采用什么手段,也不问幼女是否同意,只要与幼女发生了性行为,就构成犯罪”。同时“强奸转通奸”规定在第三部分中,因此,此处的“强奸”应为狭义的强奸,解释为排除了奸淫幼女及五种加重情形的普通强奸。[17]
其二,若采用广义的强奸概念,则存在龃龉之处。首先,在“先轮奸后通奸”的案件中,涉及共同犯罪的问题。行为人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如若对其中与受害人“通奸”的个体去犯罪化,而对其他行为人依照法律定罪裁量则会显失公平。这里不容回避的是: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各行为人实施了同样的强奸行为,为何会有不同的法律后果?行为的相等和刑罚的不等,让普通民众难以接受,刑法的权威性和威慑作用也将被削弱。其次,对于公众场合奸淫妇女的情况,由于社会影响十分恶劣,此时表现出来的负面性和反社会性更大。如果仍适用该解释,认为其不构成犯罪,则将严重挫伤民众的法感情,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无法统一。再次,在强奸妇女、幼女多人的情况下,与其中一名女子通奸,能否适用该解释?还是要和所有女子保持通奸关系才能适用该解释?若是后者,那么一名男子与多名女子保持通奸关系,这种有伤风化的行为作为阻却犯罪的法定条件是否合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不能适用该解释的。复次,在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或者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如按司法解释的规定,不以强奸罪论处,那么社会危害性如此之大的犯罪行为仍不构成强奸犯罪,必然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功能将受到严重侵蚀。最后,在奸淫幼女的情况下,即使保持通奸,也不能适用该解释。在刑法的视野下,幼女被认为不具有自主决定性行为的能力,如上所述,不能以幼女与加害人发生性关系推定为原谅,这从司法解释本身的规定中即可得出此结论。
在国外,虽然有些国家认为强奸罪是可以由被害人的原谅而不认为构成犯罪的,将强奸罪定为亲告罪,但是采取此立法例的国家,仍将加重情形排除在亲告罪之外,即,不因被害人的意志而改变发生加重情形的强奸罪的定罪处罚。例如在日本刑法体系中,普通强奸属于猥亵罪的一种。但第181条之强奸致人伤亡等情形、第182条淫行劝诱罪都不适用亲告。[18]根据平成十六年修改刑法时新增的第180条第二款规定:“二人以上在现场共同实施刑法第176条至第179条规定之罪的,不适用前款规定”。即集团强奸非属亲告罪[19]。在日本刑法典中所说的“集团强奸”即为我国刑法中的“轮奸”。可见,对于加重情形,社会危害性大,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高,应当由公诉机关介入,并进行严肃处理。综上所述,在《解答》中“强奸转通奸”的规定之“强奸”应当是狭义的,解释为不包括奸淫幼女及五种加重情形的普通强奸。司法实务中,切忌对《解答》无限扩大适用。因此,“庄志伟轮奸案”的处理,笔者认为上海某区法院的判决缺乏合理性。
3.在奸淫幼女及五种加重情形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
暂且不论在强奸案件中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就本文研究的“强奸转通奸”案件而言,笔者认为,可以尝试在奸淫幼女及五种加重情形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如上所述,《解答》不应当适用于奸淫幼女及五种加重情形,但在这类案件中若发生加害人得到被害人谅解的情况,则法律不能对此视而不见,因此,应当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加害人进行从宽处理,这也是基于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降低以及社会危害性的减小。《解答》的适用导致行为人不构成犯罪,但加重情形则导致行为人被判处至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过大,而刑事和解的引入,正是《解答》的适用与法定加重情形之间的一种过渡。同时,这也是对被害人予以谅解的行为的法定化考量,有利于加害人对被害人财物和情感上的补偿,也更加有利于被破坏社会关系的修复。但若在当下引入刑事和解制度,还需要对自由裁量进行严格的限制。亦即必须严格限制刑事和解自由裁量幅度,否则可能造成司法腐败,反而更加不利于保护被害人。当前,刑事和解制度缺乏统一立法,适用上存在模糊性和多样性,各地区司法实践不一,因此,在强奸案件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必然要立法先行,制定统一的刑事和解法规,以规范刑事和解的程序、范围、幅度等。
注释:
① 日本刑法第176条:“对于十三岁以上之男女以暴行或胁迫为猥亵之行为者,处六月以上七年以下之惩役,对于不满十三岁之男女为猥亵之行为者,亦同”。第 177条规定:“以暴行或胁迫奸淫十三岁以上之妇女者,为强奸之罪,处二年以上之有期惩役。奸淫不满十三岁之妇女者,亦同”。第 178条规定:“乘人心神丧失或抗拒不能,又使之心神丧失或抗拒不能,而为猥亵之行为或奸淫者,同前二条之例”。第 179条规定:“前三条之未遂罪,罚之”。第180条规定:“前四条之罪,待告诉而论之”。第181条规定:“犯第176条乃至第179条之罪,因而致人死伤者,处无期或三年以上之惩役”。第 182条:“以营利之目的劝诱无淫行常习之妇女而使为奸淫者,处三年以下之惩役或五百元以下之罚金”。第 183条:“奸通有夫之妇时,处二年以下之惩役;其相奸者,亦同。前项之罪,待本夫之告诉而论之。但本夫既容奸通时,无告诉之效”。第 184条:“有配偶者重为婚姻时,处二年以下之惩役;其相婚者,亦同”。
[1]陈益俊, 柳文彬, 袁玮.盗窃案牵出重大强奸案三男青年分获刑[EB/OL].http://news.163.com/07/1104/00/3SDPFTNO00011229.html, 2008−01−21.
[2]许明华, 傅登平.先强奸后通奸应以强奸罪论处[J].现代法学, 1985, (3): 24−25.
[3]董晓松.一个司法解释的困境与出路——“先强奸后通奸不宜以强奸罪论处”的再审视[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07,(4): 52−53.
[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7.
[5]徐岱, 凌萍萍.被害人承诺之刑法评价[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4, (6): 107−115.
[6]黄京平, 杜强.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的比较分析[J].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3, (2): 81−86.
[7]陈兴良.陈兴良刑法学教科书[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465−466.
[8]高铭暄, 马克昌.刑法学(第三版)[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527.
[9][日]牧野英一.日本刑法通义[M].陈承泽译.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171.
[10]苏惠渔, 孙万怀.论国家刑权力[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23.
[11]李拥军.现代西方国家性犯罪立法的特点与趋向——关于完善我国当前性犯罪立法的一点思考[J].河北法学, 2007, (7).
[12]王文生.强奸罪判解研究[M].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108.
[13]徐久生, 庄敬华.德国刑法典[Z].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
[14]李奋飞.刑事和解制度的“中国式”构建[J].中国检察官, 2006,(5): 10−11.
[15]韩轶.侵犯女性人身权利犯罪研究[M].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3: 61.
[16]赵秉志.刑法新教程[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625.
[17]房培志.怎么认定“先强奸后通奸行为”的性质[J].人民检察,2005, (10): 33−35.
[18]张明楷.日本刑法典[Z].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6: 68.
[19][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