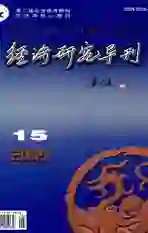法律移植与法的本土化的思考
2009-09-30向平生
向平生
摘要:法律移植是国家及民族交往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本土化是决定法律移植成功与否的关键。法律移植必须考虑本国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的实际情况。在法律移植时,应让受移植法律经过合理的处理与嫁接,使其能渗入、移植到国民的血液当中,进而得到有机的整合。
关键词:法律移植;本土化;思考
中图分类号:DF11/1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5-0254-02
法律移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法律制度互相借鉴与取舍的过程,可以说,只要存在国家和民族,那么各国家和民族文化上的冲突和融合就不可避免会发生。因而,自有国家以来,几乎任何形式的法律文化都避免不了法律之间的移植问题,因为其大前提是国家民族的文化有互动的关系,历史发展到今天(除极个别与世隔绝的部落之外)几乎无法想象存有不受他国与世界文化大潮影响的国家,所以说法律移植是国际文化交流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但是,法律移植必须考虑本土化这一环节。因为只有实现了移植法律的“本土化”过程,移植才算有了结果,才具有价值。
一、法律移植的概念
移植是法学家们从植物学和医学的移植现象的启发,把“法律”与“移植”加以组合。某一国家、地区或民族的法律移植其他国或民族法律的做法称作“法律移植”。
国内外学者对法律移植这一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的。英国法律史学家阿兰·沃森认为,法律移植是“一条规则或者一种法自一国向另一国,或者自一个民族向另一民族。”[1]德国法学家莱茵斯坦认为,“法律移植是指在一种法环境中发展的法秩序在与此不同的法环境中有意识地得到实施的现象”[2]。这一定义将法律移植局限在有意识的活动的范围内,从而排除了那些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其他法律制度影响的现象;同时,它强调法律移植的内容是宽泛的“法秩序”,而不仅仅是某种法律制度或某条规则;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这一定义并未将法律移植设定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或者民族之间,而是强调了在不同的法环境之间进行,意即相同或相似的法环境之间是不能移植的,或者起码不能算做移植。还有学者认为,法律移植最初特指罗马法的继受,以后用来泛指“世界范围中发生的法文化的相互交流现象”[2]。
二、法律移植是国家及民族交往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
历史上的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欲图生存与发展,都必须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其他国家进行交往,这种交往无论是否在友好状态下进行其结果都一样,即会发生文化上的碰撞,产生文化上的交流、制度上的相互移植与借鉴。
例如,罗马法作为一种法律文化影响到了整个世界。首先表现为罗马对其它文化的吸收,尤其是对古希腊文化的吸收。美国“新史学派”的著名学者J.W.汤普逊认为,“罗马时代的希腊是珍藏着无数优美而干燥的古物的一个极其巨大露天的博物馆”[3]。希腊的文化强烈地震撼着罗马。在“希腊化”时期,大批的希腊人生活在罗马,其中不乏教师、医生、商人、美术家等。在此前,罗马为制定《十二表法》,曾派十人代表团考察雅典。在法律制度方面,由于罗马质权的局限性,罗马从希腊引进了抵押权制度,这样就使抵押物仍为抵押人占有,从而使得物得以充分利用[4]。其次,罗马法的影响。罗马法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已为大家所熟知,这里仅举“蛮族”为例,略加说明。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各“蛮族”大都移植了罗马法。早期日耳曼人适用日耳曼法,罗马人适用罗马法,两者之间发生冲突则用日耳曼法。大概过了50—70年,日耳曼各部落的习惯也都采用了成文法的形式,各部落或多或少都受到了罗马法的影响,其中西哥特受罗马法的影响最大。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法律移植是人类文明互动的必然结果。如果否认法律的可移植性,那就等于否定了世界文明的可交流性,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人类的文明发展状态。事实上,每个文明都在吸收其他文明的长足之处而使自己更加“文明”。
三、本土化是决定法律移植成功与否的关键
本土运动是人类学家林顿所提出,指两个文化接触时,“某一文化的部分成员(因感于外来文化的压力)企图保存或恢复其传统文化的若干形象之有意的及有组织的行动,总而言之,本土运动是一个主位文化因客位文化的冲击下而引起的重整反应。”[5]本文所指的本土化,是指在法律移植时,应让受移植法律经过合理的处理与嫁接,使其能渗入到移植国国民的血液当中,进而得到有机的整合,本土化就是法律移植本土运动的过程。
众所周知,并不是什么法律都可以移植到本国来的,移植法律时首先必须考虑本国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的实际情况。一般来说,在和平时期,移植常常是主动的、有选择性的,能够充分地结合本民族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的现状加以考虑,所以这种移植很少会出现不适时的情形。而殖民时期或是受外力压迫时,其选择的余地就小。常常表现为全盘“拿来”,以至于出现诸多不能适应时代需要的法律。前者,如日耳曼人继受罗马法。日耳曼人在其征服罗马后实行属人法原则,其后他们觉得罗马法较其自身之蛮族陋习更能适合其生活。所以,在象Recesvind那样的法典法中吸收了不少罗马法规则[6]。后者,如日本与中国。日本同中国一样,在西方介入前基本上实行锁国政策。门户被打开后,中国与日本都移植了西方的法律,但在当时都没有真正得到实施。这说明在外来压力之下,由于移植的迫切性,很难考虑本国文化的具体状况,往往导致移植的“流产”。
事实上,移植法律时考虑本民族国情的过程就是一个对移植法的筛选过程。既然移植是法律文化交往当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尤其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经济组织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都无法拒绝与别国的交往,这些国家所能够做到的只能是面对现实,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找到一个最佳的契合点,使外来法与本国法有机地结合起来。笔者认为真正做到这一点,起码得考虑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对本民族传统法律资源的使用。任何国家移植外国法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学习外国法的优点,借用过来为其所用,但在此过程中不要忘了“本”,因此一定要利用好本土资源。譬如,中国与日本的调解和调停制度,它既照顾到了当事人要求明辨是非的心态,又避免当事人之间撕开面子,乃至反目成仇的现象。每一个民族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资源优势,法律移植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找到与此相适的最佳契合点,否则本土化也无从谈起。其次,实行法律移植必须做好法律移植宣传工作。必须要指出是,这种宣传应该是全面的、客观的、不是片面的、主观的。中国清末“维新”为了介绍与翻译西学著作成立了不少报社,如《强学报》、《湘学报》、《时务报》等,且组织成立了各种学会,如“强学会”等等,有此学会不仅得到当时首都士大夫的支持,而且得到地方封疆大吏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支持,这对传播西方文化,直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7]。但是现在看来,这种宣传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没有注意到本土性的相关问题。第三,移植外来法是为了改造本土法,而非取消本土法,两者的互相适应和统一就构成了法律现代化发展趋势。例如,日本人建立于1889年第一部宪法之上法律体系并非西方法的彻底翻版,它在很多方面吸收了本土因素,其中重要的是天皇制和家族制。二战以后,日本吸收了英美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形成兼有大陆法因素、英美法因素和本土法因素的当代法律体系。最后是观念问题。不少人认为,无论是移植不是本土化都只与制度有关,同观念没有多大的联系。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梁启超说,在西方打开中国的大门后,人们先是感到器物不如人,之后又感到这种不如别人不仅仅是器物上的,而且是制度上的,最后感到与西洋最根本的差异是文化上的[8]。这是从批判传统的角度来看待观念问题的。的确,任何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都会因其特有的文化传统而深深地影响着生活在其国度里的每一个人。毋庸讳言,这种传统里含有许多糟粕,但是这里面也有“珍珠”。我们强调要有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就是本土性。不过要注意的是这种本土必须是能够容纳移植法律的本土。
四、小结
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多元与法律趋同化并存的时代,法律文化作为大文化的一部分也应该是多元的。西方殖民体系崩溃后,各国法的本土化就是铁的例证。任何一个国家想把自己的法律文化强加给别人都是徒劳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法律发展运动的失败为我们作了很好的说明。随着交通通讯事业的飞速发展,国际间经济贸易范围的日益扩大,法律文化也有趋同一致的倾向。各经济区域间的互相合作,导致了区域间经济合作的法律法规的出现,这种法律法规甚至超越于国家之上,是各合作国家间的法律渊源,如欧洲共同体法等。此外,国际间的刑法、私法、商法等等方面存在广泛的合作,许多法律成为缔约国共同遵守的规范,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但是,我们决不可不考虑传统,对传统当中有用的因子必须加以挖掘,否则我们的移植将不会成功,进而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不过,从法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本土资源毕竟有限,我们老祖宗的法治精神与现代的法治精神有天壤之别。这里应该注意的是本土资源有限并不代表本土化有限。本土化不是空洞的口号,它有深刻的内涵。本土化也不是地方本位主义、家族主义乃至官僚主义,这种未进行过内在转化的“本土”是对现代法治精神的反动。
移植与本土化是近些年来人们一直关注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只要民族与国家间还存在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之间的差异,法律的移植就会产生一定的冲突,因此探讨能不能移植、如何移植、移植与本土资源和本土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对于解决中国法律移植的理论问题以及中国应如何借鉴与学习西方法律,对于建设与加强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社会实际生活当中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Alan Watson,Legal Transplants:An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Law,2nd ed,Athens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3:21.
[2]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0.
[3]J.W汤普逊.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43.
[4] 周楠.罗马法原论: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35-139.
[5] 金耀基.从全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26.
[6][美]孟罗·斯密.欧陆法律发达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02.
[7][前苏]文赫文斯基.中国变法维新运动与康有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92-93.
[8]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卷39,合集第8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39.
[责任编辑陈凤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