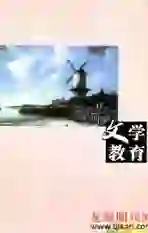贾平凹《高兴》的底层性缺失
2009-09-24王萌
王 萌
著名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发表后,立刻引起了各方的热切关注,2009年导演阿甘将《高兴》搬上大银幕,成就了一场贺岁档的狂欢盛宴,此举又把作家和这部长篇小说推到了大众视线的最前沿。
近年来,底层文学成为文坛的写作潮流,越来越多的作家加入到底层文学的创作中,书写“底层题材”,刻画“底层人物”,着眼于“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生活轨迹,描述他们的悲苦辛酸,引起读者的关注、同情和情感共鸣。其实我们的文学本就有着朴素的现实主义传统,以直面人生为己任的作家们或鞭挞、或揭露、或大声疾呼,创作出了大量有生命力的优秀作品。然而到了80年代,在“纯文学”审美趋向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作家由“写什么”转向了“怎么写”,由本质精神的发掘转向了过于追求有意味的形式,使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发生了暂时性的停滞。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底层文学的蓬勃发展,底层作家队伍的日益壮大,不得不说是文学自身要求打破束缚的客观需要,是中国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追求所谓的审美和娱乐以至于在精神上陷入了危机之后的一次自我救赎和自觉担当。贾平凹带着他的长篇小说《高兴》走进底层,以龟缩于城市中的拾荒农民为对象,描写了在垃圾上讨生活的群体的生存处境。如此的内容,如此的一群主人公,《高兴》当然是底层小说。然而我们发现,在新世纪的背景下,随着社会语境和作家生活体验的转变,《高兴》无论是对于底层群体生活的解读还是对于底层苦难意识的提炼都存在着明显的缺失。
一.典型人物处于底层之上
农民“刘高兴”是小说的主人公。他带着同乡五富来到西安,开始了捡破烂的城市生活。他们与同为拾荒者的黄八、杏胡和种猪,妓女孟夷纯,乞丐石热闹等构成了一个底层生存小群落。然而刘高兴作为底层群落的代言人,却明显投射出非底层气质。他有文化,心气高,见识、谈吐、审美、办事能力,各方面都远超过和他同样身份、同样处境的农民兄弟们。他聪明而机灵,能轻易解决穷弟兄们遇到的麻烦。他几句话就搞定了刁难五富的门卫,用廉价的西服和劣质皮鞋就为翠花讨回了身份证,扑在汽车前盖上制服了肇事企图逃逸的司机等。这些扶危济困的英勇事迹将刘高兴装点成了一位底层人民的救世主。刘高兴的身份和行为是相互剥离的。他和五富、黄八等人一样,是受到城市文明侵蚀的“进城乡下人”,是靠“拾荒”维持生计的边缘群体。在他身上承载着都市和乡村两种价值观念的巨大冲撞以及小人物在大都市挣扎的生存景况,这是时代的烙印,不是依靠“高兴”和小聪明就能回避的干净的。而小说中作家把他塑造的鹤立鸡群,高人一等。他属于底层,混迹于底层,而思想、行为
却处处凌驾于底层之上。主人公身份和行为轨迹的相互剥离,这使得小说的底层性显得并不纯粹。
二.才子佳人的故事建构削弱了精神深度
底层小说《高兴》具有丝丝温暖和浪漫主义气息,这来源于作家给读者虚构了一个才子佳人的故事,这也是整部小说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力。刘高兴是“才子”,孟夷纯是“佳人”。孟操皮肉生涯有一个光明正大、令人同情的理由——赚钱给警察,缉拿杀害哥哥的凶手。由于凶手一次次地逃逸,为了使追查不致中断,孟夷纯只好来到西安,操起皮肉生涯,赚钱以满足不断索要的追查经费。这一动因使孟夷纯令人不耻的职业变得神圣而高贵起来,也成就了刘和孟之间纯洁美好的爱情。在刘孟的相识相知中,刘又扮演了底层之上的侠义英雄的角色,将自己捡破烂得来的钱一次次送与孟夷纯,以助她完成心愿,脱离苦海。当我们借助文学表现对底层世界的关怀、批判和同情时,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底层,或者说怎样真正地进入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处境,而我们自身的立场又怎样在底层形象建构上得到展示?这是更值得深入思考和体会的主题,而不是匆匆忙忙地随潮流进入底层。底层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选择了底层题材,更重要的是需要追问其对于我们当代社会的精神净化提供了哪些有益的经验,缺乏批判精神的文学是软弱无骨的。才子佳人的爱情建构不得不说是作家对底层社会现实生活理解缺乏深度,温情脉脉的爱情造就了主人公的精神缺血,小说也自然未能达到它应有的理性批判的精神高度,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遗憾。
三.底层性缺失的思考
也许作家本身就是无奈的,在新世纪复杂的社会语境下,文学的批判精神日趋多样化。历史上的左翼作家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坚定地站在无产者一边,全力声讨剥削者、压迫者。可是在今天的价值框架中,作家们再也找不到同样的范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城市化进程,都市的扩张和现代文明的侵蚀,使乡村的可耕土地逐步减少。生存困境和都市的诱惑,使越来越多的乡下人开始了都市的漂泊生涯。汹涌的经济浪潮和强大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改变着农民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在改变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城市文明对传统乡土经济的瓦解和冲击是时代特征的必然要求,两种文化的冲突使他们无所适从。在新时代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下,单一的人物与不公社会抗争的命运悲剧也就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另一方面,虽然部分作家们先知先觉的书写着苦难,疾呼着治病救人,我们却不自觉地进入了一个全民狂欢的时代。从一轮轮“超女”、“快男”、“新主播”等选秀节目的如火如荼之势,到抗雪灾、办奥运,中国年的来临,国力的强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使得中国人民获得了空前的自信。苦难被遗忘了,抛弃了,流行文学不欢迎苦难,更多的是娱乐大众的热情。极力书写底层的苦难和社会的不合理缺少坚强的理论支撑,这些都必然会对作家的创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底层小说的悲剧色彩很难真正地建构起来。作家给主人公起名“高兴”,然而最终刘高兴还是不能真正地高兴,他无法融入这个城市,只不过是又一个游走在城市中不被接纳的无所归依的过客。
参考文献:
[1]国家玮:底层文学:“代言”的困境及其出路[J]理论与现代化,2008,(04).
[2]李云雷:如何扬弃“纯文学”与“左翼文学”——底层写作所面临的问题[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05).
[3]黄曙光:被城市分裂的身体——从《高兴》谈农民工的城市梦[J]名作欣赏,2009(02)
[4]单正平:底层叙事与批评伦理[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05).
王萌,女,河北工程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助教,研究方向:文学、邯郸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