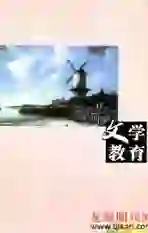开冲床的人
2009-09-24王十月
王十月
李响听不到声音,他的听力在他十岁那年就失去了,他在无声的世界中开了十年冲床,感受很多,希望也很多。后来,他可以听到声音了,他的世界从那一刻起发生了改变……
一
有个打工仔,名字叫李响。可他的世界没有一点声响,于是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李想。他希望自己是个有思想的人。还有个打工仔,来自广西,年方十八,瘦瘦小小,像棵草,工友们都叫他小广西。他俩在同一间五金厂打工,都开冲床。有一天,小广西的一只手掌被冲床砸成了肉泥,连血带肉溅了李想一脸。李想当时在神游,并没意识到溅在他脸上的是血、是肉,只感觉到有东西扑打在脸上。他纳闷地看见小广西跳起来,蹲下去,又跳起来,接着身子像陀螺一样转着圈子;小广西的嘴不停地一张一合,像一条在岸上垂死的鱼;他脸上的肌肉在抽搐、扭曲,直到把身子扭成了麻花状。这古怪的模样让李想产生了联想。他经常这样,看见事件甲,就想到事件乙,又由事件乙想到事件丙……他的联想漫无边际。李想时常觉得,这一切都是他的名字在作怪。觉得他名字中的这个想字,不是思想的想,而是胡思乱想的想。比如现在,李想想起了麻花,厂外面有卖天津大麻花的,李想第一次见到,惊讶得不行。呵!那么大的麻花!这哪儿是麻花呀,可不是麻花又是什么呢?这些,已是十年前的事了,十年前,李想十八岁,和如今的小广西一个年纪,李想从湖北来到广东打工,在老乡的帮助下,给这间厂的人事经理送了一条“特美思”———那时想要进厂不容易,何况李想这样失聪的人,就更不容易,但有了一条“特美思”,进厂又变得容易了起来。因此容易和不容易,有时是辩证的,是相对的。———李想顺利进了这家五金厂。那一年,李想见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事物,比如冲床,比如许多稀奇古怪的植物,总之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天津大麻花就是其中之一。李想对天津大麻花情有独钟,每次经过卖麻花的摊点,闻到那浓浓的油香,他就会想起过年时母亲炸的油饼。母亲在炸油饼时,李想就眼巴巴地盯着锅里,说,“妈,完球了,油没有了。”母亲鼓他一眼,朝他挥着手说,“去去去,出去玩,这么多油饼还塞不住你的嘴。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谁承想一语成谶,他竟然真成了哑巴。进厂后第四月,李想生平第一次拿工资,一百八十元。在李想看来,那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拿到工资李想就出厂门,直奔麻花摊点,买了一根天津大麻花。李想捧着天津大麻花回到宿舍,左看右看,终究没舍得吃。在家里,只有生病了,母亲才会买回几根小麻花,泡在糖水里,这是李想记忆中的人间绝味。闻着天津大麻花的油香,小学四年级那年冬天的记忆纷至沓来,他记得那个冬天下很大的雪。那时的冬天仿佛都有很大的雪,常常是清晨一觉醒来,雪已把门堵住。他喜欢雪,在雪地上追踪着兔子或野鸡的足迹,追出很远,直到雪地上的足迹突然消逝,他从来没有追到过野兔或是野鸡,却乐此不疲。那个冬天,他在追野兔时不慎掉进水凼子,爬起来时浑身皆已湿透,回到家,在火边一烤,烤得手脚生痛,仿佛有鱼在咬。当晚他就病了,高烧不退,感觉是跳进了火炉,外面的世界冰天雪地,他身体的季节却在夏天。那场病持续了一月有余。李想尚能忆起,母亲每天晚上站在寒风呼呼的山头上为他招魂,母亲喊,“响儿哎,回来哟。”父亲在屋里答,“回来了。”母亲和父亲的一喊一答,成为李想对于声音的最后珍藏。冬天过去时,李想的身体从夏天回归春天,却陷入了一个无声的世界。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是一次医疗事故,乡间的医生用庆大霉素和链霉素对李想的身体进行了轮番攻击,杀死了病毒,也直接导致了他双耳失聪,听力损失九十分贝以上……李想看着天津大麻花时就想起了母亲,想起了母亲为他招魂的声音,那声音来自他的体内,仿佛是从某个细胞里不经意逸出。李想想起母亲一辈子没有离开烟村,没见过这么大的大麻花。他抻长脖子吞着口水,仿佛一只吞食田螺的鸭,最后小心翼翼包好麻花,去了工业区邮政代办所,把那根大麻花寄回家。顺修短信一封,告知母亲,说:儿在外面一切皆好,拿了工资,不愁钱花,工作并不累。说:每天坐在冲床前,把薄铁片伸进冲床口里,踩一下电钮,如此简单。说:车间里一大排冲床,在不停地冲着铁,冲着铝,冲着不锈钢,还有电锯在锯着铁,锯着铝,锯着不锈钢,火光四散,像花一样,煞是好看……李想的思绪游走一周,他再次看着身体扭成麻花的小广西,突然灵醒过来:小广西出事了!李想觉得脸上黏糊糊的,伸手一抹,抹出一巴掌血,血中带着肉屑,那是小广西的血,是小广西的肉屑。血和肉屑一如王水,腐蚀着李想的脸。脸上的皮肉被撕裂,痛感瞬间从脸经过心脏直抵脚尖,李想的意识再次逃离了现场。“王水”二字,是从前一位工友写给他看的。厂里有个车间,车间里有个池子,池里盛满王水。李想初次见到王水,呵!好神奇。像火!像一个张着大嘴的怪物!水居然可以吃东西?李想见过一位工友的手指被王水吃掉,余下黑乎乎的一截,像根从灶里拔出的木棍。这厂子里是危险和恐怖的,到处是吃人的王水和咬人的电锯、冲床。拿着原料从仓库到冲床车间,或是从冲床车间到镀铬车间,就像是经过一片危机四伏的原始森林。李想时常觉得一双眼不够用。半年后,李想对车间熟悉了,哪里有电锯,哪里有王水池,哪里会飞出像暗器一样的铁片,哪里的地下有“绊马索”,这一切他都了然于胸。王水没有吃到他的肉,冲床没有咬着他的手。给他写下“王水”二字的工友,那只写字的手早已被冲床吃掉了,就像小广西的手一样。失去了手不久,小广西失踪了。十年来,李想习惯了这样的失踪。他知道,用不了几天,甚至是几个小时,就会有人来填补小广西留下的空位。这硕大的车间,能坚持做满二年的人已不多,能全身而退者更是少之又少。李想已记不清这车间吞噬了多少根手指……李想时常会想:他们做事何以马虎若此?李想就不一样了,他在这位置一坐就是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可能还会坐下去。李想觉得冲床很温柔,很安全,也很听话。脚尖轻点一下控制,冲床的大铁掌呼地抬起,放下要冲的料片,脚尖再轻点控制,冲床呼地冲下。一切都是那么简单。看着小广西那血肉模糊的断掌,李想木然地想,好好的人,脑子又没毛病,为何把手放进冲床口,手在冲床口里,为何又要踩控制开关?若只一个人如此尚可以理解,为何每年都有人会犯同样的错误?李想喜欢他的这台冲床,和冲床有感情。仿佛这冲床是他的恋人。每天下班,他都会拿起抹布,把冲床擦得干干净净,油光闪闪。李想甚至觉得,他和这台冲床是一个整体。他熟悉冲床,就像熟悉自己的手指,操控冲床,如同指挥自己的四肢。他向工友表演开冲床,他的动作是那么有节奏感。在表演的时候,李想闭着眼,他的心里没有冲床,也没有铁片,只有一个宽广的舞台,他在跳舞,动作舒展、轻盈。那是多么美妙的境界呀。他冲出的产品整整齐齐,铁片上冲出来的圈一个紧挨着一个,材料没有一点浪费。这事被经理抓了现行,他因此而被罚款五十,这让李想心疼了好多天。李想后来不再表演。身体被限制,思想却获得了无限的自由,坐在冲床面前时,所有的思想,最后都落在渐行渐远的声音上。关于声音,李想实在无法忆及太多,他只依稀记得母亲和父亲的喊魂声,房前屋后树林里的鸟叫,草丛中不绝的虫鸣。有时李想一边开着冲床,一边努力回忆那些鸟叫和虫鸣。他相信一定还有鸟叫和虫鸣躲在他身体的某个细胞里,在和他玩捉迷藏。他就和这些声音玩起了游戏,发誓要把它们找出来,而声音在躲避着他。他一次次徒劳无功,后来李想明白了,以他的能力是无法找出这些声音的,他想到了医生。医生在检查了一番之后,给他开出了一堆的药。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李想把工资都交给了一家又一家的医院,换成了中药、西药、藏药、各类祖传秘方……李想打工有了明确的目标:挣钱,治病,找回失去的声音。因为这个目标,再苦再累,李想也没有觉得苦和累。他更多看到的是希望。终于有家医院给了李想真正的希望:手术植入电子耳蜗。李想不再病急乱求医,他开始存钱。十万元,这是医生报出的数字。对于李想来说,这是一个无穷大的数字。然而李想从此安心地坐在了冲床前,冲床每上下起动十次就是一分钱。李想无法计算出,当他手中的钱变成六位数时,冲床要上下起落多少次。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李想读过一篇课文,叫《愚公移山》。李想还看过一个故事,叫《精卫填海》。李想觉得他是愚公,他是精卫。他在冲床上贴一张纸片,上书六字:有志者,事竟成。
二
李想和小广西睡一张床。李想睡下铺,小广西睡上铺。宿舍里八个人,小广西是李想唯一的朋友。
在小广西出现之前,李想的世界就是车间,就是冲床,就是手中的那些金属。几十台冲床在不停地起起落落,响声震天,李想安坐其中。那是李想的无声之阵,没有声音的世界里,李想早已忘记了语言。强烈的自尊,让李想不愿通过手势与人交流,也不会张开嘴发出徒劳的声音。也许是看见了小广西,让李想想起了初出门时的自己,他产生了想和小广西交流的冲动。李想听不见小广西对他说些什么,可是他喜欢“听”小广西说话。小广西出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李想在回忆他和小广西的友谊时,脑子里总是浮现他们第一次交流时的镜头:
(李想)拿出纸和笔,在纸上一笔一画地写道:我叫李想,你叫什么名字?我们交个朋友。
(小广西)脸刷地变红,嘴快速地一张一合,双手乱摇。
(李想)急坏了,在纸上快速写道:我不是坏人,看到你,想到我刚出门时的样子。
(小广西)脸更红,嘴迅速一张一合,双手不停地比划。
(李想)写:你在说什么呢?我听不见,你能写给我吗?
(李想)把纸片塞进小广西的手中。
(小广西)看着纸片,一脸茫然。
(李想)写:晚上很冷,我看你没有被子,为什么不去买,是没有钱吗?我借钱给你。
(小广西)突然痛哭,抱着头,蹲在地上,肩膀一抽一抽。
这个镜头无数次出现在李想的回忆中。当时他并不知道小广西不识字。后来,还是另外的一个工友见到在哭泣的小广西和不知所措的李想,居中翻译,把小广西的话译成字,把李想的字再念给小广西听,才为他们解了围。工友在纸片上写道:“他叫韦超,来自广西,他说他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没有钱买被子,但他说不冷。”
那天晚上下班后,李想和小广西一起去逛街,李想帮小广西买了一床被子。
一个哑巴,一个文盲,他们的初次交流,后来在这间五金厂作为笑谈被广为流传。而在这笑谈流传的时候,李想和小广西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们当真是奇妙的一对!上班时,李想的身边就坐着小广西。睡觉时,李想的上铺就睡着小广西。吃完饭,两人一起到厂外的公园走走。小广西看见什么新鲜事都会问李想,明知李想听不见,可他还是会问,还是会说。李想能感受到小广西眼里透出的情绪,那些快乐或者忧伤,于是他也被感染了,一起快乐或者忧伤。
小广西说:我喜欢上了小玲子,不敢对她说,她读过书,有文化,又是做仓管的。我晓得我们不般配。可我就是想她。
小广西说:我不想在这间厂里做了,车间里太吵,每天晚上睡着了耳朵里还在嗡嗡嗡地响。
小广西说:开冲床太危险了,听说每个月都要出工伤呢。
小广西说:你是好人,为什么不找个女朋友呢?你存了那么多的钱,肯定会有女孩子中意你的。
小广西说这些时,李想就看着他,脸上一直带着笑。
小广西有时也会使点坏,用广西话骂李想:丢雷个嘿!
李想还是笑。看着李想笑,小广西忍不住了,自己笑得不行。
李想却不笑了。他看出了小广西笑里的坏,举起拳头冲小广西挥一挥。小广西忙拱着手说对不起对不起。李想脸上便再次绽开了笑。
工友们也问过小广西:你都对李想说什么呢?你有毛病么,你说什么他又听不见,不是白说?
说:小广西小广西,你这是对牛弹琴呢。
小广西问什么叫对牛弹琴?说:这就是对牛弹琴。
小广西的脸又红了,说,你们欺负人。
厂里经常会贴出一些罚款告示:某某某员工,上班时不按规定操作,罚款一百以儆效尤之类。
小广西害怕被罚款,每次出告示都要挤过去看。看见上面有他的名字就害怕。有一次,厂里出的是奖励告示,上面有小广西的名字。
小广西紧张地问工友们:我是不是又被罚款了?
工友笑:罚了,罚一百。
小广西说:我没有犯错误呀,为什么罚我?
工友指着告示,一字一句地读:我厂冲床车间员工韦超,在上班时间不按规矩操作,罚款一百,以儆效尤。
小广西急了:我哪里不按规矩操作了,经理今天还表扬了我呢,我哪里不按规矩操作了。
围观的工友们哄地笑。小广西却哭了。
李想挤过来,看到告示,他为小广西高兴,他不明白小广西为什么哭,奖了一百块还哭什么呢?他拉着小广西,指着告示上小广西的名字,对他举起了大拇指。
这是李想第一次通过打手势来与人交流。
小广西终于从李想的表情,从工友们的坏笑里明白了,这不是罚款。小广西却高兴不起来,他学会了沉默。小广西不喜欢和那些工友们一起玩,和他们在一起时,他很自卑。他喜欢和李想在一起,和李想在一起时,他觉得他是生活的强者。和李想在一起时,他什么都说,包括他晚上手淫,包括他手淫时心里想着的人都说出来了,说出来了,他的心里就平静了,而李想是他最好的“听众”。永远也不会把他的秘密泄露的听众。
三
李想快存够做手术的钱了。坐在冲床前,他会想小广西:要是小广西还在那该多好。想他做了手术,就能听到小广西的声音了。李想感到无限遗憾,他连小广西去了哪里都不知道。小广西离开后,李想身边的冲床空了两天。第三天,冲床的座位上坐了一个陌生人,和小广西一样的年轻,和李想出门打工时一样的年轻。陌生人冲李想点头,打招呼。他的脸上写着谦卑、讨好的笑。李想熟悉这种笑,他刚进厂时,也对身边的老工人这样笑来着。这笑的意思很明显,希望得到老工人的关照。李想于是也对陌生人点头微笑。陌生人朝他伸出了手,李想也伸出了手。李想突然看见了一把刀,带着寒光,从高处劈下,刀锋横过陌生人的胳膊,像剁一根脆萝卜。李想没有想到,一个月后,他真正看到了一把刀,一把西瓜摊上常见的刀。刀握在小广西的手中。手是左手。小广西的右手成了一根光秃秃的肉棒,很怪异地挥舞着。小广西是来厂里索赔的。那时,工人们都已下班,到了吃饭的时候,有人看了一眼便去打饭了,有人打了饭又赶回来在看热闹。李想刚走出车间,就看见写字楼前围了一圈人,接着看见了小广西。他兴奋得想朝小广西跑过去,可是他才跑了两步就瓷在那里了。李想看见了一群穿迷彩服的治安员,治安员们的手中拿着一米来长的铝管,正呈扇形向小广西围过去。小广西的腿分明在发抖,李想看得很真切,为小广西捏一把汗。小广西一步步往后退,可他的身后围着厂里的工人。迷彩服在步步逼近。小广西退一步,迷彩服就进一步。小广西手中的西瓜刀在迷彩服们手中的铝管面前显得是那么幼稚可笑。谁都知道,小广西坚持不了多久就会举手投降了,他们在等着这一刻。连迷彩服们也坚信这一点,他们挥动着手中的铝管,并没有急于进攻,他们只是吓唬着小广西。那意思很明显,是想好好玩玩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就像猫戏弄老鼠一样。谁也没有料到小广西会作困兽之斗。小广西并不想这样收场,他的本意不是这样的,他只是想拿着刀来吓唬一下老板,现在的情况不妙,很可能是赔偿没要到反遭一顿暴打。他回头望了一眼,目光落在小玲子的身上,那是绝望的目光,可是大家都忽略了这一点。小广西往后退一步,突然用那没有手掌的胳膊拐在了小玲子的脖子上,手中的刀挥动着……李想目睹了这一切。他看见小广西的嘴在很迅速地一张一合,却不知道小广西在喊着什么。李想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仿佛有只硕大的爪子,一把揪住了他的心脏,如同揪住瓜蔓上的一个瓜,只要那爪子稍一用力,那瓜就要应声而落。李想的手揪着衣服的角,手心沁出了汗。李想并不为小玲子担心,他知道小广西不会伤害小玲子。他为小广西担心。他多想喊一声:“小广西,你别犯傻了,快把人放了,把刀放下。”然而他喊不出来。李想就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存够钱,没有早点去做手术。小广西劫持了人质,这一突变打乱了迷彩服们的阵脚,乱了一阵之后,警察就赶到了厂里。迷彩服开始把围观的工人往后撵。小广西早已劫持小玲子退到了一间空着的办公室,现在和警察僵持着。他手中有刀,有小玲子,刀就架在小玲子的脖子上。警察手中有枪。李想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真枪。厂门口停了那么多的车,车顶上还在闪着蓝色和红色的光。李想曾经是多么喜欢这些五颜六色的光啊,这是城市之光。乡村是属于白天的,乡村的夜晚漆黑一片,而城市不分白天和黑夜,都是那么的繁华、灿烂。李想在给母亲的信里,写下了他对城市夜晚的感受和热爱,写下了城市的灯光。现在,警车顶上闪动的灯光让李想不寒而栗。他仿佛看见一颗子弹穿过小广西的头颅,像穿过一个西瓜,小广西的头颅从中间爆开,空中飞溅着红的瓜瓤,黑的瓜子,他甚至闻到了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有警察上了楼顶,还有警察进了对面的楼里,他们手中的枪都指着一个方向,焦点就是小广西。只要他们的指头轻轻一扣,一切将无法挽回。李想多想冲上去告诉警察们,小广西是个好人,他不会伤害那个女工。可是警察把外面围得严严实实,他根本无法靠近。他想喊,喊不出声音,他找来了纸和笔,在纸上写:小广西是好人,你们不要开枪。可他的纸片无法递到警察的手中,就算递到了也不管用。他急了,一急就乱了方寸,冲警察拼命比划,可是没有人去理会他。一个警察手里举着喇叭,在对着小广西喊些什么。这样的场面一直在持续,从中午到了下午。负责指挥的警察朝楼顶上的警察们挥了挥手……李想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这时,太阳落到了五金厂厂房后面,天空在最后辉煌一下之后,迅速暗淡下去。太阳落下去了,第二天照常升起,如同李想的生活。李想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他的上铺又睡了新的工友,不过李想不再想交朋友了,他怕自己受不了那种心脏被摘除的痛。他不再与人交流,不再拿起纸和笔。每天的工作重复而单调。他的脸上再也看不见笑容。每天坐在冲床前,他的思绪依然飞得很远。思绪是天马行空的,像一条射线,他是射线的起点,另一端,伸向了无限的未知。打工的日子平淡如水,这一年,有一件事,对于李想来说尚可一提,他参加了由镇里组织的外来青工技能比武,凭借炉火纯青的冲压技术,获得了全镇第一名。当记者采访他,问他打算怎么花这一万元奖金时,他写道:“存起来。”记者问他存起来做什么用?他摇了摇头,没有回答。记者又问他有什么梦想,他在纸上认真地写道,“听鸟叫,听虫鸣。”写下这六个字的时候,李想突然泪流满面。一年后,李想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存够了植入人工耳蜗的钱,做完手术后的他,并没有回家去听鸟叫,听虫鸣。他得再存一些钱,未来的生活需要这些钱,生活远比听鸟叫虫鸣重要。他再次坐回到冲床前。车间里是震耳的噪音,噪音剧烈地冲击着他的耳蜗,这是他所未料想到的。他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十几年,记忆中,这里是那么的安宁,像梦一样。而现在,他的耳朵里被各种各样的噪音塞满了。他没有想到,冲床每冲击一下,会发出如此巨大的响声;他没有料到,电锯锯过铁片时,声音是这样的尖利刺耳。他的胃一阵阵地痉挛,想吐又吐不出来,蹲在冲床前一阵呕,终于呕出一摊绿幽幽的胆汁。李想咬着牙,重新坐在冲床前,努力调整好情绪,平静着心境。脚下轻轻一点电钮,冲床猛地抬了起来,差点把他的下巴削掉。他手握铁片,四顾茫然,怎么也不敢把铁片放进冲床的虎口里。这是李想所不能容忍的。好几分钟后,他鼓起了勇气,把铁片放进了冲床的铁掌上,脚尖轻轻点了一下那踩过千万次的脚踏开关。冲床巨大的铁掌结结实实地砸在了他的右手上。过了好一会,他才感觉到痛,他跳了起来,接着就蹲了下去,又跳了起来,身子像陀螺一样转着圈子,他的嘴不停地一张一合,像一条在岸上垂死挣扎的鱼。他脸上的肌肉在抽搐、扭曲,直到把身子扭成麻花状。
(选自《北京文学》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