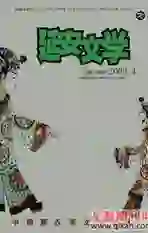纯粹个人主义与其世界的可能
2009-09-08卓青
卓 青
死亡与那个人
我坐在这里,在屏幕之前,随着键盘按键的起落,看着那字符一个个跃然而出,徐徐前行,也有时踟蹰不前。他们都来到此处,在这里展示出来,呈报上来,面目清晰可辨。以至于,这一切变得如此自然,如此顺手,他们亦以其源初的如其所是的方式展开于此,即他们被如此所用。
我们何以可以这样使用呢?我们何以可以如此的操持活动,或者他们何以可以这样来此呢?尽管这个问题不合时宜,因为这里不需要这个打断。他们本就是为……而来的,本就是用来……的,因此,我们能够这样做,可以在此与他们照面。当然,我们本就先行展开的,有所筹划的能够在此,由此也就可以先行于自身的,为了做……用而把他们引领至此。我们如此生活,我们可以如此生活。(我们何以……,我要按下W键,他就在手指之下,以至于我可以感到,我打算按下去,毫无疑问我可以这样做,而且我准备这样做。他就在这里,我甚至可以真切的接触到,在那里。我业已打算好了,你看,他可以这样被按下去,我完全可以设想这一图景。我想要……,但还没有。
那一刻仍未到来。我竟然可以这样做,我打算如此,而他竟然可以如此,我的手微微颤抖)我们何以可以这样生活?或者说,这一操劳活动是怎样发生的?我竟然可以使用他吗?我何以可以如此使他来到这个世界?不仅是那个物件,更重要的是我的身体。那发生了什么?他如何可以成为前来面对面的你?我怎样到那时候?毫无疑问,我,作为在此的我,必须取消这个问题,并且“能够”取消这个问题。我们何以可以这样做?因为我们先行于自身的打算如此,筹划了他们的有所作为。于是,我们确实做了。
这就是这个源初的盟约,这最初写下的字迹,以及后来者的替代,抹去了那消失的痕迹,也由此隐去了那神秘的力量。我们向着他们而去,向着那时而去,我们将要到那里。我们将死去。由此,我占有了我的死亡,占有了我的身体。在这里,曾经如是的存在,现在这样生存,并且将要死去的我,在这个世界中融为了整体,可以通过其死亡(出生)划定的,在世界中得以如此绽出的整体。正是在这个宣告之中,我可以,或者说,我如此这般的有所筹谋,于是就确实去做了。这一替代活动,亦即对那时,对死亡的占有,使得我获得了自由,成为了权力的主体,也就成为了这个人,成为了随时可以死去的这个人。它时刻纠缠于我,令我不得安宁。
在这个意义上,对他者的替代,这一有所指引的向着他而去,以种种方式反复补充那个出场,及其不可能,使我们的生活成为了可能。或者说,死亡,及其推迟出场,亦即推迟那个我想要-我确实有所作为的时刻,使得生存成为了可能,也就成为了不可能的可能。我们竟然可以活着?我们随时都(会)死去。
这一对死亡的占有,或者说对他者的召唤来此,以及由此而使得我作为有限的,有历史的,有着先验指向的,并可以以此方式消散于这个世界中的这个人,现代的人来临于此。因此,这个人天然的始终与肉体的控制,死亡-出生的控制相关联,我始终是权力的主体。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不难理解现代权力机构对死亡与生殖的关注,乃至于将关联与有限身体的再生产的活动赋予我的本真的意义。成为这个人,这是一个呼唤,亦是一条律令,公开的,不可违抗之律令,是构筑这个世界的约定,是那源初之书。也因此,这一呼唤不是在内的,而毋宁是在外的,是来自于良知的召唤。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成为其自身的本己的良知,成为这个人的崇高精神也就从未离开过那个可怕的魅影,那个从未在此也就无处无时不在的鬼魅,我不再是我的可能性。就好像在这公开于世上的,被指引来此照面的活动背后,玩弄的伎俩,隐匿在这一表面的连接,表面的结合之后的悄悄的搬移。谁在搬移?当然不是我。而是在这里滑脱开来的,滑过那一这个我的不可跨越的界线的,从这个躯体中脱离出来的,在其背后叨叨咕咕的,那个幽灵。正如同隐退到具体时空背景下的腐败行为。正是由于这一世界整体的构成,这一对他的占有的源初的不可能,使得这一阴谋行径始终不能避免,使得我们总有着离开这个主体,离开这个人的可能性。
而这一可能性的开端,就是那个结束——死亡。一切从我的死亡开始。
这注定是一起谋杀。必须谋害这个人,而又是不能公开的。这是在背后,在此地与彼处秘密谋划的阴谋,彼此不交一语,从无联络,仅仅暗地算计,悄悄窥视。因而,毫无征兆的,毫不引人注目的,他动手了。一切似乎都没有什么不同,或者本就没有“什么”改变,仅仅是这个世界,这个整体的世界与他的背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异。我死了,这是不可能的,我不可能死去,是作为他死去了。沙罗双树下,我之葬身之地,亦为他还魂之所。他在那里,消失于此,我的身体。那些古老的灵魂再次来临,在那面具之后。
这绝不是某种反抗。反抗将只能是某种不断自我指涉的替代,反抗将只会使新的出场占据他者。甚至这也不是违背,因为违背将会出现,将会公布于光天化日之下,并引来惩处。最终,这只能是一种背叛,是在背后的密谋,是在背后轻轻的拨弄,将那文字错动开来,亦即将那神秘的力量重新注入,让文字恢复他的魔力。于是,盟约似乎从未改变,但却全然不对,他成为了某种可以玩弄之物,一种伎俩。于是,他是也不是,在也不在,是这个意思却也不是,话中有话,弦外有音。这是一种僭越,通过杀死这个共同在此的世界中构筑起来的个人,在它的尸体之上瓜分权力,使得权力重新可以被拥有和使用,使得这个不同主体之间的生产制约关系瓦解开来,重新散落到那不可测度之地。
在这里,首要的原则即是无所作为。因为,这首先意味着有所作为的不可能。我本就不是为了什么而来的,而他更不可能是用来……的。因为死亡已经发生,不可能向着死而去。我们将他人的还给了他人,回到死亡之中,亦是让死亡归于死亡。于是,我来到这里,本就不打算如何,不过偶尔来这里看看,这不是寻视什么,不是向着某物而来,而是突然推门而入,亦不知悉他是否在此,正如他同样不知道我怎么会来。当然,我可以一时心血来潮,随即盘算着在这儿干点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附体行为,正如死灵重归。这就需要算计着他一些。不妨看一看程灵素的死,她要想到胡斐的思路,设想他的行为,由此安排妥当种种布置,而她死后,胡斐就按照她所构想的行动与思考。在这个意义上,程灵素来到胡斐的身上。而这种算计是把他当成他的,他不可能是为了……而来用的,我们得玩些心机。但是,我本不是来这里做这个的,只是偶然玩玩,这本不是我的所在之地,他亦本就是他。“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或者说,不要忘记这是一种虚拟的活动,我并非在此生存,并非生活操劳,而是在这里假装表演一下,还兴致勃勃的看看了自己的临时表演,这种戴面具的伪装成……。这始终是观看的,亦即做成一个样子,自己在后面看着玩,而绝不是要看到了并向着那去,因为那不过是偶一为之的游戏,并非真实的作为……而在。可以这样看着自己假装下去,甚至有某个终了,也可以随时抽身而去。
因为他本不是做……而向我来,我亦不负责任,仅仅是突然闯入,又匆匆离开,不去理会后果。但是,这虽是很有趣味的娱乐,切不可过分。这种快感的享用是需要节制的。决不可以无限制的尽情享乐。这也就需要与欲望的增殖相区分。尽管,这种欲望的流变同样意味着断裂,但那包含了可显现的差别,也就使得欲望爆发为个别的,在此的。或者说,欲望本就在于想要……,寻求……满足,因此是不足取的。这一我之死亡,这种无为,本就是超越为……,想要……而在。退出现场,退到那个隐秘之地,那个表象与表象间微妙勾结的,此与彼得相似与不同未曾分开之所。
在那里,在那个差异之源,我重新获得某种整体性,重重叠叠的相似性中不可还原的整体,不是可整体化的整体,不是将各部分连接起来的整体,而是间隔的整体,亦即距离的整体,我与他之间不存在的距离造成的不可跨越由此而成的整体。或者说是无边界的整体,就像有与无间的无边界。没有边界并不是无限,当然在这里也谈不到有限。
在这个无边界的整体意义上,我成为了那个人。
个人主义与社会
个人主义,看到最初的用法individulisme,就会联想起法兰西人高贵、挑剔与不安分。而我觉得并不是在颂扬个人的启蒙时代,恰恰是在大革命之后的浓重的保守氛围中,在开自四面八方的对个人的口诛笔伐中,个人主义才会显露其迷人的本色。诚如蒲鲁东所言,“在团体之外存在的只能是抽象的观念和幽灵”。那么这一幽灵何以是幽灵呢?因为他“像浮光掠影,来去匆匆”,使国家“土崩瓦解……最后在空中随风飘散”,于是“那就什么也不存在了,而仅仅是一团尘埃”。
个人之所以是个人,正在于他的飘忽不定,他的不可捉摸。我们谈论那个人,正是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他想什么,他会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他现在怎样、将会怎样,甚至由此而无法知道他曾经怎样,因为他不可预期,先前的种种猜测转瞬间就会碎裂成七零八落的片断。他未有预兆的跃入我们的视野,又莫名其妙的消失不见,这便是那个人,令我们忧烦不安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人成为了秩序与责任的敌人,他“所摧毁的恰恰是服从和责任的观念,从而也毁灭了权力和法律”。因此,纯粹的个人主义,绝对的个人主义正是要奠基于那个人,那种个人性。从而,拂去个人之上的种种在此之物,将那些使个人固定于此的各种在者剥离开去,或者说,个人由此逃逸出来,从那个躯壳中脱体而出,从那面甲之后隐去,堕入那幽暗的深渊。于是,那个幽灵便可以在这个井然有序的表象体系中来去自如,穿行于诸种符号划定的界线。那个人由此而回到了源头,回到了差异之源,回到了各种现场的遥远的绝对过去,在那里,他将权力与秩序玩弄于股掌之间。
毫无疑问,这一纯粹的个人主义将是区别于以往的在各个不同方向上展开的个人主义。首要的就是与自主的,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个性的相区分,也就是要与自由主义,或者说是与现代自由民主政治中的社会主体相区分。当然,这一现代化的过程,确实使个人摆脱旧有的家族、阶层的关联,从那个超越于个人的并使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长长的链条中解脱出来,这种松动,或者说疏远,无疑是一切个人主义的前提。事实上,在那种具体时空背景之下的环环相扣的人际联系所勾连铸就的我消散于遥相呼应的相似之中,根本还没有非我。然而,现代权力体系对此的瓦解与替代,却也抹去了人际网络中那末可名状的奇妙波动,那源于个人的突如其来的改变,代之以可以展现出来的个体差异。由此,个人的行为变得连贯而可预期,其行动与言谈通过有所差别而被整合至话语体系之中。作为这一整合的成果,个性,有个性的个人,被纳入到整个可彼此区分,又可相互对比联系的个人的差异序列之中,以至于,有个性可以成为生产与消费的环节,一如消费某种个性。在此基础之上,这个有限的,有所指向的人被构筑起来,他占有起身体与灵魂,最终,通过权力,通过在其经验世界中指向某个先验的末世论结局而连为一体。
因此,我们反对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尤其要反对存在主义的个人主义,必须从那个差异序列,那个权力-话语体系中解脱出来。这不是打破或者颠覆,更加不是解放,甚至与此相反,这种撤出与放弃,或者说归还他者,正是一种保守行为。放弃这种自主,放弃这种自我实现,亦即放弃这个我,也因此而得以从这个确实在场的个人中解脱出来,结束这种自我指向,也就结束这种向着那个他者边界的指向。让他人的归于他人。所谓个人,也就不会再负担这一先行展开的有所指向的能在,也就不再负担这个人的意义,不再受这一本己的良知的限制,那一呼唤不过是他人的呢喃,可听可不听。于是,那个死了的人,那个幽灵,飘游于这个世界,或者说到此一游,他在那面具上,在这个散落成碎片世界上,在那些规则、符号之间,与他人,与他的身体有着微妙的关系。我隐匿在那里,在那界线之外,在来来往往的表象后悠然的指手画脚,或是装成某个样子忽然出现,再转身离去。我不再有个性,而是成为那个性,那可展现的彼此不同的个性之源。那个私密之地,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隐私。他无所不在,也就本不存在,而是在那些可以公开划定的框架背后的不可告人的隐秘,而当我厌腻了某一算计,他也就被随手抹去了。在那里,我成为那个人,纯粹的个人。
个人,从其最初意义上,就是无所凭依的,亦即是无处可归的,他难以找到他的来源,他的根本。正因如此,个人不能在此,不能在何处,而是于此世界中无处不在,便如那幢幢鬼影,此隐彼现。由此,那个人也就不是这“一个”人,这一形式上的矛盾正提示我们所谓自我选择,这一自我固定行为的不可能,分延运动的显现的不可能。这一不可能正是个人源初的不自由,即为不自由的自由。这一自由的达成正是来自于脱离开有所作为,“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在那个人身上,我们隐隐窥到了古代贵族的身影,不错,这一戏剧化的死亡仪式,也正是某种降神会,他召唤那些高贵的灵魂重临人间。他使得我们借以摆脱现代社会庸俗的个体,重新凌驾于轰然做响的国家机器之上;仿佛倒退回律令飘浮不定的时代,贵族们优雅而轻巧的玩弄手中的权柄。但不要忘记,这是一种伪装,我们并非为此而来,或者说,这些幽灵并没有占有其身体,并没有合成为一个确实在场的活生生的人,而是潜于其后观看这种游乐,因此,完全没必要担心“真正”的冲突会发生,这是虚拟的真实。
正是借助于这双重的退出,这双重的解除责任与意义,往来于高贵的往昔与自由的现代,我们也就有了实现高贵的同质化的可能。死亡本就意味着终了,我们有理由希望这个终了对于社会仍旧成立,最不可捉摸的也就是难以改变的,充满愉悦的寂寥结局,或者说“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当然,这其实是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一同死去,世界将会怎样呢?而回答将是:这一切都会不同,或者说什么也没有改变,那是笼罩在一切如常上的难以言明的变化。
不妨想象一下,你与我在BBS上发生一次争执,而不幸的是(或者是幸运的?)由于设备故障,这部分数据损毁。于是我们发现,大可以再重复一下那次争执。重复,再次出现,重新作为,这里隐含了两重意思。一方面,它意味着从现场撤出,也就是我们并不在当时当地,我们并非作为争吵的双方来到这里,我们并非在此时此地为了某个分歧而即时的展开文字表达。我们不是当时的争吵者,也同样不是现在的。因为当时已经过去,我们并非为了争执而来,然而,现在只是那时的复制,并非“真正的”,而是装作那时。因此,我可以看着“自己”,从背后看着这一装模作样的行径,看得出那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另一方面,这一重复有着它所不曾包含的预
先的共谋,我们私下约定,如此再来一次。这一私地里的阴谋,使得引经据典、义正词严的争执不知怎么,不那么对味儿。尽管依旧唇枪舌剑,尽管仍然似乎是在将某一论题下将双方纳入到共同公开的概念体系之中,似乎试图逼近那真实的目标。然而,在符号的往来间,我们暗自递个眼神,相视一笑,心领神会,心中暗想我明白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在这里,你成了他,那个人,那个在堂而皇之的文本编织与符号指涉间,窥探、揣度、算计的那个人,他者。在这宏大的话语构架之下,我们拨弄着手中的规则、条款,做出各种优雅的姿态,借以遥望对方隐去的身形,暗自领会他的想法。这即是高贵者的游戏,从各个不同的个体以及它们不同的部分的连接、指示所构筑的庞然大物中解脱出来,凌驾于其上的僭越者的娱乐活动。我们如此的不同,以至于不知道究竟有何不同,这是不可出现的差异,不可展示的差异,不能够通过在某个概念序列中定位的方式出现的差异,或曰源初的差异,亦即不“是”差异。于是,我们不得不与差异告别。我们是“同样”的。我们并非真的是两个人,两个有着各自目的,并由此驱使自己展开暗地争夺的人。我们仅仅是亡灵,借尸还魂,装成这个样子来次游戏,还津津有味的欣赏这个临时的表演。这个重复的争执在双重意义上成为了虚拟的,既是你我之间预谋的虚拟,也是各自与其身体媾和的虚拟。
在这个亡灵之宴上,我们身着礼服,面带微笑,频频举杯,互致问候。仿佛世界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