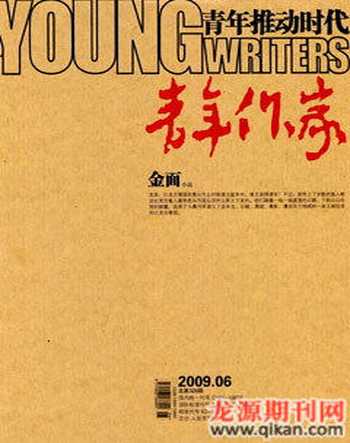中国女性文学与西方女性文学批评
2009-04-29李丽琴
李丽琴
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哲学思辩的文学批评理论,是因为中国文化观念中儒学思想对文本的“言志”和“载道”的习惯严重影响了文学批评理论的构建和发展,在客观的现实处境下,借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结合中国文化特质研究中国文学是自然并合理的,应当秉承科学的、公正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之与中国文学的联姻。自19世纪末起,中国的文学理论业已受到西方的支配与影响,因此更应该考虑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中所蕴含的西方文学理论基础。在中国文学批评的实践中,特别是从较为广泛的(国际性)观点研究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批评家将无法满足于仅是采用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为其批评架构的做法。中西文学批评的概念、方法和标准的融合,因而成为必要的工作。西方的文学理论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思辨色彩,既是哲学的,美学的,也是历史和文化的。而中国文学理论的立场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封建社会所致),政治的专制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文学。
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寻找女性”和“构建女性文学传统”一直是重要的主题,尽管发掘和寻找的方式、途径有所不同。按照英美女性主义学派的设想,文学史中隐含着一个明确的女性传统,只是被男性文学史遮盖了,这有待女性主义批评来发掘。因此,英美女性主义学派大力挖掘湮没在历史中的女性作品,重新把遭受忽视成刻意封杀的女性作家加以重新定位,重建女性文学史,并在挖掘到的历史材料中寻找女性传统,为女性传统提供大量的证据。英美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历史中寻找“显性”(visible)的女性时,法国学派则力图在潜意识中寻找“隐性”(invisible)的女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论从历史中寻找女性(注重压迫观点),或从(集体)潜意识申寻找女性(注重抑制观点),两者都和父权压抑有密切的关系,两种压制概念皆归为父权体制中范畴较为广大的总体压抑。把这种总体压抑范畴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是张爱玲,她把这个一体两面的问题——历史/潜意识的,显性/隐性的——切入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表达了最为真实的女性经验。
中国文学文本和西方论述这两者之间,存有接受、排斥和互动的关系。大体而言,在现代文学批评界里,中国文学批评和批评理论至今仍难以摆脱西方“话语”或“论述”(discomse)的影响,难以走出西方话语的“他者”的理论阴影。在批评理论问题上,阅读中国士性文学(张爱玲文本)也面对着另一个有关中国论述的主体危机。基本上。笔者致力于建构自身话语的主体性,但在中国整体论述条件的不足之下,尤其在中国自身女性主义理论的匮乏之下,而不得不借助西方女性主义理论(Western Feminist Theories)的观点。这表示说,除了西方传统男性话语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支配之外,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介入,亦使中国如胜主义文学批评同样面对主体摇摆的危机。换言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西方话语中的他者位置,同样亦落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里。在父权社会中,女性被界定为他者,并为男性主体所观照。相对于他者,男性则占据主体位置,是完整绝对的象征体。在中国的宗法父权社会里,女性在“天”、“阳”、“乾”、“君”、“父”等宗法象征主体下,即被定义为附属于男性的他者概念之下。倘若中国(男性)文学是西方论述中的他者,则中国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学批评中便是他者之他者。
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不但必须解构当代西方男性话语和女性主义理论,亦有必要化解中国本身强大的、男性中心的(androcentric)批评传统,才不至于在中国自身的女}生主义文学批评中,落在他者之他者的处境中。在中国文学的阅读上,无须完全套用西方的模式来评论中国女}生文本。但即使如此,也不可忽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其批评实践中所发展出来的女性论述架构,以及透过女性经验的研究所建构的新论述模式。
笔者将中国传统宗法父权话语下的封建礼教: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尊阳贬阴,以至“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宗法训示,视为宗法父权话语的总体压抑机制。这里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出发,试图建构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以女性为主体的女性论述。
1隐性的中国女性文学
中国先秦时期人们阅读文学作品开始偏重于好坏、美丑、爱憎等方面的直感判断。这种直观评论可以说是中国文学评论的萌芽。春秋战国时期,《诗经》出现,孔子从文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提出了“兴、观、群、怨”说,从作家道德修养方面又提出“文德”说。后来孟子总结了中国初期的文学批评经验。提出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批评原则。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批评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唐宋以后,文学批评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诗话、词话、典话,以及对小说、戏曲的评点、漫评、杂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特色。到了现代以后,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很大程度受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的文学批评,都具有强烈而鲜明的阶级意识,因而使文学批评带上明显的思想理论斗争性质和社会批评性质。另外,中国的女性由于社会自然分工的原因客观地遭到男性的统治,加上人为的权利配置——严格的父家长制,完备的宗法专制主义使中国女性陷入了长达几千年的无人格状态。男性控制了社会的、政治的、艺术的话语的绝对权利,历史上几乎没有女人的声音,更谈不上女性文学、女性文学史及女性文学理论的建立。
中国女性的文学创作活动,曾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形态和宗法制文化的背景之下,妇女传统的生存方式给文学创作带来极大影响。尽管确有一些女子在创作中发出过自己的人生之怨、不平之鸣,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女性的情感愿望,但从总体上说,由于妇女丧失了人格上的独立,困守于家庭和儒教,其创作在内容的审美价值取向、艺术表现的方式、手法乃至具体文学体裁的选择运用上,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男性话语权利设置的局限性。就其实质而言,古代妇女文学只能是作为男性文学创作的附庸而存在。
传统妇女文学的作者,大致由女皇后妃、女官宫娥、名媛闺秀、娼尼婢妾等阶层的女性构成,其作品所包容的生活空间、思维空间以及心理空间和她们创作主题所表现的,主要是妇女在宫墙、闺阁、庭院等狭小圈子之内的个人隋感,如离别之J限、遭弃之怨、寡居之悲、相思乏情,以及风花雪月引发的种种思绪等。人所可能具有的丰富的社会实践、深广的生命意识被扼杀,代之以与身边生活直接相关的个人情感,文学主题显示出很强的私人性与封闭性。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女性文学虽具有自身的特点,但始终是从属于这一文学系统。它没有形成独立的女性文学体系,没有建构起完善的女性群主义
文学理论。与西方女性文学不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是在较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的历史际遇中发生发展起来的。西方进步思潮的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发,使之从诞生之日起就同时代和社会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长期从属于民主的、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
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很多时候恰恰是女作家的创作率先引导了某一阶段文学潮流的转换或更新。例如现代文学30年间, “五四”时期冰心创作的“问题小说”:新时期初年舒婷为“人”的生命和女性价值讴歌的朦胧诗;刘真、茹志鹃的“反思小说”;八十年代中叶刘索拉、残雪等充满现代意识的“先锋文学”以及稍后方方、池莉等表现平民日常生活、心理情绪的“新写实”小说;再到九十年代陈染、林白“私人生活”主题的创作等。尽管女性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存在,但并末构成相对独立的文学运动。
在“五四”女作家个性解放的呼唤中,萌生了女性主题的幼芽。此类主题主要关注的是现代社会里女性基于性别特征所进行的社会实践、精神实践以及在其中的身心体验。然而,随着时代形势的急遽变化,这一主题未待很好地发育便很快被多数创作者所搁弃,取而代之的是带有强烈政治性、阶级性、民族性的创作。这种状况延续数十年,直到新时期以后才逐步改观。其中,批判封建传统和“左”的政治思潮对女性的压迫、扭曲和异化,寻求女性自我价值,可谓强音。然而,这显然并非女性文学“最后的停泊地”。人们很快意识到,此类创作实际上更多的依然是出自于社会视角,没有把文学视为对如-生生活和体验的再现。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在时代的变迁中,年轻一代女作家的性别意识进一步自觉,她们更强烈地追求女性精神的自由和女性生命的舒展,部分创作开始更多地向女性人生倾斜,注重从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出发,表现女性与社会、女性与他人、女性与自身以及女性与自然诸方面的关系。其中一些作品自觉地选择了向男性中心文化挑战的姿态,表现出鲜明而强烈的女性意识、女性情感。这类创作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也引发了种种争议。
女性主题显示的女性文学特色及价值,不仅在于它拥有女性观察生活、表现自身所特有的视点、角度以及鲜活生动的生存感受、内心体验。更为本质的是它源于女性生命本体、无形中打上了性别烙印的世界观、人生观。实事求是地说,女性主题绝非仅限于展露和宣泄在父系文化圈中女性所承受的性别压抑,包括生存压抑、心理压抑、性爱压抑和情感压抑等,而是同时显示了女性在认识自我、理解社会方面所达到的深度以及所面临的困惑,其中蕴合的女性自审意识和批判精神尤具现代意味。此类主题的作品生动记录了时代女性的精神成长,在文学创作中的士性思维方式、女性生存本相、如}生情感特征、女性生命感受和女性审美情趣等。当然,在历史发展现阶段仍处于男性中心文化特定语境的情况下,女性文学处境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带有“宿命”意味的,因为女性解放的程度任何时候都势必受制于历史发展的水平,同步于“人”解放的程度。尽管在具体的女性创作中,作家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策略选择,但从总体格局上看,女性文学的发展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几乎是无可避免地要面临植根于男性历史文化的悖论,它制造着女性文学发展的困境。“五四”运动中萌发的现代女性意识,还未来得及进行对女}生意识的审视与自醒,就被卷入了三四十年代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洪流中,而这个时代的女作家更多地表现出阶级的、政治的阳性关怀。
新文学中的现代革命女性形象在现实中能不能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人格和身份是令人怀疑的。实际上,革命女性形象的出现是一种匮乏自我的虚假论述,这正好以反证的模式呈现出女性在现实中的边缘化处境,足以构成女性作家的重大书写危机:失去女性自我的定位。使女性文学陷入了“男性中心论”(androcentrism)中,掉入男性模拟的死角,无法扮演真实的女性角色。在文学世界里,无论女性形象如何崇高、革新、独立,一旦落到现实中,广大女性依旧面临强大的压抑性命运。文学世界中的愿望在现实中宣告破灭,阳化女}生的面具不攻自破,女性的匮乏再度浮现。文化上习得的“女性”特征(被动性等)被看作是“自然”属性,女人同男人一样会使这些态度永久化,而在控制与从属的不平等与压抑关系中扮演这些性角色,以男性理论作为批评视角的评论把女性角色及其经验加以歪曲,从女性文本挖掘到的仍是男性观点下的女性。肖沃尔特指出父权批评下的女性典型的僵化形象其实就是父系意识形态下的女性假象,而非女性真正的经验与现实。
当二十世纪前半叶女性作家不惜戴着乐观的面具在文本的舞台上扮演阳化角色时,现代文学批评在追问:文本中有女性吗?文学史中有女性作家吗?张爱玲用她的书写模式充分表现了不屑于塑造虚假阳化女性人物的心态。她关注妇女在现实中的状况与女性受压迫的历史,既着眼于文化与历史分析,也着眼于女性经验的写作。在张爱玲的文本中,这些问题可望找到一种可供诠释的版本。她在《自己的文章》中说,即使像白流苏这样的女性,亦没有性别错位的意味:
《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回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张爱玲,173)
从文学史角度来看,五四之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涌现,无疑在某种层面上阐述了女性在历史、文化、社会中,有关两性与政治、个人与整体角色的互动关系。但是,那时期的女性文学大体上还没有较为稳定的女性文学传统,或者说,这方面的女性文学传统还有待进一步加以建构。而在张爱玲文本中所隐含的女性主题、女性亚文化群体及女性话语,所触及的中国总体父权压抑问题,以及在此压抑机制下有关如-生u禹身份、性别认同或两性差异等问题,正是今日从总体压抑范畴挖掘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女性经验(历史/潜意识的,显性/隐性的)来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关键而重要资料。张爱玲的女性经验模式以及在小说中所体现的文化素质,乃是以一种失序、疏离、丑怪、焦虑的面貌,去推演历史文化中的压抑和疯狂等女性问题。讲述了传统女性在宗法父权制中的边缘感受,一种“阴性荒凉”的情境。
2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强音
西方强烈的宗教信仰传统使女性在受压迫和主宰的同时清醒地意识到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迫切需要,因此,西方妇女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成为必然。伴随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女性文学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关注妇女作为读者或作者在文学话语中的体验,关注妇女作家的地位,妇女文学经
典的构成,小说中女性的形象,男女体验的差异等问题,也注重妇女的平等、独立和自主问题,一般具有较强的政治性,是一种具有强烈思想道德倾向的批评。当然,也有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关注文本的艺术性,
以玛丽·伊格尔顿(Mary Eafleton)编选的读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1991)面世作为界点,过去25年来,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出色地表现了矛盾、交流和争论。的确,它建立在一系列创造性的对立、批评与反批评基础上,呈现出一个不断创新的流派——它挑战、颠覆、拓展的不仅是其他(男性的)理论,而且也有它自己内部的种种立场和问题因此,在它的范围内没有“宏大叙述”,只有许多“小叙述”(petists re cits),这些小叙述立足于特定的文化政治需要和阵地——例如阶级的、性别的、种族的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竞争。这表现了西方现代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创造性地“开放”的动力,同时也表现了这个胎生的、多样的、自我争论不休的领域的某种困难。其具有竞争力的种种优点及其内部的争论,有着广大的多元性,里面滋生着各色“理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种开放与兼容的态度正是中国学者在看待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时应当秉承的态度,
随着中国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表现空前活跃、各种现代思潮纷纷涌进并发生影响的大环境中,在世界文学潮流融会渗透的文坛背景下,女性文学主题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具有现代意味的拓展但事实上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萌发、生长,又不能不受到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直接影响:一方面,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妇女解放始终没有单独地从“五四”时期“人的解放”以及其后的社会解放和阶级解放的大题目中提出来加以考虑,而是总被后者所遮蔽乃至淹没: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原因,整个中国社会人之个性意识的生长曾长期受到贬抑,正因为如此,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成长历程曲折而艰难。很多时候,女性意识实际上被忽略,甚或被消融于民族意识、阶级意识和社会意识之中。与此紧密相连,由社会运动中崛起并发展的女性文学,一直在“人的自觉”和“女性的自觉”相碰撞、相交融中起伏演变
整体而言,中国文学透过西方论述的“镜子”媒介,能否准确映照自身的实体,抑或只是西方主体的投射,一直是个争论的问题然而,这里面对的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问题语言、文化、文学和意识形态的互涉性,在某种层面的表现往往是惊人的。在中国论述迈向自主的建构历程中,虽然还有很多细节问题有待克服与消解,但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匮乏中,以及西方论述在国际学术市场上的强势渗透之下,适当地转化西方论述的资源,作为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主体性的手段,仍旧是当代文学批评发展的重要趋势。
结语
正是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中国女性缺失了女权思想的根基,尽管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是在较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的历史际遇中发生发展起来的,但它很大程度受到西方思潮的推动,没有自觉的女权意识,甚至长期从属于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因而中国女性文学不可能像西方女性文学那样形成自己一系列呈现挑战、颠覆、拓展男性的理论,和它自己内部的种种立场和问题。因此,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借用西方女性文学理论成为客观事实。面对中国女性文学在传统文学史中的荒凉处境,笔者试图阐释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中国女性文学的现实和微妙的关系来演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本土化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