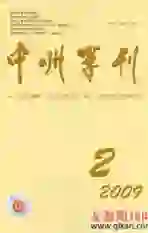略论汉代循吏和酷吏的治政策略
2009-04-14陈金花
陈金花
摘要:从治政策略来看,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汉代循吏崇尚德治,以仁爱教化治民,以化人心为务,治理效果显著,深得民心;受法家思想影响的汉代酷吏则崇尚刑法,以严刑峻法治民,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无法赢得民众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循吏的德治和酷吏的法治在实践中都有不足之处,因此最有效的治政策略是德刑相济,将道德和法律两者结合作为统治手段。
关键词:汉代;循吏;酷吏
中图分类号:K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2-0177-03
就治政策略而论,汉代官吏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循吏,他们崇尚德治,以仁爱教化治民;另一种是深受法家思想影响的酷吏,他们专任刑法,以严刑峻法治民。成帝时期,陈留太守薛宣在答吏职时说“吏道以法令为师”,琅邪太守朱博也说过“如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由此可知,汉代对“吏”的基本要求是执行法令,礼乐教化并不在吏的法定的权限之内。不过,汉代朝廷并不反对官吏推行礼乐教化的行为,因此是成为仁爱教化的循吏,还是成为严刑峻法的酷吏,可由各人的思想和性格来决定,这两种官吏在治政策略和治理效果上都存在很多差异。
一
汉代循吏往往与儒家经典有很深的渊源,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如文翁精通《春秋》;龚遂、召信臣、刘宠都是以明经入仕;任延、仇览都曾在太学学习经书,12岁的任延由于表现突出,有“任圣童”之誉。儒家治国的主要手段是德和礼,汉代循吏崇尚德治、重视教化的治政策略鲜明地体现出儒家的德政思想。
汉代循吏重视教化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景帝时期的文翁就是一个典型人物。他为蜀郡守时,建立学官,并采取措施鼓励学官弟子,“由是大化……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通过学校教育来推行教化的做法不仅得到武帝认同,而且在全国推广实行,由此可见文化对政治的影响。再如光武帝时的桂阳太守卫飒“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来教育“不知礼则”的民众,结果是期年间,邦俗从化……视事十年,郡内清理;平帝时的交阯太守锡光和光武帝时的九真太守任延则以移风易俗著称,他们“教导民夷,渐以礼义……领南华风,始于二守”。当然,史书对儒家的教化作用未免有夸大之嫌,但是却真实地反映了汉代循吏重视教化的事实。
汉代循吏不仅重视对人们进行礼乐教化,而且亲身实践儒家这种以德化民的思想,效果显著。如东汉的鲁恭、吴祐、刘宽等循吏是“并以仁信笃诚,使人不欺”。汉代循吏身上还具有强烈的自责意识。如韩延寿为左冯翊时,有兄弟为田产争讼,他自责“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于是“人卧传舍,闭閤思过”,直到他们悔过息讼为止。许荆为桂阳太守时,蒋均兄弟为财产争讼,他认为“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于是“使吏上书陈状,乞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韩延寿、许荆的自责行为带有感化他人、促使他人反思的因素,因而它既是对个人道德修养的严格要求,也是一种以德化人的统治方法。相信民众的道德自觉,也是德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循吏在这方面也不乏其例。如宣帝时,渤海由于灾荒“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新任太守龚遂就“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鉏鉤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无得问,持兵者乃为盗贼……盗贼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龚遂相信盗贼是为饥饿所迫,并不是甘心为盗,具有德化的基础,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做良民就既往不咎,这显然是运用儒家的德治之术来治盗,与酷吏严酷诛杀盗贼的方法截然不同。
由于循吏崇尚德治教化,力求以德服人,不尚刑法,所以深受吏民的拥护和爱戴,他们往往视循吏如同父母,宣帝时的南阳太守召信臣被称为“召父”、光武帝时的南阳太守杜诗号为“杜母”就是明证。汉代吏民对循吏的爱戴主要表现在为他们立祠祭祀和立碑颂德方面,如西汉的蜀郡守文翁、南阳太守召信臣,东汉的洛阳令王涣、桂阳太守许荆等循吏逝世后,吏民都为他们“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东汉的须昌长章翊则是“化有异政,吏人生为立碑”。吏民送别离任循吏的感人场面也体现出他们的深得民心,如合浦太守孟尝离任时,“吏民攀车请之,尝既不得进,乃载乡民船夜遁去”;东平陵令刘宠离开时,百姓“将送塞道,车不得进,乃轻服遁归”。这些记载足以表明,民众对循吏有浓郁的亲近感和认同感,这是因为循吏能够用仁爱教化治民,所以才能够如此得人心。
二
从酷吏的出身和所受的文化教育可以得知,酷吏往往很少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如义纵少年时“尝与张次公俱攻剽为群盗”,王温舒“少时椎埋为奸”。二人都是强盗出身;张汤、杜周则是由文墨小吏起家,这些酷吏都是极少涉及儒家经典。与循吏的崇尚儒学不同,酷吏大多喜欢法家思想,这也与他们的性格特点有关。如酷吏阳球“性严厉,好申韩之学”;樊哗“政严猛,好申韩法”。有些酷吏虽然学了儒家经典,但从政时并没有将儒家的德政思想付诸实施,如黄昌既熟悉经学,又通晓文法,为宛令时“政尚严猛,好发奸伏”;李章“习《严氏春秋》,经明教授”。他为千乘太守时,却因为诛杀盗贼过滥而被免官,他们的统治方法都是源于尚刑的法家思想。
法家极为强调法的重要性,主张以法治国。这种崇尚法令的思想被汉代酷吏所继承,其治政策略是专任刑法,以杀伐为治,因此执法严酷可以说是所有酷吏的共同特点。如王温舒是“奸猾穷治,大抵尽糜烂狱中,行论无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樊晔也是“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狱”。显而易见,酷吏是用严酷的刑罚来维持封建统治,是统治者严酷统治的最得力执行者。阳球向汉灵帝请求继续担任司隶校尉时说“臣无清高之行,横蒙鹰犬之任……愿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鸱枭,各服其辜”;周糸亏也认为臣事君,“见无礼于君者,诛之如鹰鹊之逐鸟雀”。“鹰犬之任”形象地道出酷吏用严刑峻法忠心耿耿地捍卫皇室统治的特点和作用。关于酷吏的治理之效,史书记载颇多,如义纵为河内都尉,“至则族灭其豪穰氏之属,河内道不拾遗”;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时,“郡中毋声,毋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严延年为河南太守时,“豪强胁息,野无行盗,威震旁郡”。这种猛政所带来的治理效果自然为皇帝所赏识,虽然酷吏有时因过于严酷而免官,但是由于治理有功效,仍会有进用的机会。
由于执法严酷,民众对酷吏极为畏惧。如义纵为定襄太守时,一日就报杀400多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尹赏为执金吾时,“三辅吏民甚畏之”;王吉任沛相时,“郡中惴恐,莫敢自保”。从“不寒而栗”、“甚畏”、“惴恐”等词语中不难看出人们对酷吏的畏惧之情。这种极端的畏惧感不可能使民众去爱戴酷吏,相反,他们往往对酷吏怀有仇恨情绪,如淮阳都尉尹齐“所诛灭甚多,及死,仇家欲烧其尸”。显然,酷吏缺少民众对于他们的亲近感与认同感,这也是酷吏和循吏的一个区别。
三
如果说酷吏专任刑法、否定德治教化的治政策略已经存在先天不足的话,那么由于人为因素所导致的执法不公更是强化了这种治政策略的弊端。有些生性残忍的酷吏在执法时“以暴理奸,倚疾邪之公直,济忍苛之虐情”,甚至堕落为草菅人命之官,如王吉为沛相五年,竟然斩杀万余人。还有些酷吏在执法时不依常法。如张汤、杜周是视皇帝的意愿来审案,“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周阳由是视自己的好恶来理案,“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严延年则是视犯人的身份而断案,“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内之”。作为判决依据的刑法成为酷吏可以随意屈伸的工具,刑法已经失去其客观性和公正性,带有更多的主观性,这必然会导致执法不公,并不是真正的以法为治。治政策略本身的缺陷和实施过程中的偏颇,决定了酷吏的治理效果必然是“猛既穷矣,而犹或未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与酷吏的严刑峻法相比,循吏德治教化的治政策略更具有优越性,可是德治教化并不是万能的,因为现实社会中必然有不能被道德感化、不遵礼教的人,对于这些人,纯任德政便显得软弱无力,因此就有必要用刑法来惩治他们,儒家所追求的德治之世只能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事实上,德治教化虽然是循吏的显著特征,但是汉代有些循吏也运用刑法。如颍川太守黄霸就是“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其治理效果是“道不拾遗……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郷于教化”;武威太守任延既重视礼乐教化,又敢于诛杀豪吏,为民除害,如“将兵长史田绀,郡之大姓,其子弟宾客为人暴害。延收绀系之,父子宾客伏法者五六人。绀少子尚乃聚会轻薄数百人,自号将军,夜来攻郡。延即发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内,吏民累息”;洛阳令王涣也是“以平正居身,得宽猛之宜”。同样是运用刑法,酷吏是视刑法为第一,循吏则是视刑法为教化的辅助手段,他们首先对民众施以仁爱教化,在德治教化无效的情况下,再用刑法予以惩治。
历史以雄辩的事实说明,纯任德政或专任刑法都存在着不足之处,因而都不是完美的治政策略,最有效的统治方法应该是将道德与法律、德治和法治有机地结合起来,二者缺一不可。其实强调严刑峻法的韩非并未完全否定道德的力量,主张“誉辅其赏,毁随其罚”,提倡用道德力量辅助法制的推行。儒家也没有否认政令刑罚的作用,孔子就主张治民要宽猛相济,认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所以要把教化和刑法两者结合作为统治手段,并不否定猛政。黄霸、任延和王涣就成功运用了这种宽猛相济、德刑相资的治政策略,这种统治方法当然比纯任德政或专任刑法有效得多,所以他们任职期间政绩卓著。实践证明,这种治政策略更为完善,也更为成功,值得后人借鉴。
责任编辑:何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