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愿以无涯之学 度有涯之生
2009-04-09刘明清
刘明清
“……大陆学界兴起一阵陈寅恪热,很多人感叹像这样的人物现在的时代很难再出现了。去年底钱钟书仙逝,同样的感叹再次发出。但现在有了钱文忠这样的青年才俊,顿时令人觉得中国学界还是有希望的。”
2007年,《百家讲坛》被评为年度中国最具网络影响力的央视十大栏目之一,巧的是,在那年年底,钱文忠先生开讲《玄奘西游记》,直到今年春节开始热播的《钱文忠解读<三字经>》,居然已经是先生第四次登上百家讲坛了。
第一次见到先生是在今年2月,杂志要做一期有关作家的专题,碰巧他在北京刚刚做完其讲座的同名图书——《钱文忠解读<三字经>》的签售,辗转中联络到先生,也才有幸做得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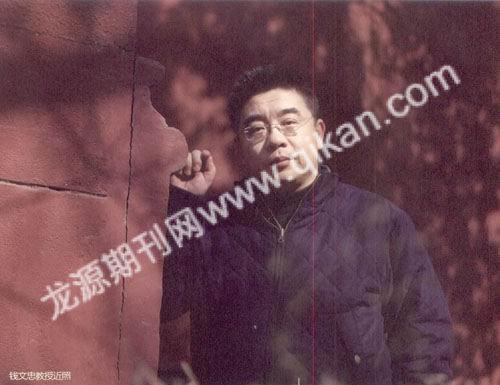
访谈的个把小时很快过去,先生只着随意一件墨绿色长袖抓绒T恤见客,却是风趣之外平添的几分亲和:从最近出版的新书,到自己的老师季羡林,再到对一支老式橡皮头铅笔的情有独钟,先生柴米油盐生活中的状态,开始在镁光灯的围攻下清晰起来。
其书: 有心
早在访谈之前便细细看过《解读<三字经>》,最直观的感触即是用心:上到编辑加工下到印刷,无论装帧或校对,信手拈来的,都是出版社之于作者、读者的责任。从先生口中得知,考虑到《三字经》这一启蒙学题材,因更偏重于对孩童的接触认知,在印刷和出版上不仅采用优质纸张,更添加某些词条的基本义校注,为的是“尽量做到准确无误的解释。”先生如是说。
新书上市不过短短三周,随之而来的,便是喜忧参半的媒体围攻—— 一边是蝉联畅销书榜首的捷报,一边则是针对图书提出的众多质疑,“《三字经》里所谓三纲五常的迂腐陈旧思想,对于当代中国还有什么值得借鉴?”“难道解读仅仅是对于《三字经》的字面解释?”……质疑层出不穷,矛头直指先生和他所解读的《三字经》。
让笔者略感意外的,是先生面对四方批评时足够的宽容,“我更感谢这些愿意说出自己对于传统经典真正想法的读者和观众,正是他们的存在才让我的讲解有了意义,也才让《百家讲坛》能够有力量越做越精确。”先生说这番话时上身略略前探,加倍的专注,让人无法不去相信眼前一个正备受争议的人物,发自心底的真诚。
“《三字经》小时候背过,现在讲授时拿起来重读,的确有些个人感悟。但千万请别以为我讲它是在做启蒙者,其实我是在和大家一起,接受再启蒙。我们中国人普遍对这本童蒙读物的看法太轻率了,以为它就是给小孩子的,大了还读它干什么。这是误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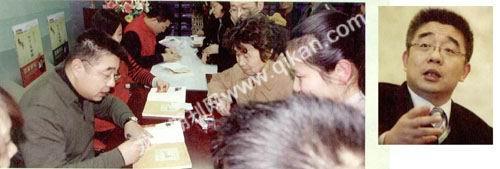
就在先生说完这番话时,突然想起去年10月那场轰轰烈烈的“莎士比亚戏剧季”,参演的8部莎剧,仅3部来自异域,却以最忠实原著的精准表演,还原了戏剧最原始的美感。这其实和百家讲坛策划的一系列经典阐释的节目相类似,我们总是热衷于对形式的翻新和对观念的探究,往往是适得其反,忽略了对于文本的理解,甚至熟知,而逐字逐句建立起我们对于经典的重新认识,钱文忠其实走在了前端。
其人: 有趣
先生研究的梵文巴利文方向虽说冷僻,也极少碰到能在同一语境酣畅对话的人,这却练就了先生健谈、风趣和极富亲和力的真性情,他能在早上和头头脑脑的领导们正襟危坐,照样也能在晚上和相识多年的老友下水摸鱼,外在的皮囊虽然多变,但未曾改变的是先生对于新鲜事物始终保持的童贞般的好奇心。
比起时尚、博学和富有,我更倾向于用有趣来形容眼前的先生,采访进行到一半,先生突然问一句,“你知道现在北京哪里还有卖带橡皮头的人民大会堂专用铅笔吗?”在场的人都被先生的“突然袭击”给蒙住了,连连摇头,谁知先生面色竟有些失落,“我上海的家里有很多,都是到处去搜集的,平时写字标注、做读书笔记,很好用。可惜了这个有意思的小玩意儿,以后估计很难再见到了。”
先生家里的藏书,六万多册,书房更是不局限于我们理解中的一间,而是整整一层。藏书多是精装版本,平时在复旦上完课,总会在附近的季风书店闲逛,同时保持着的日日买新书的习惯,也已经数十年有余。
而说起先生平日里的饮食起居,更可以用“传神”概括:尽管钻研佛业,却对吃喝并无忌讳:在四座皆食素、动辄便“有机、乐活”的人群里,先生对于荤素酒香更是来者不拒的豁达,“对于身体的调养,我更看重自然而为,想吃便吃想睡便睡,更不需要讲究什么忌讳和年龄,我现在的体力也很旺盛啊,即便是看一个晚上的书再搭一次早班飞机,我也并不觉得自己的精神受到多大影响。”
祖籍无锡的先生,身上还能看到整个钱氏家族之于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印记,老派的绅士作风时刻保持自己强烈的存在感,小到一支限量版的钢笔,大到于众高僧面前讲佛念文时的泰然自若,无一不是对先生与生俱来的强大气场一次又一次的證明。
采访快要结束时已经是夜里了,先生准备穿衣出门,因为听自己的司机师傅讲到北京的“簋街”,听上去像是“鬼街”,便嚷嚷着一定要在离开前,去探个究竟。
其事: 有料
本以为有着江南血统的先生,对于喝酒诸事必定是头痛不已,聊完天也才知道,原来先生对于酒的爱好,并不亚于北方的豪爽大汉——有桌有酒有人,先生的饭便会吃的十分愉快,同时,先生还力图纠正我们“南方人根本不能喝酒”的观念,“其实真正的南方人喝酒是最厉害的,比如黄酒,典型的南方酒样,味道醇后劲大,一桌子人吃饭,一般都能喝掉十几斤的黄酒,照样稳当。”
除了好酒外,每每提到先生的介绍,总不忘一句“师从季羡林”,其实这一称呼对于先生而言是个尴尬的存在,既不能轻易将其拿去,更不能仰仗师傅的光芒开辟自己的学术道路,因此一言一行,比起旁人更多了几分妥帖和谨慎,为的便是筛去不明就里人士们的风言风语,而骨子里的先生,其实是个遵循传统的人,从自己在高中阶段开始和季老的渊源以来,二十余年的师生义祖孙情,早已经超越了常人能够理解的范畴。
而最近季老的书画、信件的不断丢失或流失,也一再激起了看上去温和儒雅的先生的义愤,“季老已写了全权委托书,让儿子季承找北大要家里的房门钥匙,但至今北大还不给。天底下有这道理吗?北大做出这件事情,很荒唐!而我作为曾经的北大学生,更多是觉得羞耻。”
访谈录:1989年时任职台湾五南图书公司,委请钱文忠教授为约稿代表,文忠兄才华及口才当年已锋锐扬溢,替五南约到不少好稿。时隔二十年透过明清兄再次访遇,聊及传统文化已渐根基深业成大师,对白更见精华,尤盼国学之门透过文忠兄解析能引大众,深入浅出喃喃上口,慧根开启思源不断。
书香: 从您的人生经历来讲,《三字经》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话让您很有感触的?
钱文忠: 这个问题很好,但是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回答。《三字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词解,传统文化的关键词对于我们来讲是什么呢?是我们生命的血液,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我们更传统。但是如果我们是美国人,或者在美国长大,他可能非常爱国,但是他接受的教育已经是美国化了,我们之所以认为我们是中国人,是因为我们共享一种文化,我们凭这个文化来认同。也许你的外貌让人看到感觉你是日本人,但是你一开口就知道你是中国人,这不仅是因为你说汉语,还因你的文化也是中国的。《三字经》每一句话就像我们身体中的血液,血液我们都知道,人没有血就死了,但是谁能够回答每一滴血的作用?血重要吗?重要,没有血我就死了。但是如果谁问我钱文忠你哪一滴血最重要?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了。所以《三字经》里每一句话就像我们身体里的每一滴血,所以它每一句话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三字经》进入我们体内很深很,真正深入多少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由细胞组成的,我们感觉不到我们的细胞存在,犹如基因,但是我们感觉不到基因的存在。
书香: 您觉得现在人对《三字经》最大的误解,经常是在什么方面?
钱文忠: 我觉得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觉得我熟悉,很熟悉;第二个层面觉得我了解,完全了解。这是现代人对《三字经》最大的误解。要说《三字经》大家会觉得没有人不知道,你要说《论语》,大家会觉得有可能不知道。但是提起《三字经》没有人不知道,大家都觉得自己很熟悉,而且随口都会来两句,“人之初、性本善”,但是往下就不知道。我曾经问过很多朋友,每个人的社交圈子是有限制的,我的朋友基本上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毕业于名校,基本是学的人文,但是基本上背不上《三字经》十句。你说熟悉吗?不熟悉。
我讲的过程中也发现,这样的误解我不是说别人,我本人也有,我也许可以背多一点,当时我觉得《三字经》我也没有什么不懂的,但是准备讲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当时自以为是的,自以为理解的东西实际上不懂。我认为在《三字经》这个当中,没有启蒙和被启蒙,我觉得不存在这样的人,只有存在被启蒙者,我和大家一样,都是在接受《三字经》和它背后的传统文化的启蒙。所以我想最大的误解就是自以为熟悉,第二就是由之而来的自以为理解。
书香: 我觉得您讲《三字经》比“西游记”的时候平淡了一点,但是你讲《三字经》很稳健。
钱文忠:我的感觉正相反。因为讲西游记的时候,题目要比《三字经》小很多,加之多年的专业训练,我对这个问题的把握性也会比较强。但是讲到《三字经》我发现简直是浩如烟海。《三字经》最难的地方,和最要命的是深入浅出:表面很浅,但是背后蕴含的东西实在太多,所以你如何讲的大家喜闻乐见、老少皆宜?我只坚持一点:你讲的问题如果是真的明白了,你肯定能讲明白。如果不是这样,说明你没想明白,所以讲《三字经》的时候,我努力配得上它的深入和浅出,而在电视和图书里主要展示给观众读者们的主要是浅出,但是这个“浅”极难极难。过去有一些比喻,说好象有一潭水,有的水一眼看下去很浅,但是你跳下去几十米,里面的小鱼和石头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三字经》就是这样,你看得容易,但是你跳进去,你才发现它很深。
我讲出来,努力做到刚理解的孩子,四五岁的孩子愿意听,让孩子的父母也要听,让他觉得我跟孩子讲的有点问题。在电视机旁边,比如退休的老人,或者在安度晚年的七八十岁的老人突然想到自己的童年,我在有意识往这个方面努力,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做到了,但是我确实是有意识在努力。
書香:《三字经》为什么拿“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作为开头呢?
钱文忠: 实际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逻辑上是有矛盾的。但是我是这样解释,“人之初、性本善”这六个字在《三字经》的作者以前所有儒家大师的作品都没有注解,没有人讲“人之初、性本善”,孔子是不讲的,因为孔子碰到比较玄比较怪的东西都不讲,“人之初、性本善”基本上反映了《三字经》对人性的一种期望,期待,和一种盼望。其实如果天性都相同了,还教育什么?正因为《三字经》的普及,导致大家都认为“性相近,习相远”,但是和我们的日常经验是违背的,还有,如果“人之初、性本善”,那么还要有红绿灯吗?
“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话在儒家传统文化中没有依据,所以我把它认为是《三字经》的作者对于人性所抱有一种美好的愿望,是他的一种期盼和期待,这背后更多的是无奈。他先把美好的图景告诉大家,然后告诉大家“性相近,习相远”。这部书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价值一直被低估了。
书香: 听说您精通好多种语言,对学习语言有无特别的经验?
钱文忠: 季老曾经说过,学语言就是要最聪明的人,下最笨的功夫,简言之,就是必须背。
钱文忠《潜艇宣言》
一.当我们和其他人的FANS有冲突时,别忘了我们是潜艇,和钱老师一样,我们是有素质的一群;二. 如果你是学生或从事某种事业时,别忘了我们是潜艇,和钱老师一样,我们是勤奋的一群;三.当别人有困难或需要帮助时,别忘了我们是潜艇,和钱老师一样,我们是有爱心的一群;四. 当我们的人生,事业,家庭,爱情等不顺利时,别忘了我们是潜艇,和钱老师一样,我们是坚强的一群;五.当想到和某人的所谓“深仇大恨”时,别忘了我们是潜艇,和钱老师一样,我们是理智的一群;六.当我们的家人年已老迈,别忘了我们是潜艇,和钱老师一样,我们是孝顺的一群;七.当我们取得某些成绩时,别忘了我们是潜艇,和钱老师一样,我们是谦虚的一群。
钱文忠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季羡林先生。1980年代中留学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文化学系,主修印度学,副修伊朗学、藏学。著作:《瓦釜集》、《末那皈依》、《季门立雪》、《天竺与佛陀》、《国故新知》、《人文桃花源》;译作《唐代密宗》、《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绘画与表演》(合译);百家讲坛《玄奘西游记》、《三字经》主讲人。编集各类文集及古籍校理十余种,发表各类文章一百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