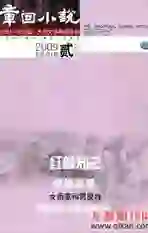萧军萧红的挚友最绀弩
2009-02-12窦景渤
窦景渤
人们对萧军、萧红并不陌生,但对作家聂绀弩,知者不多。前不久出版的《萧军回忆录》中,萧军谈到了挚友聂绀弩。作家铁峰的《萧红传》也对萧军、萧红与聂绀弩的亲密友情作了披露。
聂绀弩,现代作家。1903年出生于湖北京山,1924年就读黄埔军校一期,1925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7年回国在中央通讯社任职,1932年加入左联,1934年创办《中华日报》副刊“新向”,1936年与胡风、萧军、萧红创办文艺刊物《海燕》、《七月》,1938年与丁玲、塞克、艾青等赴延安。不久,聂绀弩即到新四军刊物《抗敌》任职。1940年与夏衍等创办杂文月刊《野草》。
1949年建国后,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1957年被划为右派,与丁玲、艾青、吴祖光等流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污蔑林彪、江青”被打成反革命,囚于山西狱中。“四人帮”垮台后被平反,定居北京,1987年病逝。
聂绀弩是文坛奇才,对散文、杂文、诗歌造诣颇深。胡乔木称聂绀弩是中国当代不可多得的杂文家。夏衍赞美聂绀弩的鲁迅笔法,几乎以假乱真。
鲁迅介绍“二萧”
认识了聂绀弩
萧军、萧红夫妇从日寇占领下的哈尔滨,逃到大连,又乘船逃到青岛。在青岛,“二萧”被国民党当局列为逮捕对象。1934年11月初,他们从青岛逃到上海,去投奔从未谋面的鲁迅。
1934年11月30日,“二萧”在上海“内山书店”第一次与鲁迅、许广平及年幼的周海婴见面。1934年12月9日,鲁迅、许广平在上海“梁家豫菜馆”宴请“二萧”及另几位“二萧”所不认识的人,餐桌上加“二萧”一共九个人。
萧军写道:“鲁迅指定了座位。同桌有一位脸型消瘦,面色苍白,具有一双总在讥讽什么似的在笑的小眼睛,短发蓬蓬,穿了一件深蓝色旧罩袍,个子虽近乎细长,但却显得有些驼背的人。鲁迅介绍说这位是聂先生!这位聂先生连身子也没欠,只是哼了一声,因为他的嘴里已经在咀嚼着什么东西。接着介绍聂先生身旁的女士,鲁迅先生说她姓周,是聂夫人。”
萧军的记忆力极好,他描述了第一次与聂绀弩见面时的细节:“席间,我注意到了那位长身驼背的人,总在不停地向他的那位夫人碗里夹这样那样的菜,而那位夫人也并不客气。这倒使我感到怪有趣的,我也学他的样子,开始向萧红的碗里夹取她不容易夹到的,或者不好意思把手臂伸得太长才能夹到的菜。这使萧红有些不好意思了,暗暗用手在桌下制止着我……”
在归家的路上,萧红轻轻地告诉萧军:许广平和她说了,“那位驼背高个子是聂绀弩,女士是周颖”。萧军写道:“鲁迅先生那次请客,实质上是为了我们这对儿青年人,从遥远的东北故乡来到上海,人地生疏,会有孤独寂寞之感,特为我们介绍了几位在上海的左翼作家朋友,使我们有所来往,对我们在各方面有所帮助。”
萧军写道:“鲁迅先生当场介绍的这位聂先生,后来我们却建立起几十年近于终生的友谊。我今年72岁,他已经76岁了(注:萧军写此段回忆录时为1979年)。我们之间的这种友谊,是经过各种风风雨雨考验的。尽管我们之间对待某一问题、某一思想、某一见解,有时有争论、有争执、有争吵,甚至到了面红耳赤的地步,但这些情况对于我们的基本友谊来说,并无任何妨碍和损害以至影响。绀弩在文化领域是具有各方面才能和知识的,他能文、能诗,从事新文学运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全有他独到的见解和成绩。”
“一九七六年他从山西狱中获释以后,我曾写下如下两首诗——《绀弩获释有赠》:”
一
又是相逢一破颜,十年囚羁两霜天!①
烟蓑雨笠寒江月,孤岭苍松雪地莲。
鹤唳晴空哀九皋,猿啼三峡过前川。
濯缨濯足浑闲事,流水高山韵未残。
注① 彼被囚于山西狱中,我被“关押改造”于京都。
二
萧萧白发两堪骄,犹爱弯弓射大雕。
狐鼠跳梁闲岁月,杨花逐水去迢遥。
恢恢天网终无漏,闲将石火教儿曹。
以上两首诗是萧军写给聂绀弩的。1976年10月27日,萧军到聂绀弩家去看望这位老战友、老朋友。聂绀弩随手找出他文化大革命前由北大荒流放地回北京后写给萧军的一首诗:
剥啄惊回午梦魂,开门猛讶尔萧军!
老朋友喜今朝见,“大跃进”来何处存?
《八月乡村》《五月矿》②,十年风雨百年人。
千言万语从何说,先到街头饮一巡。
注② 全为萧军的著作。
萧军与张春桥一伙
“打架”的见证人
关于萧军与张春桥一伙“打架”这段历史,萧军在回忆录中说,此事他记忆犹新。事情的经过是: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鲁迅在上海逝世,享年56岁。鲁迅治丧委员会由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茅盾、胡愈之、胡风、内山完造、A•史沫特莱、周作人、周建人、萧参、曹靖华、许季弗组成。治丧委员会以外,成立了临时治丧办事处,由鲁彦、巴金、聂绀弩、周颖、田军(萧军)等三十人组成。鲁迅逝世时,萧红正在日本,故此办事处名单中没有萧红。
1936年10月22日,上海一万余群众为鲁迅送葬,下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从组织鲁迅殡仪到万国公墓下葬,萧军怀着对恩师鲁迅的深切怀念和敬仰之情,化悲痛为力量,勇敢地担任了万人送葬队伍的总指挥。
鲁迅逝世一个月后,萧军把刊登纪念鲁迅文章的三份刊物,带到万国公墓鲁迅坟前焚化了。想不到此举被张春桥一伙看见了,在他们所办的小报上刊登一篇文章,讽刺萧军是“鲁门家将”,是鲁迅的“孝子贤孙”。萧军说,这类文章如刊登在国民党小报上,他是不会理睬的,但张春桥等当时是以“左翼”自居的,却与敌人一鼻孔出气,表面装人,背地捣鬼。这位脾气火爆、典型的东北硬汉找到了张春桥所办小报的编辑部,张春桥正好在场。萧军怒问:“那篇侮辱鲁迅先生和我的文章是谁写的?”一个叫马蜂的人说:“是我写的。”萧军说:“好,我也没工夫写文章来回答你们,我们打架去吧。如果我被打败了,你们以后可以随便侮辱我,我不再找你们。若你们败了,如果你们再写这类文章,我就来揍你们。”张春桥等接受了萧军的“建议”,地点选在当时上海法租界的拉都路南端的一片已收割的菜地。萧军对具体日期已忘了,只记得是某日的夜间八点钟。
双方按时到了约定地点,马蜂的见证人是张春桥自己,萧军的见证人是萧红和聂绀弩。交手后,马蜂哪是萧军的对手(萧军曾当过东北军的教官,有一定的武术基本功)。萧军两次把马蜂按倒在地,在他头上打了几拳,直到他失去“战斗力”为止。正值萧军准备打第三回合时,巡查的法国巡捕来了,“打架”就此结束。
为防止张春桥一伙下毒手,萧军原是带一根铁棍去的。到现场时见对方只有马蜂和张春桥二人,铁棍被萧红、聂绀弩夺下了。萧军回忆说:“我当时还把他们当作左翼看待,因此,并不想下毒手打伤或打死他,仅仅是把他摔倒,敲了几拳。”这种场合,萧军、萧红能带聂绀弩去,说明“二萧”与聂的友情,超过普通朋友关系。
“何人绘得萧红影,
望断青天一缕霞”
在“二萧”的人生道路上,聂绀弩给他们的帮助是多方面的。“二萧”初到上海,举步维艰。一天,聂绀弩夫妇到萧军萧红的暂住地看望“二萧”,发现他们的生活很拮据。聂绀弩劝他们应努力写些稿子换钱,解决生活问题。萧军皱着眉头说:“人生地不熟的,恐怕写出来也没处发表。”聂绀弩不假思索地说:“你去找老头子啊(指鲁迅),他会有办法的。”萧红微笑着说:“那怎么好意思呢?”聂绀弩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你们总得生活呀!没钱行吗?”萧军说:“怕写得不好,让鲁迅先生作难。”
在聂绀弩的鼓励下,萧军很快就写了《职业》、《樱花》两个短篇寄给鲁迅,请鲁迅给推荐出去。在鲁迅的鼓励下,萧红也写了短篇《小六》寄给鲁迅。鲁迅当即介绍给《太白》杂志发表了。这是萧红到上海后写的第一篇作品。
鲁迅逝世后的1937年9月,“二萧”和聂绀弩离开上海到了武汉,与胡风共创文艺刊物《七月》。
1946年1月20日,聂绀弩在重庆完成了他的散文集《沉吟》。其中《在西安——聂绀弩回忆萧红》一文,对萧红给予了很高评价:“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飞吧,萧红!你要像一只大鹏金翅鸟,飞得高,飞得远,在天空翱翔、自在,谁也捉不住你。你不是人间笼子里的食客,而且你已经飞过了。”“当你在黄昏的雪的市街上,缩瑟地走着的时候,你的弟弟跟在后面喊:‘姊姊,回去吧,这外面多冷啊!‘哦,你别送我了!你说。弟弟说:‘是回去的时候了,家里人都在盼望你的音讯咧!你说:‘弟弟,你的学校要关门了!不管弟弟,不管家人,你飞过了!今天你还要飞,要飞得更高,更远……”
聂绀弩对萧红进行了深情的回忆和极高的赞许。是的,萧红为了反对封建婚姻,反对地主家庭,宁肯流浪街头,也不向地主家庭妥协投降。一切艰难困苦都被萧红克服了,飞过来了!
聂绀弩在“二萧”的心目中,既是战友,更是兄长。当“二萧”的婚姻发生裂痕时,他们各自向聂绀弩袒露了内心的苦闷和彷徨。
丁玲、塞克、聂绀弩、萧红、艾青等从临汾去西安时,萧军留在临汾并没与萧红等同行。临行当晚,在临汾火车站月台上,萧军单独找聂绀弩谈了他和萧红的感情危机。
萧军说:“萧红和你最好,你要照顾她。她在处事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的。”聂绀弩问:“以后你们……”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聂绀弩不解地问:“怎么,你们要……”萧军说:“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这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永远是夫妇,我决不先抛弃她!”聂绀弩不愿这对儿患难与共、在鲁迅门下走出去的夫妻破裂,答应萧军尽量帮助他们和好。
到西安后,聂绀弩、丁玲等要去延安,萧红不愿同行。临行前在马路上,聂绀弩碰见了萧红,萧红一定要请聂下馆子。聂绀弩说:“萧红,一同到延安去吧!”“我不想去。”“为什么?说不定会在那里碰见萧军。”“不会的,他的性格他不会去,我猜他到别的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
“吃饭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她也不说话,只默默地望着,目不转睛地望着,好像窥伺她的久别了的兄弟姊妹,是不是和归时一样健饭似的。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她最后一次和我只有两人坐在馆子里,最后一次含情地望着我。”
不久,萧红告别了丁玲、聂绀弩等及西北战地服务团,离开西安去了武汉。
责任编辑 何苍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