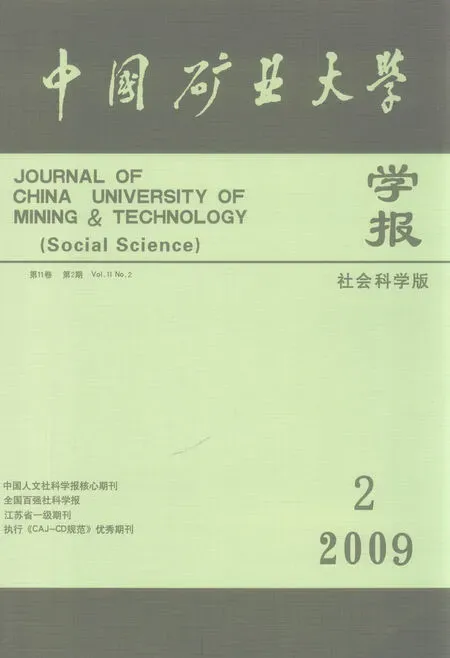意义的不确定性与多重阐释的可能
——读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
2009-02-09苏新连
苏新连
(中国矿业大学 外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2009 - 02 - 11
2009 - 03 - 10
苏新连(1961-),男,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教授。
意义的不确定性与多重阐释的可能
——读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
苏新连
(中国矿业大学 外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罗伯特·弗罗斯特是一位极受欢迎的当代美国诗人,一般认为他的诗歌通俗易读。但易读并不意味着易懂。他的诗歌其实蕴涵着一种意义的不确定性,亦即诗人以语汇、意象、修辞和格律等手段在诗歌中组合成一套复杂的意义系统,使得诗歌具有多重阐释的可能性。本文即以弗罗斯特诗歌《未选择的路》为例对此进行探讨。
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不确定性;多重阐释
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1963)在20世纪的美国诗坛可谓名重一时,他以执著的耕耘和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和诗评家的青睐,其声誉堪与庞德、艾略特这样的诗歌名家相提并论。他使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口语进行创作,而该地区的日常话题如割草、补墙、郊游、摘苹果等等皆可入诗,其诸多名篇读来清新宜人,幽默睿智,更有评论家用“抒情诗人”、“田园诗人”、“山水诗人”或者“自然诗人”这样的措辞来界定弗罗斯特,并称阅读弗罗斯特的诗歌总是一番“愉悦的经历”。在许多读者看来,弗罗斯特就像一位善解人意的智者,乐于让读者从自己的视角、按自己的方式去解读他的诗歌。但如果就此认定弗罗斯特满足于纵情在山水之间,其诗歌就像其字面表现的那样通俗易解则低估了弗罗斯特的艺术成就。弗罗斯特毕竟是一位现代诗人,他需要用诗歌去表现现代人的情感,用诗歌去探讨现代生活的复杂性。正如诸多批评家指出的那样,“‘真正的’罗伯特·弗罗斯特并非一个行走全国各地、向热心的听众朗诵简单易解的具有道德训诫意义的诗歌的老祖父形象,而是一位复杂、难懂的并且具有惊人的力量和持久重要性的诗人。”[1]937
解构主义理论认为,不可能根据任何被授予特权的文本的优势地位在语言之外永久地解决意义问题。具体到诗歌创作上,我们或可以说,弗罗斯特的诗歌具有一种欺骗性的“简单”,而在“简单”的表象下则蕴涵着诗人对于现代生活的更深邃的思考。笔者更愿意把弗罗斯特诗歌的这一特点表述为意义的不确定性,而意义的不确定性又导致了对于其诗歌的多重阐释。就弗罗斯特的诗歌创作而言,意义的不确定性具有这样的特点,即诗人以语汇、意象、修辞和格律等手段在诗歌中组合成一套复杂的意义系统,同一首诗不同的读者因其不同的背景、审美取向以及不同的观察视角而获得不尽相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认知,而且每一种读解都有十分充足的根据和理由,使得诗歌的意义具有多维指向,因而也就使某首特定诗歌的多重阐释成为可能。
以弗罗斯特的名篇《雪夜林边驻足》为例。诗人“我”在雪夜骑马赶路来到一片树林,他被林中的美景所吸引,所以希望就此歇息下来,但想到还要“遵守诺言”,因此最终决定继续赶路。按常识理解,“旅行”喻指人生,这首诗可以解读为诗人对于人生的思考。任何人如果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付出努力,不因任务的艰辛而抱怨,也不因生活中的诱惑而放弃,就像诗中流连于雪夜中树林的美丽景致的“我”,要信守自己的“诺言”,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另一种解读是依诗中特定的场景,即介乎于“冰冻的湖”和“人家”之间的树林,表达了诗人对于人类社会和自然关系的探讨。可以说,这两种阐释本身并不矛盾,各有其合理性。另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诗人对于人生和死亡的思考,其依据是“我”停留的近乎荒唐的时间和地点,即“一年中最黑暗的夜晚”和远离村庄的树林,更有诗人在最后一节两次重复“睡眠”这个词汇,无疑更强化了死亡的意象。从韵脚上说,四节诗每节两韵,分主韵、辅韵,即aaba、bbcb,上一节的辅韵成为下一节的主韵,以此类推,造成一种绵延不断的音响效果。但到了第四节,诗人只用了一韵,即dddd,破坏了前三节形成的思维预期,造成一种停顿、结束的印象,而这无疑与死亡意象有密切的关系。
另有《补墙》一诗也属此例。诗中“我”与邻居在春天来临时相约补墙,“我”认为“我”的园子里长的是苹果树,邻居的园子里长的是松树,苹果树不会吃掉邻居的松球,因而也完全没有必要修上一堵墙把邻居们分隔开来,这表现了“我”开放的生活态度和与人沟通的愿望。而邻居则谨遵父辈的教导,言称“高墙出睦邻”,因此在“我”看来邻居活脱脱就是一个封闭、保守的“野蛮人”。一般情况下多数读者会更多地认同“我”的观点,因为开放和沟通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更具有积极意义。但辩证地看邻居的观点似乎也不无道理,毕竟“高墙出睦邻”这样的谚语是父辈人生智慧的结晶,邻居间或者从广义上说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亲密无间地相处有多大的可能性?人类社会的冲突和纷争能够就此避免吗?也许人们会记起多年以前美国的一位智者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的另一句谚语:“鱼和访客三天变臭”。如此看来,“我”的期望是不是也仅仅是“我”的一厢情愿呢?为了避免让读者先入为主地简单认同“我”的观点,诗人分别在诗的中间和结尾两次重复“高墙出睦邻”这句谚语,以强调邻居观点的重要性,同时也与诗中的“我”拉开了距离。这样的对话式或者说是辩论式的行文方式所造成的效果是激发读者更加客观全面地思索两种不同观点的优点和缺点,尝试辩证地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诗歌《补墙》的意义就在于告诉人们,一个大家都认为是明智、安全、稳妥的解决方案可能蕴涵着潜在的危险。
有评论家曾经说过:“对于一位作家来说,最司空见惯的事情莫过于被误解。大多数作家会因为这种误解身受其害,但有极少数人会从中获益,而罗伯特·弗罗斯特就是这极少数人之一。”[2]198具体地说,弗罗斯特的诗歌具有表面上看来轻松明快、通俗易懂的特点,并因此拥有了众多读者。与此相反的例子是T.S.艾略特,他的诗歌以玄奥、艰深出名,因而也使一般未受过专门训练的读者望而却步。就有批评家认为,艾略特的诗歌表面艰深,实则易懂;而弗罗斯特的诗歌表面通俗,实则难解。在这方面很具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弗罗斯特的诗歌《未选择的路》了。
《未选择的路》最初创作于1913年,于1915年发表,后又结集发表在1916年出版的诗集《山间》,并作为这部诗集的卷首诗,以斜体排出。《山间》是弗罗斯特发表的第三部诗集,也是诗人在自己的祖国出版的第一部诗集,而在这样一部诗集里把《未选择的路》放在如此显要的位置说明诗人对于这首诗还是十分看重的。全诗共有四节,每节五行,格律是不十分完整的抑扬格五音步,韵脚每节1、3、4行押韵,2、5行押韵,所以从形式上看并无特别之处,这或可看成是弗罗斯特所倡导的“旧瓶装新酒”里的“旧瓶”,我们再品尝一下瓶中的“新酒”。
诗中一个行人“我”来到一处三岔路口,为不知走哪条路而委决不下。“我”驻足良久,抬眼远眺,觉得其中的一条路芳草萋萋、鲜有人迹,于是最终选择了那条“少有人行走的路”。可以说,稍有一点文学常识的人都会认定这首诗的主题是关于人生和人生的选择,任何人一旦做出一个重大的抉择势必会影响以后的抉择,这一连串的抉择又造就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而做出抉择的人就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所有的后果,好的或者是坏的。很多读者会十分欣赏“我”的巨大的勇气和开拓精神,因为“我”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行走的路”。更有评论将此与弗罗斯特的生平和事业联系起来,这是很有道理的。弗罗斯特年轻时生活困顿,其诗歌在美国得不到承认,难以发表,于是在1912年卖掉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的农场举家迁往英国,并在英国出版了两部诗集,受到评论界的广泛好评,这其中包括业已成名的美国著名诗人埃兹拉·庞德,而此时弗罗斯特已届不惑之年。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值得庆幸的,这一切又都缘于他当初选择的“少有人行走的路”。关于这一点,诗歌的最后三行说得也再明白不过:“两条路在林中分岔,而我——/我选择了少有人行走的路,/而这就造成了所有的差异。”但弗罗斯特毕竟是弗罗斯特,这还不是答案的全部,甚至也不是惟一的答案。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诗中的“我”对那两条路的描述多少有些含糊其词,至少并不肯定“我”选择的就是一条“少有人行走的路”。诗中第二节第四、五行是这样说的:“虽然那行人的踏痕/把两条路踩踏得其实差不多。”再有第三节第一、二行:“那天清晨两条路一般地覆满/树叶并没有行人踩踏。”至此,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两条路都一般无二地在树叶覆盖之下、而且此前又没有行人由此路过,又何来“少有人行走的路”?如此看来,“我”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我”的勇气和开拓精神何在?“我”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岂不是要大打折扣?或者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诗人希望表明的意思,即人生的复杂性实在非寻常人力所能参透,任何个人仅凭一时一地浮光掠影式的认知更无法预见未来人生可能遵循的发展轨迹,诗中“我”对于道路的选择是否更多出于自身一厢情愿、因而也是很主观的判断呢?美国诗人兼评论家兰德尔·贾瑞尔曾经这样评价弗罗斯特的诗歌:“当你理解了弗罗斯特的诗歌,你就会十分透彻地理解世界对于一个人意味着什么。”[2]938也就是说,在贾瑞尔看来,弗罗斯特诗歌的复杂性是与世界、抑或是人生的复杂性等量齐观的,这也就不难理解“我”为什么要在两条路前“驻足良久”了。
弗罗斯特诗歌的复杂性还不止于此。诗歌最后一节中还有两个词值得推敲,亦即第一行的最后一个词“叹息”(原文sigh)和第五行的最后一个词“差异”(原文difference)。为方便讨论,我们把最后一节完整摘录如下:“我将叹息一声讲述这个故事/若干年若干年以后:/两条路在林中分岔,而我——/我选择了少有人行走的路,/而这就造成了所有的差异。”
有评论据此认为,诗人弗罗斯特的诗歌生涯虽然起步很晚,但他大器晚成,声誉日隆,一生获得的荣衔无数,曾接受过世界上44所大学的荣誉学位,美国联邦参议院还曾两次通过决议为其祝寿。而就在诗人去世前两年,诗人以87岁高龄还受邀在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就职典礼上朗诵自己的诗歌。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说,这都可谓成功的一生,诗人显然颇为满意,因而有此一声“叹息”。但需要记起的是,《未选择的路》这首诗成诗很早(1913年),彼时的弗罗斯特于生活尚处于温饱线上,于诗歌还在苦苦打拼之中,所以此说并不十分可靠,而且还有将诗人弗罗斯特庸俗化、简单化的嫌疑。我们知道“sigh”一词在英文中一向有两解,搭配起来可以有“宽慰地叹息”和“哀伤地叹息”这两种组合,因而“我”的叹息究竟属于哪一组合则难有定论,或者这含糊其词本身就是诗人有意为之,是他献给读者的“新酒”。再有诗歌最后一行的“差异”又是什么意思?与前文的“叹息”一样,此处“差异”也可以有两解,即想要的和不想要的。“我”现在得到的是“我”想要的还是“我”不想要的?是“我”意料之中的还是“我”意料之外的?如果联系到弗罗斯特的生平,则或可以解释为此时弗罗斯特的心境,也就是说他本人已届中年,事业尚未成就,前途更难以预料,但无论如何他当初作出举家迁居英国的决定对于他的一生具有重大的意义,或是功成名就、饮誉诗坛,或是继续一文不名、最终退回到原点。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一般评论往往忽略的问题,即这首诗的标题是“未选择的路”,而诗人谈论的却是“我”“已选择的路”,而且是“少有人行走的路”,大多数读者其实关注的也是这条已选择的、“少有人行走的路”,这就造成了一种诗歌内容与标题名不符实的阅读效果,也在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不由使我们想起19世纪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的名篇《我的前公爵夫人》。
《我的前公爵夫人》使用的是戏剧独白手法,几乎通篇都是说话人费拉拉公爵向一位贵族专使谈论他已故公爵夫人的一幅肖像。由公爵不屑的叙述中我们得知,公爵夫人原来是一位美丽、善良、热爱生活、具有平等思想的高贵女性,而由于她的举止行为冒犯了公爵家族的所谓“荣誉”和公爵的“尊严”,于是公爵密令谋杀了自己的夫人。至此,我们读者所阅读到的内容与标题所表明的意义指向是吻合的。但由于这首诗戏剧独白手法的使用,读者却更多看到了说话人费拉拉公爵黑暗的内心世界,他虚伪、高傲,冷酷、贪婪,却又故作高雅,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统治集团的一个典型代表,并与公爵夫人的形象成为截然相反的对比。造成这样特殊的名不符实的阅读效果,我们不能不赞叹诗人勃朗宁手法的高妙。回到弗罗斯特的《未选择的路》上来,这首诗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戏剧独白”,但却是诗中“我”的内心独白,而“我”假想的听众就是广大读者。“我”谈论的是“我”“已选择的路”,一条一般认为是比较艰难的人生道路,人们在赞赏“我”的执著和胆识的同时其自身也受到鼓舞和启迪,因而坚定对于人生的信念。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情况是,“我”行走的是一条“少有人行走的路”,其同时还念念不忘的是那条“未选择的路”,因此就有了最后一节那模棱两可的“叹息”和“差异”,并且暗中与诗歌的标题呼应。这恐怕也是诗人弗罗斯特刻意在诗中营造的内容与标题名不符实的阅读效果的用意所在——两条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所形成的巨大反差。
那么,作为读者,我们是应该更关心标题,还是应该更关心内容?是应该更关心字面上的东西,还是应该更关心字面以外的东西?就弗罗斯特而言,这似乎都是一些无解的问题,因为二者本就浑然一体,也没有办法拆解。抛开这首诗与弗罗斯特个人生平的联系,诗中关于两条路的选择其实超越了一时一地、一人一事的范畴,在更高的层面上具有了普遍意义。在人类社会中,人们往往习惯于以结果论成败,成功则过往所有的努力都会得到肯定,失败则所有的努力都不值得一谈。如果我们逆向思维,诗中“我”当初的选择就是主观、随意的,那该如何解读最终的结果呢?又比如说,如果“我”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而结果却并不是自己所希望得到的呢?这样关于可能性的组合其实还可以继续推演下去,所引发的问题很可能比人们期望得到的答案要多得多,由此可知人生的繁复变化也莫不过此。
关于弗罗斯特的复杂性,或者说是弗罗斯特不为一般人所知的另一面,美国评论家莱昂奈尔·特立林曾有非常精辟的描述:“我得说我的弗罗斯特并不是我以为我看到的存在于众多崇拜者心目中的那个弗罗斯特。他不是那个以自己出名的富有民主观念的简洁的表述来颠覆最具典型性的现代诗歌创作的那个弗罗斯特:恰恰相反。他不是那个把人类生活的痛苦的现代窘境加以转换的弗罗斯特:与此相反。他不是那个以自己对于古老的美德、简洁、虔敬和情感方式的肯定消除我们疑虑的那个弗罗斯特:决不是。”[1]944如此说来,弗罗斯特岂不是一位遭到广泛“误解”、或者说是不可知、不可解的诗人了吗?其实不然。以弗罗斯特所拥有的读者之众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由于弗罗斯特诗歌普遍蕴涵的意义的不确定性的特点,读者就有理由提出不同、甚至是完全相悖的阐释。就像评论家朱迪丝·奥斯特所言,弗罗斯特是通过其“评价的不确定性和开放式的结尾以及对文本宽泛的释义,帮助建立了一种现代阅读方法。”[3]
[1] Elliott, Emory. gen. ed.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2] Chang, Yaoxin. A Survey of American Literature[M].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03.
[3] Oster, Judith. Toward Robert Frost: The Reader and the Poet[M].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1:12.
UncertaintyinMeaningandPossibilityofMulti-interpretations——Reading Robert Frost’s “The Road Not Taken”
SU Xin-li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Robert Frost is a popular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 whose poetry is generally believed to be easy to read. However, being easy to read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being easy to understand. There actually exists a quality of uncertainty in meaning, namely, a complex meaning system employing vocabulary, images, rhetoric, meters, etc., which creates the possibility of multi-interpretations of his poetry. A case in point is his “The Road Not Taken”.
Robert Frost; poetry; uncertainty; multi-interpretation
I712.072
A
1009-105X(2009)02-01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