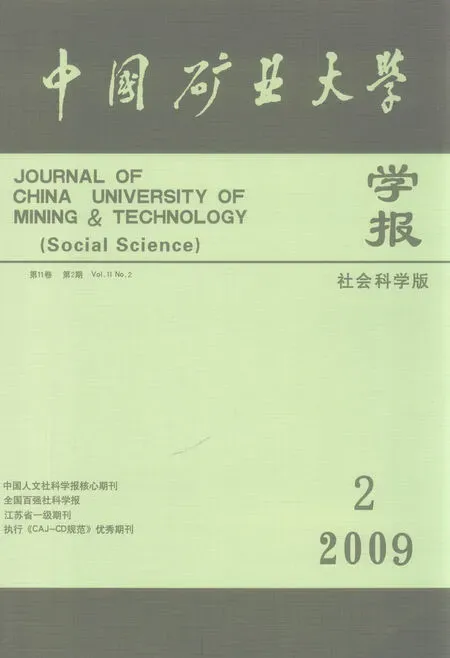论崇高在中国古典艺术中的嬗变
2009-02-09肖爱华高淮生
肖爱华, 高淮生
(1. 中国矿业大学 学报编辑部, 江苏 徐州 221008;2. 中国矿业大学 文法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2009 - 04 - 21
肖爱华(1979-),女,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
论崇高在中国古典艺术中的嬗变
肖爱华1, 高淮生2
(1. 中国矿业大学 学报编辑部, 江苏 徐州 221008;2. 中国矿业大学 文法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崇高作为美学风格之一,在中国古典艺术中有着独特的表现形态,经历了萌芽、形成、发展和式微四个阶段。崇高萌芽于原始社会晚期,处于混沌未分的状态,兼有功利与审美的特性;正式形成于中国青铜时代,在秦汉大一统王朝产生明显转向:在艺术领域呈现出对人的勋业的肯定和赞美。在理论上,先秦的孟子对人的内在德性予以讴歌和肯定,这一理论在宋明理学中得到强化,在明初走向僵化,严重制约了艺术创作的个性和创造性。明朝中叶以来,文禁松弛,至心学盛行,“童心”说大行其道,艺术的各门类涌动着浪漫主义思潮,表现市井社会人情世态的市民艺术蔚为大观。至此,崇高作为一种美学风格,全面溃退,走向没落。
崇高;中国古典艺术;嬗变
美学四大范畴之一的崇高,在西方美学理论中有完备的理论体系。作为美学风格之一,崇高在中国古典艺术中有着独特的表现形态,经历了萌芽、形成、发展与式微四个阶段。本文结合史料,梳理崇高在中国古典艺术中的不同阶段,以期廓清其“源”与“流”。
一
崇高作为美学四大范畴之一,在中国古典艺术中萌芽于原始社会晚期,更准确地说,萌芽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这可以从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了打击乐器,如鼓、磬、摇响器、陶铃、陶庸;吹奏乐器,如哨子、骨笛、陶角等[1]47-61。考古出土的原始乐器在其形制、功用方面,已具有崇高的萌芽和因子。
河南内乡朱岗于1975年出土陶鼓一件(由当地农民挖出),“陶鼓为泥质红陶。鼓身作筒形,鼓面作喇叭状。在鼓面与鼓身结合处外部有突起的齿纹一周……鼓身表面绘有黑褐色花纹。”[2]朱岗遗址出土的陶鼓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文化,其外形特别:鼓身为规则的筒状,鼓首喇叭状,鼓首与鼓身结合处有高1.0厘米、宽1.2厘米的齿状突起一周;且有黑褐色不规则的几何图案作为纹饰[1]47-61。这件出土的原始社会晚期的鼓,无论其形制,还是纹饰都透露着神秘的气息。
由于原始艺术在其产生之初并无审美自觉,其审美的一面尚未独立、亦未分化出来,而是和原始宗教、图腾崇拜互相融合在一起。产生于原始社会晚期的乐器,其主要功能不是审美,而是为完成原始宗教活动而服务。因此,乐器也就被赋予了神圣、神秘的色彩,其中,对鼓的神秘崇拜尤甚。例如,当时社、庙之中均陈放有专门的鼓,用以禳除日月及水火之灾,如《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夏书》云:
辰不集中房(杜注: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则食),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
即凡有日月之食,则有瞽(盲乐师)击鼓以禳救。在祭祀祖先和诸种鬼神、驱除疫疬等宗教巫术活动中也要用鼓,即所谓“鼓之舞以尽神”(《易·系辞》),到了春秋时期,还常有“衅鼓”的原始遗风,即杀人以祭鼓[1]46。
除原始音乐之外,原始社会晚期的建筑,玉雕,大量存在于陶器、玉雕的装饰图案,岩画,已经隐约可见崇高因素的萌芽。这些考古发现的原始遗存,例如,原始建筑之一的祭坛以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最有代表性。该祭坛遗址高8米,面积1万余平方米,周围古河道环绕,气势恢弘……赵陵山文化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厚达9米多,上层为春秋时代遗存;中层最厚,为良渚文化时期,这里的中心部位是一个人工堆筑的大型土台,东西长约60米,南北长约50米,高约4米。……土台南部有两层70平方米-80平方米范围的大土坯状的红烧土层……红烧土之下,叠压着一批特殊的墓葬。所谓特殊,是因为在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埋置的杀殉人骨,有的发现单独一个人头骨,有的在墓主两腿之间埋放一个头向与墓主一致的婴幼儿童,还有的人牲骨架反映死者生前被砍掉下肢, 有的双腿呈捆绑状,还有的仅有头骨而无躯体骨架[1]152。这些遗址现象表明该遗址是原始祭坛。
考古发现原始社会晚期的舞蹈——普遍存在于陶器纹饰、岩画之中,这些陶器纹饰和岩画中的舞蹈场面,充满神秘色彩。以福建华安汰溪仙字潭岩刻和广东珠海高栏岛岩刻为例,画面线条硬朗,画面图像稠密,但图像中人物有主次之分,主要人物被置于领舞者位置而突出显示。画面内容被认为是具有宗教性质的舞蹈场面[1]74。巫山县大溪出土的石雕人面,距今约5000年,该石雕人面像为双面人像,面部椭圆形,鼻部与眉部一线相连,张口吐舌瞪眼;另一面则为稍瘦削的人面像[1]162。这双面雕刻人像,透着神秘与紧张之感。考古出土的玉器,其纹饰已经出现神人寿面纹,也有神人、兽面和神鸟组合而成的纹饰[1]175-176。殷周青铜器中大量出现的纹饰“饕餮”纹也在属原始社会晚期的龙山文化中出现——1953年山东日照出土一件玉圭,其上用阴刻的技法,刻有“饕餮纹”的兽面纹饰,其面目狰狞:一对圆大的眼睛,露出獠牙的嘴巴。其风格已经和殷周青铜器纹饰的“狞厉”*李泽厚《美的历程》提出殷周青铜器纹饰美学风格“狞厉”之说。风格很接近了。
总体而论,无论考古发现的原始陶鼓、原始祭坛、原始舞蹈,还是玉器纹饰,都具有向殷周青铜器纹饰过渡的痕迹和特征:早期以植物、动物为主要图案内容的陶器纹饰逐渐被想象中超自然、具有无比威力的兽面、神人、神鸟纹饰所替代。美学风格由活泼愉快走向沉重神秘[3]29。
二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过渡的过程是血腥的、暴力的,部落战争就是过渡中常规的手段之一。部落之间相互吞并使得战争频繁而惨烈,规模也越来越大,传说中炎黄大战、黄帝战蚩尤其实即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阶段的部落战争。见于正史杂史的记载比比皆是:
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脩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批山通道,未尝宁居[4]。(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第一》)
自剥林木而来,何日而无战?大昊之难,七十战而后济;黄帝之难,五十二战而后济;少昊之难,四十八战而后济;昆吾之战,五十战而后济;牧野之战,血流漂杵。(罗泌《路史·前纪卷五》)*转引自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伴随大规模的部落吞并战争而来的是“大规模的、经常的屠杀、俘获、掠夺、奴役、压迫和剥削,便是社会的基本动向和历史的常规课题。暴力是文明社会的产婆。炫耀暴力和武功是氏族、部落大合并的早期宗法制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光辉和骄傲。”[3]34与这一历史阶段相应的社会意识之一的艺术,便具有夸扬、歌颂本部落祖先赫赫武功的意味。考古出土的殷周青铜器,礼器体量巨大,原因是“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具有表示等级和身份的作用,等级高的贵族为了表示自己的权力和财富,不惜投入大量的铜料来铸造,使它们往往具有令人吃惊的体积和重量。”[5]220巨大的体积给人强烈的凝重感和稳固感,使人感到青铜器的拥有者的庄严伟岸和无比的力量。除了其体量巨大给人以凝重、压力感,殷周青铜器的纹饰也给人强烈的神秘感和恐怖感:殷周青铜器纹饰以神秘的动物形象为主,其最常见的是现实中没有的动物的形象,其形象恐怖神秘,以“饕餮纹”为最。《吕氏春秋·先识览第四》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6]86此外,还有“虁龙纹”和“凤鸟纹”,这三种动物纹样及其变体通常居于主题纹样的地位,在它们的周围往往衬托有细小如水涡或卷云的“云雷纹”等几何纹样,使得青铜器纹饰通常显得复杂难辨、更具有神秘意味[5]220。
流传后世的三代乐舞艺术和出土的同时代的青铜器一样,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艺术精神内核:歌颂本氏族领袖的武功、虔诚地向祖先/图腾致敬。歌颂大禹治水功勋的乐舞《大夏》,歌颂商汤开国功绩的乐舞《大濩》,商汤为求雨而祭神之乐舞《桑林》,等等[5]175-176。我们可以看到,三代艺术在其产生之日,功利性压倒审美性、功利性与审美性兼顾。功利性在于实用、适用——祭祀图腾、神祗,夸扬祖先功勋;审美因素——通过材料的选择、器物造型、纹饰的精心创造给理念赋予有意味的形式。该阶段艺术,气势恢宏,但“有些暧昧,有些神秘的性质”[7]481。按黑格尔对艺术类型与种类区分的意见,它们是象征艺术的典范,因为,这些艺术品的创作者力求把其“所朦胧认识到的理念表现出来,但是还不能找到合适的感性形象,于是就采用符号来象征……用形式的离奇而体积庞大的东西来象征一个民族某些抽象的理想,所产生的印象往往不是内容与形式谐和的美,而是巨量物质压到心灵的那种崇高风格”[7]481。
三
象征艺术,或者说,崇高风格的艺术在三代形成并臻至鼎盛,同时也在其形成过程中走向世俗人际:第一,由神的威力走向人的勋业。第二,由外在功勋走向内在德性。即由崇高走向壮美,由功业的伟大走向道德的伟大[8]248。
崇高艺术风格的上述转向有其深刻的文化因素。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共同特征是:礼乐文化[5]8,共同特征是三代文化前后相因相承的一面,但也有不断演化、互有差异之处。一般论述夏代文化为“尊命”文化,其宗教观念尚处于原始巫觋水平,神灵观念不发达,事鬼敬神而远之;殷商文化是“尊神文化”,其鬼神祭祀观念空前发达,作为人文之道的“礼”已产生,但在当时文化体系中不占据主导地位,在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鬼神祭祀观念;周代文化是“尊礼”文化,标志着人文理性自觉的“礼”的观念在其文化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鬼神祭祀作为一种传统虽仍存在,但已退居次要地位。对三代文化的传承、变化,孔子有精准的表述:“子曰:‘夏道尊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9]641。
春秋战国时期,王纲解纽,礼崩乐坏,思想禁锢荡然无存,形成了思想活跃、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局面。“其中所贯穿的一个总思潮、总倾向,便是理性主义。正是它承先启后,一方面摆脱原始巫术宗教的种种观念传统,另一方面开始奠定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3]45。理性的觉醒,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为以儒、道、墨、法等学术流派为代表的百家争鸣与殷商时期的尊神事鬼文化揖别,而把各自学说的重心转移到世俗人事方面;在艺术领域,崇高转向对人之勋业的肯定,转向对内在德性的赞美。这可以在《诗经》和《孟子》的一些篇章中看出崇高的上述两重转向。
对《诗经》的研究表明,《诗经》是西周至春秋时期数百年间宫廷和民间流行歌曲的歌词总集,其内容主要分为:劳作歌曲、爱情歌曲、讽刺劝谏歌曲、军旅征战歌曲、传统叙事古歌、祭祀歌曲和宴宾歌曲[5]91-94。其中,传统叙事古歌和祭祀歌曲中保留了民族史诗性质的长篇叙事诗,歌颂祖先的丰功伟绩。《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篇,反映了周部族的发展史;《周颂》中的篇章《武》、《酌》、《赉》、《般》、《桓》等篇章是周代乐舞《大武》舞的歌词,《大武》的舞蹈是模拟武王伐纣的战斗场景[5]53。《大武》六章,编次顺序与各章顺序如下:
第一章,《诗.周颂.武》;
第二章,《诗.周松.时迈》;
第三章,《诗.周颂.赉》;
第四章,《诗.周颂.酌》;
第五章,《诗.周颂.般》;
第六章,《诗.周颂.桓》[10].
《大武》舞蹈演出效果如何已很难推测,但从该舞蹈是模拟武王伐纣的战斗场景这一点来看,其必定气势恢宏,震撼人心。从《诗经》流传下来的《大武》各章演唱的歌词来看,其对周人先祖泽被后世,建功立业的文治武功的衷心赞美则是无可否认的。赞美英雄人物不朽功勋的传统始终不断。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艺术实践领域呈现出沉雄恢弘的气度[11]18,其实质则是对新兴地主阶级上升阶段文治武功的肯定。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气象万千,气势雄浑壮观。绵延不绝的万里长城、显现在出土画像石和画像砖中的汉代乐舞,等等,呈现了一种“独特的矫捷流走、最能表现动势的造型艺术语汇”,虽然各造型艺术的手法和意趣不尽相同,“但共通之处,是贯穿其中的雄劲、矫捷、流转、遒美的气象。”[11]18在文学艺术领域,汉赋重修饰、铺张臻于极致。枚乘、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汉赋大家,他们的文章极尽铺写之能事,铺张堆叠的手法与华丽繁缛的辞藻无以复加。考古出土的汉代文物,“于楚国故地长沙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画,构图繁密,描法流畅婉转,使用朱砂、石青、藤黄、银粉等多种颜料,渲染浑厚,敷色绚烂富丽。”“出土的汉锦,织‘延年益寿’、‘长乐光明’、‘广山’等文字为装饰,辅以龙螭、虎豹、麒麟、辟邪、祥云、水波、回纹、方点种种纹样,或褐地而作黄蓝二色显花,或蓝地而作黄、绿、褐三色显花,华纹彩饰,交织辉映”[11]21,各地出土的汉画像石、画像砖,画面内容丰富,涵盖了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庶民生活的多个方面,除了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神异祥瑞之外,世俗生活中的宴饮乐舞、车马出行、生产劳作的场景无不囊括于其中。“画面紧密繁复……充满奇幻流美的意象,亦为汉代艺术奢华风格的表现”[11]22。
秦汉艺术总体风格以磅礴的气势、繁复明丽的色彩、铺张扬厉的笔法为其独特之处,也是其明显有别于其他时期艺术风格之处。这种独特之处,亦即崇高风格的外在表现——对世俗生活、对人的功业的肯定和赞美。而这种肯定和赞美则长期在中国古典艺术中绵延不绝,形成了一种艺术创作的集体无意识——盛唐诗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始终洋溢着对建立不世功业的热烈期盼和赞美!
崇高转向对人之德性的赞美和人性的自觉、理性的觉醒密切相关。人来自自然界,具有自然性/动物性的一面,在中国哲学文化体系中,“人的存在和本质被放置在人的社会性的基础之上”[12]29,在西方哲学文化体系中则被规定为理性动物,即人的规定性、或曰人的本质是人的理性。中国哲学文化体系对人的规定性可以概括为“道德底理性”*参阅《贞元六书》,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第392页。,西方哲学对人的规定性可以称之为“理智底理性”。中国哲学文化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最初是孔子建构起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孟子那里得到发展,发展到宋明道学阶段即僵化。儒家经典《论语》几乎所有篇章都有关于“礼”的言论,限于篇幅,不在此一一引证。儒家另一经典《礼记》在开篇《曲礼上》中即说:“人而无礼,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9]429“礼不是别的东西,它就是人的存在和活动的社会性形式。人的不同于动物的社会本质,正是通过‘礼’而获得实现和客观化的。”“‘礼’是人的社会性的外部形式,‘仁’则是人的社会性的内在根基”[12]30。“仁”的含义,新儒家认为是基于亲疏远近的“等差之爱”*参阅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第54-55页。。这“等差之爱”实质即外在社会规范化为内在自觉意识,孟子将这一点发扬到极致。“孟子强调人禽之分在于人能具有和发扬内在的道德自觉”[13]42,这所谓的内在的道德自觉即著名的“不忍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而且,孟子赋予了“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以形上先验的性质:“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14]78。孟子的道德自觉既是人和禽兽区别之处,也是“圣人”不同于“凡众”所在。通过后天的学习,可以达到“人皆可以为尧舜”[13]42。这种绝对道德人格的达到,有一个逐级递升的层次:“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15]怎样才能达到绝对道德人格?孟子给出的答案是:养吾浩然之气*见《孟子·公孙丑下》。。
孟子大力提倡的绝对道德人格,是崇高发生转向的先导和理论准备。但理论并不必然与艺术实践同步。在孟子的绝对道德人格论提出一千多年后,其绝对道德人格论在宋明理学家那里才得到回应并在艺术创作领域有所体现。
北宋建国后,理学产生、发展并盛行起来。宋代理学从孔子所论不多而孟子极力提倡的道德自觉入手,建构起宇宙论和道德伦理为一体的庞大理论体系。“理学的核心是讲‘理’(即‘天道’)为宇宙的本源,而儒家的伦理道德则是‘天理’的体现,凡是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思想、行为则被斥之为违背‘天理’的‘人欲’而加以排斥。”[16]26理学的盛行对艺术创作及理论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宋诗的艺术风貌。宋诗的创作中“用一般非文学的方法来写诗,以文字、议论、才学为诗,用抽象思维来代替形象思维,用过多的议论和说理和堆砌典故来代替文学的感情抒发和形象描写,而不重视意境的创造。”[16]30
明朝建立后,统治者大力推行程朱理学,实行八股取士。理学的盛行和科举取士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对艺术创作产生了消极影响。明初流行的台阁体风格,不仅限于诗歌创作,流弊及于戏曲、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台阁体在诗文创作中,“表现的思想感情‘雅正平和’,有浓厚的道学气”,以反映上层官僚生活的应制、唱和之作数量为最,内容上以歌功颂德、点缀升平为主,抒情要“适性情之正”[17]226。戏曲创作也刻意迎合官方意识形态,自觉为政治教化服务,大量充斥着点缀升平的娱乐之作和宣扬封建道德的作品。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邱濬所作《五伦全备忠孝记》最有代表性。该剧的“说白唱词大段抄录经书,充满封建说教的陈词滥调”[17]228。书法艺术“为迎合帝王的爱好和体现皇家的气派,书法风格也追求庙堂之美,逐渐形成了规正婉丽、中和端庄的‘台阁体’。这个书风……刻板划一,最终导致千字一体、千人一面,扼杀了书法艺术的个性和创新。”[18]6绘画方面,则成立了宫廷画院。“创作上完全以体现帝王意志为主旨。尤其人物画突出政教功能,往往借历史故事以示‘鉴戒’。……这类作品主题鲜明,技艺也很高,但缺乏有感而发的激情,殊少艺术感染力”[18]6。
至此,古典艺术对绝对道德和人之内在德性的提倡达到空前的程度。所谓盛极必衰,从明中叶,一股冲破程朱理学思想禁锢的浪漫思潮风起云涌。王阳明心学的发展者李贽倡导“童心”说不遗余力,公安三袁“性灵”说与之遥相呼应。在整个艺术创作领域,表现人情世态及市井小民愿望、要求的佳作不断涌现,抒写士人襟怀的小品文蔚然成风。这些都表明,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于是,崇高作为一种美学风格,全面溃退,走向没落。
结语
崇高在中国古典艺术中萌芽于原始社会晚期,也即新石器时代向奴隶社会过渡阶段,处于混沌未分的状态,兼有功利与审美的因素,功利因素压倒审美因素;形成于青铜时代,该期艺术作品风格狞厉,形制奇特、体量庞大,呈现以巨量的物质压倒心灵的面貌;分化发展于秦汉及其以后的时代。具体而言,有两个维度:对人世勋业的讴歌和肯定与对人的内在德性的赞美。这两个维度并行不悖,长期存在于中国古典艺术领域,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具体的、历史的原因,呈现不同的样貌。至两宋始,理学建构起庞大的理论体系,并在明代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与此相一致,在艺术领域,崇高一面倒地呈现宣扬封建道德的态势。明中叶以后,理学日趋僵化,发展出其自身的破坏性力量——阳明心学及李贽的童心说,艺术创作领域呈现浪漫主义洪流,宣扬封建道德的崇高风格式微。
回顾崇高风格在中国古典艺术中的渊源流变,对于正确理解其异于西方美学中的崇高、对了解崇高在中国古典美学理论体系中的发展,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和准备。
[1] 李希凡.中华艺术通史:原始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 赵世纲.仰韶文化陶鼓辨析[J].华夏考古,1993(1):73.
[3] 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4] 史记[M/OL]..http://wenjin.nlc.gov.cn/zjtj/book.jsp?bookid=1000001_01&filename=T00001_00.pdf&booktitle=%CA%B7%BC%C7&bookadded=1
[5] 李希凡.中华艺术通史:夏商周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6] 吕不韦.吕氏春秋:先识览第四[M/OL]. http://wenjin.nlc.gov.cn/zjtj/book.jsp?bookid=1000003_08&filename=T00001_00.pdf&booktitle=%C2%C0%CA%CF%B4%BA%C7%EF&bookadded=1
[7]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8] 李泽厚.华夏美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9] 礼记[M]//四书五经.陈戍国,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6.
[10] 转引自: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M].修订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45-346.
[11] 李希凡.中华艺术通史:秦汉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2] 刘纲纪.孔子思想的世界意义[M]//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13] 李泽厚.新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14] 孟子.公孙丑上[M]//四书五经.陈戍国.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6:78.
[15] 孟子.尽心下[M]//四书五经.陈戍国.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6:134.
[16]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M].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7]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18] 李希凡.中华艺术通史:明代卷(上编)[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TransmutationofSublimityinChineseClassicalArt
XIAO Ai-hua, GAO Huai-she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Xuzhou 221008, China)
As one of aesthetic styles, sublimity shows unique pattern in Chinese classical art, and has experienced the embryonic, formative, developmental and falling stages. Sublimity in chaotic state sprouted in the late primitive society. It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tility and aesthetics. Sublimity took shape at the Age of Copper, and then it obviously changed directions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praising great achievements and success of human beings in the field of arts. In terms of theory, Mencius in the pre-Qin Dynasty admired inner human virtue, moreover, it was strengthened by Neo-Confucianism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but later it became rigid. As a result of the rigidness, art creativity and personality were seriously restricted. From the middle period of Ming Dynasty, cultural limitation was reduced and Mind Study prevailed. Under their influence, romantic thoughts activated in all respects of arts, which resulted in great popularity of the ways of the world and the citizen’s arts. So up to this point, sublimity, as an aesthetic style, collapsed in a complete way.
sublimity; Chinese classical art; transmutation
B83-0
A
1009-105X(2009)02-01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