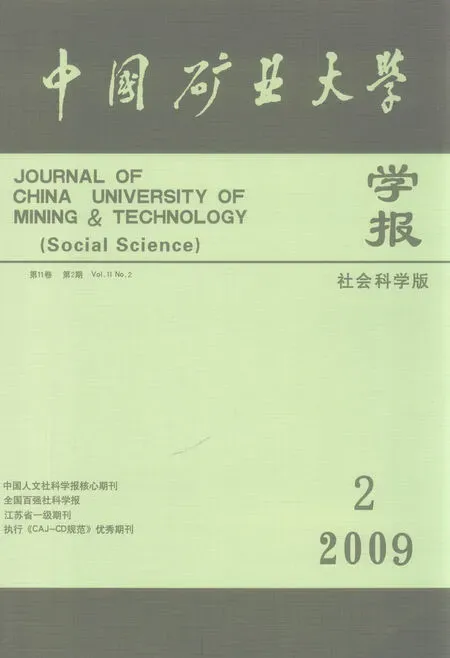关于环境税的几个问题
2009-02-09邹爱勇王春霞
邹爱勇, 王春霞
(西北政法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3)
2009 - 03 - 09
邹爱勇(1983-),男,西北政法大学环境法硕士研究生;
王春霞(1983-),女,西北政法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硕士研究生。
关于环境税的几个问题
邹爱勇, 王春霞
(西北政法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3)
环境税作为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然而在环境税的定义、有效性、比较税率、税收归属、征收方式、税收支出等方面依然存在诸多疑惑。基于此,本文在回顾环境税历史渊源的基础上,逐一对以上疑问作出分析,以期进一步深入探讨环境税相关问题。
环境税; 双重红利;征收方式;税收支出
我国针对实施环境税的探讨,自1996年至今已有10多年的历程。在经济发展仍然是以牺牲巨大环境价值的背景下,是否应开征环境税一直争论不休。尽管如此,理论的研究终将推动立法者作出相应姿态。2007年6月4日国务院印发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明确要研究开征环境税,表明开征环境税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虽然环境税逐渐成为学者、政策制定者热衷的话题,但是从环境税的定义到有效性、使用方式等问题都没有统一的定论,本文拟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 开征环境税的历史渊源
从比较法的观点来看,国外环境税研究的历史显然更悠久。一般认为,英国人庇古在其1920年出版的著作《福利经济学》一书中,率先提出的“政府利用宏观税收调节环境污染行为”的理论,是环境税收得以产生的思想基础。外部经济效果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并没有从货币上或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1]。庇古试图通过征税来弥补私人边际成本同社会边际成本的偏差,使得外部经济效果内部化,消除外部效应带来的效率损失。所以理论上把对单位污染所征的等于污染所造成的边际社会损失的税收称为庇古税。自20世纪70年代起,经济发达国家尤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广泛利用税收经济政策来保护环境。80年代以来,OECD成员国纷纷实行了以减少个人所得税和公司利润税、增加消费税和社会保障税等的税制改革。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的《21世纪议程》、《生物多样化公约》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普遍受到各国的关注,其中通过环境税以改善环境的经济手段,引起了各国的广泛讨论。近年来绿色税制改革(green tax reform)已是大势所趋,各国为改善环境所采用的手段,逐渐由单纯的管制手段(Command and control instrument)转向经济刺激手段(Market-based instrument),比如税收,以图更加有效地控制环境恶化的趋势,并实现生产的转型。也就是所谓的产生环境改善与减轻税收制度扭曲的双重红利(Double Dividend)效果。
二、 环境税的概念界定
(一) 何为环境税?
环境税并非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定义,在不同的语境和视角下会产生不同的定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3年在一份关于税收与环境的报告中认为环境税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初始即为实现特定环境目的而设立和征收的、并且被明确确认为“环境税”的税收,如排污税等;二是最初并非以环境保护为目的而设立、但是对环境保护有影响而后从保护环境的立场修改或减免的税,如能源税、燃料税等[2]。在德国,学者对环境税的定义显然走得更远。比如有学者从控制目的与财政目的两方面着手,将环境税划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情形。广义的环境税费“首先是长期以来就一直征收的使用费和残渣消除费,如水费、排水费、垃圾运输费以及开采费”[3];狭义的环境税费“首先是指出于控制目的而非出于财政目的制定的环境控制税费。其首要目的并不是征收尽可能高的税费,而是处于财政目的之外。因此,其在制定中,总是尽量回避税费要件”[3]。而从实践来看,西方各国普遍开征的环境税主要是空气污染税、水污染税、固体废弃物税、噪音税、垃圾税,也就是说环境税主要是污染税。这些环境税的理论支撑主要是污染者付费原则。污染者付费原则,强调环境是公共财产的一部分,污染环境的人有治理环境的责任,并利用经济刺激手段的资源再次分配,达到降低污染、抑制资源使用的泛滥,减少非污染者的税收支出。而我国学者往往认为,环境税的概念可分为狭义、中义、广义三种[4],将“环境税”分成资源税和污染税两大块。只是在“环境税”的法定名称有不同的观点,这些争论完全可以通过相应的立法技术来解决。
从中外的不同定义来看,环境税概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作为观念层面的环境税;第二个是作为制度层面的环境税。从观念层面来看,环境税包括资源税无可厚非;从制度层面来看,将资源税纳入制度层面的环境税就容易产生内生的冲突,因为根据税法原理,资源税往往属于财产税范畴,其主要功效在于调整资源级差收入的不均,所以其重在调整社会资源财产的分配不均[4]。显然两者不可相互交替使用。我们认为环境税比较狭义的定义是:基于污染者付费原则向污染者征收的税。广义的环境税则可以由污染者付费原则扩及到使用者付费原则,与此相对应的环境税定义就是,由环保等机关向受益者或使用者征收的稅,征税对象主要是煤炭、燃油等潜在污染产品,以促使消费者减少有潜在污染产品的消费数量。
(二) 德国环境税定义引起的思考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德国在环境税定义问题上争论也极其大,但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德国学者对此定义的视角显然不仅仅是文字游戏的一种争论,他们的探讨产生了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观点。如德国联邦环境机关,在其刊物版本上对环境税费作了如下定义:环境税费是“为达到环境政策目标而由公法上的公共团体依据公法征收的金钱给付”[3]。此定义就是在公法视角下的界定,即从厘清征收环境税的法理依据上寻找突破。其环境税定义不是采取我国学者习惯的“主体到客体”下定义的方法,而是在征税正当性、合理性作出努力。
三、 环境税的有效性问题
从现实来看,我国环境问题的根源并非在于未开征环境税,而在于政府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忽视环保。因此,针对环境税的有效性问题主要有两种意见。支持者认为,环境税的开征将会产生双重红利效果,虽然政策制定者声称环境税开征的目的在于希望通过新的经济刺激手段,促使生产者主动改善生产,减少环境污染以及税收的扭曲效应。然而反对者认为,开征环境税除了增加纳税人的税赋,并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一) 开征环境税能否产生双重红利效果
所谓双重红利(Double Dividend),是指征收环境税可将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以增进环境效益,同时若降低所得税则可以提高就业率。早期的研究虽然认为绿色税制改革(green tax reform)具有双重红利效果,因为他们认为环境税是一种矫正性税,不仅可以通过征税增加污染企业的私人边际成本,使其外部成本内部化,同时,政府还可以把征收的环境税收入用于对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的改革,从而在总体上不减少税收总量,并实现税制优化的效果。但后来发现环境税本身不仅对劳动供给也存在扭曲效应,从短期看,在其他经济部门吸收劳动力和新的生产结构出现以前,会造成失业率的暂时提高。此外,如污染企业所增加的成本,势必最终还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而且相关的实证研究还发现双重红利并不是一定存在的。一般来说,双重红利的存在与经济结构、税收体制等因素有关,因此利用环境税减少所得税的扭曲性效应是否能产生双重红利的效果,必须视经济结构和税收体制而定。对环境税是否能发挥双重红利效果,学理上的探讨在不同的前提与数据面前会有不同的答案。
从实施绿色税制改革的国家来看,征收环境税实现双重红利并不明显。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4年对英国、爱尔兰、德国、法国、丹麦5国环境税的研究表明,单靠提高环境税不可能实现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的目标,而且环境税的政治可接受度低[5]。但这并不足以否定环境税的价值。因为环境税的最主要目的在于以经济手段改善环境质量,如若在征收环境税的同时,妥善利用所征收的税,进行税制改革,进而能实现双重红利固然好。进一步来说,征收环境税的目的并不仅是利用环境税减少所得税的扭曲效应,对环境税的利用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将环境税用于增加企业经济效益方面的投资。总之,征收环境税一般对改善环境具有正效应,即不仅能增加一定的财政收入,而且可促进绿色产品的使用的观点获得了普遍认可,但对提高就业率,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 征收环境税的公平性问题
当征收环境税成为必然,我们所面对的实际问题是:开征环境税会不会增加公民的负担?环境税如何在发展经济与环保之间达到平衡,即税收中性原则——纳税人支付的环境税与获得利益大抵相等,保证公民税收负担的总体水平不增加。然而现实是增加环境税可能产生低收入者负担较重的累退效应,特别是当这种征税产品为一般生活必需品的情况下,影响就更为明显,这显然与环境税的预期相背离。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首先,税率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到税赋水平,应以环境税的负担能满足政府为治理污染而需要的资金为最低限度;其次,可以把从环境税中取得的部分收入用于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或降低低收入家庭的劳动力税、消费税负担。这一点,在我国环境税改革中应予以注意。
其实环境税的中性原则问题在策略上应是容易解决的,倒是环境税存在的本身就有不义之取之嫌。因为该税具有公益价值,征收环境税等于透过消费手段把财政压力转嫁给社会个体了,也就是说,社会问题被个人化了。如果政府征收环境税主要目标仍然是收入补充和调节、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等,而不是保护环境,那么环境污染现象仍将继续恶化。此外,在我国公众参与公共预算的程度不高的背景下,以公共名义征收的款项往往不能实至名归地用于公共利益,这对公民来说,环境税存在的公平性问题就更无从谈起。虽然政策制定者一直希望以环境税来取代所得税以实现税制的“绿化”,使政策的实行具有可行性,然而更为现实的是,要人们认识到环境税是以一种支付方式取代另一种支付方式,在新的征税方式下并不会增加税赋的负担。因此必须公开环境资讯,提供更详细的资料,一方面让人们理解税制需要“绿化”的原因,以保证纳税人理解政府为什么要征税以及有哪些可供替换的降低污染的生产和生活消费方式,另一方面规定环境资讯公开责任也可以避免无谓的排放。
四、 环境税的比较税率
究竟多高的税率既能达到治理污染的目的,又不会危及到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从理论上说,为了使污染企业的全部成本内部化,环境税税率应该确定在能够使减污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损失的交界点上。税率定得太高,有可能加大企业的成本,降低纳税企业国际竞争力,造成生产抑制;税率定得太低,不能发挥提高相对价格的作用,对污染企业也没有约束力,环境状况恶化的趋势将难以改变。显然,确定这个交界点是征税的难点所在。但一般来说,对污染环境的物品或行为征收的税率要高于对不污染环境的物品或行为征收的税率才具有合理性。就具体产品而言,应体现税收差别并应有适当的弹性,如普遍实行的对含铅汽油的较高税率和对无铅汽油的较低税率就是比较税率的具体运用。
环境税是采用“以价计征”还是“以量计征”也是值得注意的。一般来说,污染的大小是与其生产和消费的数量多少有关的,而不是由其价值大小决定的,同时“以价计征”可能促使生产者通过降低产品质量来降低价格,而不是减少污染排放量。从这里来看,“以价计征”既不能真正改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环保伦理观,也有失公平性。因此,“以价计征”并不具有天然的优越性。
对比较税率的探讨告诉我们,征收环境税并不是加强环境保护的惟一有效手段,它不仅需要与其他手段配合,更需要其内部的相互协调,才能实现最佳的环境目标。因此必须正视环境税与其他税种税率的差别,如对环保产业能源税的减免等是环境税设计时应考虑的问题。此外,由于环境税的征收涉及诸多环保技术问题,因而在该税种的征收管理过程中,税务部门应加强与环保部门的联系与协作[6]。
五、 环境税的征收方式及税收归属
对环境税的征收方式,也就是环境税费应否整合的问题,即是采取分散征收还是整合成独立型环境税统一征收。前者并不主张设立独立的环境税税种,而是对消费税、资源税、水资源环境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以及车船使用税等单独进行征收;后者主张把以上税种整合成独立型的环境税统一进行征收。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必须全局性地了解和考虑这两种做法的成本与收益。整合成独立型的环境税优势在于,征收成本较低,管理也较简便,成本易于衡量,稳定性较强,对付外部性的矫正功效较强,有利于筹集专项资金治理污染。但缺点也是明显的,政治接受度不高,易于造成经济扭曲效果,推行起来比较困难;而分散式的单独征税的征收成本较高、征收效率低,如部分环保资金被环保部门用来维持其机构的经常性开支。
我们认为,所有与环境与资源保护有关的税收应进行整合,原因如上所言。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整合的同时要注意避免重复征税,即对已经征收了的税费又再次征税,以减少施行的政治阻力,提高环境税的可行性。
环境税税收收入的归属(环境税收入定格于国税还是地税)是一个涉及面极其广泛的问题,不仅需要符合税法相关原则,也需要考虑环境问题的特性。环境问题分为全球性与地域性。前者如地球变暖导致南极冰盖融化。地域性污染如太湖蓝藻事件。就地域性环境问题而言,地方政府身处事件发生地,对环境资讯具有更直接的了解,因此处理环境危机更具及时性。但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扩及性,往往会由地域性问题转化为跨区域性问题,因此需要中央级别的机构统一指导、协调。就此而言,基于污染者付费和受益者付费原则考虑,地方政府应具有一定的环境税收收入以补偿因环境污染而遭受的损失,而如果环境税收入仅仅是国税,缺乏利益激励,那么地方出于自身经济发展需要,必然会进一步忽视环保工作。当然我们也要注意,由于存在寻租的可能,地方政府会为了竞争税源而忽视环境治理,从而很难实现利用环境税改善环境的预期目标。
我们认为,税收归属的不同划分会直接影响环境税能否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因此环境税的归属问题应在合理衡量中央与地方两个层次的环境税税收利益关系的基础上通盘考虑。应该注意到的是,在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状况由于财权、事权的不对等显得相对紧张,而中央财政经过20多年的持续增长,治理环境的支付能力明显强于地方财政,这显然是赋予地方治理环境问题的权限不足的反映,因此有必要赋予地方部分征税自主权,但必须严格管理,明确限定范围以确保资金用到环境治理上。总之,环境税既不应完全归属中央,也不应全部归属于地方。
六、 环境税收入的使用
对环境税收入的使用问题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环境税收入应实行统收统支,纳入一般预算收入使用;另一种观点认为,环境税收入应实行专款专用,指定用于特定的环境保护活动,充作特种环境基金的来源等等。就专款专用而言,是指将税收指定由环保行政机关专用。但正如我们所知,环境治理并不仅由环保行政机关决定就能一劳永逸,相反很多涉及环境保护的事项是属于其他部门的业务范围,如实行进口差别关税政策,就需要海关总署、税务总局等部门的配合。指定用途的后果,就会出现支出增加,效率低下等问题。此外,专款专用易于导致寻租的出现,使环保部门在收取税收后,不再关心污染治理,从而背离环境税设计的初衷。不过从公平角度来看,专款专用却较具有合理性。因为环境税收入专门用于特定的环境保护活动,能补偿那些因环境负外部性受到影响的人们,似乎也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尤其在环保资金缺乏的背景下,专款专用有利于改善环境。而就前者而言,统收统支的环境税收一般用来制定补偿计划,以抵消环境税可能带有的累退性以及减少所得税的扭曲效应,实现税赋公平。从这里来看,环境税收入应与其他税收收入一样,作为一般性财政收入,而不宜实行专款专用。正是基于以上种种顾虑,发达国家尤其是OECD成员国在将环境税专款专用的同时,设立国家级综合环境基金,以进一步发挥环境税的作用。国家级综合环境基金可以划分为国家环境基金和地方环境基金两部分。国家环境基金主要在国家级环保项目中发挥作用;地方环境基金则主要支持区域性生态环境建设。
上述问题都有待于各界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导向,发挥我们的智慧去解决。客观地说,由于国内环境税的相关研究甚为欠缺,使得环境税改革缺乏有力的理论基础。但是我们认为,作为政策工具的环境税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开征环境税不应背负太多的包袱。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政策制定者出台环境税的决心可以触动学界对此问题的更深入探讨。
[1] [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569.
[2] 李挚萍.西方国家环境税的发展及中国的对策——兼谈中国加入WTO后如何面对绿色非关税壁垒[C]//适应市场机制的环境法制建设问题研究——2002年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论文集(下册),2002.
[3] Kloepfer.s.322.Rdn264,参阅:周晨:德国环境税费制度概述[J].中德法学论坛,2006年第4辑.
[4] 徐祥民,王郁.环境税:循环经济的重要手段[J].法治论丛,2006(4).
[5] 王卉彤.我国循环经济中环境税费的合理利用[DB/OL]http://www.stockstar.com/info/darticle.aspx?id=GA,20060619,00235954&columnid=2457.
[6] 丁芸.构建绿色税收体系的设想[J].税务研究,2007(7).
OnEnvironmentTax
ZOU Ai-yong, WANG Chun-xia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 710063, China)
A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component of economic system Environment tax has been given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doubts about the definition of environment tax, effectiveness, comparative tax rates, tax attribution, collection methods and tax expenditures. Because of this, the present paper analyzes the above doubts one by one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origin of the environment tax to further explore issues related to environment tax.
environment tax; double dividend; collection methods; tax expenditures
D922.229
A
1009-105X(2009)02-005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