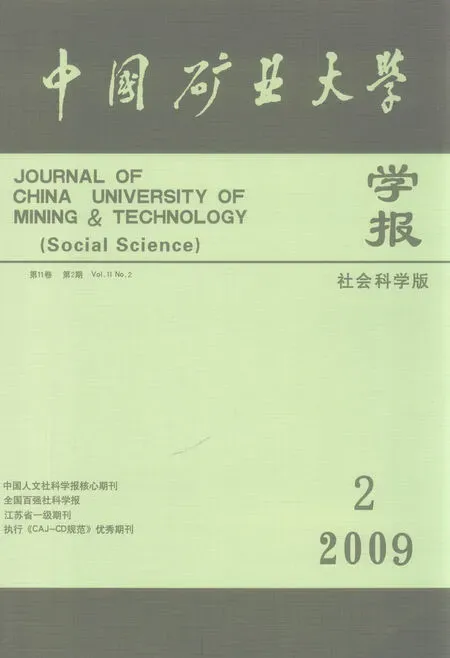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和谐关系研究进展
2009-02-09包庆德潘丽莉
包庆德, 潘丽莉
(内蒙古大学 哲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2009 - 01 - 18
2009 - 03 - 12
包庆德(1960-),男,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
潘丽莉(1988-),女,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2007级本科生。
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和谐关系研究进展
包庆德, 潘丽莉
(内蒙古大学 哲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全球性生态危机促使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内的“生态和谐”这一时代主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高度重视和深度反思,因为从“社会和谐”到“自然和谐”的生态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极其重要的生态环境条件和自然资源基础。就此意义而言,没有生态和谐的社会不是真正意义的和谐社会。在当代,生态环境因素与自然资源要素极大地渗透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水准及其价值走向。本文从生态哲学维度,就和谐社会构建的生态和谐思想渊源、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和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三个层面进行逻辑梳理与文献述评。
和谐社会;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全球性生态危机促使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内的“生态和谐”这一时代主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深度反思和高度重视,因为从“社会和谐”到“自然和谐”的生态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极其重要的生态环境条件和自然资源基础。就此意义而言,没有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内的生态和谐,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的和谐社会。在当代,生态环境因素与自然资源要素极大地渗透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水准及其价值走向。本文从生态哲学维度就生态和谐的思想渊源、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和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三个层面进行逻辑梳理与文献述评以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 关于生态和谐思想渊源
学界从不同角度论述和谐思想渊源。郑慧等人通过系统的梳理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长河中为实现理想曾设计或尝试过许多方案,为后世留下弥足珍贵的“和谐”思想和理念。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赞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和谐”社会,追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和谐关系,崇尚“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时地利人和”等和谐思想行为准则[1]。于语和等人通过考据认为,“和”,最早见于甲骨文,本指乐器和声音的相应和谐,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谐”,本指音韵和洽,引申为协调关系或适当状态。“和”、“谐”合用表达了人们对匀称、适当、适中和协调的追求。古代的和谐观念意在强调一种有价值的普遍的和谐关系[2]。李中华认为,任何民族的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下形成和发展的[3]。这也就是说,和谐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谐社会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理想。对此,季羡林认为,“从中国文化的传统来说,我们是不讲弱肉强食的。中国宋朝思想家张载在《西铭》中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民,都是我的同胞兄弟;物,包括植物都是我的伙伴。这就是中国的思想。现在我们提出‘和谐’这个概念,有助于全世界人民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爱护,不要斗争。”季羡林说:“我觉得‘顺其自然’最有道理,不能去征服自然,自然不能征服,只能天人合一。要跟自然讲交情、讲平等,讲互相尊重,不要讲征服,谁征服谁,都是不对的。”[4]无论从原初起始意义,还是最终终极意义上,自然都是人类生存与发展须臾不能离开的家园,人类应该而且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协调发展。
邓伟志认为,在西方有毕达哥拉斯的“整个天是一个和谐”,莱布尼茨的“宇宙是一个由数学和逻辑原则所统率谐和的整体”以及马克思的和谐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之后有些社会学家的诸如社会均衡论, 协和社会论和社会系统论[5]等,对包括人与
自然关系之生态和谐在内的和谐社会构建具有启示意义。由此达到诚如马克思所言的“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费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6](926-927)之理想境界。
安启念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各个方面之间的激烈冲突催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上述冲突的真正解决,是人的个性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其主要特征是和谐。和谐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目标,冲突只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7]。潘岳认为马克思生态观的第一个观点是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等于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绿色思想,其核心就是要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即恩格斯所说的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第二个观点是阐明人的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二重性,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上的积极顺应自然,从而实现社会化的人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第三个观点是生产力学说,马克思从改造自然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相统一角度论述生产力,指的是社会力量和自然力量的结合,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取决于人类的劳动量与生产资料量之间配置是否适当[8]。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为先进的理论成果,对其和谐思想进行具有当代水平的深入解读,是深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时代要求。因此,构建和谐社会首先是从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妥善处理现实各种不同利益关系,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事业的良性运作和科学发展而提出的,同时,辩证扬弃中外思想史上的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在内的所有和谐思想成果,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强有力的和谐理论支撑。
在我们看来,和谐社会的建构应至少包括三个有机构成:其一是人与人(社会)之间的和谐,我们将其概括为“人际和谐”或“人态和谐”,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人文关怀、发展方式和交往状态的和谐,它居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层面;其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我们将其概括为“人地和谐”即“生态和谐”,也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能量转换和信息交换状态的和谐,它居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层面;其三是人与自身的和谐,我们将其概括为“人己和谐”亦即“心态和谐”,也就是人与自身的心理状态、生理状态及其身心状态的和谐,它居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层面[9]。而这三个维度之间又是互为中介的辩证关系。
比如传统伦理学只研究人与人的直接伦理关系,对于人与人之间间接而复杂的被生态环境中介掩盖了的伦理关系严重忽略。而环境伦理学第一次从理论自觉角度,把伦理关怀的范围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使生态环境这一被掩盖了的中介终于浮出水面。环境伦理学之所以强调破坏生态污染环境是不道德的,是因为一些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直接或间接损害到另一些人的利益,因此,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有机构成,从而具有了伦理意义。也正是从人类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才应该而且必须维护生态系统的协调平衡,使人类生态环境不会因开发自然资源而遭受破坏和污染。而居于基础层面的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和谐,其实质乃是事关保障人类生存发展的生产力之和谐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
二、 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
生态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石,没有生态和谐就没有真正的和谐社会。然而,由于生态哲学维度的深度缺失和生态思维方式的深层缺位,以往对文明成果与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力发展的考察和评判,存在着严重的单向度价值取向和过于简单化的历史时弊——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其中并由此须臾不能离开的生态环境,不是在文明和生产力评价系统之内,而是几乎统统在其评价系统之外[10]。
问题在于,自产业革命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人类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的同时,人类遭遇全球生存环境危机,人口爆增并面临资源短缺挑战。20世纪上半叶的所谓“八大公害”就是明证。
欧阳志远指出,在人类社会早期人的生存能力极为低下,人与自然关系是一种纯粹依赖关系。在这个时期人类对自然界的扰动不大,特别是在进入农耕阶段以后,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之间达到相当程度的协调,人民群众中有一种安土重迁、安居乐业的普遍愿望。越是传统农业发达的地域,这种愿望就越是强烈,古代中国就是这样的典型[11]。在农耕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和谐的,人们非常了解土地、河流、森林、植被对物质生活的重要性。虽然人类也不断向自然索取,但在整个农耕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在总体上尚没有超出自然界自我调节和再生的能力。人与自然的关系一般来说是和谐的,自然的秩序没有发生紊乱,生态环境没有出现失衡[12]。然而,这种和谐的基础是相当脆弱的。由于开发自然的手段低下,加上认识的盲目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简单劳动数量追加,于是造成经常性的人口和土地匹配失调,进而造成大规模的土地开垦与生态破坏。工业经济体系的建立是人地关系的一次跃变,这次跃变是人对自然需求层次上升的结果。这个时期人地关系的基本特点有三:一是对天然材料进行深化加工;二是对天然能源进行转化利用;三是对生产过程进行精确调控[11]。王志禄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人类对自然产生的影响与作用及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类需要从自然界索取资源、空间,享受生态并向环境排放废弃物,利用改造着自然;另一方面自然规律也约束着人类的行为,自然资源会对人类生存发展形成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更会对人类产生负面影响。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结合互为作用的[13]。
李明华赞同马克思“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的观点。人实现了自然主义,同时自然界实现了人道主义,自然界在和谐社会中真正地复活,人与自然界在美好的理想社会中完成了本质的统一。社会和谐寓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之中。这是对人类理想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经典描述[12]。
曹孟勤认为,人与自然存在着两种基本关系:一是“浅层关系”,即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统一关系;另一是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即人类学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统一关系。人与自然的“浅层关系”将人等同或还原为生物性存在,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则是使人生成为人的关系,是在人之为人的价值上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是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它是人从中涌现出来成之为人。这意味着,人不仅存在着一个向社会生成为人的问题。即用自然来规定自己的本真存在,使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最终达到“天人合一”境界和“小宇宙”与“大宇宙”和谐状态。深层生态学反对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传统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赞同一种“形而上学的整体主义”。就是说,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分界线,现实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或者说是“无缝之网”,人与其他自然存在物都是这个无缝之网的网结。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应该是人与自然在本质或本性上的关系,而不应该是人与自然界的这种外在关系。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应该是人与自然在关爱生命上的内在一致,而不应该是人归属于自然界,成为自然界的成员。人向自然生成为人,简单说,人即自然,自然即人,才是人与自然的真正的深层关系。这种深层关系是由于人与自然在本性上达到内在一致。易言之,保护环境即保护人类,保护人类即保护环境[14]。
张纯成认为,人类中心论自产生以来,经历各具特点的历史发展阶段,即由“强式”到“弱式”的转变。强人类中心论由于是伴随着工业文明的成功形成的,它过分或片面强调人的作用和能动性,认为人运用科技成果可以解剖自然,从而使人的私欲无节制地得到膨胀。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主张人的意志决定一切,人对自然享有绝对的权力,人对其他物种具有绝对的支配地位。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忘却孕育、哺育人的自然的承载力,对自然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和征服。这种掠夺和征服是人在强人类中心论指导下所犯的错误。弱人类中心论的产生无疑是对人与自然关系恶化反思的结果,是人对自然进行掠夺和征服所造成的生存问题反思的结果。弱人类中心论的产生,说明人已经认识到片面强调人的能动性,必然导致环境的破坏,危及人的生存。非人类中心论的产生与生态危机直接相关,也是对当代社会面临困境质疑的结果。非人类中心论在对当代生态危机和产生的根源作了分析之后,认为日益恶化的全球环境是科技的“伟大杰作”,科技是破坏生存环境造成生态危机的“魔鬼”。在强调自然价值与权力的非人类中心主义阵营中,有痛苦中心论、生命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的区分。各种形态的非人类中心论,尽管侧重点不同,但在反对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方面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只有回到以大自然为中心的世界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非人类中心论对伦理的思索已经超越了人与人的关系,开始了人与物的思考[15]。
孙家驹认为,自从人类掌握使用和制造工具之后,利用自然过程向征服自然过程演变,人与自然同一关系也开始发生裂变,由与自然同一走向与自然对抗。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由同一走向对抗,源于社会生产能力水平的提高和对自然的幼稚认识。生产力水平的一定提高使产品开始有了剩余,对剩余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人类社会内部发生裂变,由原始共同体的同一走向阶级的对抗。生产力水平的一定提高,使剩余产品的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成为可能,促进了人的智力开发活动。人类需要解释他们所面临的一切,社会和自然开始作为对象来研究,将自然现象超自然化、神秘化、拟人化、实用化以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结构作辩护的思想文化体系开始形成[16]。路日亮则批判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都是错误的。构建和谐社会,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然自然界不能满足人的需要,人就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人的劳动使自然界更加适合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17]。
对此,王正平进一步指出,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处于积极的占主导地位的永远是人。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化的是人,扭转这一紧张化趋势的也只能是人,人具有合理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部责任和义务。人作为自然中的人,作为自然史中的人,不仅应当承担他在社会中的道德责任,更应当承担他在自然界中的道德责任。将人置身于自然中,把自己视为“自然—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人类应当从自然的征服者转变为生态共同体的平等“公民”。因而他的道德责任不仅是公正、仁慈地对待他人,尽力增进社会整体的利益,而且要尊重生态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把是否有助于生态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作为评判自身行为的善恶准则[18]。
三、 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对于如何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学界也见仁见智。自人类从自然界诞生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就随之产生并不断演化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与自然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类走过原始社会、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正在迎来信息社会。同时,源于自然的人凭着自身不断增强的力量,企图超越自然界限,在对自然漠视与疯狂掠夺中企图驾驭、控制、主宰自然。然而如罗马俱乐部倡导者佩西所说,我们继续不屈地攀登,不知道究竟是在开创有决定意义的新的历史里程碑呢,还是在挖掘自己的墓穴。人类要缓解生态危机、摆脱生存危机,根本出路就是调整并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19]。
方世南从政治学维度审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时认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说,人与自然能否和谐,已经是关系到我国的现代化事业能否持续进行,小康社会建设能否达到全面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能否成功,社会主义道路能否畅通无阻,生产力和文化的先进性能否体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达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否得到保证的重大政治问题。要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状态,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促使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政党和政府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都必须具有强烈的生态政治意识,要从政治学的高度充分认识生态环境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特殊价值,人与自然和谐对于社会全面和谐以及持久和谐的重要性,充分认识生态环境危机会引发的一系列严重的政治问题,进而把政治与生态环境有机辩证地统一起来,使政治发展的过程成为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的过程;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的过程也就是政治不断发展的过程。在政治绿色化和绿色政治化的双向运行中,促使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项事业的不断进步。生态问题说到底是人的问题。人是生态环境危机的始作俑者,也是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实践主体。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不仅需要政党和政府将生态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予以重视,更重要的是需要亿万公民的共同参与和支持,开展一场以公民的绿色政治参与和制度创新为内容的绿色政治文明建设。在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的态势下,生态政治实质上已经超越了国界,成为跨国间的政治。解决生态问题需要世界性的视野。只有加强国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整合国际上各种生态政治力量,才能以全球性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态势,促进国内和谐社会的建设[20]。
李明华指出,当代生态危机警示我们,以往的文明模式,即工业时代的文明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代人类的实践,已经无法正确处理当代人和自然的关系。尽管在“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思维方式下人们可以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而善待自然,可以采取某些措施阻止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发生,但是由于工业文明模式的内在局限和缺陷,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球性、整体性的生态危机。正如人类历史上经历过狩猎与采集文明、农耕文明的先后更替一样,工业文明的时代已经走向衰落,过时的文明形态必须终结,而应该代之以新的、生机勃勃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需要说明的是,人类必须结束的是一种产生危机的文明观,而不是文明的历史。人类文明的历史是一条连绵不断的长河,每一种新近的文明形态都是对前一种文明形态的扬弃。生态文明对工业文明既有否定也有承续。工业文明时代所创造的辉煌的科学技术、伟大的思想理论、不朽的艺术成就和空前的社会发展,我们必须充分肯定和继承。但是工业文明时代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我们却要进行清理,特别是那些关于要做自然的主人、要主宰和控制自然的思想,需要进行根本性改造。因此我们要终结的是一个时代的文明模式,而人类文明的历史是不会终结的[12]。
欧阳志远主张在意识形态进行改变。环境意识也称生态意识,它是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的解决社会和自然关系问题方面所反映的观点、理论和情感的总和。这种意识的核心是对自然资源利用方式的反省,它的上升会促使人类重新审度自己的思想、行为和人生的意义,进行自我评价。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社会冲突问题最后都可以在自然资源的占有问题上聚焦。当人们认识到生态危机的本质、进而认识到自己活动的结果不是增强了自己的主体性,而是成为实现自由的桎梏时,贪图财势的价值观念就会逐渐淡漠,而社会的公共利益也会日益受到重视。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从西方社会开始,在公众中萌发滋生了一种淡化物质享受、追求生态平衡的精神寄托,这种精神寄托无论对人地和谐还是对人际和谐都是极其有利的。实际上,就是在民主和法制比较健全的西方国家,人们也认识到了生态寄托对规范人的行为、进而对实现社会和谐的重大作用。我国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生态寄托应当得到更完整的建树[11]。
许海波等人认为,要积极发展绿色产业,大力推进现有产业的绿色化改造,努力倡导绿色消费。所谓绿色消费是指人们在环境友好理念的影响下所进行的有利于资源保护和生态平衡的,或者不至于恶化资源供求关系和生态环境的消费[21]。罗尚贤指出,自然生态的失衡和社会生态的失衡,归结起来就是天下之“和”遭破坏,天下生机受损伤。在此文明断层的险境中,当代的先进智士们挖掘几被埋没的和生理念,揭示生态平衡规律并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工业文明土壤中萌发的新质因素。促使人类以和谐生衍为基础的和生文明在不断涌现。和生文明的根本特征是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消除人间对抗,造成互助友爱,调节人与自然平衡发展[22]。
在发展观方面王志禄指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发展观,强调人与自然发展的各个方面的配合适当,这内在决定了它是一种适度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观。首先,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一种适度的发展观。从总体上讲,发展必须尽量减少和消除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能源及资金的不必要或收效很小甚至是负效应的投入,确保有限的资源能够满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必须要保持适度的人口数量、合理的人口布局和人口生产,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历史经验表明:只有人类合理适度地利用自然界,与自然处于平等、互利、和谐的关系,自然才能为人类提供祥和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才能维持和发展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其次,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一种协调的发展观。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还必须做好区域的协调、国际的合作和利益协调,保证人与自然的态度、标准、尺度的统一和公正、公平。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是要在发展的出发点和目的上,协调人对自然的各种需求和利益,满足人的合理性的需求,压抑和禁止不合理的和过度的需求,要从全国人民、全人类的利益出发,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限制少数人的利益及少数人的不正当利益追求,同时兼顾方方面面的利益,解决好方方面面的矛盾;在发展的过程中,协调好人口增长与资源开发、环境利用的关系,解决好自然的公共性与主体活动的自私性的矛盾,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统一。再次,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一种可持续发展观。要科学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一方面,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必须尊重各种自然规律,并在发展中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利用和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另一方面,人是社会的存在物,所以人的活动还必须尊重各种社会规律,实现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最后,要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综合手段约束人对自然的行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既需要主体遵循各种自然社会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需要主体从自身及其自然社会实际状况出发树立现代科学自然观,更需要现代化主体不断反思自身行为的合理性,自律自控自身行为主动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它是一个主体能动与受动、目的与手段统一发展的过程[13]。
我们认为,主客体思维方式的转换在当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生态主体是人,生态客体是自然界(包括作为生物存在着的人)。从认识论角度讲,认识主体是从事着生态—社会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人,认识客体是进入生态认识主体和实践领域中的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包括作为认识客体或对象存在着的人)。从实践角度而言,是对生态客体既利用和改造,又保护和建设的生态主体,以其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最佳的生态效益的过程。而把具有社会属性并作为生态主体的人,仅从生物属性切入降格到和其他生物一样而提出的所谓泛主体论,在哲学层面上是很难站得住脚的[23]。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标志着我国发展观的重大变革。而这一重大变革是在人们对传统发展观的内在缺陷及其在实践中的巨大负面效应的深刻反思过程中实现的,其实质是人们关于经济-社会-生态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念的全面性更新和创造性转换。有理由相信,人类通过不懈努力,能够真正摆脱愚昧无知,科学处理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开创更加美好的生态文明与和谐发展的新时代。
[1] 郑慧,王义宝.试论意识形态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和意义[J].政治学研究,2005(4):6-10.
[2] 于语和,刘志松.“和谐社会”溯源[J].新华文摘,2007(9):159.
[3] 李中华.“和”论[J].新华文摘,2009(1):41-43.
[4] 季羡林.和谐是中国文化的精髓[EB/OL].http://news.xinhuanet.com/2007-04-23.
[5] 邓伟志.论“和谐社会”[N].学习时报,2005-01-03.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7] 安启念.和谐马克思主义:一个被长期遮蔽的视域[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3):81-90.
[8] 潘岳.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N].科技日报,2006-07-07.
[9] 包庆德.生态哲学维度:环境教育与人的生态意识之提升[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1):41-48.
[10] 包庆德.生态文明:技术与能源维度的初步解读[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2):34-39.
[11] 欧阳志远.论生态寄托的社会协调功能[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6):9-16.
[12] 李明华.和谐社会中的人与自然[J].学术研究,2004(11):5-9.
[13] 王志禄.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哲学意蕴[J].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38-40.
[14] 曹孟勤.人与自然“深层”关系辨析——从深层生态学出发谈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5-9.
[15] 张纯成.天人关系与人的生存[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7):11-13.
[16] 孙家驹.人、自然、社会关系的世纪性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2005(1):113-119.
[17] 路日亮.对自然、人和社会和谐发展的辩证思考[J].哲学原理,2005(12):15-19.
[18] 王正平.环境哲学: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智慧之思[J].新华文摘,2006(16):36-38.
[19] 王茵.当代人与自然关系的若干思考[J].湖北社会科学,2004(12):100-101.
[20] 方世南.从生态政治学的视角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J].政治学研究,2005(2):41-48.
[21] 许海波,丁宪浩.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积极建设生态文明[J].理论界,2005(6):14-19.
[22] 罗尚贤.论和谐社会与和生文明[J].学术研究,2004(11):10-13.
[23] 包庆德.生态哲学十大范畴论评[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7):73-79.
HarmonyBetweenManandNature:ResearchDevelopmentinEco-harmonyofHarmoniousSociety
BAO Qing-de, PAN Li-li
(School of Philosoph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1, China)
Global eco-crisis makes the theme ‘eco-harmony’, which inncludes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o be much more concerned and reflected on. The eco-harmony from ‘social harmony’ to ‘natural harmony’ is extremely important eco-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 foundation to construct socialistic harmonious society. In this sense, society without eco-harmony is not the harmonious society in its true significance. In modern times, eco-environment factors and natural resource factors extremely influence people’s value systems and constructive level of harmonious society. From eco-philosophical dimension, it has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oughts of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society,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natur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harmonious society; man and nature; eco-harmony; scientific development; harmonious development
N031
A
1009-105X(2009)02-003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