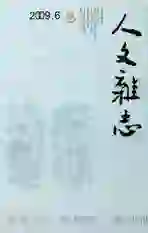唐代河东承天军史实寻踪
2009-01-18贾志刚
贾志刚
内容提要 被传世文献忽略的唐代河东承天军的历史踪迹在几份唐朝碑志中留下痕迹,通过碑志与文献的互证,可以发现河东承天军是在唐朝河朔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后组建而成,其兵数消长、军职编制以及战略地位的变化,反映着唐政府与河朔藩镇之间的微妙关系。尤其是前后相差十年的唐《承天军城记》与唐《妒神颂》二碑所保存承天军较为完整的武职题名,介于开元兵制向藩镇兵制过渡的关键时期,对考察唐朝基层兵制的变化轨迹有着相当学术价值,值得学界充分重视。
关键词 唐朝 河东道 承天军 基层军职题名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6-0124-07
唐大历元年(766)胡伯成所撰《铁元始像赞》、《承天军城记》,(注:陆耀遹:《金石续编》卷8,潜丘道士胡伯成《铁元始赞并序》原注:“高三尺五寸,广五尺二寸,前刻《铁元始赞》,后刻《承天军城记》,并行书,《赞》字八行,行三十一字至三十四字不等,在山西平定州东北九十里娘子关坡底老君庙内。”《承天军城记》原注:“此刻《赞》后,行书,三十三行,行三十字至三十三字不等,石缺下方右角,在山西平定州。”又见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7,等。)大历四年无名氏所撰《张奉璋墓志》,(注:《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历010《唐故河东节度使右厢兵马使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文安郡王张公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98页。)大历十一年李諲所撰《妒神颂》,(注: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64《妒神颂并序》原注:“碑立在平定州娘子关。”第441页;又见于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7,陆耀遹:《金石续编》卷8等;董诰:《全唐文》卷408,只收录正文,删去题名。)长庆元年(821)河东节度使裴度等59人的摩崖石刻题名等,(注: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8,舒元舆《裴度等承天题记》原注:“摩崖刻石文左行,凡四段。字大寸许,就拓本量之,广一丈,高二尺九寸,记文十四行,行二十字至八字不等。题名裴度名题两行,自卢恽至通事舍人。又行题两名,共四十五行,行三十二字至九字不等,今在平定州。”正文又见于陆心源:《唐文续拾》卷5,但无题注,无59人题名。)五块石刻资料都涉及到唐代河东承天军的史实,碑刻资料所记承天军及其创筑者张奉璋的情况,不仅可以补正传统史籍的相关记载,还提供了重要的专题研究史料,更为难得的是《承天军城记》与《妒神颂》二碑是同一军府不同时间的题名,各自记录了所处时代较为完整的军府武职序列,使考察唐朝基层军职变化轨迹成为可能,属于学界孜孜以求却不得其解的领域。从各方面衡量,这些碑志所显现的学术价值仍有重新强调的必要,今略加考述,就教于方家同仁。
河东承天军始末
《新唐书》特别注意记载唐朝军府布防情况,如《兵志》不厌其烦地罗列唐朝前期全国80军之名称,其中河东道列出四军,但没有提到承天军。(注:《新唐书》卷50《兵志》,河东道有天兵、大同、天安、横野军四,1975年版,第1328页。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卷2,认为天安军当为大安军之误,苛岚守捉应为苛岚军,还有和戎军、静难军等。未提及承天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2-49页。)而《地理志》各条又多出中唐以后所增加的47军,属于河东者三,仍然没有提到承天军,其他史籍亦然。(注:《新唐书》卷39《地理志》记河东新设三军分别是:乾元二年设置的河中耀德军、永泰元年的代州代北军和贞元十五年的蔚州清塞军。另《唐六典》卷5,《唐会要》卷78,《通典》卷172,《元和郡县图志》卷13,《旧唐书》卷38,《资治通鉴》卷215,《玉海》卷138,等,均记载了河东道军府的设置、布防,却没有提及河东承天军。)故《承天军城记》等碑中关于河东承天军的记录可补史缺。
传世文献于河东承天军虽有提及,但多是只言片语,其始末原委似乎已无从得知,幸而赖几份石刻资料始可得见其创设之事。据唐人胡伯成所撰《承天军城记》载:
时元戎蓟公……申命开府张公奉璋严戎式遏……遂度地势,笼山截谷……城成,帝嘉之,号“承天”,信承于天也。
据碑末所记知此碑于大历元年(766)撰立,追叙安史之乱中河东道奋力抵抗叛军之功业,着重记载河东节度使命令张奉璋在井陉故关筑城设防,并由皇帝御赐承天军名。据此可知,筑城在先,赐名承天在后,但筑城的具体时间或者承天军建军的时间都未予交待。联系前后文,知碑文中“蓟公”应为李光弼。李光弼在至德元载(755)到乾元二年(759)曾任河东节度使,(注: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4,河东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12-413页。)故其城应在这期间修筑,但确切的筑城建军时间仍无法确定。
检《册府元龟》卷180《帝王部•失政》记:“肃宗至徳二年六月,将军王玄荣杀本县令杜徽,罪合死。帝以其能修守备之器,特放逸,令于河东承天军效力。”此条涉及承天军的材料有明确时间记载,可能是关于承天军的最早记载。此事司马光《资治通鉴》也有记录:“将军王去荣以私怨杀本县令,当死。上以其善用礮,壬辰,敕免死,以白衣于陕郡效力。”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特别提到:“《实录》云:‘于河东承天军效力。据《贾至集》,陕郡也。”(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9,唐肃宗至德二载六月条,1956年版,第7026页。)此仇杀县令的将军名字,诸书多与《通鉴》相同,是王去荣,而非王玄荣。(注:《旧唐书》卷119《贾至传》:“至德中,将军王去荣杀富平令杜徽,肃宗新得陕,且惜去荣材,诏贷死,以流人使自效。”1975年版,第4298页。《文苑英华》卷619,贾至:《论王去荣打杀本部县令表》:“臣某言:伏见宰臣奉宣圣旨,将军王去荣擅打杀富平县令杜徽……缘新收陕郡,防遏要人,特宜免死,削除在身官爵,白身配陕郡展效者。”第3211页。均记为将军王去荣。)据此可知,王去荣免死效力之地应当是陕郡,并非河东承天军。虽然《册府元龟》此条的记录可商可议,但司马光的意见却印证了《册府元龟》上揭材料来源是《实录》。此《实录》当是唐《肃宗实录》。不管王去荣是免死效力河东承天军,还是陕郡,至德二年(756)就有承天军被《实录》提到,对于确定承天军的建军时间有重要的启示。
虽然河东承天军之名出现在《实录》中,却因本条材料有不实之处,材料的可信度就会遭到质疑,且记承天军出现在至德二年仅此一条,也有孤证不立的嫌疑。幸而《唐故河东节度右厢兵马使……张公(奉璋)墓志铭》及时提供了关于河东承天军的又一记录,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墓志载:
至德中……(张奉璋)充承天军使,其城即公之所创也。密迩就敌,城孤援绝。
与《承天军城记》所记相比,张奉璋也曾任承天军使、河东节度右厢兵马使等职,可以肯定墓志中的张奉璋与《承天军城记》的立碑者张奉璋系同一人。《墓志》所言“其城”,当指承天军城,并确言张奉璋乃其城的始创者,且记载筑城时间为至德中。因为唐肃宗至德三载就改元为乾元,故所言张奉璋在至德中任承天军使,应当为至德二年前后,恰与《实录》所记时间相符,说明河东承天军筑城、建军时间应该在至德二年前后。
《承天军城记》碑文又提到与承天军城相配合的其他防御设施,“又于黄沙路筑德化城,示怀也;慕荣隘筑灭胡城,示威也;复联建三堡,绝细径也。”可知,张奉璋在修筑承天军城的同时,还修筑了德化城、灭胡城,另修建三个堡垒,形成三城三堡的防御格局。
综上所述,河东承天军城是至德二年(756)张奉璋奉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之命在井陉故关修筑,由唐肃宗赐名“承天”。
河东承天军驻防于张奉璋修筑的承天军城内,此军规模如何,诸书均未记载,虽《承天军城记》中稍有提及:“设以楼橹,实以军府”,“铁骑千匹,虎贲万计”是讲承天军筑城而守,拥有士卒上万,骑兵千人,但碑文是确指还是虚言,有待细审。
传统文献虽没有直接记载承天军兵额多少,却记了其建军前的情况,《资治通鉴》卷217,唐肃宗至德元载二月条:“时常山九县,七附官军,惟九门、藁城为贼所据。(李)光弼遣裨将张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余皆三百人戍之。”据此所知,张奉璋只有500人,即使把七县守兵都算在一起也才有2300人,尚不到3000,何谈万计呢?也许2300是承天军的未建军时的规模,上万人是组建后的规模。据《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条:“诸军各置使一人,五千人已上置副使一人,万人已上置营田副使一人。”注曰:“五千人置总管一人……一千人置子将一人……五百人置押官一人”。《承天军城记》碑末现任军职的题名中,不仅有副使之职,也有营田副使之职(详下)。营田副使的设置规定证明承天军的规模应该在万人以上。还有,石碑题名共有将职10名,分别是“将”9名与“子将”1名,且子将排在其中第3位,看不出子将与将有何区别。据上揭《唐六典》文,子将领兵千人,如果将职都按子将的标准,10名将可领兵万人,也与碑文中“铁骑千匹,虎贲万计”相接近。由上所推,河东承天军大历初兵额万计大体接近事实。
《承天军城记》碑立于大历元年(766),距承天军建城已有十年,建军前后变化很大,但此后承天军有何变化,不得而知,幸而另有碑刻、文献资料有所涉及,可以帮助了解承天军此后的存废情况。
首先要提到的是刻于唐大历十一年(777)唐人李諲所撰的《妒神颂》。碑中提到:
我承天军使节度副使……上柱国党公讳升,镇兹巨防……(铭曰)光我承天,井陉西南,太原东北,妒祠之水。
据碑文知承天军使党升祭祀妒女祠并为之立碑刻颂,此举是否属于淫祀之范畴,与本题无涉,暂置不论。而首任承天军使张奉璋也有树碑立像的记录,只不过他崇拜的是元始天尊。张奉璋塑元始像的举动在大历元年所刻的《铁元始像赞》碑中有记录:
河东节度兵马使开府仪同三司张公……志清国难,戍此累霜,初则环山作城……遂锐精足巧,范铁装金。
此《铁元始像赞》与前提《承天军城记》刻在同一块碑上,大致记录了河东节度兵马使张公范铁塑像,并请人题赞刻石的经过。此河东节度兵马使张公也许就是前揭《承天军城记》上以河东节度兵马使兼任承天军使的张奉璋。承天军使张奉璋既筑城,又塑像立碑,二者其实是统一的,因为他想借塑像立碑以祈求承天军城能够“守则固,战常克”,也从“张公范金列于此,保国宁家千万祀”之语中反映出来。前后两位承天军使都有祈祷刻碑的举动,反映了当时官兵在战乱年代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对此《妒神颂碑》的作者李諲有精辟概括,“君依神以徼福,神依君以庇躬,事势相因”。我们不管二位承天军使的意图如何,其所立的三块石碑均证明唐代承天军对保卫北都太原发挥着重要作用。(注:杨志玖:《娘子关与娘子军》,《历史教学》1983年第3期。纠正相关地方志、工具书误将娘子关与唐代平阳公主联系的说法,认为娘子关之名称与妒女祠有关。)
另一块要提到的碑就是原刻于山西平定的唐长庆元年(820)摩崖石刻文。此摩崖石刻因涉及唐河东节度使裴度等59人的题名而称为《裴度等承天题记》,此题记留下关于长庆年间承天军的些许信息,今摘录其中与本题有关者,
有唐长庆元年……冬十月,师次于承天军……凡五十九人,列于承天军城西石壁。(注:缺文据陆心源《唐文续拾》卷5,舒元舆《承天军题名记》补,加囗。)
文中一次提到承天军,一次提到承天军城,特别是在59人的题名中有:
右押牙兼承天军都囗囗囗囗殿中侍御史赵囗囗。
此赵某可能就是长庆年间承天军的指挥者。裴度屯军承天军城之事也见于文献记载,(注:《旧唐书》卷142《王廷凑传》长庆元年十一月:“裴度率众屯承天军,诸将挫败”。第2886页;《新唐书》卷211《藩镇镇冀•王廷凑传》:“裴度以河东节度使兼幽镇招抚使,屯承天军”。第5960页。)而摩崖石刻文所记录的包括承天军使在内的59人的具体官职却独此一处,此文是研究唐朝中后期行营制度的第一手材料,因于本题无关,暂置不论。题名中既提及承天军,又提到承天军城,还提及承天军使,更说明承天军在长庆元年不仅依然设置,且建制完整,仍旧发挥着重要军事作用。
在前揭诸碑所记的大历与长庆之间,白居易所草拟的《与希朝诏》中也涉及到承天军的情况,正好可弥补其缺。诏文记:“敕希朝,省所奏,请自部领当道兵马一万五千人,取蔚州路赴行营,并奏土门及承天军各添兵士备御者。”(注:白居易:《白居易集》卷56《翰林制诏三•与希朝诏》,第1175页。)此诏可能是发给河东节度使范希朝的,范氏任河东节度使在元和四年到五年间(809-810年),(注:《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元和四年六月条:“以灵盐节度使范希朝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第428页。元和五年十一月条:“王锷……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第433页。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4,河东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21页。)诏文特别指示承天军添兵加强防御,也反映出元和年间承天军是河东防御的关键要地。
承天军经唐末五代,一直存在,后唐有康福,后周有翟守素曾先后担任过承天军使,(注:《旧五代史》卷91《康福传》:“少事后唐武皇,累补武职,充承天军都监”。第1200页;《宋史》卷274《翟守素传》:“历汉、周,迁供奉官,领承天军使”。第9362页。)到北宋升“娘子关为承天军”,后来又以“承天军为寨,属平定县”。(注:《资治通鉴》卷242,唐穆宗长庆元年十月条:“裴度自将兵出承天军故关以讨王庭凑。”胡三省注曰:“(宋朝)以承天军为寨,属平定县。”另引宋白曰:“承天军,太原东鄙,土门路所冲也。”第780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宋太祖建隆元年(960)条:“升镇州娘子关为承天军”。)承天军仍作为北宋的军事镇守要地,只不过改名为承天寨罢了。
综上所述,兵数一度达到上万的河东承天军及所筑军城,从唐朝至德二年(756)初建,经大历、元和、直到长庆元年(820年),均为河东军事防御要塞。事实上,其存在时间历唐、五代至北宋,长达二百余年。曾经是中唐以来中央政权与河朔藩镇的必争之地,也成为五代以来抵御北方民族南犯的咽喉要道,竟然在详载唐朝各道军府的诸种文献中缺名不载,令人费解。幸好几块石刻资料的传世,又让复原承天军这段历史成为可能。
承天军武职题名对于探索唐朝基层军职变化的价值
唐朝基层军职尤其是中唐以后的基层军职变化很大,但是,现存各种典籍对这种变化却关注不够,令读史者于此多生疑义,唐代《承天军城记》和《妒神颂》两碑所附军职题名,对考察唐朝基层军职前后变化轨迹有一定价值,兹考述如下。
唐长孺先生曾就唐代军事制度变化问题发表了大量的论著,指出唐朝军事制度由前期征兵制向募兵制过渡,进而发展成后期藩镇兵制,雇佣化、职业化、终身乃至世袭化。(注:唐长孺系列论著:《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国立武汉大学社会学季刊》1948年第1期;《唐西州差兵文书跋》《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吐鲁番文书所见的西州府兵》《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唐书兵志笺正》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与此同时,军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基层军职也经历着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有军职序列的改变,也有职能职守的变化。
唐初沿袭西魏北周以来的府兵之制,几经变化之后,“贞观十年,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诸府总曰折冲府”。(注:《新唐书》卷50《兵志》,第1325页。)以折冲府为基本单位,“每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别将一人,长史一人,兵曹一人,校尉六人”。(注:〔唐〕杜佑:《通典》卷29《职官十一》武官下折冲府条,第810页。)其基层指挥系统包括折冲都尉、果毅都尉、别将、校尉等职级。自唐高宗、武后以来,直到唐玄宗开元时期,府兵制日渐崩坏,天宝八年(749)折冲府均无兵可交,但其兵额、官吏仍存,(注:《新唐书》卷50《兵志》,第1327页。)原来府兵的基层指挥系统如何向募兵制官职体系过渡,未见明确的记载。
唐代开元时期的基层武职在成书于开元二十七年(739)的《唐六典》中有较详细的记载:“诸军各置使一人,五千人以上有副使一人,万人以上有营田副使一人……凡诸军、镇每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一千人置子总管一人,五千人置总管一人……若讨击、防御、游奕使、副使。”诸军武职因所辖兵额的多少有不同,具体有军使、副使,有营田、讨击、防御、游奕使和相应副使,有总管、子总管(子将)、押官等。可知开元时期的军职已与唐初府兵制下的军职有很大差异。(注: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认为开元军将序列由前期行军制度转化而来。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孙继民:《关于唐代前期行军中押官一职的探讨》,《河北学刊》1991年第6期。)而《唐六典》在记录以上文字时,所附注文中透露出前期府兵制向开元兵制过渡转型的些许信息,注曰:“五千人置总管一人,以折冲充;一千人置子将一人,以果毅充;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以别将及镇戍官充”。“副使、总管取折冲已上官充,子将已上取果毅已上充。”(注:《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条,第158-159页;又《资治通鉴》卷211,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六月条,胡注:“子将,小将也。唐令:制每军大将一人……副二人,分掌军务……判官二人,典四人,总管四人,二主左、右虞候,二主左、右押衙……子将八人,资其分行阵,辩金鼓及部署。”第6719页。但不知何据。)以府兵制下的折冲、果毅、别将等军职充任开元新兵制下的总管、子将、押官之事,正是旧兵制向新兵制转型的痕迹,也是由府兵制编制转为募兵制序列的痕迹。虽然此后府兵制下的军职仍偶有存在,却并不影响基层武职的总体转型。
安史乱后,唐朝武职军将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严耕望等先生曾经予以专门研究,(注: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唐代府州僚佐考》,均载于《唐史研究丛稿》台湾新亚出版社1969年版;日野开三郎:《唐代藩镇的支配体制》,《东洋史学论集》第1卷,三一书房1980年版;张国刚:《唐代藩镇军将职级考略》,《学术月刊》1989年第5期;王永兴:《关于唐代后期方镇官制新史料考释》,载于《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荣新江:《唐五代归义军武职军将考》,载于《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杜文玉:《晚唐五代都指挥使考》,《学术界》1995年第1期:冯培红:《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武职军将研究》,载于《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冯培红:《敦煌文献中的职官史料与唐五代藩镇官制研究》,《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冯金忠:《唐后期地方武官制度与唐宋历史变革》,《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等。)但多集中于藩镇或州府武职军将,并未触及基层的军镇武职转型,特别缺乏各种军职以完整序列形式出现的资料,这种资料在《承天军城记》和《妒神颂》碑末题名中找到了,这些题名是军府职掌的实际情状,反映基层军职阶段性变化,也就提供了低层军职从开元兵制向藩镇兵制过渡的极好参照。虽然观察这种转变过程存在着相当难度,但把握基层军职的变化节奏更有助于认识唐代整个军事体制的演变规律。
《承天军城记》题刻时间是“大历元年(766年)”,碑末题名共17人,职务涉及承天军大使张奉、管乐囗副使王丕、节度经略副使陈遵峤、游奕副使同讨击副使吴庭珍、营田副使张如珪、防城副使廉明、都虞侯孙希晏,押衙(缺名)。另有将10人,分别是:步光庭、张鸾、武怀进(子将)、刘浩、王引、聂庭宾、曹龙兴、步元英,另二人有职缺名。
题名所见军职见于《唐六典》记载的有节度经略副使、游奕副使、讨击副使等,超出《唐六典》的有防城副使、管乐囗副使。其中管乐囗副使因缺字难以通解,暂且存疑。其次,题名中都虞侯、押衙也是《唐六典》未提及的新职。专职副使的增加,新职名的出现,预示开元新兵制也在发生变化,显示出唐朝基层军将职名正在经历又一场变化。再次,题名所记将职最多,如果把其中名字无考的二人算上,正好十人。这些将职,与上提总管、子总管有何关系?尚待通解。因题名中有“子将武怀进”一条,前揭《唐六典》正文记一千人的指挥者是子总管,而注文却记为子将,似乎千人子总管可以称为子将,那么,此碑之“子将”与《唐六典》之千人子将可能为一种军职。此“子将”与其他人的“将”是什么关系,有待研究。(注:杨铭:《吐蕃“十将”(Tchan bcu)制补证》认为吐蕃占领敦煌后(八世纪末),在各部落下设十将,左一到左十,右一到右十,且左十将与右十将分属不同部落。还提到吐蕃十将与千户长的关系,十将径称子将的现象,以及吐蕃本土十将制与占领敦煌后十将制的不同。(《中国藏学》1996年第2期)。)还有,承天军中十员将职与唐中后期武职军将中常设的“十将”如果不是偶然的巧合,(注: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6《阵图》太白营图篇:“一将一千人,十将一万人……十将幡旗,图会五色,五行列。”分别分成左、右五将:左一将到左五将,右一将到右五将。又教旗图篇:“乃命十将、左右决胜将,总十二将,一万二千人……分为左、右厢,各以兵马使为长。”(此条杜佑《通典》卷149《兵二》法制条转引,但稍有不同),左、右厢兵马使各领左、右五将,可知兵马使与十将的关系。同时,十将与左右决胜将并列,显示十将之外更有他将,也是将职编制突破十员的萌芽。荣新江《唐五代归义军武职军将考》认为晚唐方镇地方军每军共有十将,十将是将头的总称。(《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76-87页);齐陈骏、冯培红《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政权中“十将”及下属诸职考》认为十将是将职之一而非十员将校,其下面分设左右厢十将头。(《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35页)。个人认为十将是职名,其编制由起初十员将职逐渐发展成多少不定。)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妒神颂》的题刻时间是大历十一年(776年),碑末题名共27人,分别是承天军使党升、副使同经略副使廉明、游奕副使步光庭、都虞侯王昙;将职10人,其中将3人:杨进朝、张鸾、聂庭宾;散将7人:刘浩、马崇敬、崔元英、蔡希滕、梁昱、巨超俊、葛日新;判官、节度逐要官3人:许勉、郭崇隽、辟闾珣;孔目官张崇珍,节度随身官燕润国;副将3人:孟太津、曹龙兴、郭季膺(丰川府折冲);衙官姚庭秀、刘成广;总管囗囗僧,窦光超,陈超等。
此碑也为河东承天军所立,与《承天军城记》碑相隔十年。相较前碑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些变化,具体可概括为三方面:一是人员调整变化大,不仅承天军使变成了党升,各级军职的变化也很明显,其中有6人之名两碑俱载,其职务发生变更的有4人,(注:《承天军城记》与《妒神颂》两碑题名中均出现者比较表
步元英和崔元英可能是同一人,其他人均不重复,即保留的6人是原武将编制17人的不到1/3;只是新序列27人的不到1/5,其余都换成新人。
二是军将职名也有变化,除承天军使外,前碑有管乐囗副使、营田副使、防城副使、讨击副使,后碑只剩下节度副使、经略副使、游奕副使。都虞侯前后碑都有。将职前碑是10人,后碑则区分为将3人、散将7人和副将3人,共13人;前碑有押衙1人,后碑未见,但有衙官2人;后碑有总管3人,还有其他职名如判官、节度逐要官、孔目官、节度随身官等。从其中职员变化来分析,后碑营田副使的缺失,说明承天军在大历十一年兵数可能已不足万人,但在兵数减少的情况下,承天军的武职却由17人增加到27人。因为名额的增加,必然对职位造成影响,不仅在旧职名上增加副职,也增加散职,更添不少新职名。
三是武职序列发生变动。从题名排列顺序来看,明显是按职级自高而低排列,排在最后的居然是太原府丰川府折冲郭季膺和三名总管:囗囗僧、窦光超、陈超。按前引相关材料,在唐初府兵制下,折冲府中折冲都尉是长官,即使进入开元兵制下,折冲也可充任领兵五千人的总管之职,当然总管在开元时代更是以领兵众多而职重位尊。但不论是折冲,还是总管,在大历十一年的军府题名中,只能名落碑尾,甚至于排在众散将、副将之后,这种现象反映出旧官职在新序列中变得无足轻重,或已经变成闲散杂任之流。昔日位重职尊的官职日益闲散化,许多因事而置的使职却成为身居要职的实力派。
唐人杜佑曾敏锐地把当时各种职掌分成官职和使职,“长史、司马及诸曹是曰官名,副大使、副使、判官乃为使职……参杂重设,遂为其例。”(注:〔唐〕杜佑:《通典》卷32《职官十四》都督条,第895页。)杜佑注意到使职的出现造成官制参杂重设的现象,但当时使职已无处不在,并且有使职排挤官职的趋势。同样问题基层军镇武职也存在,即基层军职的使职化倾向,这种倾向是临阵作战的暂时职名(行军编制或练兵编制)的制度化。唐人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记录各种布阵教战图,涉及到左右厢兵马使、兵马使、都虞侯、虞侯、押衙、十将等临阵作战职名,(注:〔唐〕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6《阵图》太白营图、教旗图、风后握奇垒图篇。)张国刚先生曾据此得出结论:“藩镇军将职级,本来就渊源于行军军将在战时的统兵体制,当行军变成镇军,总管制变成节度使制后,过去临战时才有的编制和职官便成了常设的正式职官。”(注:张国刚:《唐代藩镇军将职级考略》,《学术月刊》1989年第5期。)值得一提的是,《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的成书年代,孙继民先生认为可能在宝应二年(763年)到大历十四年(779年)间,(注:孙继民:《李筌〈太白阴经〉琐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期,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1985年。)正与二碑刻成时间(766年、776年)相近。现实军职与兵法阵图的一致性,证明二者都是现实的反映,是同时期的产物,也是军职由开元常行编制转向藩镇临阵编制的结果。
由上分析可知,至德以后,唐朝基层军职体系又经历了一次变化,主要表现为使职挤压正职的使职化趋势,临战编制取代常行编制的倾向,“为官则轻,为使则重”的现象,也体现在基层军职中。
二碑反映出来的基层军职体系也只是正在变化中的形态,还不是转型完成后的定制。如果从基层军镇职名的角度看,广明二年(881年)由满城县令王悚所撰的《开元寺陇西公经幢赞》保留了易州高阳军的武职体系,对于转型后的唐后期军府军职序列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所记高阳军军职有:高阳军使李綖、副使张建时,军事判官摄易州长史郭筠,都押衙兼马步都虞侯石彦昭,讨击副使充军城都虞侯张审言,左厢兵马使吴棠,衙城都虞侯兼右厢兵马使王景芳。(注:陆耀遹:《金石续编》卷12《开元寺陇西公经幢赞》,注:在直隶易州……四行第八面。)虽说有4人是身兼二职,并不影响分析军职构成,据经幢题名知高阳军的武职序列为:军使、副使、讨击副使、军事判官、都押衙、衙城都虞侯、军城都虞侯、马步都虞侯、左厢兵马使、右厢兵马使等。与开元基层军职相比,军事判官、都押衙、各种都虞侯、各种兵马使均为新面孔。与上引二碑题名相比,都虞侯由一名变成了三人,押衙也变成都押衙,增加了左、右厢兵马使,或者还有都知兵马使、马步(都知)兵马使、十将等更多军将使职。(注: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唐代府州僚佐考》,均载于《唐史研究丛稿》台湾新亚出版社1969年版;张国刚:《唐代藩镇军将职级考略》,《学术月刊》1989年第5期;荣新江:《唐五代归义军武职军将考》,载于《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等。)这种情况既是使职差遣制对基层武职体系的影响,也是军职体系适应动乱局面的结果,由常行编制逐渐转向临战编制。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河东承天军在唐朝平定安史之乱时组建,此后,无论在唐朝推行削藩政策之时,还是姑息藩镇之时,承天军都起到对河朔强藩的防御和威慑作用,与唐代历史变化有密切联系。通过几块唐代碑志与传统文献的比较发现,前后相差十年的唐《承天军城记》与《妒神颂》二碑所保存的大历年间(766—779)承天军武职编制材料,介于开元兵制向藩镇兵制过渡的关键时期,对考察唐朝基层兵制的变化轨迹有相当学术价值,应该得到充分重视。因为这个时期正处于唐朝兵制变化最剧烈的阶段,此军府题名为观察唐中后期兵制转型提供了较为完整的阶段性参照资料。因而承天军这段历史因几块唐碑的记录而不致于湮没,值得庆幸。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