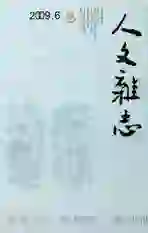我与国内理论界某些高层人士交往的若干回忆
2009-01-18徐博涵
徐博涵同志是我院一位退休的资深研究员。他的这篇回忆性文章,涉及到了他曾积极参与的一些重大的理论、历史问题,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若干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进程,故予发表,以供参考。
——编者
建国60周年、恢复建院30周年大庆已经来临。我从事专业政策、理论研究工作也近50周年了。在这个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日子里,我回想起了我与国内理论界某些老同志、老领导的交往旧事倍感亲切珍贵。现记录下来以免遗忘。
一
1960年9、10月间,我从北京调到了设在西安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从此开始了我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政策、理论研究生涯。我来西安不久,我国国民经济即呈现出了严重的困难局面。这时,毛泽东主席说了两句很有份量的话,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向农民寻求真理”,要“向马、列寻求真理”。研究室的领导向我们传达以后,我即开始研究、思索这些问题。不久,我随下乡工作组来到陕西省周至县哑柏公社的一个大队作调查研究,听取农民群众和农村基层干部对恢复农村经济、发展生产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也开始系统研读马、列的有关著作,特别是列宁十月革命以后的著作。在同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座谈中,我逐渐了解到,农民对如何才能度过难关的普遍看法是:只有实行包工包产到组,才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于是,我在工作组内讨论时,竭力给予支持。在系统阅读列宁有关著作后,我又惊讶地发现,原来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也曾极力提倡在农村建立共同占有生产资料,集体生产劳动,在公共食堂吃饭的农业公社。在农村组织公社,原来并不是什么“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人家列宁早就“创造”过了。但是,列宁很快发现,公社不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多数情况下,它们往往成了养老院”,于是决定把公社逐步解散。晚年病重卧床后,他又让其夫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从国家图书馆借来了许多国外和旧俄时期出版的有关合作社的专著阅读,最后,口述了一篇名为《论合作社》的重要遗著,主张以农民自愿联合耕作的合作社来代替农民公社。读到这些,我的心情十分沉重:难道党内和国内理论界的那些权威人士都不知道这些?出于一个共产党员和政策研究者的良心,我于是把列宁的有关论述摘编了一份资料呈送给有关领导。我的顶头上司接过资料大体翻了一下,就轻轻地对我说:“你敢搞这个材料!”就往他的抽屉里一塞,再不提这件事了。看来,他是觉得事关重大,为了保护我这个当时年仅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就有意识地把事情压下了。不久,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三自一包”的右倾单干风。这时,回想起这些往事真有点后怕。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纠正以往工作中的失误”,我从下放的地方回到西安的省社会科学院,才又重新检起了这个问题,更加系统、深入地作了一番研究,终于在1983年9月写成了一篇有关的学术论文《列宁〈论合作制〉的真谛》,打印后分寄给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老革命家杜润生同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社的负责人等。当时中央报刊还在大力宣传要坚持人民公社制度。论文寄出后,我还真有些提心吊胆。我与杜老以前素不相识,更无交往。没有想到,杜润生同志却在当年农历除夕亲笔给我写来一封短信,对拙稿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信中写道:“大作收到。甚有裨益。望进而结合我国情况,做点研究。至盼。祝工作顺利”。杜老的来信,是对我的莫大鼓励。我的心终于放下了。不久,我院的《人文杂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等,也先后发表了这篇论文。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刊复印资料还全文复印了该文。我的这项研究成果终于获得了各方面的承认和肯定。从此,我对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决心和信心更加坚定了,对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更加充满希望了。
不久,我又申报了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列宁晚期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获得了批准。为此,我在90年代初又被派往前苏联进行了一百天的学术考察访问,收集了大量有关资料,最终完成并出版了一本反映列宁晚年的思想和工作的学术专著《一份珍贵的理论遗产——列宁晚期思想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予以正式出版。该专著出版后,我带着该书亲赴杜老家中呈献,并对杜老说:“您对我的支持和嘱咐,现在以这本书来向您汇报。”90多岁高龄的杜老接过拙作,点头微笑,表示了高兴和满意。
二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我国理论界曾广泛运用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论述来论证我国和其他经济落后国家可以避免或跨越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然而,马、恩的有关论述究竟应作如何理解?他们所论说的“跨越”,条件是什么?主体条件是什么?客观条件是什么?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践检验结果又是怎样的?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实事求是地加以再研究、再探讨。经过一番全面、系统的学习和研究,我终于在1996年先后在陕西省委党校的《理论导刊》和中央编译局、中国共运史学会联合主办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谈个人学习、研究的一已之得、一孔之见。
个人认为,纵观马、恩有关论著,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论述,见诸于1881年2月底至3月初他起草的给俄国流亡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写这封信时,曾经反复斟酌,五易其稿,十分谨慎。关于“跨越”的提法,虽曾在草稿的初稿和第三稿中出现,但在最后定稿时都全部删除了。他并且在定稿中写道:“很遗憾,我对您尊敬地向我提出的问题不能给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的答复”。这封复信在马克思生前始终没有发表,只是到1924年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出版时才予以公布。在最终的定稿中,他只是表示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下同,从略〉第19卷第268—269页)
统览马、恩有关论述,其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1881年2月16日查苏利奇的来信中说:“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你会明白……你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是多么引起我们的注意”。(《马恩全集》中文第19卷第637页)因此,马克思的复信,首先是要答复查苏利奇在来信中提出的问题,否定某些打着马克思的“真正的学生”的旗号,以“历史必然性”为由从“左”的方面宣称公社“注定要灭亡”的观点。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是通过各种“偶然性”而发挥作用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马恩选集》中文第一版〈下同,从略〉第4卷第393页)在论述俄国农村公社命运问题时,马克思一再强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二)马、恩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实现直接过渡的论述,是就俄国农村公社制度而言的。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在每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形态,从横断面上来看,并不是单色的,而往往是多色彩的,是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的局面,只不过是其中某种占据着主导地位或者优势地位而已。当马、恩论述俄国农村公社制度命运的时候,他们当然十分清楚,当时的俄国,封建地主“霸占着将近一半土地,而且是优等地”,还有“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剥削已经“渗入公社内部”,更不用说沙皇的专制独裁统治了。马克思在谈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时,并不是笼统地讲俄国,而只是把俄国的农村公社制度单独地抽出来,研究它在当时背景下可能的发展及其条件。马克思认为,俄国当时的农村公社制度具有土地公共所有和个人小块使用这样的二重性,属于由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阶段。农业公社天生的这种二重性使得它的发展只能是: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马克思所说的“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等,看中的是农村公社这种二重性中的土地公有制,不能随意扩大理解。马、恩并不支持俄国农业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把俄国农民描绘成为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使之与西欧工人社会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相对立。马、恩有关“跨越”的论述,强调的是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特定的条件。(三)涉及的条件有:1蔽鞣椒⒋镒时局饕迳产的存在和发生危机;2蔽髋肺薏阶级取得了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生产资料公有代替资本主义私有,西方为落后的俄国做出榜样并给予积级的支持;3北竟肃清了妨碍农村公社制度自由发展的各种破坏性影响,包括沙皇专制制度、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国家干预等等,并且国家提供财政支持和适合于联合耕种的物质技术装备。(《马恩全集》第19卷第435、451、326、130—131、第22卷第510页)(四)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已经对俄国这时是否还存在能“直接过渡”的农村公社表示了怀疑。他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的跋》中写道:“我不敢判断目前这种公社是否还保存得这样完整,以致在需要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在同西欧的大转变相结合的情况下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恩全集》第22卷第510页)。
1997年2、3月份,我在刚刚创刊的《百年潮》杂志1997年第1期即创刊号上读到了该刊社长郑惠同志于1996年10月间对我国著名学者、我国党史研究大专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同志的访谈录。其中,曾涉及马克思提出的关于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引起了我的高度关注和兴趣。读后,使我对年迈八旬的胡老甚为敬佩。胡绳同志不愧为我国著名的理论家和党史学家。其中谈到的一些看法,个人觉得对我国学术界和党的高层领导都十分重要,甚有启发。例如,胡老提出,按照马克思当时的论述,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果不经历一些过渡阶段,不能保证社会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不能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是不可能径直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成熟的。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成功和失败,由此提供的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都证明了这个观点的科学性。”对于这个观点,“要加意维护”等等。这是十分正确的。当然,有的提法,个人也未必能够完全苟同。例如,他说“资本主义欠发达、仍背着前资本主义的许多负担的国家,无论就国家的数目和人口数计,都在世界上占多数。是否它们都必须经过‘卡夫丁峡谷,如何才能够不经过这个痛苦的‘峡谷,又能享受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一切积极成果,这实在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因此,我于1997年3月28日将本人发表在1996年第11期《理论导刊》上的上述拙文《马、恩关于跨越“卡夫卡峡谷”的论述之我见》复印后呈寄给了胡老。胡绳同志收到拙文后即看了一遍。不久,患病住院,又将拙文带到医院。1998年5月15日,胡老的秘书黎钢同志给我寄来一信,其中转达了胡绳同志在敝信上的批语:“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八日在医院又读一遍,信中附文论点明确,是对的”。胡老的批语,对我鼓舞甚大。个人随即发函黎钢同志,请他将胡老的批件复印一份寄赠,以便保存。当年6月2日,黎钢同志复函:“徐博涵同志:……5月19日的来信收到。实在对不起,我没法满足您的要求。因为我们一般不保留信件,答复之后就处理掉了。我想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应保留一段时间。这次无法弥补,请您原谅。”此时,胡绳同志已经病重时久,不久,即2000年11月即与世长辞。这就成了我终身众多憾事之一了。
三
于光远同志是我久仰的著名经济学家。年轻时读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是由他主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同他还有过一点接触。一次是在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举办布哈林及其思想研讨班。我参加了,还翻译了一篇文章,后来收进了马列所编的译文集中。当时,于老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好像还兼管着马列所,曾经到研讨班去过一次,但同我并无直接接触。另一次是80年代中期,我应邀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科学社会主义卷的统稿审稿。于老当时是该卷的原定主编,偶尔见面。但当时我个人同于老没有什么直接的理论学术交流。在各种私人、公开场合,于老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头脑敏锐,思想解放、活跃,是个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理论求索的老革命、急先锋。
大约在1994年前后,于光远同志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提出,马克思论述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自始至终都是“社会所有制”,从未讲过公有制。中文译为公有制是不对的。这一说法公之于众后,立即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映和关注。不久,中央编译局的同志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为以往马、恩著作中的译法作辩护,说马、恩始终都使用了“公有制”的概念,批驳了于光远同志的说法。读到他们的这些论点,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个人觉得,于老提出的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决非单纯是个概念问题,需要好好认真地研究一下马、恩著作的原文。我原来学的是俄语,并不懂得德语。为此,我专门买了一些德语课本、德语语法、德汉辞典等,自修了德语。经过一番反复细心的学习、查对和研究,个人以为,于老提出的看法是我们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和飞跃。以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阐释,往往单纯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和对于社会利益、社会价值的追求,经常引用的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片面强调人的社会性和在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性,而忽视人的个体性和自然属性,忽视人对个人利益、个人价值的关注。在“文革”时期甚至发展到胡说什么“私字是万恶之源”,要在全社会“割私有制的尾巴”,要“消灭‘私字一闪念”等等。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人的社会性的同时,也十分关注人的个体性、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他们的理论学说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恰恰是人的自由个性的解放。他们在1845—1846年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出,共产主义所要建立的制度,正是为“联合起来的个人”奠定“这样的一种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马恩全集》第3卷第79页)马克思还曾在给俄国人安年柯夫的信中指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马恩选集》第4卷第321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写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马恩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生产力相当发达的前提下,在共同占有,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既摆脱了对人的依赖关系,又摆脱了对物的依赖关系,真正消除在社会联系中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已性和独立性,人们才真正开始了他们自己的自由社会生活,真正成为他们自己的主人,真正实现了自由个性,人类才进入了高级的第三个社会形态,亦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境界。因此,社会解放的程度是与个人解放的程度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可以说,个人解放的程度同时也是社会解放程度的标尺。恩格斯说过:“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马恩全集》第20卷第318页)
综上所述,按照马、恩的观点,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与个人是高度和谐统一的。社会即是联合起来的个人,而每一个人又是摆脱了“某种独立”于个人,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的“那种虚构的集体”而处于“自由人的联合体”中的个人,是已由分散的、孤立的、单独的、私的个人真正变成为“社会的个人”。社会利益、社会价值的实现与个人利益、个人价值的实现,完全融合为一体。马、恩表达社会与个人的各种高度和谐统一的概念,就是“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自由人的联合体”或者“联合起来的个人”。未来社会也就是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或者联合起来的个人的社会。
那么,这种未来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将是什么样的形式呢?马、恩最一般、最基本的提法是“社会的所有制”或“社会所有制”,德语原文为“gesellschaftliches Eigentum”。在我国出版的马、恩著作中,这个概念往往被译为“公有制”,这是不妥当的。这种“社会所有制”,马、恩基于上述观点又称之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马恩全集》第48卷第20—21页、《马恩选集》第2卷第267页)这就不难解开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不解之迷:为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4章未尾要说,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期也曾使用过“财产公有”或“财产共有”的口号,德语原文为“Gutergemeinschaft”,但是后来,他们抛弃了这一提法。恩格斯曾明确指出过这一点。1850年,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的公式。就此,恩格斯在临终前不久所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在谈及马克思该著作意义时曾写道:“使这部著作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这样,这里就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和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马恩全集》第22卷第593—594页)因此,于光远同志提出的见解,对于深刻理解马、恩思想理论的原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应当予以明确的肯定。但是,另一方面,中央编译局的几位同志提出的见解也有一定的道理。经过个人对马、恩若干重要著作德语原文查对、研究,马、恩不仅早期使用过“财产公有”或“财产共有”的口号,而且在《资本论》和以后直至晚年的著作中,也还偶而使用“公有制”(德语原文为“Gemeineigentum”)一词。这同他们的基本提法并不矛盾,因为“社会所有制”也是一种“公有制”,只不过这个概念还不足以确切、清晰地表达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本思想,还有些“模糊”不清而已。完全否认马、恩有过“公有制”的提法,也是不妥善,不全面的。
我把以上这些看法写成了一篇文章,标题为《还马、恩关于所有制改造理论以本来面目》,发表在我院的《人文杂志》1997年第1期上,并且复印了一份呈寄给了于光远同志,以表示对他意见的关注和支持。我还直接给于老打了一个长途电话作通报。于老接到电话后很高兴,并且希望我能帮助他把《马恩全集》德文版中有关“公有制”论述的德语原文全部查一下。我感到此项任务难以完成,只好婉言推辞。因为在西安地区,除我院和西安外语学院有若干册德文《马恩全集》外,根本无处可以找到有关书籍。而我本人现在已是退休之人,根本没有经费去北京乃至国外查阅有关资料。这也只能成为我的又一桩憾事了。
2009年10月4日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