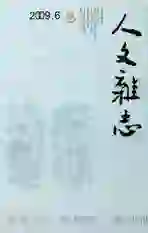理性与认知合理性
2009-01-18翟志宏
翟志宏
内容提要 西方哲学在知识的合理性评价问题上所提出的“理性”标准,在历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理性”作为知识的合理性标准,即使不是唯一的,起码也是最为主要的。然而,当基督宗教依照这种标准建构自身的合理性认知体系并评价其知识地位的时候,却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其结果是导致了“理性”含义的重新界定,并在当代的不同知识领域之间引发了富于戏剧性的争论。
关键词 理性 合理性 基督宗教
〔中图分类号〕B02;B503;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6-0031-05
在西方认识论的历史上,有关知识的合理性评价标准一直是不同时代的思想家们极为关注的问题。由于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了一个思想体系本身的自我评价,同时也关乎到了不同思想体系之间在知识地位上的关系。因此,来自不同体系的思想家们都试图找到一个理想的标准,以此来界定认识或知识的合理性意义。从古希腊时期以来,在知识的认知合理性与“理性”之间建立起一种必然的内在相关性,一直是哲学家们持守的立场和为之努力的方向。由哲学家们提出的“理性”的合理性标准在不同时期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并在启蒙运动时期的基础主义-证据主义中获得了其最为严格的表达形式。然而,这种立场在历史上并非始终是以所有人都认同的方式出现的,不是没有遭遇到看似有理的挑战和反对的。在这些挑战中,涉及的范围最广并表现得最为剧烈的是来自基督宗教方面的。也就是说,当基督宗教面对着自身信仰体系认知合理性意义的建构、面对着如何看待哲学关于知识的理性合理性评价标准的时候,内涵在哲学评价标准中的问题就凸显出来,进而引发了他们对这种标准的绝对性和过分单一化的质疑和反对。当然,来自基督宗教的不满和微词,在主要的方面虽然并不是试图彻底颠覆知识评价的合理性标准,但却就“理性”的含义及其范围做出了不同于哲学传统的界定。这种界定所引发的争论,不仅促成了中世纪和近代的知识理论在不同方向的展开与深化,而且也成为当代认识论问题研究中最富于张力的领域。
一、知识的合理性标准与神学的理性化
1990年前后,有两本书名截然相反的著作在美国出版。一本是费耶阿本德的《告别理性》(注:Paul Feyerabend,
Farewell to Reason, New York: Verso, 1987. 中文版由陈健、柯哲、陆明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另一本是克拉克的《重返理性》(注:Kelly James Clark, Return to Reaso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0. 中文版由唐安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由于在通常的语境中,“理性”是一个积极并具有至高价值的语词,因而,即使就它的确切含义与适用范围还有着争论,但当面对着“重返理性”和“告别理性”这两个对立的概念时,我们往往会想到,前者是一些认可理性价值和意义的人们的立场与劝告,如理性主义哲学家,而后者则可能是那些根子上对理性颇有微词的人们所生发的不满与怨言,如神学虔信主义者。然而历史往往会呈现出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东西。费耶阿本德作为科学哲学家提出“告别理性”,而具有深厚神学背景的宗教哲学家克拉克却倡言“重返理性”,这多少会使人感到诧异。
虽说费耶阿本德和克拉克的身份只是一种象征,但分别由他们所提出的这两种对立立场,则表达了现当代西方思想界在看待理性的意义及其地位时的某种复杂情感和矛盾心理。当然,这种复杂的状况不是最近几十年才开始产生的,它实际上反映了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与基督宗教之间长期的恩怨情仇。由于在一开始,哲学—理性就缔结了内在的盟约,随后在与宗教—信仰阵营发生无尽征战的过程中,结成了坚固的生死同盟。两种阵营之间长期的矛盾冲突使人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它们的关系似乎会以这种历史方式长久地延续下去。但是到了20世纪以后,事情却出现了奇妙的变化,坚固的阵营开始有了裂缝。针对理性,哲学中发出了反叛的呐喊,神学中却提出了回归的呼吁。
然而,从西方历史上看,哲学中的反叛较为少见,而神学中的理性化呼声却不绝于耳。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既决定于这两种思想体系各自的基本特征,也与它们所形成的历史时代及其所处的历史地位相关。毕竟哲学本身就是理性的,理性是哲学的本质,这也是古希腊哲学在建构其理论体系和问题意识时所具有的基本出发点与核心立场。随着古希腊哲学的成熟,理性也获得了至高的地位,成为核准和评价各种思想体系之认知合理性的原则与标准。“哲学理性”自然合流,具有了历史的优先性。
因此,当后起的基督宗教在希腊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罗马帝国中建构其神学体系的时候,哲学理性就成为它难以回避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内在性的需要,因为任何思想体系的系统化与条理化都要借助于某种逻辑的或理性的手段;另一方面乃是源于外在性的评价或关系,即基督宗教神学在面对其他知识体系,特别是希腊哲学时所感受到的一种压力——一种必需要表明或提供其思想合理性的压力。因而基督宗教神学在其一开始的时候就必须处理它与理性的关系,表现出对理性某种程度的认可与依赖。然而在当时的处境中,诉诸理性就是诉诸古希腊哲学。因而早期神学家们对古希腊哲学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兴趣。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神学家都对希腊哲学有好感,有些神学家甚至表现出了对哲学强烈的排斥倾向与抵触情绪——他们称那些过分理性化的希腊哲学家为“愚顽的希腊人”。但总体上,在使信念理性化——以理性的方式表达、认识信念——的过程中进而达成与希腊哲学融洽的对话与交流,是早期神学的基本选择和主流倾向。
公元2世纪至5世纪的教父哲学家大多就是以这种方式安排他们的神学体系并为之辩护的。这种倾向到了11世纪之后的经院哲学时期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示,并在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中达到历史的顶点。阿奎那在与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对话中,将基督宗教信念作了尽可能全面的理性化建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自然(理性)神学体系。如果历史按照这样的逻辑发展,或许在某一天,一个全面理性化的神学体系被建造起来也并非是没有可能的——当然,这时的“理性”会以不同的面目出现。问题就出在神学的理性化过程是不可能完全以纯粹内在性的方式展开的,哲学会时时从外部进行审视与干预。哲学不会对理性的问题长期保持沉默——一旦哲学感到“理性”被错误理解或被不正当使用,它就会表示抗议。
二、“理性”标准的重构
但是,问题并不仅仅出在外部。实际上,神学的理性化诉求在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它起初是以古希腊哲学的理性为标准来建构神学,并以此为基础来为其信念的合理性辩护。然而,宗教—信仰与哲学—理性在学科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它们有着相互歧异的思想基础和认知起点;因此,神学一旦开始以哲学为参照系来使自身的信念理性化,其结果极有可能或者是把信仰与理性以两张皮的形式粘贴在一起,或者是因信仰不能被理性化而最终放弃理性(当然它是不会放弃信仰的),或者是以修正或限定理性的方式使信仰理性化。然而,如果要坚持理性化,那么前两种结果就不会被接受。看来第三种方式是最有可能性的,确实,它在实际上也是被运用最多最持久的。但是,以修正理性或限定理性的方式使用理性,理性就极有可能偏离它原初的哲学轨道而被搞得意义模糊,甚至变得面目全非。或许,神学对此并不介意,但哲学却必定会怨声载道。也就是说,当神学在以自身的方式使其信念理性化、并看来取得某种成就的时候,哲学则不再保持沉默而奋起反击。
这种反击源于哲学对理性纯粹性的守护。因为哲学认为,既然神学愿意以理性为手段来表述自身并以此为基础来阐释信念的认知合理性,那么这种“理性”就应该保持它在哲学中的原初意义,而不能附加过多的条件或作任意的修改。否则的话,理性就不再成为理性了。为此,哲学一方面对神学中运用理性的正当性与可能性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并对这种运用的不严格性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也对合理性的含义作了进一步明确的界定。这种批判和界定最为充分地体现在启蒙运动期间,并随后形成了基础主义和证据主义的立场。
启蒙运动哲学家强调,任何合理的知识理论必须建构在充分论证和可靠证据的基础之上。他们把合理性的知识理论(以命题的形式表达)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础性命题或基本命题,这类命题是那些其本身就是确定的和可信的命题,它们的真假不依赖于其它任何的命题;另一类是派生命题,这类命题的真假依赖于其它命题(基础命题)的支持,或者说是从其它真的命题中推导出来的命题。这既是所谓的基础主义立场,从中形成了证据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如果一个知识理论或信念是值得接受的,则它必定是理性的,而一个合乎理性的信念则必须是一个得到证据支持的信念。在近现代,证据主义对基督宗教信念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认为这种信念既不是基础性命题,也不是得到经验证据支持或验证的命题,从而是不合理的和非理性的;即使那些做了理性化改造的自然神学,在启蒙运动哲学家看来,同样也是证据不充分或论证不严格的,不具有知识的意义。
这种辩护与批判的交织,在历史上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哲学在早期思想体系建造中所赋予理性的至高地位,使得后起的基督宗教神学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通过信念的理性化来为自身寻找认知的合理性。但是神学的理性化由于过分关注信仰自身的问题,而使它所使用的理性游离出哲学为其设定的轨道,从而引起了后者的不满。哲学表达这种不满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重新界定理性——建立起严格的理性意义和理性标准,把不合理性的东西排除在真正的知识之外。虽说这种界定的主要成果是基础主义和证据主义立场的形成,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彻底终结。由于在长期的理性化过程中,神学在自身的范围内也为理性开辟了另一个战场——形成了自身关于什么是理性与合理性的看法,即使这种看法与启蒙运动哲学家们关于理性的立场相左或不同,但它却有着自身的历史相关性和意义的自洽性。因此,实际上,在这场哲学与神学的对话与冲突中包含了或孕育出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理性本身的问题。什么是理性?理性的客观性何在?如何确定理性的评价尺度?或者说,是否任何知识的合理性都必须在哲学理性的基础上得以确立?诸如此类的问题把理性本身推到了争论的前沿。
三、“理性”的意义与困境
针对理性本身的质疑伸展到了20世纪并在众多领域展开,其中有两个方面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相关。一个是科学哲学关于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理论或命题的讨论,一个是宗教哲学对基础命题的范围和理性基本含义的扩充。这两个方面都涉及到了如何把握和确定理性的意义以及如何评价知识的合理性之类的问题。
20世纪科学哲学秉承证据主义的立场,试图在具体的细节上把这一立场进一步向前推进。虽说证据主义认为一个合理的知识理论是一个以正确的基本命题为基础、通过严格的逻辑推理而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并把这些基本命题确定为是自明的、感觉明显的或不可更改的命题;但它关于合理的知识体系的说明仍过于抽象,涉及到的更多的是基本原则,尚需要一些可操作的补充条款。在科学哲学看来,这些具体的可操作方法应该从那种被公认为客观的、理性的、具有积极价值和成就的理论——如自然科学——中获得。为此,它对自然科学的基础、性质、结构和发展诸方面作了全面细致的分析研究,在把合理的知识理论转化为真理性(真正的科学)命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经验的可证实性原则、经验证伪原则等判别这类命题的标准。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哲学发现,作为真理性命题范例的自然科学,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纯粹理性的。科学中除了理性的东西之外,也不乏非理性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不仅关于科学基础的“经验”的确切意指是什么难以达成共识,而且所谓客观中立的经验观察也是不存在的。任何观察证据都渗透着理论,都蕴含着一定的本体论承诺,从而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为真理性命题辩护的标准也是不够客观的。科学理论的深处活跃着“形而上学鬼魂”,科学评价的客观标准难以建立,任何科学方法都是有局限性的,甚至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也多少有着人为的因素。
对这种看法表达得最为彻底的是费耶阿本德。他不仅在科学研究中倡导无政府主义认识论,倡导“怎么都行”的多元主义方法,而且对不论是哲学还是科学中所追求的客观理性的理想,也予以了坚决的否定。他指出,纯粹理性长期以来一直是哲学和科学致力的目标,从柏拉图到萨特的哲学家们和从毕达哥拉斯到蒙那德(Monod)的科学家们,都一直在制定一个单一的客观标准,来为“理性”和“合理性”张目,但是他认为,真正促进人类繁荣和发展的是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理性的单一性。相反,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很多事情是受理性所害,而不是受它之助”。②费耶阿本德:《告别理性》,陈健、柯哲、陆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17页。)因此,鉴于对理性的失望,费耶阿本德宣称,“是时候告别它了”。②
当然,像费耶阿本德这种极端的看法不能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是人们大多都会对古典证据主义提出质疑,认为从纯粹客观的理性中寻找唯一的判别知识合理性的标准,并不是恰当的,也与历史的实际状况不符。这表现出了20世纪中后期科学哲学研究中的一种较为流行的情绪,一种对单纯的客观理性不满的情绪。不论这种不满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历史的现实,它都意味着必须对传统哲学所持守的理性做出新的考量与评估。
然而,与费耶阿本德等人的沮丧和失望不同,现当代宗教哲学则对理性保持着一份耐心,一种奢望。它从基督宗教的立场出发,希望在与理性的对话中,找到确定有神论信念认知合理性的新的可能。只是这种对话在当代宗教哲学家那里已不像在古典时期那样以被动的方式展开——即不是从信念如何理性化开始的,而是率先对理性与合理性概念作出新的诠释,以期使这种对话得以按照他们自己设定的路线进行。
参与这场对话的有众多的当代宗教哲学家,尤以阿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为代表的改革宗教认识论的影响最为显著。克拉克的《重返理性》对这场运动作了简要的概述,指出这场运动是从重新思考合理性概念开始的,“我们需要的只是关于合理性的全新观念,一种对宗教信仰更为包容的观念”。凯利•詹姆斯•克拉克:《重返理性》,唐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页。)现当代宗教哲学家之所以从重新思考合理性概念出发,乃是鉴于证据主义对宗教信念的批判,而这种批判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任何一种合理的知识体系或信念体系,必须是在可靠的基本命题的基础上按照逻辑的方式被建构。在这里,重要的是基本命题,它们构成了一个合理的知识体系的前提或根基。因此,如果要辩护认知合理性问题,就必须从这样的基本命题出发。
普兰丁格等人在提出自己的看法之前,先行对古典证据主义的立场作了检验。他们认为,古典证据主义为知识体系的合理性所设定的那些基本命题是有问题的。首先,是自指性问题。也就是说,证据主义认为合理的知识体系必须以基本命题为基础,但是相信或接受这种看法本身是否合理?证据主义只是指出了什么是基本命题,但对于为什么要把这些命题作为知识合理性的基础,并没有做出充分的论证。对于基础主义本身是否属于恰当的基本信念,我们并不清楚。其次,即使基础主义本身是恰当的,相信它也是合理的,但它所设定的基本命题的范围却是有问题的。因为古典证据主义只是把那些自明的、感觉明显的和无法更改的命题作为基本命题,从而把那些大量的日常生活信念排除在合理性的命题之外。而这些日常信念,诸如某人记得他今天早上吃过早餐,坚持说闻到了某种气味,相信外在世界存在,天是蓝的,等等,这些信念虽然是不可论证的,不能按照严格的逻辑程序提供证据,但却是可以被人们合理地拥有的,从而也是在某种意义上得到辩护的。
因此,普兰丁格等人认为,古典证据主义的错误不在于它为合理的知识体系设定某种基础,而在于它所设定的这种基础过于狭隘了,从而把大量恰当的知识信念排除在合理的命题之外。在他们看来,除了理性推理可以产生合理的信念之外,还有其他许多认知功能,如感觉和记忆等,也能够合法地形成可靠的信念。证据主义由于过分推崇逻辑理性,而使自己流于苛刻。为了消除这种苛刻性所造成的对众多合理性信念的排斥,他们对合理性观念作了修正,把众多的信念——诸如自明的、感觉明显的或不可更改的信念和记忆信念、对过去的信念、对外在世界的信念、对其他思想的信念、对别人见证的信念以及有神论信念等等——都纳入到基本命题之中,以一种扩展了的基础主义代替狭隘的古典基础主义。
四、“理性”意义的扩展与重返理性
基于对这种扩展了的基础主义的认识,现当代宗教哲学家提出了一种新的合理性原则——“证明有罪之前为清白”,以代替古典基础主义的“被证明清白之前为有罪”的合理性原则。前者是一种无罪推定原则,在清白的假定下,应当接纳所有的信念为合理的,除非理性提出了实质性的质疑;而后者是一种普遍怀疑的方法,拒绝一切可疑的东西,只认可那些建立在确凿证据基础上的或毫无疑问的信念。他们认为,相对于古典原则来说,新的原则有利于扩展我们的知识结构,把众多的信念纳入到合理性的范围中来。其特点是为常识建立了一个可信赖的合理性基础。
从普兰丁格等人关于扩大了的合理性观念来看,他们是从常识理性、而不是从哲学理性看待合理性问题的。这也就是克拉克所说的“我祖母的合理性”。他说,他的祖母是一位普通的有信念的妇女,她不会也不可能为她的信念提供充足的命题性证据,但她却“合理地”长期持有这种信念;而如果证据主义是对的,那么他的祖母就是智力上有缺陷的。为此,克拉克的立场是,“我选择站在我祖母的角度观察此事:她没有智力的缺陷,所以是证据主义错了”②凯利•詹姆斯•克拉克:《重返理性》,唐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6、126页。)。在他看来,证据主义由于把理性限定为一个“计算机的样式”,寻求数学式的精确性,从而是一个不合宜的和过分挑剔的合理性模式。
克拉克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理解理性并“重返理性”的。仅从概念本身所体现的理论旨趣来看,“重返理性”和“告别理性”确实体现了对待理性截然不同的态度;但是从长期的哲学与神学的征战关系来看,这两种态度却同时表现出了对理性的认同和持守——即使它们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和不同的情感。早期哲学在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合理性标准,古典证据主义为这种标准建立起了更为严格的表达形式。
但是,当20世纪科学哲学试图在自然科学中为它寻找具体可行的操作准则的时候,却发现纯粹的客观理性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理想——科学理论中充满了非理性的因素,过分苛刻的理性要求对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发展会产生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影响。由此不仅产生了费耶阿本德式告别理性的极端态度,而且也形成了关于理性的自然主义倾向——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对常识理性的开放和认同。
而基督宗教在处理它与理性的关系上走的则是另一种不同的道路。面对着希腊哲学关于知识合理性的挑战,它首先采取的应对策略是把信念理性化——其典型形式是自然神学。然而这种理性化过程最终面临着不可消解的难题——在其内部,始终有一些信念是不可能以理性的方式被认识的;在其外部,则遭受了启蒙运动证据主义的强有力批判。为了改变这种因合理化难题所造成的困境,基督宗教采取了一种新的应对方式,即通过修正理性概念及其合理性标准而不是改变信念来解决困难。这既是普兰丁格等人所做的,在扩展理性概念和基础主义命题的前提下为其合理性地位张目,这种扩展当然也受到了20世纪科学哲学对纯粹理性不满的激励与鼓舞。也许正是看到了现代哲学对古典证据主义理性的不满,他们才可能有信心地说,“让我们远离启蒙运动的毒害,重返理性”。②
然而,就其根本的思想倾向来说,不论是“告别理性”还是“重返理性”,仍然表明了对理性的一种信心,对理性作为知识合理性标准的维护。只是在这种维护中,理性已被宽泛地理解,从传统的意义上被放大,因为“告别理性”只是告别传统的纯粹理性,而“重返理性”则是重返常识理性。虽然哲学和神学之间围绕着知识合理性问题而展开的长期的征战,看来在对理性的现代解读中有着达成某种共识的希望,但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理性如何被放大、如何被宽泛地理解,而在于理性的底线如何被持守。因为如果不坚持一种相对严格的合理性标准与知识底线的话,那么理性则会有流于被彻底解构的危险,而这种危险是任何对理性仍抱有信心的人们都不愿看到的。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责任编辑:张 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