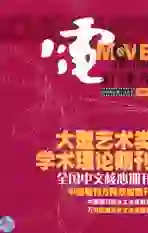从“恋父情结”解析李安电影中的文化内涵
2006-12-01伏蓉
伏 蓉
[摘要]李安的影片屡屡在国际电影节上摘金夺银,赢得了东西方观众的喜爱和认同,其作品的魅力不仅在于细致生动叙事,更在于影片中所蕴含的深刻的文化内涵,李安通过象征和承载关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家庭”的解构和重构过程,表明了他对置身于现代困境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思索。“从父”的文化和影片中鲜明的“恋父情结”恰恰揭示了导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对“根”的依恋。[关键词]文化内涵“从父”文本恋父情结
李安是90年代初新崛起的台湾导演,他凭借“父亲三部曲”声名鹊起。并成功执导了《理智与情感》等英文片。更以《卧虎藏龙》一举囊括2001年第73届奥斯卡四项大奖。李安以他的作品摘取了国际影坛的桂冠,震撼了西方世界,赢得了全球关注,促进了华语电影的国际化,带动了东方电影评论的长足发展,引起了境外知识界对华语电影的热切关注。他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看世界。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以更平等的对话姿态进入西方主流电影,运用西方通俗家庭伦理剧的模式在中国文化奇观的涵盖下发掘世界性的电影题材,表现在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扩大的当下现实境况中东西方人民普遍关注的文化、人性、情感问题。他的影片成为了华语电影被西方认同的突出范例,不仅受到国外观众和媒体的热烈追捧。同时也深得华语地区观众的喜爱和推崇。有人曾评价李安是个“有文化”的导演,而他的电影最为人津津乐道、交口称赞的正是其所具有的不可多得的深刻的文化内涵。虽然在美国学习、工作、生活多年,但在李安的大部分作品中我们都可以通过浓厚的“恋父情结”和“从父”的文本形式轻而易举的归结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认同和情感皈依。
李安影片所具有的这种独特的文化内涵与他个人的成长经验和文化体验息息相关。出生于台湾传统家庭的李安,自幼接受中国儒学的熏陶,在父亲的庇护和关爱幸福无忧地生活。联考失败后,在父亲的鼓励下,小小年纪的他离开台湾到美国求学,获得电影硕士学位。作为一个兼得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精神文化的电影人,李安所处的文化背景是复杂的,然而他毕竟是一个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精神的人,传统根植于他身上的深度和力度是他自身无法抗拒和超越的。李安是一个“恋父情结”很重的人,他对父亲所代表的父权秩序和传统的中国文化都怀有一份浓浓的依恋。他曾坦诚的承认“父亲对我确实影响很大,因为从小他就是家里的大树干,我们家里又是典型中国式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他又是很有威严的一个人。”[1]李安对父亲怀有一种很深的敬仰和情感,这种深刻的父子感情转化为李安内心深处不得不表达的创作冲动,从而形成了“父亲三部曲”中连续的父亲形象。
用李安自己的话说,他的“父亲三部曲”都是:“使传统上以父亲为主的一个家庭关系,得以从一个假象的平衡状态,历经危机和冲突之后,重新寻得一个新的平衡。”[2]他运用好莱坞家庭情节剧的叙事类型,表现了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和家庭模式在现代工业社会的跨文化的生存环境下面临的冲击,着重剖析和展现了在新的历史时代条件下。中西、新旧文化之间差异一对立一冲突一交融的过程。在他的影片中。恪守传统文化的父辈和接受了现代思潮的子辈在价值观方面的矛盾和情感交流上的障碍,导致了传统东方家庭的解构,父子之间的冲突直接推动了影片的叙事进程。在李安的电影文本中,虽然以夫妻为轴的家庭关系、同性恋、强调个性自由等现代意识和西方文化挑战和动摇了东方家庭中传统父性秩序的权威,但在影片的结尾我们通常可以看到一个融入了异质文化的“新型家庭”重新建构起来。迥异于张艺谋对传统文化、人伦道德的坚决批判和彻底否定,李安影片中“家”的重构和表露无遗的“恋父情结”折射出他对新旧、东西文化冲突所持的“中和、包容”的态度。暗含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对“根”的依恋。
“家”是中国文化基本结构的隐喻和象征。李安将自己的“恋父情结”放置于“家”的空间之内进行演绎,使其影片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由于“君本”社会体制的延续。造成了中国家庭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地位的家庭结构。“儒家的中心价值观便是‘中和,它强调宇宙间一切的普遍和谐,但这种和谐必须环绕着父权体制这一‘中心而建构起来,它的基本准则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君的忠和对‘父的孝互相阐发。互为一体。在‘家的意义上则是父权秩序和权威的不可侵犯。”[3]“父亲三部曲”中的父亲是传统文化的象征,李安分别赋予他们太极高手、将军和国宴厨师的职业。“这三种职业不仅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符码中的精华部分,而且是最具父权秩序的象征。而对于那些异域文化介入者,李安却使他们的身份呈现为一种负性趋势。”[4]
《推手》中的父亲老朱是个技艺超群的太极拳师,他代表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武学文化。为了家庭团聚,老朱不远千里来到美国与儿子和洋媳妇生活在一起。他每天在家里气定神闲的运气练功,韬光养晦,与其相对应的儿媳却是个整天耗在电脑前,烦躁焦虑地敲打键盘可总也写不出名堂来的蹩脚作家。镜头在表现老朱时,运镜缓慢。画面是一种沉稳的基调,而表现洋媳妇玛莎的画面,却处处给人一种浮躁的感觉。此外李安常以仰拍的角度处理父亲练拳、教拳和打架的段落,这一精心的设计使得身材瘦小的台湾著名演员郎雄在扮演父亲角色时显得身形高大威严,颇具气势和风度。影片中大肆铺陈的太极推手既是一项中国功夫,也是父亲老朱的养生之道。推手场面贯穿影片,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逐渐领教了中国功夫的高深莫测:看似弱小的老父,一推手能把身强体壮的硬汉推出数丈远:餐馆里,老朱一发功七八个人也无法让他移动半步:推手还能给人治病。在一系列的叙事过程中,西方观众大开眼界,充分领略到中国功夫的神奇。
《喜宴》里高伟同的同性恋人赛门是个美国青年,他热情直率,感情外露,喜怒哀乐全部写在脸上。为了骗过一心要抱孙子的父母,伟同明里和威威结婚,实际上却依旧和赛门暗渡陈仓。这对同性鸳鸯以为老父听不懂英语,所以在一起时都用英语交流。当两人因为伟同的假戏真做而发生激烈争吵时。全然不顾近在咫尺的老父。老父表面上不动声色,其实早已洞晓了二人瞒天过海的骗局。他老谋深算,工于心计地凭借以退为进的计策最终达成了自己的心愿。
《饮食男女》的开头,导演行云流水般渲染展示了精美绝伦的中国饮食,浓墨重彩地表现了身为国厨大师的父亲煎、炸、烹、煮的十八般武艺,而这令人眼花缭乱的绝技功夫却只不过是为了准备一次家庭聚餐。
李安的电影中的父亲形象深深渗透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在他的作品中高大威严的传统父亲个个身怀绝技,通过对一系列父亲形象地刻画和表现,李安有意识的展示了太极推手、中国书法、烹调艺术等中国文化奇观。这些富于东方文化神秘色彩的内容不仅是电影叙事不可缺少的部分,更注入了导
演对传统文化的思考,是其文化寄托的含而不露的表达方式。
除了精心塑造父亲的形象,并借此大张旗鼓的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之外,李安的“恋父情结”还突出表现在其影片所呈现出的“从父”文本。
影片《推手》中,代表传统文化的父亲与代表西方文化的洋媳妇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极。父亲与妻子之间的种种矛盾和隔阂使夹在两人中间的儿子晓生痛苦不堪。面对父亲和妻子的冲突,晓生既要尊重妻子的感受又不能违背中国人传统的孝道。处于两难境地的他采取主动调和的态度试图平息两人的矛盾,以期达到二者在同一“家庭”空间中的共存,然而收效甚微。为了避免冲突的继续升级,他有意撮合父亲和陈太太,却导致了恪守传统观念的父亲更深的误解与恼怒。父辈与子辈情感交流上的障碍最终使父亲搬出了儿子的家。
片中儿子晓生在维护自己夫妻之家安宁的同时,也背叛了父亲和传统伦理的孝道。本片中以个人主义、夫妻关系为主轴的美国文化,压倒了以父性权威为秩序、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中国文化。老朱养儿防老、三代同堂的愿望陷入了艰难的境地,西方现代文明无形中侵蚀了被中国人奉为天经地义的孝道和父子问的天伦之情。老朱的离家出走既是为了给子辈一个幸福的生活,也是为了保全父性文化的尊严。
构成影片《喜宴》剧情的是父辈和子辈所代表的中西方两种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集中体现为伦理价值观的冲突。剧中的子辈高伟同长期生活在美国,特定的美国文化语境使他接受在同性恋中寻找感情依托。可是在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和伦理观念中,“父为子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向来是以父权为中心的传统宗族社会的伦理核心。高伟同蒙受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其所承袭的中国式的伦理纲常、传宗接代的生命观和根深蒂固的孝子思想与他同性恋的生活事实相悖,这使他陷入焦虑的漩涡之中。他编织谎言搪塞父母,依旧继续自己的同性恋生活,实际上是对代表传统文化的父权的另一种形式的反抗。为应付来美国看儿媳的双亲,他与女孩威威假结婚,却又不小心使威威怀了孕。伟同的将军父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在中国传统的孝道礼仪中,无后属不孝之最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致命的软肋。儿子的同性恋行为无疑给盼望“烟火”延续的父亲迎头一棒,然而老人压抑住心中的怒火和不满,以装聋作哑隐忍的方式向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特生活方式妥协,最终换来了想要的结果:威威决定生下孩子——尽管这是一场假结婚的产物。影片结尾由两男一女建立起独特的“新家庭”,儿子伟同也因此得以继续保留父亲眼中违反伦常的同性恋生活。
《喜宴》中虽然儿子高伟同接受了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渴望摆脱父母的安排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自由选择个人生活,但当他发现自己的同性恋事实对传统父亲来说是不可承受的致命打击时,又费尽心机扮演好孝子贤孙的角色,并最终使威威生下孩子完成了延续香火这一东方传统文化中最大的孝道。
《饮食男女》以退休名厨朱师傅同三个女儿和女邻居之间的微妙关系,巧妙地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的“恋父情结”与东方传统人伦交错在一起。鳏居多年的老朱和三个女儿生活在一起,每周都有一次豪华的家庭聚餐。老朱三个未嫁的女儿表面上都想填补空缺的母亲的位置,完成孝道,但实际上却各自打算着冲出象征着父权秩序的大宅院。本以为会最晚离家的小女儿却因未婚先孕最先走出家门,最具现代意识的二女儿早就作好准备到国外工作,而从不谈及感情一向清心寡欲的大女儿,自认为会陪伴父亲终老,可是一受到爱情的滋润后立刻义无反顾地随丈夫而去。伦理责任在个人欲念面前苍白脆弱,不堪一击,这个看似温馨的“父女之家”已经摇摇欲坠。女儿们决绝的离家行为可以视为一种对父权秩序的逃避和反抗。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当老朱开始正视自己的情感需要,摆脱以往刻板的父亲形象,重新追求人性和爱情的自由,抛开世俗的眼光组建了老夫少妻的新家庭后,最为叛逆的二女儿却默默地选择了回归,选择向原有的父性秩序的回归。她主动留在了空荡荡的老宅里并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承担起父亲的原有的责任——准备家庭聚会大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似乎在回归老屋的二女儿身上得到了延续。
同样的“从父”文本在李安打造的武侠片《卧虎藏龙》中也可以看到。大侠李慕白欲收玉蛟龙为徒,传授她正宗的武学心法,以去除她的心魔,引导其走上正途。但玉蛟龙生性自负乖戾、蛮横任性,她对江湖充满狂热绮丽的幻想,根本听不进李慕白苦口婆心的教诲。她的我行我素,狂妄自大使她分辨不清是非善恶,终被碧眼狐狸所利用成为其复仇的工具。为闯荡江湖完成自己的梦想,玉蛟龙甚至抛下深爱着她的情人罗小虎,更在武林掀起一阵血雨腥风。此时的她已经迷失了本性,远离了武学的根本,一步步滑向毁灭堕落的深渊。为救玉蛟龙,李慕白中了奸人碧眼狐狸的暗器,他的死终于唤起了玉蛟龙对人生的顿悟。玉蛟龙虽是出身高贵的王府格格,但李慕白才是引导她走向成人世界的精神之父。影片的结尾玉蛟龙纵身跳下武当山,这既是她惨痛而辉煌的拜师仪式。也是其冥冥之中的“认父”之举。
站在传统的深处,李安以感性的心灵和理性的目光捕捉到中国传统文化最本质的伦理道德文化,他选择家庭伦理为其电影的常规命题。文化之异,伦理之别彰显于李安的电影文本世界里,交错纠合,妥协共存。其影片中的当代自我出于对新异文化的兴趣和渴望,挣脱父性秩序,走出家庭。然而当他们发现潜存于内心深处的父性尊严受到威胁时,最终不惜以牺牲自己的解放为代价重返家园,回归原有的父性秩序,捍卫父亲的尊严。
细细品味这几部影片,可以发现李安没有回避处于现代生存背景下的传统伦理儒家文化所面临的危机,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是传统文化的失落,东方家庭的岌岌可危,父辈子辈之间的隔膜,人伦亲情的疏离淡漠,使现代化生活中的都市男女感伤怅惘,人们愈发怀念中国传统文化。愈发体味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李安自觉的文化审视意识并非刻意张扬地表现于他的作品中。而是随着它营造的故事进展自然而然地彰显出来。他的影片不具有剑拔弩张式的批判揭露的锋芒,而是以平和的审视方式对处于现代文明和西方文化夹击之下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地反省与期待。在每部影片的结尾,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不再是对立和冲突,而是走向了和解与共处。李安通过象征和承载着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家庭”的解构和重构过程,表明了他对置身于现代困境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思索,“从父”的文本和与东方人伦交织的“恋父情结”恰恰揭示了导演对中国传统伦理特别是其中那些具有经典意义的价值观念的理解认同和情感皈依。作为一个炎黄子孙,这很显然地表明了李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切和热爱。”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在作品中表达“对中国文化的一点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