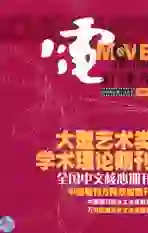在出世表象与世俗本质之间
2006-12-01潘永辉
潘永辉
[摘要]当前的银幕荧屏有不少僧人道士形象,而同时大陆佛教界道教界内部出版发行的刊物几乎没有那一家关心银幕荧屏上的僧道形象。这种现象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饶有兴味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影视如此殷勤地与僧人道士拉关系?为什么现实中的僧人道士对此又表现得如此冷淡?二者到底是何关系?从文化的角度应如何分析之?[关键词]僧道形象市井文化出世表象世俗本质
如果我们注意观察当前的银幕荧屏,会发现很多影视产品,尤其是武侠影视,有不少的僧人道士形象,他们在影视中充当着各种各样的角色;而同时,只要我们翻阅一下大陆佛教界道教界内部出版发行的几十家真正宗教意义上的佛教道教刊物,会发现这些刊物几乎没有那一家关心银幕荧屏上的僧道形象,仿佛这些世俗文化中塑造的僧道形象不曾存在似的。这种现象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饶有兴味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影视如此殷勤地与僧人道士拉关系?为什么现实中的僧人道士对此又表现得如此冷淡?二者到底是何关系?从文化的角度应如何分析之?
让我们从真正宗教意义上的僧人道士形象说起。
佛教的创立者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幼名乔答摩·悉达多(意为“义成就者”),生于公元前6—5世纪的迦毗罗卫国(属古印度,今尼泊尔境内),为该国王太子。王太子幼而心性慈慧、悲天悯人,长而睹人生弱肉强食、生老病死相,因发心求解脱之道。后不顾家庭劝阻,出家求道,经历长期艰苦的参学自修过程,终于彻悟宇宙人生真谛,获得大解脱。释迦牟尼成道之后,便开始向世人教授佛理,普渡众生,遂渐渐建立僧团与居士组织。佛教由是在古印度兴起。释迦牟尼入灭之后,在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的大力支持下,佛教在印度得到很大发展,形成了诸多教派。如部派佛教、中观学、唯识学、密教等。随着势力繁盛,开始向外传播,约于东汉永平年间传至中国,并与中国本土儒道文化相抗相融,走上了佛教中国化的文化历程。中国佛教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迅速发展,于隋唐时期达至高峰,形成诸多宗派,于宋元明清之际广泛向民间渗透,影响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佛教所要证得的最高境界是“空”,也即通过觉悟宇宙人生的梦幻不实去解脱对生老病死、人我众生、恩怨情仇的执著,从而解脱一切痛苦。这个空,在释迦牟尼的原始教法中,用“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寂静”的命题来表达:在中观学中,用“缘起性空”的命题来表达:在唯识学中,用“万法唯识”的命题来表达:而中国佛教的禅宗,则把这种即色即心如梦如幻的宇宙人生实相,称为自性、本心。佛教同一般哲学与世俗观念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承认世界当下即空,此外别无实在的物质、理念或造世主。基于这种空的觉悟,佛教在心性修养与处世方式上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法与态度,如宁静、无执、与世无争、忍辱、慈悲、施舍等。
与佛教由外传人不同,道教是中国本土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约形成于东汉期间,最初以一些民间教团的形态出现。后经两晋南北朝多位高道整顿、开拓,获得了重大发展。形成多家教派。至唐宋时获得最高统治者的极高待遇,达到发展的一个高峰。道教以老子为教主,以《老子》、《庄子》、《列子》等为根本经典,以得道为最高目的。至于何为得道,如何得道,教内不同教派的解释与做法则颇为不同,有的希望通过行善积德、修炼丹功以达到肉身长生、羽化飞升的目的,有的则致力于炼气全神、识心见性,与佛教禅宗合流。道教的处世观与佛教相类似,主张清静无为、恬淡寡欲。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真正宗教意义上的僧人道士形象,应该是一种出世的形象,应该是心性修养的导师、道德行履的典范。然而,当我们拿这种正统宗教所要求的形象去对照活跃于当前银幕荧屏上的僧道形象时。却发现他们不但相去甚远,有的甚至完全相反。后者主要地不是与出世、清静、超脱、慈悲、无我等联系在一起,而更多地是与竞争、帮派、暴力、怪诞、金钱、酒色、超自然力量联系在一起。
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后者虽然披上了僧人道士的外衣,骨子里却完全是市井文化的产物。所谓市井文化,现代性语境中又叫做市民文化、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文化,按照商业逻辑运营,生产者以获利为动机,消费者以消遣为目的,制作较为粗糙,精神品位较为低劣,同具有政治道德意义或艺术鉴赏价值的“人民文化(学)”与文人雅文化有着明显区别。
市井文化中的低级部分不离三个基本主题:金钱、暴力、色情。要表现这些世俗主题,本应采用世俗的文化表象。但市井文化为什么一定要把与自身关系甚远的出世的佛道形象强拉过来作为自己的文化符号呢?除了可以从历史传承方面追溯原因(古典社会也有描写僧道世俗行为的通俗小说)。我们更应结合这些僧道形象的现代性特征展开分析。首先,大陆的市井文化主要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港台市井文化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港台的佛教道教比较兴盛,市井文化的生产者易接触到佛道的表面形象与表层观念。有的还有一定的兴趣,制作市井文化产品的过程中顺手把佛道形象牵入自己的精神世界并加以改造利用,十分方便。受其影响,大陆的市井文化生产者也东施效颦,纷起模仿,于是扮佛妆道蔚然成风。其次,大陆确立市场与竞争体制之后,社会关系急剧变化,心理环境变得恶劣,潜意识中的很多原始性因素浮上意识层面,作为其文化表象的怪力乱神纷纷亮相,文化的暴力感与怪诞感大大增加。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中,最具超人感与神秘感的文化部分无疑是佛教道教,市井文人借佛教道教的躯壳来表达自身的暴力心理与怪诞心理,幻想拥有超人的能力,渴望在社会竞争中取胜。再次,竞争社会使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不缺少生存的疲惫与心理的紧张,而佛教道教的教义教规展示了与世俗观念完全不同的人生观处世观,可以给疲于奔命的俗人提供暂时性的心理按摩,潜在地对世俗社会有一定的吸引力。既想在世俗社会中争名夺利,又不得不承受由此带来的压力,这种生存的困境与心理的矛盾,便表现为现代市井文化中既俗气难除又能够念诵几句佛语禅言的僧道形象。
市井文化占用宗教表象带来了相应的文化后果。市井文化的生产者对佛道文化的理解十分肤浅,往往从自己的想象与需要出发,任意改窜佛道教义教规。扭曲佛道文化形象,对观众构成误导。市井文化的生产者不断地向神圣领域扩张,敢于利用一切神圣事物谋取名利,(其他相关例子如恶搞红色经典与红色英雄)表明这部分人的心态趋于放肆,心性中的最后一方净土已被蚕食。市井文化抢占宗教地盘,同时抢占文人雅文化地盘与革命文化地盘,势力十分强大,表明中国的社会体制、文化性质正在改变。历史的先例值得回顾: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卜迦丘,以充满肉欲描写的《十日谈》向基督教挑战,带动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心理;中国明清时期的若干文人,以同样性质的描写挑战儒家文明,使古典社会的天理向近代的人欲滑动。今天的中国文化面临着同样的境况,只不过到底是复辟还是开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市井文化的基本功能,一是为大众的世俗欲望提供刺激机会,二是为大众的心理压力提供释放渠道。这种通过不断地刺激精神以达到放松身心目的的方法,并不是什么好方法。欲望导致竞争,竞争产生疲劳,疲劳通过精神刺激来放松,放松是为了追逐新的欲望,形成了恶性循环,用佛教术语来描述,就是心理始终都在紧张的轮回中。只要看一看资本主义社会里心理病人的比例就可以明白。看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释放内在的紧张,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不是一定要象市井文化一样沉没于暴力、色情、怪诞场景才能释放内在的紧张呢?有没有既不违反道德文明又能释放心理压力的方法呢?佛道信徒提供了答案,他们处理心理压力的方法不是发泄释放,而是化解升华,通过观照宇宙人生的实相,通过开拓心灵境界,通过剥落心理尘垢,便可以使身心解脱,活得从容自在。只要读一读各种佛教文本,读一读真正的僧人的形象与心性,我们就能回答为什么现实中真正的出家人对市井文化中的僧道形象视若无睹,因为他们毕竟是“空门”啊。只可惜市井文化利用了佛教形象却又扭曲了佛教形象,把一片心性的和谐意境化成了银幕荧屏上的刀光剑影、酒色财气、怪力乱神。
从市井文化的僧道形象中,我们读到了人类的困境,读到了人类生存的疲惫与放松的渴望。人类不应该永远承受世俗竞争的痛苦,也难以完全放弃欲望渡到宗教彼岸。能否在人间建立一个和谐幸福的天国,使我们既不用沉湎于暴力中以求发泄,又不用孤独地跑到宗教世界寻找解脱?这应该成为文化研究的重大课题。这个课题需要研究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体制、文化性质、人性状态、人际关系以增进人类整体幸福的办法。社会主义文化比资本主义文化更加先进之处,就在于它敢于提出这个理想并努力实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