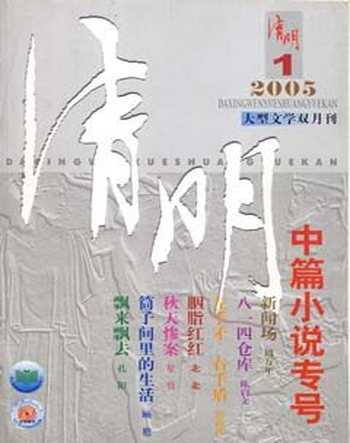我不能不杀你
2005-04-29张新荃
张新荃
西瓜还没有成熟,奎屯河畔的连队就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对连队来说,这是连队有史以来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连队每天都发生事,婆媳吵嘴,两口子打架,丢鸡骂街,寡妇偷汉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但像杀人,两口子被杀的案子,在连队还是第一次,几十年来的第一次。
被杀的是秋姐和她的男人。对秋姐的男人安呼噜被杀,人们议论的不多,好像一块泥巴扔进水里,没起波浪就化了。但是对秋姐就不一样了,说什么话的都有,而且还谈论了很长时间。尤其是连队上的男人们,他们惋惜痛苦。他们叫喊着要是抓住凶手,最低也是五马分尸,零砍碎砸也不解恨。而女人们却不一样,有了些幸灾乐祸的高兴。这不能怪连队的男人和女人们,因为秋姐太迷人了。
秋姐和她的男人安呼噜被杀,第三天才被人发现。是一个放羊老汉发现的。据连队人们回忆说,那天晚上突然下了雨,开始是小雨,后来越下越大,好像天破了一样,雷声和暴雨闹腾了两天,没人下地。第三天早晨,天刚放晴,在家憋闷两天的放羊老汉出了门。羊群来到瓜地边的林带里,放羊老汉就跑回来,到派出所报案了。
过了几天,有人从派出所得到消息,案破了。是在他家干活的民工干的。
在审讯室里,杀人嫌疑犯李福贵,也就是秋姐家雇佣的内地民工坐在那里,低着头,什么也不说。
警察怎么问,气得拍桌子,李福贵还是低着头,什么也不说。
李福贵终于开口了,没有说话,而是像戈壁滩上的狼一样地嚎啕起来。那哭声悲沧而又恐怖,让人毛骨悚然。
好长好长时间,大概李福贵把心中的怨恨都发泄了出来,他才慢慢地安静下来。
安静下来后的李福贵抬起头,看着面前的警察,说了他来秋姐家发生的事。
秋姐那天昂着头在前面走着。她走在灿烂的阳光下。她走在连队家属区羊肠小路上。她脸上的笑容里晃动着细碎的阳光。她显得很得意。满脸春风的她边走边不时地同相遇的人们打着招呼。
我提着包裹在后面跟着。
有人说,男人跟在女人后面走,只能走向一个美丽的陷阱。女人跟在男人后面走,说不定就会走向理想的天堂。
我不知道自己走向了一个温柔的陷阱。
我跟你们说,我来连队时是今年春天。那天,连队的小会议室里挤满了疙疙瘩瘩的人,闹哄哄的像自由市场一样。有来领人的,也有来看热闹的。来了十几个人,男男女女的,一会儿就剩我自己了。
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像地摊上的一件旧货,被看来看去,就是没人动心。我又想起了家乡的牲口市场,买主相中哪个就牵走哪个。我就像一头没人要的牲口,孤独地坐着。
真丢人啊!早知这样,何必跟他们出来呢,几千里路呢,借钱来丢人。我当时真后悔。连队围观的人嘴是不把门的,七嘴八舌的说什么的都有。这个说,这么大的年纪还来新疆干啥。那个说,不穷谁来呢。还有的说,人家才是转换观念呢,哪像咱们死守在这里门都不出。人多嘴杂说什么的都有,话儿就像风一样,眨眼间,我的耳朵就被灌得满满的。我低着头不说话,活像一尊雕塑。
这时,人群里响起一个女人高八度的声音“让一让,我来看一看还有没有民工啦。”
“有,留着给你当老公呢。”连队的人口无遮拦,喜欢开个玩笑。
人群里一片骚动和哄笑声。
“当老公咋啦,要是婚姻法同意,我非娶两老公不可。”。“秋姐,你还真行啊,能受得了嘛。”哄笑声中,人们的话更加肆无忌惮了。
我实在听不下去,一下子站起来,朝着一圈的人发狠地说:“我是来干活的,不是来让你们哄笑的。”
我没想到我凶狠的吼叫震得乱哄哄的办公室眨眼间静得没有一点声音,围观的人都极无聊地你看我来我看你,全没有了意思。
这时,连长进来了。连长是个年轻人,他看了看满屋人说:“你们没事都挤到这里干啥,下地干活去。哎,这里还有一个民工,谁家缺人?”
人群中挤出一个四十多岁女人。她看着我说:“老乡,你跟我走吧。”
我看了说话的女人一眼,就觉得自己没魂了,弯腰提起包裹,就跟在这个女人后面,像牲口一般被她牵出了连队办公室。
我听到了背后的议论声。我没有回头。我看到前面的女人也没有回头。但是,后面的话音还是紧迫不舍,像条尾巴一样跟着我们。
“秋姐家有好戏看了……”
连队家属区的路,曲里拐弯;像走迷宫。我一会儿迷了方向。
女人边走边问我:“老乡,你叫啥名字?”
我说:“李福贵。”
她又问:“五十几啦?”
我有些生气。我大声说:“三十二,刚过。”
女人突然不走了,转身看着我。我差点走到她的怀里,我吓得赶快站住不动。我觉得女人的眼睛像锥子,扎得我脸上火辣辣的生疼。
女人看了我一会儿,转身就走。她边走边说:“面相老,是家里老大吧?”
我说:“是。”
她又问:“几个娃娃了?”
我一听这话,更生气了。我又一次大声说:“没家,没娃娃,跟着娘过。”
女人又一次转身,看了身后的我一眼。
她说:“你以后就叫我秋姐吧。”
女人说完,又转身往前走。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我想起刚才会议室的玩笑话,心里乱鼓一样地狂敲。虽然相隔十万八千里,可女人们都一样,开起玩笑就像一个娘生的。
我突然想从后面看看秋姐,秋姐剪短发头,发梢打着弯。秋姐的背很直,腰很细,猛看像花瓶。秋姐的屁股很大,来回扭着,女人味十足。
我看得心里乱跳,眼睛有些走神。
走在前面的秋姐没有回头,而是领着我转连队的家属院,转了一排房子又一排房子,好像在逛庙会。走在路上就要碰到人。碰到人就要说话打招呼。团场连队的人见面爱开个玩笑,玩笑又都带点荤味。
“哟,秋姐,家里来亲戚了?”
“不是亲戚是民工,来家干活的。”秋姐喜盈盈地说。
“啥活都干?”
“可不是。”秋姐边走边说。
“看着身体挺结实的,安呼噜的活也让他干算了。”
“老安的活他自己能干。你家老黄那玩意我看不行了,哪天让他去你家拉个边套咋样?”
“算了,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没事。咱姐们,有啥说的。啥时睡不着觉,要解闷,招呼一声,保险比老黄强。”
秋姐哈哈大笑着往前走,人逢喜事精神爽嘛。
我是个没结过婚的老光棍,但在村里,老娘们的浑话也听了不少。这阵儿,脸却被臊得通红,头更低了。
秋姐领我来到一家院门口,对我说:“这是我家。”
我抬起头,仔细看了起来。院子虽然破一点,倒也整齐,有点像家乡的农家小院。我心里一下就有了一种亲切感,好像我出门又回来一样。院子里有一片地,什么也没有种,全是稀稀拉拉的干草,太阳一照,就像一个长满癣的瘌痢头一样难看。我看着心痛,要是在家乡,这片地不知要种多少庄稼呢。
秋姐看我愣在那里,脸有些红:“一个人忙不过来,只有闲着啦。你来就好了,过两天咱俩把地翻一
下,种点菜。”
我听了秋姐的话,在心里说:这个女人过日子也挺难。
秋姐领我进了屋。我一进门,就被吓了一跳。
破旧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五十多岁。像个怪物,一动不动,两只眼睛闪着寒冷的光,死死地盯着我。看的我顿时头皮发麻,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全身一抖。
秋姐说:“这是你姐夫老安。外号叫安呼噜。”
我急忙笑着打招呼:“大哥,你没出去?”
男人不理我,却朝秋姐发火:“我让你领俩女的,咋领个男的回来了?”
我一下呆在那里,不知道干啥才好。我看到了墙角的一堆垃圾。
“要不是看他年龄大,我一个也领不上。福贵,来,你住这间房子。”
秋姐说着,就打开旁边的一个门,让我进去。
屋子里有一张床,是单人的,上面落满了灰尘。屋内很凌乱,墙边横七竖八地站着铁锹、锄头一类的劳动工具,化肥和饲料一袋一袋地堆放着,占去了屋内大部分空间。
秋姐边收拾床铺边说:“儿子上学走了以后,这屋就当库房了。你一个人,住着不小吧。”
我客气地说:“秋姐,你忙去吧,我来收拾。”
秋姐说:“没事,你那么远来也不容易。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啥事都要担当点。我会照顾你的。我这人大大咧咧的,往后有啥事你也别计较。年底我也不会亏你,连队是有规定的。”
说心里话,我一辈子没有女人,从小到大只有娘给了我女人的温暖和体贴。看着秋姐铺床的背影,我就想到了娘。我记得娘也是这样铺床的。
秋姐把床铺得展展平平的,扭头看着我问道:“这样行不行?”我一下就脸发烧,两手来回搓着,躲开秋姐的目光,低下了头说:“好,好。麻烦你了,秋姐。”
“客气啥。你先休息一下,下午咱俩下地。”秋姐说着,往门外走。
“秋姐。”我不知咋回事,就喊了一声。
“还有啥事?”秋姐停住了脚步问我。
“有啥活我去干。”我想了想,说。
“要干的活多着呢,你不用急。我去做饭,做好我叫你。你要想干,那就帮我收拾一下这屋子。”说完,秋姐出了门。
我看着新铺的床,心里热烘烘的,眼窝有了些湿湿的。我坐在了床上,用手摸着床铺,软软的让我想了许多。一路上的奔波,现在一下停下来,我便有了家的感觉。家是新家,是别人的,现在我住了进来,我的心里就有了阳光,暖洋洋的。我想到了娘,想到了千里以外的那个家。不知娘过得咋样。我有个弟弟和妹妹,他俩都已成家。妹妹嫁到了外村,很少回家。弟弟虽然在本村,但弟妹太奸滑,对娘不好,弟弟又是一个怕老婆的男人。临出门的时候,我一再关照弟弟好好照顾娘,弟弟答应得好,但我还是不放心。不是为了还债,打死我也不会出这么远的门。想到娘,我的眼窝里就有了泪水在滚动。不能照顾娘,我只有在心里祝福娘了。
想了一会儿,心里舒服了许多。我擦去眼角的泪水,站起来去收拾屋里零乱的东西。收拾了一阵子,屋里便不乱了,看着顺眼多了。
秋姐推门进来叫我吃饭,看到屋里的变化,大吃一惊,眼里露出了高兴的光彩,满意地说:“福贵,想不到你个男人心这么细。累坏了吧?”
我拍拍手,脸有些红红地说:“这点活累不着,没啥没啥。”
“走,洗一洗,吃饭。”秋姐边说着边出了房门。
饭已摆在桌子上,秋姐的男人老安坐在那里像个泥塑,一手拿着馍,一手拿着筷子,两眼贼狠狠地盯着我,什么话也不说。我心里就不舒服了,不敢去坐,而是像个要饭花子站在那里。忙着端菜的秋姐看我站在那里不过去,就招呼着我“站着干啥,快坐呀”。我只好低着头,很别扭地坐下来。
馍是白面馍,汤是面筋汤,菜有四盘。一盘炒鸡蛋,一盘炖茄子干,一盘炒土豆,一盘炒白菜粉条,没有肉菜,但我有一种作客的感觉。在家乡,我和娘生活,顿顿只是一个青菜,不过年不过节是很少见到油腥的,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到一顿肉莱。我心里很明白自己的身份,自己只是一个打工的,又不是本地人。一个外地陌生的干活的,能吃到这么多的菜,我已经很满足了。唯一让我不舒服的是秋姐的男人的眼光,他看我,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秋姐不停地说让我吃菜,老安却一句话不说,倒像个要饭的低着头,狼吞虎咽地大口吃着菜,面筋汤喝得溜溜响。秋姐白了他一眼,就给我夹了一筷子鸡蛋说:“别客气,多吃点,下午要干活。”
秋姐的男人看到了,停下筷子,粗声粗气地说:“他自己不会吃,你想喂他是不是!”
我的脸一下子发烫,心里堵得慌。我放下了筷子,站了起来,想走。
秋姐拉住我的衣服说:“别理他,咱们吃饭。他有病,心烦。随他怎么说,我已经习惯了。吃饭吃饭。老安,你吃饭。”
我当时气得脸发胀,气喘得有些不均匀。我低下头,谁也不看,默默地吃饭。我有些饿,但心里不顺畅,只吃了几口,就没有胃口。我放下筷子,离开了饭桌。
“吃好了?”秋姐问道。
“吃饱了,秋姐。你们慢吃。”说完,我就出了门。
我听到背后传来秋姐和她男人老安的磨擦声。这一顿饭,我吃得肚里疙里疙瘩。我生气得喘着粗气,蹲在门外的墙根边,掏出烟吸了起来。浓浓的烟雾在我脸前飘荡。看着院里瘌痢头般的地,我想到了家乡的庄稼地。
出门的时候,麦子已经埋住脚脖子了。在家乡,我和村里人这阵儿正在麦地里撒肥,可这里还没有播种呢。我就想到了娘。不知娘吃过了饭没有。我抬头看了看太阳,太阳刺眼,高高地黏在蓝天上,像块火炭。
我站起来,背着手在院子里走了起来。我看了看棚子,是做饭的地方。我看了看院墙,院墙是高梁秆扎的,有的地方歪了。我用手扶了扶,把豁口的地方用高粱秆扎好。我来到院里的地里,站在那里看着,地是荒地,长着稀稀拉拉的枯草。我心里合计着这里种白菜,那里种豆角、西红柿、辣子、茄子什么。想着想着,我就又想到了家乡的菜院子,豆青柿红韭黄,那才叫过日子呢……
“福贵,走,下地了。”秋姐的一声喊,把我从沉思中拉回来。我接过铁锹,跟着秋姐出了院门:
活儿很简单,犁好的瓜沟要把它平整好。秋姐给我做了示范样子,我做了一辈子农活,看了一遍,也就看懂了。我身体好,干活不怕出力气。我和秋姐一人一条瓜沟,秋姐干完一条瓜沟时,我已经干完了三条瓜沟。
干了一会儿,秋姐招呼我,让我休息一下。刚才一阵猛干,耗去我不少力气,这会儿一停下来,我才感到汗在不停地往下流。我撩起衣服擦擦汗,看到秋姐坐在瓜沟边直喘气。我想。秋姐的男人是什么病,不能下地干活。看他吃饭,不像有病的人。
我想问秋姐,可话到嘴边,想一想不合适,就把话又咽下去了。我蹲在地头抽着烟,吐着烟圈想,一个家,男人不行,这个家就完了。秋姐看起来是好人,可命苦。
想想她的家,看看这些地,要是我不来,可够她忙的。既然人家要咱了,咱要好好的帮她一把。我想了一会儿,烟吸完了,就站起来,又使劲干了起来。
太阳掉到地下的时候,西边天边只留下一抹绛红色,田野里飘浮着淡淡的烟雾,天色灰朦朦的。一阵潮湿的春风轻轻刮着,空气中充满了戈壁的干燥气息。
秋姐看了看地里干了一半的瓜沟说:“明天再干一个上午就完了。福贵,看不出来,你干活真利索,像小伙子一样。”
秋姐表扬我,我不好意思地说:“在家干惯了。”
“走,回家。”
我就跟着秋姐后面往家走。路上,遇到人,秋姐就和人开玩笑。没人的时候,秋姐就和我说话。秋姐问一句,我答一句。秋姐不问,我们两人就哑巴一样走着。
到了家,秋姐让我去洗一洗,休息一会儿,她自己就去厨房忙着做饭。
老安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见我进来,只翻了一下眼皮,什么话也没说,只顾看自己的电视。
我想和他说句话,看他的样子,就什么也没说,进了自己的房间。我把铁锹放下后,出了门,来到厨房说:“秋姐,要我干啥?”
秋姐也不客气,说:“你去把猪喂一喂。”
我问:“猪在哪?”
“房后的圈里。”
我从厨房提着猪食桶来到房后。
猪圈是个坑,圈墙是土块垒的。里面有两头小猪崽,身上的毛白白的,一看就是刚买来不久的满月猪。猪崽看到我来,哼哼唧唧地叫着,扬着头看着。我心里就有了一种亲切感,觉得秋姐的男人还不如这两头猪,没有一点人情味。我边倒着猪食边说:“饿坏了吧。今天叫你们吃个饱。别争,争啥咧,就你俩,没人和你俩争。哎,好好吃,吃饱了睡个懒觉,这样长膘快。”
喂完猪食,没事,我就坐在圈栏上,看着猪崽津津有味地吃着,心里就有了想法。猪比人有福气。人要干活,要挣钱,还要养娘。猪啥也不干,啥也不想,吃饱就睡,活得有滋有味。下辈子我也变成猪,也享享福。就是被杀,活得也值。
直到秋姐喊我吃饭,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猪圈。
饭后,秋姐忙着收拾碗筷,老安一挪屁股坐在了沙发上。两眼又死盯在了电视节目上。我用眼瞄了一下电视机,电视屏幕上几个露胳臂露腿的漂亮女人红红绿绿的猫一样地走来走去,做着怪动作。
在家乡我很少看电视,自己家没有,又不好意思到别人家去看,怕惹人烦。这会儿看到电视里漂亮女人扭来扭去,扭得我心里痒痒的。想看,但看到老安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想走开,又舍不得走开,只好站在那里树桩一般。
秋姐进来,看我站在门口,就推着我说:“去,坐沙发上看去。”
老安一听,一扬腿躺在了沙发上,像躺在床上一样舒服,谁也不理。秋姐白了老安一眼,拉了个凳子摆在我的面前说:“你坐在这里看。”说完,她又恨恨地瞪了老安一眼,出了门。
我没有坐下看电视,我看得出来,自己在老安的眼里,是个不受欢迎的人。我没有办法,要是秋姐不要我,我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我只好忍了忍心中的闷气,去了自己的房间,拿起铁锹出了门。
那晚月亮特别的亮堂,星星很远,看不清楚。晚上的风带着戈壁的气味。干热的空气里夹杂着干草和牛羊的粪味。狗的叫声一会儿远,一会儿近,在夜空中传得很远很远。
我来到了院里,借着窗户里透出的灯光,看着面前的地。灯光下的地灰白色,几丛枯草歪七扭八地站立在地上,没有一点生气。我抓起一把土,又湿又黏。我想,多好的地呀,太可惜了。
温馨的月光下,我拿起铁锹干了起来。
后来,秋姐告诉我。那天晚上,她在厨房里忙完活,一出门就看到月光下的我一锹一锹地挖着地,心里不平静了。她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洁白的月光照在新翻的土地上,淡淡的湿气在慢慢地升腾,在我的脚下盘旋。她说,当时她感觉我就是天上下来的神仙,专门来帮她的。
秋姐说,月光下,我的脸成了一个光影,灰蒙蒙地在淡灰色的月光里一下一下地跳动着,就像月亮里的吴刚在砍树,做桂花酒。她的,b里就有了喝酒的感觉,醉醉的。
秋姐说,她看得有些痴迷,仿佛在看一个小伙子一样的专注,心里有了些少有的冲动。她心里暗暗地满意我是一个勤快人,她留用我看来是对的。
我低头挖着地,感觉到一滴汗水流到了眼睛里,我直起腰用手擦眼睛时,看到了月光下的秋姐。我就说:“秋姐,你看电视去吧,这,一会儿就完了。”
秋姐说:“不要挖了,回家看电视吧。”
我不想说老安不让看电视的事,怕惹得人家夫妻闹意见不团结,而是说了句违心的话:“没看电视的习惯。秋姐,你去看电视去吧,这里一会儿就完了。”说完,我挖地的劲头更大了。
秋姐看了我几眼,什么话也没说。她心里很清楚,决不是我不愿看电视,肯定是老安变着法不让我看电视。老安的心眼呀,针尖大,什么样的男人都容不下。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进了家门。
老安躺在沙发上活像一只大豆虫,看秋姐进来,头都没有抬一下,吸着烟,哼着小曲,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秋姐不看则已,一看到老安那出土的花生——论堆的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满肚子的火直往上冒。她来到沙发边看着老安厌烦地说:“起来,要睡觉到床上去。”
老安丝纹不动,吐了一口浓烟说:“我的家,我想怎样就怎样,谁他妈的也管不了。”
秋姐看老安不动,无奈地坐在椅子上,泪就涌满了眼眶。
两人谁也没有讲话,屋里只有电视机里传出的声音在流窜着。院子里挖地的声音在屋里荡着,震荡着两人的心灵。
老安的话语打破了屋里的静默:“行啊,找了一个好劳力。”
秋姐听着老安不阴不阳的怪话,狠狠瞪了老安一眼,什么也没有说,擦了一下眼泪,就从椅子上站起来,端了一杯开水,拿了毛巾,出了门,门在她的背后哐地关上了。
老安抬起头,往门瞄了一眼,嘿嘿地笑了两声,又安逸地躺下,哼起了自己才能听得懂的小调。
半夜里,我被一阵哭泣声惊醒。我心里有些紧张,望着窗户。
窗户外面黑蒙蒙一片,什么也看不到。
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但又不像。我屏住呼吸仔细听了一会儿,果然一个女人的哭声隐隐约约从外面传来。夜半哭声,莫非有鬼。我浑身一个激灵,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我一动不动,又细听了一会儿,确信哭声来自院子里。谁在哭呢?我很纳闷。我拉亮了电灯,坐起来穿衣服。这时候,院子里的哭声消失了,传来门开门关的声音。我努力地听着,声音去了秋姐的房屋。我脱了刚穿在身上的衣服,拉灭了灯,躺在了床上。
夜很静,院子里的哭声没有了,但是秋姐房子里的声音却传了过来,咕咚咕咚地一阵响动,好像在打架,夹杂着听不清的吵架声。我又坐了起来,这次我没有拉灯,而是坐在床上静静地听着,心里一阵阵的不平静。
好一阵儿,秋姐屋里的声音没有了。我看了看窗户,外面仍是黑黑的。我躺在床上,两眼看着灰蒙蒙的顶棚,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家里,一会儿这里,像放电影一样跳来跳去的,更睡不着了。躺了一会儿,心里烦,我就坐起来,披上衣服,摸出香烟,吸了起来。烟头的火光在黑暗的夜色里一闪一闪的,
烟雾在黑暗的夜色里流淌着,弥漫在屋里。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老安没有起床,饭是我和秋姐两人吃。老安不在,我就想起昨晚的事。我仔细看了一眼秋姐的脸。秋姐的脸上有一块乌紫的肿块,眼睛红肿。我想问,又觉得不太合适。人家两口的事,自己是不能乱搀和的。可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吃起饭来嘴里没有味道。想想今天要干活,不吃饱又没有力气,我就强迫自己吃。咸萝卜干,我吃了一根又一根,就着馍馍,喝着玉米稀饭,我在跟自己赌气。
这时,老安从东屋里出来,看也不看我一眼,径直出了门。
出了门的老安在门外大口吐着痰,声音很响,震天动地的。
坐在对面的秋姐却说:“吃饭,别理他,死不了。”说完,大口喝起了稀饭,喝稀饭的声音特别的响,满含着怒气和抗争。
我本来就没有胃口,这会儿更不想吃了,放下筷子,我就站了起来。
秋姐抬头望着我说:“咋,不吃了?”
“吃饱了。秋姐,我先回屋拿锹去。”说着,我就回了西屋。
一会儿,秋姐在喊:“福贵,下地了。”
我拿着铁锹就出了房门。客厅里,老安站在那,两只眼像狼一样地看着我。我把脸扭向别处,不看老安,拿着铁锹出了大门。出了门后我觉得自己很别扭,心里怎么想也不是滋味。这算什么事嘛?
走在路上,我一直想说话,但看秋姐没有讲话的意思,到嘴边的话就又憋了回去。我俩哑巴一样地走着,一直到了瓜地,谁也没有说话。
太阳挂在碧空中央的时候,秋姐说:“福贵,休息一下吧。”
我就停了下来。我有些累,坐在瓜渠埂上,掏出烟吸了起来。
秋姐看了一会儿我做过的活,满脸的高兴。她来到我的面前,坐在了我的对面,把水壶递了过来。
我接过水壶,看秋姐的眼睛里有些不一样的神色,心里一跳,急忙把目光从秋姐的脸上挪开,猛喝几口水。
我说:“秋姐,我想……”
秋姐看着我说:“有什么话你就说嘛,吞吞吐吐干啥,是不是在这里不习惯?”
我鼓足勇气说:“秋姐,大哥不欢迎我,我想换个人家。”
我说完,低下了头。这话我想了一夜。
“别理他。他有病,心里烦,看谁都不顺眼,总爱找事。我都习惯了。秋姐劝导着说。
秋姐看着我叹了一口气。那叹气声中我可以听出来,耿姐的心里也不是很舒畅的,显得很忧伤。
我还是憋不住,看了一眼秋姐,想问昨晚的事,可话到嘴边就变成了另一句:“大哥得的是什么病?”
“肌肉萎缩,治不好的病。”秋姐说着,泪水就在眼眶里闪闪发光。
肌肉萎缩,我听不懂,但治不好的病,我听了心里就有些紧张。治不好的病,那就是说没有几天活头了。秋姐命苦呀。我想到这里,心里就酸酸的不是滋味。我嘴笨,也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劝秋姐,只能低着头狠狠地吸烟,以此来排解心中的酸楚。
秋姐看我不说话,就又说:“老安心里烦,话说得难听,脸色也不好看,你不要计较,全当没有看见和听见好吧。”
我只好点了点头。
秋姐又说:“他不是烦你。他是想让我在家伺候他,地里的活就不要干了。你想一想,这成吗。两人都不干活,吃什么喝什么,总不能两人在家喝西北风吧。再说,儿子在外地上学,还需要钱呢。今年我包了地,他不愿意,和我打了一架。我让你来干活,他又不愿意,昨晚我俩又干了架。我在院里哭的时候,你拉了灯。我不好意思,就回了房。回房后,我俩又干了一架。你也听到了,反正你听到了,我也不瞒你。没办法,摊上这种病,谁也没有办法。医院也治不好,花了几万元钱。过去连队负担一些,现在承包了,一切费用都是自己掏。掏不起,医院不让住,只有回来在家里等死。他烦,我心里也烦。一烦起来,我俩就吵就打。吵完打完了,心里就痛快一些,日子就这样过。说心里话,谁也不想这样,可没有办法,就这命。”秋姐说着,用袖口擦了擦眼睛。
我心里起了波澜,用同情的眼光看了看秋姐说:“秋姐,我不会怨大哥的。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不走了,就在你家干;要不你就回家呆着,伺候大哥,地里的活我一人干也可以。”
“那怎么行。我还是想下地干活。在家里,心里憋闷得很,那还不天天吵嘴打架呀。”秋姐忧愁地说。
“再说啦,两人干活总比一人好吧,不管怎么说,说话也有伴。”秋姐说到这里,眼睛里有了些暖意。
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静静地听着。秋姐命苦,我心里想。秋姐是个好人,我要帮她。想到这里,我就站起来,发狠地干活。
我感觉坐在瓜渠埂子上的秋姐没有动,而是用眼睛久久地看着我。我干活不喜欢拖拖拉拉的,瓜沟在我的脚下一米一米地拉长,平平展展的煞是好看。秋姐就说,看着我干活,她的眼前就出现了自己当姑娘时干活的情景,活就是这样干的,修过的瓜渠就像画一样的好看,笔直笔直的。
我干活时偷瞄了秋姐一眼。秋姐看得入迷,有了些痴情,目光呆呆地不动。我心里就有了些抖动,好像平静的湖水落进了一块石头,涟漪一圈圈地扩散,很长时间都不能平静下来。
看秋姐坐在那里看我,我就想起了娘。在家乡自己的地里干活,娘就是这样地坐在地边,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用眼睛看着我干活,目光是那样的慈祥,深情,给了我全身的力量。身后的秋姐虽然不是娘,但那神态就和娘没有两样,同样给了我全身的干劲。我就狠劲地干着。我想,自己多干点,秋姐就能少干点。她太苦了,摊上那么个男人,不但不帮她干活,反而还常常欺负她。我要是她的男人,决不能干这缺德的事,要好好地待她。想到这里,我的脸火烧了起来,在心里骂自己,胡乱想,真不要脸。
秋姐没有动,仍然静静地坐着,呆傻地望着我的背影。
秋姐后来说,明媚的阳光下,我干活就像在跳舞,舞姿矫健,洒脱,优美。每一个动作都刚强有力,散发着男人的魅力,久久地吸引着她的目光。
秋姐后来告诉我,老安年轻的时候也没有我这样健壮,像个没营养的豆芽,从来都没有见他直起腰过,总是低着头走路。俗话说,仰脸女人低头汉,不好惹。老安就是这样,干活偷奸耍滑,从来不舍得下力气。秋姐看不起他,常常骂他是头瘟猪。可老安的贼心眼忒多,在一次夜班棉花浇水时,乘秋姐疲乏熟睡时,强行占有了她。为了姑娘的好名声,秋姐万般无奈嫁给了老安。连队里的人都说,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老安没皮没脸地乐呵呵地四处说,他这块牛粪让鲜花开得更好看。秋姐听到后,凄然泪下,心里像塞满了黄连一般,乱糟糟,苦兮兮的。
婚后的日子就是苦难的开始。老安白天像个瘟神一样蔫头呆脑没有一点精神,什么活也不干,什么活也不想干,四处游逛,犹如流窜的鸭子一样,那里有人就在那里扎堆聊天、睡觉、打呼噜。时间长了,大家就喊他安呼噜。他也不在意,反而乐呵呵的,好像被大家授予光荣称号一样不知羞耻。可到了晚上,老安的精神就像吸了鸦片一样,疯狂的像头叫驴,在床上一次次地折磨秋姐,发泄着体内的性欲。
无奈的秋姐把自己当作一堆烂肉,任他蹂躏,摧残,清冷的泪水滴湿枕头。多少次,秋姐想离他而去,但儿子在一天天长大,牵挂着她无法下狠心。后来,秋姐就认命了,浑浑噩噩地在苦水里泡着熬着。后来,儿子上大学走了,土地也实行了承包制。老安更不干了,地里的活全压在了秋姐一人身上。两人打打闹闹了几年,老安得了病,秋姐就只有认命了。多少次,秋姐想找个帮工的,老安不愿意,和她吵,和她闹。开始,秋姐迁让着他,后来,秋姐想了想自己太累,也就理直气壮地不让他了。我来她家当晚老安又寻衅闹事。秋姐第一次不屈服,同老安对打起来。想想自己的苦难日子,秋姐的心里就难受得滴血流泪。
日头升上中天的时候,秋姐看着我把一地的瓜沟全干完了。
下午,点瓜种。我在前面挖坑,秋姐跟在后面点种,两人配合得很默契。太阳很毒,热辣辣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两沟皿点完时,我满脸都是汗水。我脱下外衣,穿着满是补丁的衬衣继续干着。秋姐没撒种,而是眼睛看着我。我看秋姐看我,就停下手,问:“秋姐,是不是干错了?”
“没错。”
“那你看啥咧?”我有点纳闷。
“晚上我给你找件衣服,你身上的衣服太破了,早该扔了。”秋姐说。
我的脸一下就红了。在家乡我都是光着脊背干活。干农活,没啥讲究的。在这里,不像在自己家,要讲个文明,我就只好穿着衬衣了。我忘了衬衣上面的补丁,可秋姐看到了。看到补丁的秋姐要给我找衣服,衣服没穿上,可话听着舒服,像娘讲的一样叫我心里热乎乎的。
秋姐真好,我边干活边在心里说。
晚上,吃过饭的我坐在屋里吸烟。老安还是一脸不友好的神色。我没法和他计较,只好回了自己的屋里。我没有文化,从来不看书,又没有其它的事情可做。我唯一的嗜好就是吸烟,没事的时候我就默默地吸烟。烟雾缭绕,就像天上的云,在狭小的房间里飘浮。
门开了,秋姐进来了。
进来的秋姐拿着几件衣服。她挥动着衣服驱赶屋里的烟雾,说:“这么大的烟,你不呛吗?少吸点烟,对身体不好。”
我笑了,有点不好意思。
“这几件旧衣服,不要嫌弃,先凑合着穿。”秋姐把衣服放在了床上。
衣服有八成新,洗得很干净,我看着衣服,眼睛里就有了些湿润。我想说什么,可嗓子眼堵堵的,说不出来。
秋姐走了。我坐在床上,怀里抱着衣服。衣服散发着温馨的香味,在我的眼前飘荡。我静静地坐着。坐着的我想了很多很多,而想得最多的还是娘。过去只有娘给了我女人的温暖。现在秋姐给了我娘一般的温暖,而秋姐又和娘不一样。秋姐是另一种女人,另一种女人给我的温馨,我就有些另一种的感觉了。
这一夜,我是抱着秋姐给我的衣服睡的。我睡得很死,很香甜,完全陶醉在自己的美梦之中,一点也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
这一夜,秋姐又和老安打架了。老安下手太狠,秋姐的头被老安打破了,流了许多的血。秋姐也愤怒了,把老安的脸抓破了,满脸是血。
这一夜,是两败俱伤的一夜,充满了血腥味。
早晨吃饭的时候,老安不在。我看到秋姐的头上系着一个方头巾,红格格的,很好看,忍不住就多看了两眼。这一细看,我就看出了名堂。秋姐的脸上又多了一块伤痕,右眼上有一片青紫色。
秋姐还是那样大大咧咧的,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饭吃得很香。
我看着,听着秋姐吃饭的声音,我知道秋姐是强压着痛苦装笑脸,心里突然一酸,想哭的滋味涌了上来。我停了吃饭,使劲往下压,没有哭出来,但肚子却胀胀的,一点胃口也没有了。
秋姐和我来到地里时,起风了。瓜地里的塑料薄膜被掀起,散落的乱七八糟。秋姐就教我铺地膜,秋姐骑在薄膜上,扯展着薄膜,弯着腰在前面走,我端着铁锹在后面给薄膜压土。压着压着,我的脸就火烧了起来,心里像有只小兔一样怦怦狂跳起来。我的速度不由地慢了下来,头低着,不敢往前看。
秋姐不知道后面发生的一切,仍然在前面走着。她叉着双腿,跨立在白白的薄膜上,弯着腰,双手扯着薄膜的两个边,在地上比量着。风灌进了她的衬衣里,鼓鼓的,于是,她的两个饱满的乳房就裸露了出来,随着身体的抖动而晃动,像两团白色的火焰。
跟在后面的我就看到了前面的两团白色的火焰,眼前一片眩晕。我闭上了眼睛,可又忍不住。我看着,看着,心里就乱了方寸。我无法控制住自己,全身着火一样,口里干渴得不停的咽唾沫。
我是一个健康的男人,贫穷让我没有女人。我弟兄两个,家里穷,到了结婚年龄,没有人来提亲,后来就耽搁了。弟弟比我精明,自己找了对象。为了弟弟,我舍弃了自己。后来,弟弟结婚,欠下了一屁股债。我更不敢想结婚的事。为了给弟弟还债,我才不得不远离家乡,来这里打工。
秋姐看我站在那里发愣,就放下手中的薄膜,来到了我的面前,亲切地问道:“福贵,是不是哪不舒服?还是累了。要不咱休息一会儿。”
我看着面前的秋姐,看着秋姐有些透明的花衬衣。隐隐约约地就看到了那两个白馒头一样的乳房在晃动。我摇了摇头,闭上了眼睛,强迫自己不往那里看。
秋姐没有发现我心里的秘密,以为我累了,就又说:“咱们休息一下。走,去林带里喝口水。”秋姐说着,就前面走了。
我满脸发烧,心里扑通扑通地跟在后面。
林带是老林带。秋姐说:“这粗壮的柳树是当年开荒时种下的。”我看柳树有一抱子粗,伸展着浓密的树枝,犹如一长溜大伞,遮挡着酷热的阳光。
凉爽的林阴里,秋姐坐在渠埂上,用手绢擦着脸上的汗。她擦完脸上的汗,就把手伸进衬衣里,在胸前胡乱擦着,衬衣被带起来,白白的肚皮就一亮一亮地在我的眼前闪动。
我坐在秋姐的旁边,动也不敢动,浑身火烫得坐立不安。我拼命地喝水,想扑灭心中的火焰。
秋姐擦完了胸前,就擦后背。她边擦着身体边说着话。
秋姐说:“福贵,你该成个家了。”
我低着头答:“是的。”
秋姐又说:“家里没有合适的?”
我埋着头又答:“没有。”
我边说着,边喝水。一会儿,肚子就觉得鼓鼓的,想解手。我抬起了头。我看到了远处的奎屯河。阳光下,青青的芦苇在摇晃,光斑在芦苇叶上闪耀着,一明一灭。
秋姐没有发现我憋急的脸色,仍照着自己的思路说:“成家的事我来给你张罗,给你找个合适的,把家安在这里,以后把你娘接来。”
我只好哼哈着,站了起来。我实在忍不住了,下身鼓胀胀的,脸憋成了黑紫色,一脸的汗珠。
秋姐看着我的样子,顿时明白了一切,突然就大笑了起来。秋姐边笑边说:“不要憋坏了,快去吧。”说完又大笑了起来。
我弯着腰,快速地跑向奎屯河,跑向奎屯河畔的芦苇丛中。
我站在茂密的芦苇丛中,吸着奎屯河飘来的潮湿味,美美地撒了一泡尿。撒完之后,我有了一种非常的快感,痛快地摇了摇头。当我要迈步走出芦苇
丛中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远处的草丛中蹲着一个人。我开始并没在意,以为那个人也和我一样。我走出芦苇,站在高处时,就瞄了一眼那个人;结果就这一眼,我就像定身似的站在那里动不了了。
草丛里真真切切的那个人是老安。他在那里干什么?我就有些纳闷。我细一想,就想出了答案。
老安是特务,他在跟踪。
我就有了些恼怒,有了被欺辱的感觉。愤怒的我硬着脖了就朝老安走去。我迈着大步,一步一步地走到了老安的面前。
老安从草丛中站起来,站得有些畏缩,像缺少营养的豆芽,弯着腰。他的眼睛乱闪着,躲避着我咄咄逼人的眼光。
我停下脚步,眼睛里喷着火,怒视着抖动的老安。我想挥起拳头,痛打老安一顿,解解心头淤积的怨气。但是,我最终没有把拳头举起来。老安抖抖索索地快要瘫成一团,使我的头脑清醒了许多。
病人。一个快要死的病人。
想到了这,愤愤地瞪了老安一眼,转身走了。
老安支撑着快要倒下的身体,朝着远去的我恨恨地骂了一句恶毒的话,一扭一扭地远去了。
日子就这样过着。转眼到了压瓜秧的季节。
老安自从在草地里和我正面交锋以后,就开始躲避我了。老安心里明白自己不是我的对手,他把对我的怨恨都聚集在折磨秋姐的身上,白天无战事,夜晚就是一场残酷的男女战争。
我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有几次,我想好好的整治一下老安,但都被秋姐拦住了。秋姐的泪水,浇灭了我心中的怒火,同时激起了我心中对秋姐的怜悯和同情。
压瓜秧是西瓜丰收的关键。压瓜秧的同时要给瓜秧打杈。礼品瓜不同于普通的西瓜,它的种植要求很严,成熟期很短。秋姐给我讲着要领,犹如专业技术员一样。
老安又来了。这几天,老安不像过去那样藏在草丛里窥视,而是坐在瓜地边的渠埂上,像只狗一样地蹲着,虎视眈眈地看着秋姐和我干活。
我看到老安蹲在大柳树下,心里就有了屈辱,就有了愤怒。我干脆不干了,坐在了瓜埂上,掏出了烟,吸了起来。我一口接着一口吸着,浓浓的烟雾弥漫了我的眼睛。
秋姐看我不干活了。她想说,但她看到了柳树下的老安,到嘴的话就又咽了下去。她起身来到了老安的面前。
秋姐说:“你又来干啥?”
老安不吭气,只是默默地看着地里的我。
“你咋不死呢。”秋姐恨恨地说。
老安笑着说:“我就是不死,让你们活受罪。我就是让你俩干熬。”
秋姐骂道:“不要脸!”
老安得意地说:“我活着,你俩就搞不成。”
秋姐又骂道:“你真是牲口!”
老安不接话,反而笑了起来,笑得很疯狂。那笑声像老鸹叫的一样,在瓜地里流窜。
秋姐流泪了。秋姐含着眼泪离开了老安。
秋姐来到我的跟前说:“咱们不理他。咱们干咱们的活。死畜生一个。”
我看出了秋姐的痛苦,可我没有办法。我甩掉手上的烟头,用脚狠狠地踩了一下,下到瓜田。
太阳越来越热了。没有一丝风,空气中翻滚着热浪。
老安倒下了。老安终于忍受不住地里的高温,倒在了大柳树底下。秋姐没有看到,是我看到的。我干活的时候,不时地看一下柳树下的老安。我不是关心,而是愤恨。我希望老安离开这里,不离开就像肉中刺一样地看着难受。
我看到老安倒下时,心里一阵高兴。但是这种念头只是一瞬间,像闪电一样的很快就消失了。我对着秋姐喊道:“老安倒了。”
我冲向了大树下的老安。
我摸摸老安的鼻子,有呼吸。我就喊:“大哥,大哥。”
老安闭着眼睛不说话。
秋姐来到我面前的时候,老安在我的怀里,静静地躺着。
秋姐说:“福贵,放下他。他是装的。”
我没有放下老安。我说:“不像,肯定是病了。”
秋姐上前就拧了老安一下。老安没动。秋姐就慌了,说:“快背他回家,去医务所。”
我就背起老安,朝连队跑去。
秋姐跟在后面。跟在后面的秋姐心里就有了怨气。她看着前面的我背着老安,在不平坦的路上一颠一颠的,对老安的气就更大了。
秋姐边走边数落着:“不在家呆着,跑来干啥。”
我喘着气说:“秋姐,现在啥也不要说了,抢救病人要紧。”
秋姐不说话了,可老安说话了。原来老安在我的背上一颠一颠的就被颠过来了。
老安说:“你把我背回家,我还是要来的。”
我听到了老安的话,停下了脚步,不知如何是好。
秋姐也听到了老安的话,上前就把老安往下拉。秋姐边拉边骂道:“你是不是人?地里活你不干,还想着法欺负人。你不是人。把他放下来。”
我手一松,老安就被秋姐拉下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秋姐拉住我的手,说:“走,咱们别理他,咱们干活去。”
我不忍心,看了老安一眼,本想帮老安一下,可我看到老安的眼睛里,发出的眼光特别的恶毒,好像要杀人一样,我心里就有气了。
我心里想,不是我拉秋姐的手,是秋姐拉我的手,我怕什么。
我这样想着,就任凭秋姐拉着。三十多岁了,第一次让一个女人拉着手,我的心里就有了从来没有的滋味。我觉得自己好像在飞,脚步轻轻的,一点都不累。
老安在后面叫了起来:“狗男女,不要脸。我杀了你们。”
秋姐站住了。
我站住了。
老安果真拿着一把闪光的刀子冲过来。
秋姐惊恐地抓住我的衣服,浑身有了些抖颤,说道:“他疯了,他疯了。”
我开始还有些害怕,但秋姐一拉我的衣服,站在我的身边,我不由自主的心里升起了一股豪气,有些威风凛凛了。
我站着没动,等老安扑过来的时候,我顺势抓住老安的手腕,一把就夺过了刀子,一推,老安就躺在了戈壁滩的草地上。
我把刀子朝远处一扔,生气地说:“秋姐,我不在你家干了。”
我大步朝远处走去。我边走边想,这样干下去,说不定还要出人命呢。
老安愣了。
秋姐傻了。
他俩谁也没有想到我会来这么一下子。
秋姐一股火涌上心头,朝地上的老安狠狠地踢了一脚,骂道:“你不是人,你是畜生!”
秋姐丢下老安,朝我追来。
躺在地上的老安,揉着被踢疼的腿,从地上爬起来,看着远去的秋姐和我,牙齿咬得格格响;大声骂道:“狗男女,我绝饶不了你们!”
我来到了奎屯河畔,坐在一棵古老的胡杨树根上,喘着粗气。我看着河水,河水不慌不忙地流着,阳光照在河面上,光斑闪闪,晃花了我的眼睛。我突然觉得心里很委屈,鼻子酸酸的,眼泪就流了出来。
追过来的秋姐停下了脚步。秋姐本想过来,但她看到阳光下的我脸上的泪珠在闪光,她就站着不动了。
男人有泪不轻弹。
秋姐后来告诉我,她看我在哭,心里很难受。她觉得自己对不起我。我在帮她,五十亩瓜地不说,门前院子里的菜园子经我的手,辣子开花了,西红柿结
果了,豆角爬秧了,小白菜绿绿的,吃了几顿了。圈里的猪都有三四十斤了。这一切都是我干的。可老安还要折磨我,欺负我。要是我走了,谁来干呢。
秋姐想着想着,眼泪就出来了。
秋姐心里憋得很,就大哭起来。
秋姐痛哭的时候,我不哭了。我扭头看到秋姐哭得很悲哀,坐在草地上,鼻子一把泪一把的。
我来到秋姐的跟前劝秋姐起来。秋姐甩动着两只胳臂,哭着说:“福贵,秋姐我对不起你。你帮了我这么多的忙,还要受这么多的委屈。你走吧,在谁家干都比我家强。我家有个畜生,他不是人。”
我说:“秋姐,对不起了。我不能再在你家干了。我怕出事。”
秋姐说:“福贵,你是好人。你在我家干这几个月,我看得出来,你是好人。我不想让你走,可我家的畜生逼你走。你走吧,我也再不找人帮忙了。”
秋姐说着,泪更多了,哭声更悲戚了。
我站着不动,心里翻江倒海般的难受。
老安站在远处在笑。秋姐没有看到,我看到了。我看到老安得意了。得意洋洋的老安一歪一扭着身子走了。
我搬出了秋姐家。
经秋姐介绍,我在徐嫂家干活。徐嫂家的瓜地挨着秋姐家的瓜地。我想,这可能是秋姐的特意安排。秋姐的心思我知道,她不想让我远离她。徐嫂本来不要人帮忙,秋姐苦口婆心地说了很多的话,井一再说只干一个月,瓜大的时候,还要我回来看瓜。
自从我离开秋姐家,老安每天来地里看秋姐干活,可他从不到地里帮秋姐一下忙,反而像个地主监视长工干活一样,坐在地边的柳树下吸烟,满脸的得意洋洋。每次看到这些,我就想跑过去掐死他,至少狠狠地痛打他一顿。可是我不能,因为我没有权利,他们毕竟是夫妻。但是徐嫂看不下去,站在地里大骂:“安呼噜,你是人吗?秋姐累得那个样子,腰都直不起来,你不干活,送口水也行吧。你还有脸坐在树底下吸烟,还不如到奎屯河里淹死算了。”
老安说:“我才不死呢。我要活着,让他们难受。只要他们难受了,我才高兴。”
我气得牙齿咬得腮帮子疼,拳头都攥出了汗。
徐嫂的男人在旁边看不过去,劝徐嫂说:“那是头驴,你理他干啥。叫秋姐过来歇一会儿。”
徐嫂就喊:“秋姐,来我们这边歇一会儿吧。”
秋姐说:“不了,马上就完了。”
毒辣的日头烧得地里冒热气,就像出锅的蒸笼。我穿着秋姐给我的背心压瓜秧,浑身汗淋淋的,背心都湿透了。我看远处的秋姐,飘来飘去的热气里,秋姐身上的汗衫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不知怎么回事,我的心里堵得慌,一阵难受。
老安在树底下得意地哼着小调,说着怪话:“真凉快呀。这天咋不热呢。”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一下站起来。徐嫂的男人看着我说:“那是一堆烂刺,动了扎手。”我气得蹲在地上,吸起了烟。
突然,徐嫂叫了起来:“安呼噜,秋姐咋了?你还不看看。”
我抬起了头,看到秋姐躺在瓜沟上,一动也不动。我急了,刚要迈步,就被徐嫂的男人拦住了,他说:“你别惹事。我们去看看。”
我看到徐嫂和她男人跑了过去,老安像狗熊一样坐着不动,好像天塌下来和他无关。
徐嫂朝老安喊:“安呼噜,你老婆真不行了,你还不来救她。”
老安说:“死了好,省得我天天来地里受罪。”
徐嫂的男人说:“人都成这样了,你还见死不救。你还是人吗?”
老安说:“要救你们救去,我要回家睡觉了。”
老安说完,站起来,离开了地边,朝家里走去。
徐嫂喊道:“秋姐,你不要吓我,你醒一醒。你睁开眼,睁开眼嘛。”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几步冲到了秋姐的面前。我看到徐嫂怀里的秋姐脸色灰白,眼睛紧闭着。我一下惊呆了,傻子一样地站在那里。
徐嫂的男人朝我发火吼道:“你傻站着干啥,还不背着赶快去医务所救人!”
我啥也不想,背起秋姐就往连队的医务所跑去。
徐嫂和她男人紧紧地跟在后面。
我们追上了老安,跑到了老安的前面。
我听到老安在我的后面喊叫起来:“耍流氓了,快看呀,耍流氓了。”
我一下就站住了。我想和老安拼命。
徐嫂的男人推着我说:“不理他,救人要紧。”
徐嫂骂道:“不要脸,安呼噜,你去死吧。”
我背着秋姐在前面跑,老安在后面乱骂,什么难听话都骂了出来。
我们来到连队医务所,医生急忙抢救。好一会了,我看到秋姐才吐出了一口气。她的眼睁了一下,又闭上了。
我问医生:“啥病?没事吧?”
医生说:“主要是疲劳过度,加上今天天气热,中暑了。不过不要紧,好好休息一下就能缓过来。还多亏你们送来的及时,要不然,还真要出事了。”
我坐在椅子上,什么也不说,看着床上的秋姐,等着她醒来。
徐嫂和她男人走了。
我听到徐嫂边走边说:“秋姐还是有福气的,碰到这么好的男人。”
徐嫂的男人说:“走吧,回家你给秋姐弄点吃的送来。”
徐嫂和她男人走了好一会,我看到秋姐的眼睛睁开了。
我问道:“秋姐,你好一点了吗?”
秋姐想坐起来,我急忙按住说:“秋姐不能动,你打着吊针呢。”
医生在旁边说:“你不要动,好好躺一会,打完吊针再回家。”
我看到秋姐的眼睛里有了泪水:“福贵,谢谢你了。”
医生说:“可不是,你可真要好好谢谢他。要是再晚来一会儿,还真要出大事呢。”
我用手擦着秋姐脸上的泪水说:“秋姐,你对我那么好,我不能不讲良心。”
这时候,老安进来了。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老安这个时候会进来。
老安看到了我给秋姐擦眼泪,就骂着朝我扑过来。我握着拳头一下就站了起来。
老安被医生挡住了。医生说:“病人需要安静,你出去。”
老安跳着脚骂我,我走了过去。
秋姐喊我:“福贵。”
我站住了。为了床上的秋姐,我强压着心里的怒火。我觉得自己浑身都在冒火。
老安被医生推出了医务所。医生关上了门。
医生对我说:“老乡,你走吧,离开这里。要不,会出事的。”
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喘着粗气,什么话也不说。
床上的秋姐说话了:“福贵,你哪也不要去,明天还是回来吧,在我的地里干。这几天,我也想通了,什么也不怕了。”
我看到医生看了我一眼,就出去了。
秋姐看着我说:“你过来,坐到我跟前好吗?”
我走过去,坐到了秋姐的面前,看着秋姐。我觉得自己的眼睛湿湿的。
秋姐伸出手,抓住我的手,紧紧的,怕我走掉一样。
我把脸贴在了秋姐的的手背上,一动也不动。
秋姐打完吊针以后,精神好多了。徐嫂把饭送来了。一碗鸡蛋捞面务。秋姐说啥也不吃,非要让我吃。徐嫂劝了一会了,看秋姐很犟,就让我吃。吃面条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眼泪流在了碗里。
我要送秋姐回家。秋姐不让送,徐嫂也不让送。
徐嫂说:“安呼噜疯了,坐在门口大骂,骂得死难听,好多人围着看。”
秋姐说:“这日子过到头了。”
我看到秋姐的眼泪亮亮地流了下来。
徐嫂说:“福贵,你回家吧。我送你秋姐回家。”
看着徐嫂相伴着秋姐往秋姐家的方向走去,我心里酸酸地闷着头去徐嫂家。
快到徐嫂家的时候,我听到了老安和徐嫂的男人在吵架。我心里一急,感觉要出事,就跑了过去。
我看到老安拿着一个烂盆子,徐嫂的男人拿了个棍子,两个男人对峙着。老安在不干不净地骂着,徐嫂的男人在训斥着。我闻到了一股臭烘烘的味道。我看到我住的房门上全是黄黄的屎,老安拿着烂盆子还流着稀稀的黄屎。我一下冒火了,冲过去把老安手里的烂盆子夺过来,扔出去了很远。
老安低着头朝我冲过来。
徐嫂的男人朝我喊道:“福贵,你快跑。千万不要动手!”
旁边看热闹的人推了我一下,说:“你走吧,这个人谁也不敢惹。”
老安被人抱住,挣扎着要和我拼命。
我走了,离开了连队家属区,朝远处的戈壁滩走去。
我也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在这里,我没有亲人,没有家,只有一块来的同乡。可他们在这关键时候,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好像我是一个瘟神要传染他们一样。
我在戈壁滩上乱走着,心里乱麻麻的。不知什么时候,就到了奎屯河边。奎屯河边有两棵很老很老的胡杨树,就像两个老人站着在聊天。我坐在了一棵老胡杨树下,看着慢慢流淌的河水发傻。看着看着,我想起了家乡的娘。我的泪水出来了。我觉得自己太委屈了,憋闷心中多日的苦水往外流。我哭了,大声地哭了。对着奎屯河,我大声哭喊起来。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呀?
我哭着,拳头捶打着古老的胡杨树。我的手都流出了鲜血,可我不知道疼。我心里难受哇。我的心里就像有只猫在抓挠我的心,撕心裂肺的难受。
我用头碰着胡杨树。我哭着,我碰着。也不知什么时候,我就歪倒了,歪倒在胡杨树下,什么也不知道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我醒来了。天灰蒙蒙的,一大块灰云遮住了太阳。我感觉到一滴一滴水掉在我的脸上。我睁大眼,看到秋姐的眼睛看着我,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我想坐起来;可动不了。原来我躺在秋姐的怀里,被她紧紧地抱着,抱得死死的,一点也动不了。
秋姐看我醒来,就哭着说:“福贵,你可要想开呀。”
我说:“秋姐,我不会死的。”
秋姐摸着我的头说:“那你碰树干啥?”
我说:“我心里难受。”
秋姐说:“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听人说,你往奎屯河跑,我心里一下就毛了。我就什么也不管了,任那个该死的在家胡闹,我就跑来了。我顺着奎屯河找了好远,啥也没有找到。还好,在这找到你了。”
我什么也不说,把脸紧紧地贴在秋姐鼓鼓的胸脯上。我闻到了女人特有的气息。我想到了娘。想到娘,我的眼泪就出来了。
秋姐把脸紧紧地贴在了我的脸上,我感到暖暖融融的。
秋姐说:“我是不会让你走的。不管连队上的人怎么说,怎么看,我这次认了,豁出去了。”
我的泪流得更快。我哭着说:“秋姐,我不想看着你受气,不想看着你挨打。咱们走吧。走得远远的。我有的是力气,我来养活你。”
秋姐的泪水流到了我的嘴里,咸咸的。我咽了下去。
秋姐说:“不走,咱俩谁也不走。气死他。”
我流着泪说:“秋姐,我咋回连队,我没脸回连队呀。”
秋姐把我抱得更紧了,我都有些喘不过气来。我没动,一点也不想动。我当时心里想,就这样死在秋姐怀里算了。
秋姐搂着我说:“我找人明天在瓜地给你搭个瓜棚,你就住在瓜地吧。”
我说:“我会搭瓜棚。秋姐,在家乡,我给人搭过瓜棚。”
秋姐一听,笑了。她笑着,眼泪就掉在了我的脸上。
她亲了我一口,说:“我真没看错你。你是男人,是我想要的男人。”
我心里一下就热了起来。我俩就忍不住,干了那事。
干完那事后,我俩都很累。我背靠着胡杨树,抱着面条一样的秋姐。我看到,西边的天上血红血红的一大片,把我们头顶上的树叶都染红了。
那天晚上,我和秋姐呆在胡杨树下,说了很多的话。我觉得自己一辈子也没有说过那么多的话。我俩抱着,一直抱着。话说完了,谁也不想说了,就这样抱着。
我觉得自己嘴里干干的,想喝水。可我不想动,也不敢动。我怕惊醒秋姐。秋姐躺在我的怀里,睡得很香,还打着轻轻的呼噜。我听着特别的亲切,像娘晚上哼的家乡歌谣。
我又想娘了。
我的泪水流了出来。
我泪眼蒙蒙地看着奎屯河。河水哗啦啦地流着,散发着湿湿的气味,跟着风跑来。我吸着,吸着,就觉得嘴里没有那么干了。
我就这样坐着,抱着睡得很香的秋姐。
我就这样坐着,看着夜晚的奎屯河。
月光下的奎屯河很美。明亮亮的月亮,照在奎屯河上,我看到了一层薄薄的白雾,飘着飘着,朝着我们飘过来。我就觉得我们在天上,在云彩里面坐着。
我听着奎屯河的水哗哗地流着。我听着河边的芦苇在摇着,唱着好听的歌儿。我还听到野鸭子在叫着,就像电视里的歌星在唱歌,好听极了。
我一直这样坐着,一动也不动。我看着,一直看到天边白了,就像河里的鲤鱼翻了白肚,一长溜,上面一大片红红的鱼鳞光。
秋姐醒了。她没动,还窝在我的怀里。
秋姐摸着我的脸问:“你坐了一晚上?”
我没有说话。
秋姐扭了扭身子,笑了。
秋姐说:“我一辈子都没这样睡过,真香啊。”
我抱着秋姐说:“你再睡一会儿。”
秋姐坐了起来,说:“不了。我该走了,回家给你做饭。你也该干活了,去瓜地搭瓜棚,等着我给你送饭来。”
我把瓜棚搭好,都没有见秋姐来给我送饭。我只好坐在瓜棚门口吸烟。吸着吸着,我突然就感到心里难受起来。一个念头冒了出来:秋姐不会出事吧?
我站起来,就见徐嫂远远地跑来了。一定出事了。我心里琢磨着,朝徐嫂跑去。半路上,我和徐嫂站在那里。徐嫂告诉我:“秋姐被老安打断了腿,送到团里的医院了。”
我问:“老安呢?”
徐嫂说:“被派出所抓走了。你快去团里医院吧。”
我撒开丫子跑了起来,徐嫂在后面喊的什么,我一点也没有听到。
一个月后,秋姐出院回来了。
老安也被派出所放了出来,说是取保候审。我恨派出所,为什么放他出来?为什么不关他一辈子?
派出所的人告诉我:“两口子打架,又没有出人命。再说,我们去医院调查了,老安也只能再维持一个月。快死的人,我们关他干啥,总不能让他死在派出所吧。”
我无话可说。我又不是警察。我只好回来了。尽管我心里怨恨,但我没有办法,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毕竟是个外来户,一个来打工的内地民工。
我住在了瓜地,每天精心伺候瓜。瓜也越来越大,看着喜欢人。
秋姐不能来瓜地干活,只能每天拐着腿来给我送饭。看着秋姐那个样子,我心里很难受。可秋姐每次看我难受,就摸着我的脸劝我。我端着饭碗,泪就掉到碗里。我怕秋姐看到,几口就把饭吃完,每次都这样。
我和秋姐见面,谁也不提老安,害怕伤心。我知道,我俩都在等待。等待什么,我俩心里都很明白。
每次看到秋姐一拐一拐地走了,我就大骂老安:“快死吧。快死吧!”
瓜棚门前有棵胡杨树,树皮让我每天跺得没有了。没皮的那一边,露出白白的树干,就像人的骨头,白森森的。
那天晚上,秋姐来给我送饭。秋姐还给我带来了一瓶酒。秋姐说,“晚上天凉,喝点就不会冷。”我就喝了酒。秋姐也喝了酒。我喝过酒以后,看秋姐特别的好看,像七仙女一样。秋姐的脸红红的,像家乡的红桃花。秋姐喝了酒以后,就哭了,哭得很伤心。我的心里也酸酸的。我知道秋姐心里苦。秋姐哭着哭着就扑在了我的怀里。我就紧紧地抱着她。抱着抱着,我俩就想干那事。我俩就干了起来。
突然,外面就下起子雨。
秋姐心里害怕,把我抱得更紧了。
我俩就紧紧地抱着,用体温在互相暖着。
这时候,一个闪电,把天照的很白。我看到瓜棚门口站着一个人,脸白白的,像鬼一样。我一下就惊跳起来。
老安举着菜刀向我俩砍来。我一闪,菜刀就砍在了秋姐的身上。秋姐哎呀一声就倒在了地上。我拼命上去夺菜刀,一拳把老安打倒在地上。
这时候,闪电一个接着一个,把瓜棚照得雪白。雷声一排一排滚滚而来。我觉得山崩地裂了。
我抱起秋姐,看到秋姐白嫩的大腿鲜血直流。我一下怒火冲天,把老安按倒在身下,举起了菜刀。可是,我下不了手,菜刀举了半天都落不下来。我没有杀过人,又从来不敢杀人。
秋姐大喊着:“砍死他,你给我砍死他!”
我一下就血冲脑门。我想起了我受的千般委屈,我想起了老安百般折磨秋姐的事。我越想越血火攻心。老安在我的身下挣扎着,叫喊着:“有种你砍呀。你不砍我,我就要砍死你。我要砍死你俩。”我当时心里的火烧得头发懵,一刀就砍了下去。老安身上一冒血,我一紧张,菜刀就掉在了地上。秋姐爬过来抓起菜刀,发疯一样地朝老安身上乱砍起来。我看到秋姐的脸上身上全是老安身上溅起的血。老安一动也不动。我夺过秋姐手里的刀,喊道:“别砍了,他死了。”
秋姐笑了:“他死了。他终于死了。”
我看秋姐已经发疯了。我抱着秋姐。她浑身不停地颤抖着,好像打摆子一样。
外面的雷声更大了,更响了,好像天塌下来了一样。
秋姐躺在我的怀里说:“你把我也砍死吧。”
我说:“秋姐,咱们跑吧。”
秋姐瘫软在我的怀里说:“我哪里也不去,我就死在这里。”
我说:“秋姐,我背你走。咱们离开这里。我送你去医院。”
秋姐像根软面条,声音也越来越小:“福贵,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我大声喊道:“秋姐,你不会死的。要死咱们死在一起。”
秋姐说:“你不要死。你走吧。你娘在家等着你呢。”
我说:“秋姐,我带你一块看我娘。”
秋姐说:“你要想带我去看你娘,就答应我一件事。”
我说:“秋姐,你说,天大的事,我都答应你!”
秋姐说:“我死后,你把我的骨灰带走。”
我不吭气了。
秋姐声音很小地问我:“福贵,你不能答应就算了。”
我哭着点了点头。
秋姐就笑了。秋姐说:“福贵,你要骗我,我到阴间地狱也要缠着你。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放声大哭:“不,秋姐,我不让你死,我送你到医院去……”
外面的雷声更响了,雨更大了,像黄河垮口一样。我听到了外面全是哭喊声,铺天盖地来了。
瓜熟的时候,垦区法院在团里开了公审大会,连队上很多人都去了。回来的人说,他们看到李福贵了。李福贵被五花大绑地押上台时,头抬着,眼睛乱看着,好像在找什么人,又好像要说什么。大家都在等着,等着李福贵说什么。主席台上的法官说的什么,大家谁也没有注意去听,都在等李福贵说话。李福贵什么也没说,满脸的泪水往下流。他的泪水流了很长时间,一直到被武警押走,都没有说话,只是在流泪,一点哭声也听不到。于是大家就觉得很失望。要是李福贵说点什么就好了,一句话也行,可他一个字都没有说。
徐嫂和她男人谁也没有去看团里的公审大会。他俩为秋姐难受,为李福贵心里难受。徐嫂问从团里回来的人,李福贵判了个啥。是不是?谁也说不清楚,只说当时看李福贵没有声音的哭,不说一句话,法官说的啥,他们没有听清楚,反正看到李福贵被武警押上了车,警车叫着走了。
徐嫂当时很难受,使劲地憋着,跑回了家。
回到家的徐嫂,趴在床上大哭了一场,谁也劝不住。
责任编辑陈晓农